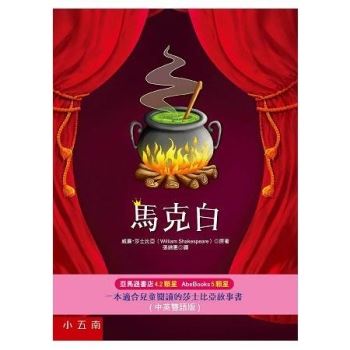自序
我寫《儒林鹿渡》,用的是比較嚴肅的創作題材。
一位朋友讀完初稿,曾經問我,裏面某些情景和人物,是否截然可辨?這可能是因為三篇小說中之一的點題篇〈鹿渡〉用了第一人稱作為敘述者而引起的錯覺吧。我覺得《紅樓夢》作者開宗明義讓甄士隱(真事隱)借太虛幻境的牌坊兩邊那副對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賞給了我一個蓋全的回答。
在我第一本短篇小說集《投影》的序文裏,那時年輕的我,說:一個小說創作者,在創作的時候,往往擺不脫他生活圈子裏所接觸到的人物和事序在他心版上投下的形象;過了這麼些年,我對我小說裏面的人物和情節的營造,仍然抱著同樣的看法,書中故事、人物、時間、地點、事件等等,固屬虛構。但是,骨子裏,這些小說結構的基因後面,其個體經過了社會現實種種的磨練後,個別或系統地凝合起來,再從我的小說中出現的時候,已經是跟我親自經歷過、認識過、或者看過和見證過的,有了層次上的區別。
我們這一代人的一生,哪兒能活在虛幻中不接觸現實?一旦插足現實,即使是一寸光陰,一方塊地皮,就算是來自立杆的影子,甚或是浮游在空氣的因子等等,在在構建了個人身心裏那些離不開甩不掉的成分,與個人獨有的想像力共存亡。我的看法,作者就是這麼一個混凝體。我是沒有能力去分解這混凝如玉蠟般的個體的;當混凝質體軟化時擺灑出來的,或點點滴滴,或如潤物無聲的細雨,都含著現實與虛幻的基因,既有獨立的存在,更有真假的凝結,這影像不知怎的卻令我想著莊子形容時至的秋水,讓人處身渚崖之間,不辨牛馬。
我的體驗是:小說的寫法,不是講故事,小說的讀法,也不單是看故事。我自己讀別人的小說,除了欣賞作者的文筆和感性之外,我最愛發現作者那精心運籌的佈局、伏線的安排、情節的前後發展照應是否妥貼、比喻是否過露還是潛浮、語氣感性的素質適合當前的局面否;有的時候,讀到一兩句看起來是等閒的對話,讓我領悟到作者為何會讓主人翁這樣說的時候,我就其樂無窮地會心雀躍起來…… ,凡此等等,都是我自動去領略某些作者那猶如出竅般的寫作過程,這也是我自己在寫小說時自勉要走的步伐,期間往往有非下筆不休的時段。也有揪心難以再續的光景。為此,此書萌芽和孕育的年月不算在內,加上動筆時需要到本地大學圖書館翻撿一些法律條例和資料,我寫得特慢,歷時三年,可以說字字瀝心,句句扣神。以前,我在胡菊人和戴天兄們編刊的《盤古》發表了一個題名〈膿〉(見《香港小說選》,盧瑋鑾、黃繼持等編)的短篇,借一位代課老師的經歷,諷刺當年香港的小學制度存在的弊端,那時,我是個香港官立小學的老師。如今,這本《儒林鹿渡》,諷擊的是美國現代高等學府的校園政治,特攻某些教授級的老師在校園運作的行為和心態。
在〈一條在江心補漏的船〉這篇裏,主要是寫一位越裔美籍女教授祝芷雲,自從她在宜州大學當上了助理教授後,環繞在她身旁的正反人物,莫名地引出離奇曲折的事端,是職外人難以想像到的,她跟系裏對她施邪穢手段的莠者,差不多是孤身面對,獨鬥了十幾年,極力去討回公道,值得我們去學習。
〈鹿渡〉裏的主角人物,是一位在宜州大學東方語文系任教的美籍華人應儒河教授,自他入職到獲得終身教職後在職途上微妙的演繹,他所看到校園政治場上正反人物詭譎的心計,雖然達不到「苛政猛於虎」的地步,也可見到職場上無血的生殺,會使個中人後半生無所適從。幸而,人世間還是光明與黑暗並存,篇中寫的羅副校長,就是我心目中嚮往的衷誠服務教育界的楷模,寫他的正義品格時,我想著我們的文天祥;寫他的他公正嚴明時,我想著我們的包龍圖。
〈一顆剝了皮的石榴〉寫的是宜州大學文學院裏藝術系的一件腐敗的事情。這一篇,敘述時用近乎報告文學般的手法,是我從前沒嘗試過的。本來想用的題目,是西方諺語「打開一罐蛀蟲」;想了很久,還是不能用,因為這是一句令人,最少令我,一想就會渾身起了雞皮疙瘩,異常醜劣的形象的話;宜州大學毛病雖多,用此喻之,仍嫌有誇大其詞的任性吧;也許,不是每個人都意悟其中放射性的衝擊,所以,就改了題目,起碼,剝開了皮的石榴,不是人人都認為「一身都是瘡」的,我願意讓讀者有見仁見智的空間。
這本小書得以完成,以致行將出版,我不由衷心感謝我的兩位師弟—— 維樑和子程,他們多年來一直未停筆耕;我的文友小思和偉唐,從不捨棄對文學創作的努力和關注;這都使我持續著勇氣,把多年來藏在心裏的書稿付諸秉墨。
我特感激初文出版社的社長黎漢傑仁弟的賞識,爽直地負起出版的責任;我更為我們都是文學的有緣人而異常欣喜。
陳炳藻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號除夕爆竹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