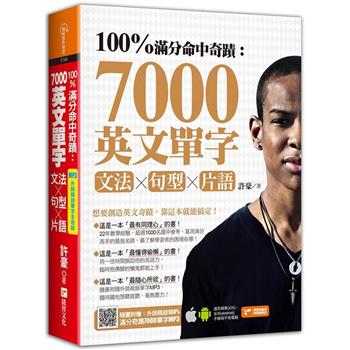「所以秦敘,你厭世社恐、閉塞耳目,卻又為什麼這麼堅定甚至執拗地在夜晚做無人餐廳的主廚,到底是因為什麼呢?」 「我的餐廳每日都有人,只是……」他淡淡地轉過身,「只是你看不到他們。」曾經不及吧檯高的男孩子,已經身形修長,獨自支撐着這裏的一切。 風吹長街,葉滿古巷,舊人再未歸來。
城市的一隅,古舊老宅閃着溫暖的餐廳招牌,這間只做街坊生意的「有家小店」,已經開了十八年。
老店主人秦敘有兩個身份:白天他是上市公司令人聞風喪膽的資源重組高級專員,被稱為恐怖的「職場死神」。他的調查冷血無情,終結了多位高管、總監的職業生涯;傍晚,他回到老宅為清冷的餐廳烹煮佳餚,成為另一個自己。
直到一場颱風前夜,門前的鈴鐺響起,一個有着熟悉藍風鈴香氣的女人推開了這間無人餐廳的門,彷彿沉睡之地忽然迎來了夏天,盛開如花……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今年夏天盛開如花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今年夏天盛開如花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寶劍鋒
本名林庭鋒,廣東陽江人。起點中文網創始人,閱文集團創始人,廣東網絡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網絡作家協會副會長。
網絡文學商業化運作發起人和網絡文學商業模式創建者。
第一代網絡幻想文學代表作家,2001年首批登陸台灣幻想文學出版市場的大陸作家之一,作品成為當年年度暢銷作。
於2001年創立中國玄幻文學協會(CMFU),2002年發起成立了起點中文網,迄今起點中文網已成為全球最大的華語文學網站。
作為網絡幻想文學首席專家、評論家,網絡閱讀正版化的倡議者,參與並制訂了網絡原創文學編輯的工作模式以及作者培養流程的行業標準。
近期作品有《冬日不曾有暖陽》等。
寶劍鋒
本名林庭鋒,廣東陽江人。起點中文網創始人,閱文集團創始人,廣東網絡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網絡作家協會副會長。
網絡文學商業化運作發起人和網絡文學商業模式創建者。
第一代網絡幻想文學代表作家,2001年首批登陸台灣幻想文學出版市場的大陸作家之一,作品成為當年年度暢銷作。
於2001年創立中國玄幻文學協會(CMFU),2002年發起成立了起點中文網,迄今起點中文網已成為全球最大的華語文學網站。
作為網絡幻想文學首席專家、評論家,網絡閱讀正版化的倡議者,參與並制訂了網絡原創文學編輯的工作模式以及作者培養流程的行業標準。
近期作品有《冬日不曾有暖陽》等。
目錄
第一章 有家小店001
第二章 薪資的一半是受委屈013
第三章 我們很熟嗎021
第四章 煩惱誰人知031
第五章 暗流湧動044
第六章 糖葫蘆058
第七章 颱風過境066
第八章 雨夜來客076
第九章 劍拔弩張085
第十章 驚怒受傷096
第十一章 白青招認109
第十二章 真相大白119
第十三章 戰功彪炳133
第十四章 衝動互毆146
第十五章 微光長明159
第十六章 風過無痕170
第十七章 救人一命181
第十八章 不為所動191
第十九章 聲勢浩大205
第二十章 登門拜訪216
第二十一章 露出破綻227
第二十二章 真相大白238
第二十三章 李叔過世251
第二十四章 差不多活着264
第二十五章 趕盡殺絕276
第二十六章 來者不善288
第二十七章 往事如煙300
第二十八章 新不了情310
第二十九章 孤勇者325
第三十章 思念沉重336
第三十一章 喜歡就是喜歡349
第三十二章 一念之差358
第三十三章 濱海明珠368
第三十四章 一團亂麻377
第三十五章 前度女友388
第三十六章 好事多磨398
第三十七章 說走就走409
第三十八章 風過巷尾419
第二章 薪資的一半是受委屈013
第三章 我們很熟嗎021
第四章 煩惱誰人知031
第五章 暗流湧動044
第六章 糖葫蘆058
第七章 颱風過境066
第八章 雨夜來客076
第九章 劍拔弩張085
第十章 驚怒受傷096
第十一章 白青招認109
第十二章 真相大白119
第十三章 戰功彪炳133
第十四章 衝動互毆146
第十五章 微光長明159
第十六章 風過無痕170
第十七章 救人一命181
第十八章 不為所動191
第十九章 聲勢浩大205
第二十章 登門拜訪216
第二十一章 露出破綻227
第二十二章 真相大白238
第二十三章 李叔過世251
第二十四章 差不多活着264
第二十五章 趕盡殺絕276
第二十六章 來者不善288
第二十七章 往事如煙300
第二十八章 新不了情310
第二十九章 孤勇者325
第三十章 思念沉重336
第三十一章 喜歡就是喜歡349
第三十二章 一念之差358
第三十三章 濱海明珠368
第三十四章 一團亂麻377
第三十五章 前度女友388
第三十六章 好事多磨398
第三十七章 說走就走409
第三十八章 風過巷尾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