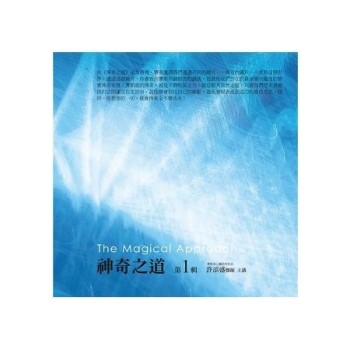第一章
宓兒慢慢攪著杯裏的咖啡,不時望著咖啡館那扇碎花玻璃的大門。
咖啡館位於鬧市街角,兩邊的牆面街,也是碎花玻璃。遠看,像個彩色玻璃匣子立在街口。外面的人看裏面,花中有人,人中有花;裏面的人看外面,揚著手的,喔著嘴的,抄著腰的……斷片似的。
碎花玻璃的隔音效果很好,把噪音和人流完全隔在了門外。偶爾「吱呀」一聲,門開了,瀉進一溜聲音,一兩個人。咖啡館裏人不多,稀疏坐著。兩人聊天的,獨自抿飲的,對著電腦做事的……很安靜。
宓兒今天來遲了一會兒。臨出門時,她覺得自己的衣服不太合適——太沉靜、太日常了。雖然子域常說,她不用妝扮,她就是他想要的「那種樣子」。他理想的「樣子」。哪種「樣子」?問他,卻只笑不答。二十歲,他們相識時他便這樣說了;三十五歲他們再相遇,他還是這樣說。
後來的語氣卻帶著絕望。
宓兒回去換了身衣服。今天不一樣,今天她要穿得漂亮些。
前一晚在電話裏,他們商量為她慶祝生日的事——她的四十五歲生日。電話是子域在紐約打來的,他在那兒公幹,今天趕回香港。他們再遇後的十年裏,每年她的生日,兩人總是想方設法一起過。生日相伴,權當人生依然。
他們和命運負隅頑抗。
老之將至的生日。電話裏她嘻嘻自嘲。
在我眼裏你永遠二十歲!子域斷然說。
她默然。她知道。
子域說在紐約為她挑選了一件禮物。也是給我們自己的禮物——
子域說著,停頓下來。
一個千言萬語的停頓。
她知道那是甚麼禮物,她也停頓著。這停頓是巨壑,填不滿她和子域曾經的萬千掙扎。
今天,本是個不敢期望的日子。
她換了一件暗紅色的羊絨連衣裙,顏色既喜氣,也不誇張。式樣也適合她,收身貼腹,襯出她盈盈一握的腰肢。她端詳著鏡子裏的自己:人到中年,身材卻和年輕時並無二致。這和她沒有生育過有關。身材完好,其實缺憾。每次照鏡子,她就心生黯然。
現在,一切或有可能了!宓兒心情很好地為自己配了一對低幫羊皮黑靴穿上,出了門。
今天她沒有佔到角落裏的那個座位。對於她和子域來說,那個座位太好了:角落裏,不顯眼,不顯聲,聊天正好。更難得的是邊上還有一條通道,指示牌上寫著「工作人員通道」。這通道其實連著邊門,邊門出去是靜靜的後巷。後巷轉個彎,穿過去,就是地鐵站。大多時候,他們便從這兒離開,然後告別。十年前,她和他再遇,後來相約見面,就選擇了這個咖啡館。當時,他們並不熟悉這個咖啡館,只是因為這兒離中環遠些,少熟人,近地鐵。來了之後,才又發現了這個角落,這個通道。
十年了,她總是早點來這兒候位。子域太忙,每分鐘都在計算著過。她就攬下了候位的事。他們需要這個座位。
十年來,他們便在這兒見面。喝喝咖啡,聊聊天。時斷時續的對話,時望時避的眼神,時喜時憂的靜默……盡寄情意。
本來以為這就是一輩子了。
宓兒走進咖啡館,那角落的座位還真讓人佔了。那裏坐了個年輕女子,秀眉輕鎖,抿著咖啡。她也有憂傷要掩藏嗎?宓兒遠遠看看她心想。好在今天的宓兒已經不在乎了,依然來這兒,只因為習慣了這兒。今天的他們其實可以坐在任何地方。
宓兒挑了個相對安靜的位置坐下,怕子域進來看不見她,宓兒留意著大門。
手機響了,宓兒忽然有點害怕,怕是子域的電話,怕他又被工作耽擱了。總是好事多磨。
宓兒遲疑地拿起電話,一看,鬆了口氣。
生日快樂,壽星女!一接通,東尼那一把特有的聲音傳了過來——語速快、齒音清晰。香港不少人說話帶懶音,常叫人聽錯意思。東尼是個律師,宓兒常說這聲音很適合他的職業。
宓兒剛應了一聲,東尼就急急問,有冇人同你一齊慶祝生日呢?如果冇人嘅,不如我嚟啦,OK?
宓兒笑了,說,子域回來啦!他正在路上。謝謝你!
和東尼講話,宓兒是輕鬆愉快的。女人在喜歡自己的人面前,總是輕鬆愉快的。
東尼喜歡她,很喜歡她。多年來,一直不離她左右。但世上唯感覺這東西是不能騙自己的。「東尼是我的藍顏知己」,宓兒對人說。「女未嫁,男未娶,點知將來?」,東尼一口否認。
交朋友,東尼卻是有趣的。世上的事,只有你不知,沒有他不曉。圈內朋友各自忙,難得相聚。一朝見了,話題卻又不知從哪兒說起,常常冷場。東尼一來,則無疑投進一顆燃燒彈,頃刻熱烈起來。東尼有一套理論最是蠱人。甚麼 「下半身激勵上半身」「下半身是動力開關」「下半身不呃人」云云。在座男女,受過一定的教育,講話斯文有禮。他「上上下下」地講,弄得人就有些不自在,就有人駁斥他,卻不知那是給他遞了一把火。東尼一時間上下五千年,引經據典,旁徵博引,最後還能一言以蔽之,反問:「唔覺男女同工,做事輕鬆咩?」也是啊,眾人被問住,語塞,猶疑不定。少頃,待悟得此中偷換概念、定義謬誤、邏輯黑洞等等,這才萬炮齊轟。東尼常常卻已狡黠地轉了話題。人以為得勝,鳴金息鼓,隨他笑說其他。不料,又是一個陷阱……
如此一趟趟。
氣氛卻總是這樣叫他搞活了。
聽到電話裏東尼洩氣的「嗐」「嗐」聲,宓兒笑著補充說,大家再約,OK?
今天,她要獨獨和子域在一起。今天以後,她和子域就會共同邀見朋友了。
宓兒的話,東尼從來沒辦法說「NO」。
東尼只好假裝傷心的聲音,OK,無計啦,心思思以為今年有機會,候著有人出埠公幹,冇得返歸!
宓兒笑了。東尼很會裝,他能氣也不喘地裝出各種情緒的聲音,快樂的,悲傷的,甚至悲從中來的。常讓宓兒和朋友們笑得前仆後仰。
她由他裝去。
唉,舊年係咁,今年又係咁!
甚麼舊年今年的,亂七八糟。宓兒不明白,但也不打斷他。東尼的笑話篇篇新章,句句發噱。
東尼裝得來勁,繼續裝,舊年有人也出差,聽講回唔到香港,哈,機會來啦!收工我即走,換衫,買花,速速趕去咖啡館。估唔到,好遠睇到有人也在花檔買花。嗟,趕返來了!無法啦,我自然唔做電燈膽喇,唯有返歸囉!
東尼從不掩飾對子域的醋意,更不直呼子域的真名,只用「有人」代替。
「有人」好忙㗎?
「有人」又出埠啦?
「有人」型仔過我啊?
……
宓兒笑出聲來,編得真像!今日心情好,便逗他,說,繼續繼續,甚麼花啊?好看嗎?
唯是去年生日,她沒有收到子域送的花。
去年生日,她像每年一樣,下班後早早坐在了那角落。她知道子域在紐約開會,也知道他會趕回來。
可是,那天快到晚上八點,才見子域走了進來。背著背囊,穿著風衣,臉色灰沉沉的。筋疲力竭的樣子。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雙城故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57 |
小說 |
$ 308 |
中文現代文學 |
$ 343 |
中文書 |
$ 351 |
華文愛情小說 |
$ 351 |
小說 |
$ 351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雙城故事
兩個城市,編織了兩個人半生的愛情故事~
——別人看見他買了一束花,去為愛戀著的她過生日。可她並沒有收到花。花呢?給了誰嗎?那短短的小街上發生了甚麼?面對各種疑問,他卻默然不語;
——她人到中年,日子過得仍如「煲老火例湯」似的細慢,求著醇香和濃厚,她似乎將成為生活的棄兒了,卻為何人急她不急;
——她處在命運的低處,自匿於社會和生活,有一日走到了人前,卻叫人大吃一驚;
——他喜愛優雅的女子,那優雅卻壓抑著他;他沒有大志,為了愛情,展開事業,愛情卻沒抓住,事業卻成了;
——她是強硬的,對一切阻礙她的必將反擊之,有一日卻柔軟了,後來更柔軟了。
故事講述兩個城市,編織兩個人半生的愛情故事。從上海,到香港,兜兜轉轉,從分開,到再遇,女的處在命運的低處,自匿於社會和生活,有一日走到了人前,卻叫人大吃一驚;男的沒有大志,為了愛情,展開事業,愛情卻沒抓住,事業卻成了……
作者簡介:
朱華
本名朱志華,筆名海倫、朱華等。曾任上海市屬區文化館話劇創作員、深圳影業公司影視劇編劇。九十年代移居香港,現為獨立寫作人。寫作及發表劇本、中短篇小說、散文、詩歌等。獲各類獎項。作品散見萌芽增刊、長春、作家、新民晚報、香港作家、香港文學、明報等等報刊雜誌。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宓兒慢慢攪著杯裏的咖啡,不時望著咖啡館那扇碎花玻璃的大門。
咖啡館位於鬧市街角,兩邊的牆面街,也是碎花玻璃。遠看,像個彩色玻璃匣子立在街口。外面的人看裏面,花中有人,人中有花;裏面的人看外面,揚著手的,喔著嘴的,抄著腰的……斷片似的。
碎花玻璃的隔音效果很好,把噪音和人流完全隔在了門外。偶爾「吱呀」一聲,門開了,瀉進一溜聲音,一兩個人。咖啡館裏人不多,稀疏坐著。兩人聊天的,獨自抿飲的,對著電腦做事的……很安靜。
宓兒今天來遲了一會兒。臨出門時,她覺得自己的衣服不太合適——太沉靜、太日常了。雖...
宓兒慢慢攪著杯裏的咖啡,不時望著咖啡館那扇碎花玻璃的大門。
咖啡館位於鬧市街角,兩邊的牆面街,也是碎花玻璃。遠看,像個彩色玻璃匣子立在街口。外面的人看裏面,花中有人,人中有花;裏面的人看外面,揚著手的,喔著嘴的,抄著腰的……斷片似的。
碎花玻璃的隔音效果很好,把噪音和人流完全隔在了門外。偶爾「吱呀」一聲,門開了,瀉進一溜聲音,一兩個人。咖啡館裏人不多,稀疏坐著。兩人聊天的,獨自抿飲的,對著電腦做事的……很安靜。
宓兒今天來遲了一會兒。臨出門時,她覺得自己的衣服不太合適——太沉靜、太日常了。雖...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自序
——別人看見他買了一束花,去為愛戀著的她過生日。可她並沒有收到花。花呢?給了誰嗎?那短短的小街上發生了甚麼?面對各種疑問,他卻默然不語;
——她人到中年,日子過得仍如「煲老火例湯」似的細慢,求著醇香和濃厚,她似乎將成為生活的棄兒了,卻為何人急她不急;
——她處在命運的低處,自匿於社會和生活,有一日走到了人前,卻叫人大吃一驚;
——他喜愛優雅的女子,那優雅卻壓抑著他;他沒有大志,為了愛情,展開事業,愛情卻沒抓住,事業卻成了;
——她是強硬的,對一切阻礙她的必將反擊之,有一日卻柔軟了,後來更柔軟了...
——別人看見他買了一束花,去為愛戀著的她過生日。可她並沒有收到花。花呢?給了誰嗎?那短短的小街上發生了甚麼?面對各種疑問,他卻默然不語;
——她人到中年,日子過得仍如「煲老火例湯」似的細慢,求著醇香和濃厚,她似乎將成為生活的棄兒了,卻為何人急她不急;
——她處在命運的低處,自匿於社會和生活,有一日走到了人前,卻叫人大吃一驚;
——他喜愛優雅的女子,那優雅卻壓抑著他;他沒有大志,為了愛情,展開事業,愛情卻沒抓住,事業卻成了;
——她是強硬的,對一切阻礙她的必將反擊之,有一日卻柔軟了,後來更柔軟了...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