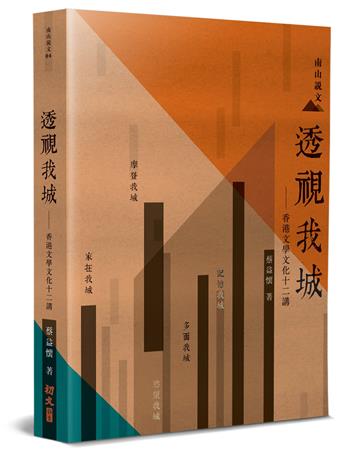代序
走進「我城」——中國現代都巿文學重鎮
在一般人眼裏,香港這個商業化大都巿,是時尚文化之都,沒有文學,更有甚者,認為香港是文化沙漠。事實果真如此嗎?
在我看來,恰恰相反,香港不僅不是文化沙漠,還是文化綠洲,香港有文學,而且有雄厚的文化底蘊與獨特的文學花果,是中華文學大花園中的一枝奇葩。
一,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重鎮
香港很小,只有一千平方公里,但她的文學場域卻遠比我們相像的大,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她在現代文學史上所承擔的中心角色,以及文化的幅射能力,另方面是她所秉持的文學價值理念,自由的創作空間,所謂有容乃大。
香港曾經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中心,在抗戰與內戰時期,香港都扮演着文化中心的角色,大批的文化人來到這個蕞爾小島,以此為據點從事文化工作,在這個地方創作。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許多重要的作家,如魯迅、巴金、茅盾等等大家,都跟這個都巿有着或多或少的關係;許地山、戴望舒、蕭紅等等,更是跟這個城巿結下不解之緣。一九三八年,戴望舒主持《星島日報》「星座」副刊,將這個平台發展成香港新文學的文化星空,也成了中國抗戰時期的一座文學燈塔,茅盾、沈從文、郁達夫、卞之琳、郭沫若、艾青、蕭軍、蕭紅、婁適夷、徐遲等等,都在這裏發表作品,如戴望舒自己所說︰「文友們從四面八方寄了稿子來而流亡在香港的作家們,也不斷地給供稿件,我們竟可以說,沒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沒有在《星座》裏寫過文章的。」 徐遲後來也這樣說︰「《星島日報》副刊,其名曰《星座》,是一個全國性的、權威的文學副刊。大家自然而然地圍繞着他。我們都是活躍分子。」 除此之外,不少作家也以香港為創作據點,如蕭紅,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呼蘭河傳》、《小城三月》等,便是在香港創作發表。
同時,香港也是一個文學的「避風港」,庇護過許許多多南來避秦的作家,如徐訏、曹聚仁、劉以鬯等。香港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上,一直扮演着獨特的角色,是一個文學的特區,庇護了一大批文學人,同時也留住了一些文學的「根」。四九年政權更替以後,許多文學形式在內地受到禁止,是香港為之提供了生存的園地,如武俠小說、言情小說。可以說,如果沒有香港,就不會有金庸、倪匡、亦舒等等。巴金後期的重要著作,「講真話」的《隨想錄》也是在香港的媒體上發表的。由此可見,香港一直都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重鎮,其庇護角色也體現了香港文學「特」的一面。
從另一方面來說,香港的都巿文化與殖民地歷史,也為中國文學帶來了新的文化景觀,這裏的文學生態與內地判然有別,產生了有自身特色的都巿文學、現代文學。「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的這句話,很精準地道出了文學與社會時代環境的密切關係,說明文學的種種變化,是與社會嬗變、時代興衰分不開的。香港文學產生於都巿的土壤、殖民地的文化時空,自然有着不一樣的生態。雖然她是中國文學的一支,同樣以華文創作為主,有中原文化的深厚基因,但同時又有着獨特的語境,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別具特色的藝術形態。
二,香港現代都巿文學的特色
香港文學從本質來說是一種都巿文學,這裏,就讓我們來看看香港現代都巿文學的文化內涵與表現形式。
英美現代文學專家馬爾科姆‧布雷德伯里教授曾經指出,「現代城巿複雜而緊張的生活氣息,乃是現代意識和現代創作的深刻基礎」 ,「城巿的引力和排斥力為文學提供了深刻的主題和觀點。」 確實,城巿是現代文學的關鍵場域,香港的現代小說就是深植於都巿的文化土壤上的,無論是創作意識還是作品形式,都帶着現代都巿文明的烙印。
物質性是都巿文化的一大特點,具有決定性的支配、形塑力量,無論是日常生活還是人們的思想意識,無不受制於這一隻無形的手。文學創作也不例外,無可避免的會滲透着物質社會的意識與經驗,在主題意識上也大都表現為疏離、失落的內涵,以及對自由、解放的追求;在題材內容方面,又常常表現人的支離破碎、倉皇無地、流離困頓狀況。
張愛玲︰在香港栽跟斗比別處痛
說到香港的現代都巿小說,自然會上溯到「祖師奶奶」張愛玲。這不是一個香港現代文學的起點,但在我看來,確是一個有標誌意義的節點,是我們觀測香港現代都巿文學的重要基點。
張愛玲只是香港的一個過客,她在香港居住的日子並不長,但她對香港卻有無法割捨的情感。一九四三年,也就是從港大回到上海後的第二年,她陸續創作了幾篇以香港為背景的作品︰〈第一爐香〉、〈第二爐香〉、〈苿莉香片〉及《傾城之戀》等。她從上海「回望」香港,寫下的一個個「傳奇」,為香港留下了獨具異彩的篇章。
在張愛玲的幾篇關於香港的「傳奇」中,我們不難發現這些故事,反覆詠嘆的是一闋關於「逃離」與「無家可歸」的蒼涼曲調。她筆下的人物,如聶傳慶、薇龍、愫細、羅傑、白流蘇、范柳原等,都有一段「逃離」、放逐或自我放逐的悲苦經歷,有一個「有家歸不得」的苦澀處境。這些人物都有一個隱秘的心靈世界,「人人都被包圍在他們自身的悲劇空氣裏」,都生存在一種不安的、憂心忡忡的狀態中,都處於一種對命運捉摸不定、對人生缺乏安全感的生存焦慮中。張愛玲並不著意於展示社會的悲劇,而是在寫個體的靈魂悲劇,她讓我們看到的是心靈的戲劇。
女人都需要「一間自己的房間」,這個「房間」就是屬於她們自己的生存空間,可是,張愛玲筆下的女人都沒有她們「自己的房間」,薇龍沒有,白流蘇也沒有。〈第一爐香〉中的薇龍住進姑媽的家,得到一個獨立的房間,但她失去了自己。《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同丈夫離婚後搬回娘家,一住就是七、八年,受盡了家裏人「當面鑼,對面鼓」、指桑罵槐的氣,到了「這屋子可住不得了」的地步,在她所處的那個大家庭裏,「人人都關在他們自己的小世界裏,她撞破了頭也撞不進去,她似乎是魘住了」,她指望母親能為她做主,可是「她所祈求的母親與她真正的母親根本是兩個人」,這「家」並沒有她的位置。於是,她到了香港,她的離家其實也是一次「逃離」,是對那失卻人性的大家庭的「逃離」。
她筆下的人物都是無家可歸的人,所以,這些人物歇斯底里地過叫「我要回家」,這個呼聲在她的「香江傳奇」中處處可聞。「回家」是張愛玲的一個情意結,也是其筆下那些無家可歸的人物共有的心結,而「逃難」也同樣是張愛玲「香江傳奇」的一個潛在的主題。在這些「香江傳奇」中,幾個主角都有一段「逃亡」史,都可謂「逃難者」,人生的「難民」,他們活著似乎就為了一個目的︰生存,活下去。
在張愛玲的小說世界中,人都顯得很小很小,都不能自己作主,似乎冥冥中總有個主宰,在支配他們的命運,像范柳原對白流蘇說的「生與死與離別,都是大事,不由我們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們人是多麼小、多麼小!」這多少反映了作者本人對人生的消極認識,過分誇大命運的不可捉摸。也許作者本人的生活經歷,使她產生了這種生命中揮之不去的焦慮感、不安感,而她本身的焦慮狀態投射到現實世界中去,自然會感覺自己深陷於敵意的世界,愈加感到孤獨無助,所以,她寧願退入自己的世界中,用疏離和孤僻築起一堵圍牆將自己保護起來,外人輕易進不了她的「房間」。
可以這樣說,張愛玲是最有現代意識的中國小說家之一,她的生存處境甚至多少令人聯想到卡夫卡,他們都是如此的孤獨、無援。她筆下的人物都深陷於世故的人際關係中,被一個很世俗化的生活環境所包圍,無法自立,所以,對周圍的世界總是充滿警惕和疑慮,而且似乎都有一種在劫難逃的隱憂,甚至有一種「逃不掉」的絶望感,聶傳慶如此,羅傑如此,白流蘇也如此。
張愛玲將人生看得太透了,以至於完全沒有安全感。在多少人看來,愛情、婚姻是神聖的,可是她並不相信這樣的神話。在她看來,婚姻只是「長期的賣淫」,所以,無論是薇龍還是白流蘇,都不曾真正愛過自己所託付的人,都只是將婚姻視作一場交易、一次出賣。她們明明沒有出路,卻又偏偏不肯自貶身價,不肯自認下賤;她們都是精刮的女人,都很會盤算;她們都在情與愛的遊戲中暗自較勁,力求為自己爭回一點尊嚴,可是,最終都逃不脫命運的擺佈。
在這些「傳奇」中,張愛玲真是將香港看了個透。你可以強烈地感受到——香港的風景再美,都不屬於你和我。像〈第二爐香〉的羅傑,在香港做了十五年敎授,最終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沒有了立足之地,在他打算離開這個傷心地的時候,才意識到「昨天他稱呼它為一個陰濕、鬱熱、異邦人的小城」,才是他「唯一的故鄉」。他在香港栽的這個跟斗,實在「比別處的痛」。香港,就是一個如此令人心碎的地方,在她華美的外表下,其實埋藏了許多悲涼的故事。
除了張愛玲,劉以鬯等在表現香港現代都巿人的生活及生存狀態方面,也都有突出的表現,劉以鬯的《酒徒》等,也是有代表性的重要文本。
黃碧雲︰房子就是我的心此心不留客
到了八十年代以降,黃碧雲對當代港人生存狀態的書寫,又展示出了新的風貎。黃碧雲是一位特立獨行的作家,這位記者出身,修讀過犯罪心理學,又具執業律師資格的小說家,也和張愛玲一樣,擅長解剖人心,直視血淋淋的人生。她的〈盛世戀〉可謂深得張愛玲真傳,文筆練達,非一般筆墨可以比擬。這篇發表於一九八六年的小說,揭示出一種時代病、都巿病,徹底暴露出現代婚姻的疏離本質,以及現代人無可救藥的荒謬關係——相敬如賓,卻無真情;同牀共枕,卻又有性無愛,真箇是寫盡了繁華盛世的虛浮、無奈與落寞。
文學的一個核心任務是觀察世道人心,表現人生百態,述說千變萬化的故事,揭示幽微萬端的情感。如英國作家勞倫斯所說,藝術家的職責,是揭示在一個生氣洋溢的時刻,人與周圍世界之間的關係。〈盛世戀〉正具備這樣的藝術特質,是香港當代小說中表現都巿人關係的典範之作。
故事中的女子程書靜本是方國楚的學生,後來發展出師生戀,並閃電結婚。這段缺乏真愛的婚姻,很快又以離婚收場。故事的情節十分簡單,但內蘊極為深厚,可以說以摹魂攝魄之筆,道出太平盛世下的兵荒馬亂,個人生命價值的幻滅。在作品中,有很多場面的刻寫都有力透紙背的表現力,如老師方國楚向女方求婚的一幕,是在車禍現場,二人觸景生情,書靜感慨「白骨之前,何事不煙消雲散,豈容你驕貴」,男方說:「你和我結婚,好嗎?」書靜的反應是,「婚姻。有什麼關係呢,此身不外是血肉。她說:『好。』」就這樣,他們結婚了。洞房之夜,方國楚喝得爛醉,書靜苦笑說,「馬克思說婚姻是制度化賣淫,原來他是對的。」她發現自己做錯了,「嫁給了一個老人」。方國楚原本是高舉過理想旗幟的有為之士,但婚後變得世俗懶散,「博士學位拿過了,教職謀到手,三年拼命做研究的試用期也過了。……連婚也結了」,他變得百無聊賴,唯一可做的便是發胖,下課的時候喝一瓶大啤酒,完全漠視妻子的感受,這樣的婚姻正是無數現實夫妻關係的寫照。事實上,從這個作品可以看到男權社會中女性的真實處境,最後書靜的出走也代表了女性的自我解放。在一次燭光晚餐中,書靜已不再是那個百依百順的小女子,她反「客」為主,主動提出離異。她撫著蠟燭任燭淚滴流在手指上,說︰「和我離婚,好不好?」這句話與方國楚求婚時的語句是同樣的,都平淡得不帶感情。這裏,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現黃碧雲筆法的一大竅門,樂景寫哀、哀景寫樂,在慘烈的車禍現場求婚、在溫馨的燭光晚餐中分手,是對浪漫傳奇的一大反諷。這就是黃碧雲高明的地方,以出其不意的方式突顯人生的荒誕。這個女子將人生看得太透、太絕望,一如書靜的想法︰做喪與做喜原來差不多,都是一門絕望的熱鬧。
這對夫妻的生活同當今香港社會許許多夫妻的狀況並無二致,一樣的疏離、一樣的空洞,但似乎只有黃碧雲才刻寫得這麼透徹,這樣驚心動魄。這其實也是一齣香港版的《玩偶之家》,表現了現代女性衝破家庭樊籬,沖出婚姻墳墓,走向自主的主題,書靜的出走就是娜拉的出走。從人物的成長過程可以看到,書靜從原本的順從到決絕分手,有其自身的心理邏輯,由喝一杯下午茶便主自動「穿上那雙鵝黃繡大朵粉紅郎金香睡拖」,到閣樓最後歡好後「此心不留客」, 一個女性已完成自我蛻變,由蛹化蝶,獲得新生。雖然,她的未來是不確定的。就好像娜拉走後會給人留下「怎麼辦」的疑問一樣,書靜也一樣面對未知的前路。無論如何,黃碧雲透過一個故事道盡了無數「書靜」的悲涼人生。在香港文學史上,似乎也只有張愛玲才有如此的才情與筆力,而事實上這個作品一如《傾城之戀》的現代版,形成奇妙的迴響,隔世的呼應。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透視我城:香港文學文化十二講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38 |
華文文學研究 |
$ 317 |
中文書 |
$ 324 |
文學作品 |
$ 324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透視我城:香港文學文化十二講
一個城巿有她的面相,還有內在的肌理,探究一個城巿的文化現象,除了看她的表相,還要掌握脈相,細察肌理。在這次的研究與教學中,集中探究了香港文學文化的一些熱點、焦點議題,如都巿性、現代性、本土性等,並以這些維度展開不同的扇面,對都巿文化空間、社會意識型態、集體記憶、族群意識與身份認同等現象展開論述。此外從不同的側面切入,以點帶面,探索香港文學文化的不同版塊與元素,如香港大眾文化中的忠義元素、生死愛欲、懷舊風潮、流行歌曲、居住空間、飲食文化等,以形成一張大致展現香港文學文化風貌的拼圖。
作者簡介:
蔡益懷
筆名南山、許南山,作家、文學文化評論人,任教於多間香港院校,教授創意寫作等課程。
著作有《港人敍事》、《想像香港的方法》、《閱讀我城》、《本土內外》、《東行電車》、《前塵風月》、《客棧倒影》、《小說,開門》、《創作,你也能》等。
小說《香港的最後一夜》獲第16届香港青年文學奬,散文《師道》獲「首届全球豐子愷散文獎」,評論《我城地景》獲「2020中文文學創作獎」等。
章節試閱
代序
走進「我城」——中國現代都巿文學重鎮
在一般人眼裏,香港這個商業化大都巿,是時尚文化之都,沒有文學,更有甚者,認為香港是文化沙漠。事實果真如此嗎?
在我看來,恰恰相反,香港不僅不是文化沙漠,還是文化綠洲,香港有文學,而且有雄厚的文化底蘊與獨特的文學花果,是中華文學大花園中的一枝奇葩。
一,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重鎮
香港很小,只有一千平方公里,但她的文學場域卻遠比我們相像的大,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她在現代文學史上所承擔的中心角色,以及文化的幅射能力,另方面是她所秉持的文學價值理...
走進「我城」——中國現代都巿文學重鎮
在一般人眼裏,香港這個商業化大都巿,是時尚文化之都,沒有文學,更有甚者,認為香港是文化沙漠。事實果真如此嗎?
在我看來,恰恰相反,香港不僅不是文化沙漠,還是文化綠洲,香港有文學,而且有雄厚的文化底蘊與獨特的文學花果,是中華文學大花園中的一枝奇葩。
一,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重鎮
香港很小,只有一千平方公里,但她的文學場域卻遠比我們相像的大,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她在現代文學史上所承擔的中心角色,以及文化的幅射能力,另方面是她所秉持的文學價值理...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前言
「我城」,是香港的代名詞,香港人的想像共同體。
自從西西以《我城》為題寫下她的香港故事以後,這個詞匯就日益成為此城的自我稱號,凝聚了香港人對居於斯、感於斯、戀於斯的一種感念與情意結。一個城巿的身世,說到底是人的故事;她的前世與今生,始終關乎人的生存處境與命運。「我城」代表的是香港的一個人文形象,一種情感投射。
那麼,「我城」是如何被形塑出來的?這個「城」有甚麼特性與面向?
這個夏天,我有幸為大學中文系的研究生開一門「香港文學專題」,於是借此機會重新審視調整了一下自己的研究方向。過往,我更多的是...
「我城」,是香港的代名詞,香港人的想像共同體。
自從西西以《我城》為題寫下她的香港故事以後,這個詞匯就日益成為此城的自我稱號,凝聚了香港人對居於斯、感於斯、戀於斯的一種感念與情意結。一個城巿的身世,說到底是人的故事;她的前世與今生,始終關乎人的生存處境與命運。「我城」代表的是香港的一個人文形象,一種情感投射。
那麼,「我城」是如何被形塑出來的?這個「城」有甚麼特性與面向?
這個夏天,我有幸為大學中文系的研究生開一門「香港文學專題」,於是借此機會重新審視調整了一下自己的研究方向。過往,我更多的是...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目錄
前言
代序 走進「我城」——中國現代都巿文學重鎮
第一講 解讀我城——流行眼、文化心、文學地圖(導論)
1. 文化本是平常事
2. 藝文解讀與品鑑
3. 文變與時尚
4. 思想方法與研究步驟
第二講 摩登我城——藝文都巿風及凝視方式
1. 都巿文化的經典論述
2. 閱讀城巿(香港經驗)
3. 觀照與書寫(審美形式)
第三講 多面我城——香港都巿形象的文學形塑
1. 「傾城」與「燼餘」
2. 「我城」與「浮城」
第四講 記憶我城——文字與影像中的族群意符
1. 獅子山精神
2. 紅白藍意象
第五講 漫遊我城——香港文學中的「酒徒」現象...
前言
代序 走進「我城」——中國現代都巿文學重鎮
第一講 解讀我城——流行眼、文化心、文學地圖(導論)
1. 文化本是平常事
2. 藝文解讀與品鑑
3. 文變與時尚
4. 思想方法與研究步驟
第二講 摩登我城——藝文都巿風及凝視方式
1. 都巿文化的經典論述
2. 閱讀城巿(香港經驗)
3. 觀照與書寫(審美形式)
第三講 多面我城——香港都巿形象的文學形塑
1. 「傾城」與「燼餘」
2. 「我城」與「浮城」
第四講 記憶我城——文字與影像中的族群意符
1. 獅子山精神
2. 紅白藍意象
第五講 漫遊我城——香港文學中的「酒徒」現象...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