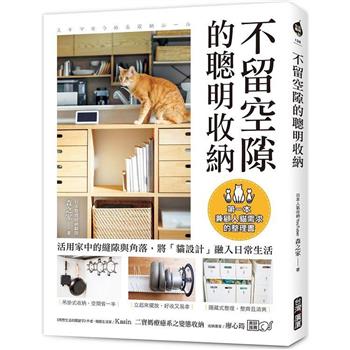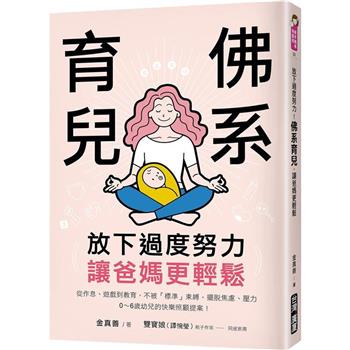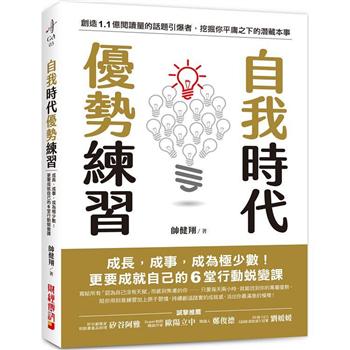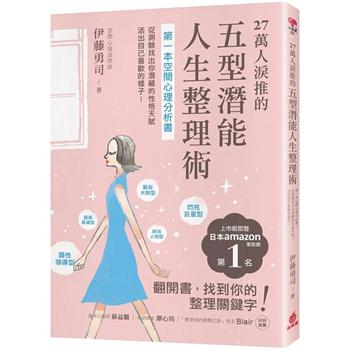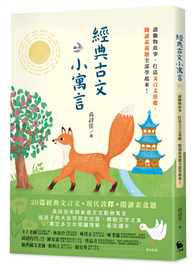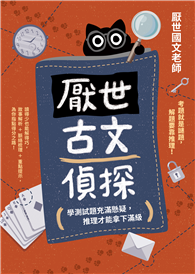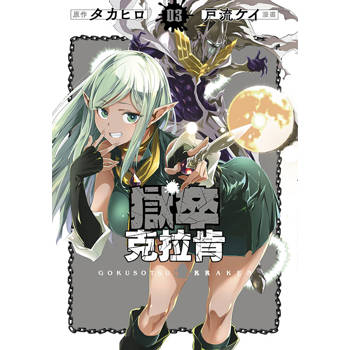殖民主義與西方流行音樂的香港意義
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不只表現於攻城奪池,亦表現於文化霸權、經濟和流行文化的消費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關係產生了中心和邊緣的二元對立論述。西方殖民主義的源頭即是建構的中心,被殖民者和其所處地即是邊陲。如此說來,西方舶來品,無論高級或通俗的、都會較本地的來得優越,例如宗主國的文字,奉為官方用語和法律的藍本,而本地被殖民者的文字淪為次等,可見一斑。由於政治、經濟、社會和教育均牽涉權力的支配,文化產物的欣賞和消費亦以宗主國為效尤和優待。相形之下,本地文化創作被忽略,邊緣化,故其呈現和發展,尚待爭取認受的地位和尊重。故後殖民論述發展愈成熟,本土論述和創作,得到肯定,藉以抗衡根深蒂固的殖民主義遺風,這亦正是後殖民的中心論述。
97年前的香港教育是殖民地教育,有意或無意的灌輸宗主國的文化優越,薰陶莘莘學子。英語在法律上凌駕中文,亦是法律條文的依歸。風氣所及,一切與英語有關的事物均沾上了前述的優越感:英文教育得到家長和社會的肯定;西風美雨的事物具舶來品的稀有元素,亦是優越的象徵。英美來的流行文化,例如流行音樂(pop music)自然受到時下年輕人的喜愛,人人均能哼幾句,更有自組樂隊,模仿英美流行樂隊,成為六、七十年代本地一股「西洋風」潮流。這便是香港流行文化重要的一頁,亦是英美流行歌曲在香港的黃金年代。貓王皮禮士利(Elvis Presley)、白潘(Pat Boone)、奇里夫李察(Cliff Richard)、保羅安卡(Paul Anka)、力奇尼魯臣(Ricky Nelson)、莊尼馬菲士(Johnny Mathis)、湯鍾士(Tom Jones)、英格柏咸拔甸(Englebert Humperdinck)和康妮法蘭西絲(Connie Francis)等,均風靡一時。本地的流行歌手和樂隊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Sam Hui and The Lotus, Joe Junior and The Side Effects, The Mystics, The Menace, Astro-Notes, Thunderbirds, Mod East, Magic Carpet, The Black Jacks, Anders Nelson and The Inspiration, Danny Diaz and The Checkmates, Roman and The Four Steps, Christine Samson and The D’Topnotes, The Blue Star Sisters, The Reynettes, Marilyn Palmer and Irene Ryder等,亦有大量本地擁躉,與英美歌手,不遑多讓。2016年六月香港中華書局出版了李信佳著的《港式西洋風:六十年代香港樂隊潮流》記載了這一段在殖民統治下香港流行音樂的光輝歷史。可惜本書只著意記載這一段香港流行音樂的歷史,很少著墨這一種流行文化背後的政治和文化的影響。
當時英美傳入的流行歌曲(Hit Song)鮮少涉及政治和社會爭議的主題。無論表達形式和歌辭內容,都只是一般青春期的情愛題材,有各地年青人普遍性的共鳴,避過了因不同社會和文化造成的隔閡。這類流行歌還未沾上越戰時的反戰和種族等意識型態。故亦能輕易登陸香港的流行文化市場,影響本地青年爭相效尤。前述本地組成的樂隊,雖有自己的風格,但基本是模仿西方傳入的流行音樂,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西洋風」,猶如媲美十八、九世紀西方在文化上曾出現過的「中國風」(Chinoiserie)和「日本風」(Japonism)。都可看成是一種藝術創作上的仿效(Mimicry)。正如荷里活泰倫天奴(Quentin Tarantino)導演的電影Kill Bill, Volumes I & II, 是中國風和日本風的混合體,既有日本劍術,又有中國功夫的元素,透過荷里活的市場包裝,面向全球觀眾的一種流行文化。
英美流行歌曲在五、六十年代流行於香港,除了挾英國殖民宗主國語言的光環和外國月亮是圓的因素外,本土消費文化市場的貧瘠,容易受到外來流行文化(例如西方流行音樂)的攻佔。五、六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的創作,才剛起步。粵語流行曲,傳統粵曲只能吸引年長和低下階層的聽眾;南來的國語時代曲亦只限於南來的聽眾,未能照顧戰後的嬰兒潮(Baby Boomer)所產生的龐大青少年消費市場,英美流行音樂挾文化優越,時尚和偶像歌手的包裝,與荷里活電影,成功打入本地流行文化市場,造就了前述的「西洋風」。亦可說是一種流行文化的殖民主義。與香港的殖民地身份巧妙的結合起來。
英美流行歌的盛行,旋律和歌辭各有吸引的地方,亦是構成其部份的意識型態,其他部份還包括歌者的生動傳神演繹。歌曲流行與否不但靠歌辭,還要靠歌者如何在臺上或空氣中通過個人的聲線去表達(perform)。流行音樂著重舞臺上的表達,歌辭變成歌者聲線表達工具,最終的消費品是集合音響、節奏、歌辭和歌者個人形象和身體語言。尊,史托尼(John Storey)對流行音樂的感染力有如下的分析:
音樂產生的快樂,不是表達發生他處的意義反思,而是來自演繹眼前實實在在創作產生的感覺。
The pleasure of music is not the pleasure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something
that happened elsewhere(a reflection of meaning)but the pleasure of what is
being made(the making and materiality of meaning),見Cultural Studies &
the Study of Popular Culture: Theories and Methods, Edinburg University Pres,
1996, p.106.
當時受歡迎的樂與怒歌手都有獨特的音色,例如皮里士尼。除了演唱狂野,獨樹一格的唱腔,他的聲線具有一種韻味,正如Roland Barthes分別 “meaningful singing” and “singing that makes meaning,” 指出後者有一種音質上的砂感 “The Grain of the Voice” ,(“The Grain of the Voice,” in Image, Music, Tex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7, p.157.)非常罕有而具一牽人心魄的真實感。文化評論家Simon Frith參考Roland Barthes的文章後,指出只有Elvis 和Sinatra等歌者才具有此砂礫的魔力。(Sound Effects-Youth, Leisure, and the Politics of Rock’n’Rol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1, p.165)兩人均有不同年代的擁躉,風靡一時,但前者正如約翰連儂所描述: Before Elvis, there was nothing. 分別在於二人對流行音樂的真人演繹上。二人均有迷人的感性表達(Performance of emotion),但前者更能創做表演過程中的情感(emotion of performance)。這正是 John Storey 所分析的流行音樂的引人入勝處——“The pleasure and power of popular music is not in the performance of emotion but the emotion of performance”。(見前p.106)香港六十年代的「西洋風」歌手中能有接近這種 “the grain of the voice”,記憶中有 Michael Remedios和Joe Junior等人。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通俗與經典的圖書 |
| |
通俗與經典【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出版日期:2021-05-28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37 |
Literature & Fiction |
$ 264 |
中文書 |
$ 270 |
華文文學研究 |
$ 270 |
文學作品 |
$ 270 |
世界文學論集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通俗與經典
本書橫跨幾類文本論述,有英語學習的探討,流行文化的分析,電影及舞臺演出的評論,以及一些往事掠影的散文和短篇。內容有通俗淺出的、亦有較學術性深入的闡述。
「通俗篇」的文章環繞着流行音樂與文化,「經典篇」的文章觸及文字及媒介表達的問題,結尾部份加入七篇有關「啓蒙與成長」主題散文和創作,構成一往事掠影的卷外篇。
這本集子的文稿都是自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後東扯西湊,毫無心理壓力下寫成。文體帶點像西方自十九世紀流行的Causerie味道,這種書寫又稱Causeries du lundi,英語即 Monday Chats,具文藝性之餘,亦可下具家常,街談巷議,而不需服膺一般學院式的Publish or Perish 的標準,在人到「聽雨僧廬下」的境地,亦誠一樂事。
作者簡介:
陸潤棠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赴笈加拿大約克大學攻讀英國文學碩士,研究對象為英國戲劇家哈勞.品特(Harold Pinter);後轉美國密芝根大學,攻讀比較文學博士學位。畢業後曾任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和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以及台灣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國科會訪問教授,佛光大學文學系教授,劍橋大學羅便臣學院訪問學人。2009-2018年任香港恒生管理學院英文系教授、主任及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現任香港珠海學院英文系教授及代理文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著作有《電影與文學》,《西方戲劇的香港演繹:從文字到舞台》、《中西比較戲劇和現代劇場》,Studies in Chinese-Western Comparative Drama, Before and After Suzie: Hong Kong in Western Film and Literature等書。
章節試閱
殖民主義與西方流行音樂的香港意義
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不只表現於攻城奪池,亦表現於文化霸權、經濟和流行文化的消費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關係產生了中心和邊緣的二元對立論述。西方殖民主義的源頭即是建構的中心,被殖民者和其所處地即是邊陲。如此說來,西方舶來品,無論高級或通俗的、都會較本地的來得優越,例如宗主國的文字,奉為官方用語和法律的藍本,而本地被殖民者的文字淪為次等,可見一斑。由於政治、經濟、社會和教育均牽涉權力的支配,文化產物的欣賞和消費亦以宗主國為效尤和優待。相形之下,本地文化創作被忽略,...
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不只表現於攻城奪池,亦表現於文化霸權、經濟和流行文化的消費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關係產生了中心和邊緣的二元對立論述。西方殖民主義的源頭即是建構的中心,被殖民者和其所處地即是邊陲。如此說來,西方舶來品,無論高級或通俗的、都會較本地的來得優越,例如宗主國的文字,奉為官方用語和法律的藍本,而本地被殖民者的文字淪為次等,可見一斑。由於政治、經濟、社會和教育均牽涉權力的支配,文化產物的欣賞和消費亦以宗主國為效尤和優待。相形之下,本地文化創作被忽略,...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自序
本書題目為:《通俗與經典》。橫跨幾類文本論述,有英語學習的探討,流行文化的分析,電影及舞臺演出的評論,以及一些往事掠影的散文和短篇。有通俗淺出的、亦有較學術性深入的闡述。
「通俗篇」的文章環繞着流行音樂與文化,由〈殖民主義與西方流行音樂的香港意義〉,到通過如何從聽英美流行歌學習語文和語文背後的文化認知,論析中兼及性別、種族、階级和女性主義等意識型態問題,例如:〈聽Oldies學英文Ⅰ-Ⅱ〉、〈趣談英文歌辭的數字〉、〈美國流行音樂中的情歌續唱現象1〉、〈美國流行音樂中的續唱情歌2〉、〈英文流行歌...
本書題目為:《通俗與經典》。橫跨幾類文本論述,有英語學習的探討,流行文化的分析,電影及舞臺演出的評論,以及一些往事掠影的散文和短篇。有通俗淺出的、亦有較學術性深入的闡述。
「通俗篇」的文章環繞着流行音樂與文化,由〈殖民主義與西方流行音樂的香港意義〉,到通過如何從聽英美流行歌學習語文和語文背後的文化認知,論析中兼及性別、種族、階级和女性主義等意識型態問題,例如:〈聽Oldies學英文Ⅰ-Ⅱ〉、〈趣談英文歌辭的數字〉、〈美國流行音樂中的情歌續唱現象1〉、〈美國流行音樂中的續唱情歌2〉、〈英文流行歌...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自序/3
卷一:通俗篇
殖民主義與西方流行音樂的香港意義/9
聽Oldies學英文Ⅰ/13
聽Oldies學英文 Ⅱ/15
趣談英文歌辭的數字/17
美國流行音樂中的情歌續唱現象/19
Oldies中的性別岐視/23
英文流行歌與女性主義/25
流行文化與意識型態/33
國語時代曲與香港/37
〈玫瑰玫瑰我愛你〉的西方演繹/41
中英夾雜語法的商榷/49
大學的英文系是怎樣的一門學科?/51
卷二:經典篇
西方電影與文學的香港城市景觀/57
「洋為中用」︰西方文學批評詞彙的應用問題:以「悲劇」和「浪漫主義」為例/69
粵劇戲曲電影及粵劇戲曲藝術:題材和媒介...
卷一:通俗篇
殖民主義與西方流行音樂的香港意義/9
聽Oldies學英文Ⅰ/13
聽Oldies學英文 Ⅱ/15
趣談英文歌辭的數字/17
美國流行音樂中的情歌續唱現象/19
Oldies中的性別岐視/23
英文流行歌與女性主義/25
流行文化與意識型態/33
國語時代曲與香港/37
〈玫瑰玫瑰我愛你〉的西方演繹/41
中英夾雜語法的商榷/49
大學的英文系是怎樣的一門學科?/51
卷二:經典篇
西方電影與文學的香港城市景觀/57
「洋為中用」︰西方文學批評詞彙的應用問題:以「悲劇」和「浪漫主義」為例/69
粵劇戲曲電影及粵劇戲曲藝術:題材和媒介...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