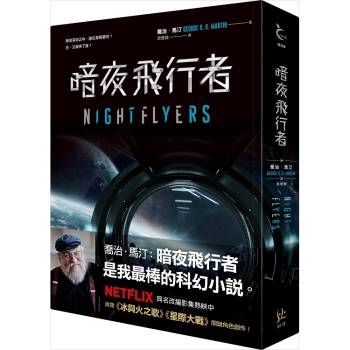香港的現代主義旗手
久被文學史遺忘的文學多面手
本書收錄廿五篇盧因作品,除了小說,還有散文,或可歸類為散文化的小說,寫作年份從1960到1990年代末——〈拉撒路〉於1960年1月發表,作者執筆時還是1950年代——足足四十年,這本書從寫作年份到文類都較為複雜。
一本書收錄了作者四十年來的作品,固然是作者個人的精心安排,於讀者而言,卻方便了對作者創作生涯的審視,從而對作者的作品有更廣闊及更深入的認識。以《拉撒路》來說,書裡有五篇小說寫於1960年代,然後是二十篇寫於1980到1990年代的小說與散文。
沿著本書從頭到尾讀下來——從作者廿多歲的作品到六十多歲的,可以清楚得見作者心境與文風的轉變,從青年時代悶雷似的憤懣不平,中年後轉而為戲謔嘲弄,到了1990年代步入黃金之秋,作者的文章已經寫得瀟灑自由,完全是豁然開朗雲淡風輕。
作者簡介:
盧因
原名盧昭靈,一九三五年於香港出生,祖籍廣東番禺,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作家,筆名有盧因、洛保羅、馬婁、張學玄等。自一九五二年起向《華僑日報》、《香港時報》、《新生晚報》、《星島日報》、《星島晚報》、《新思潮》、《好望角》、《中國學生周報》、《香港文學》、《城市文藝》及《文學世紀》等報刊發表散文、短篇小説和文學評論。
一九五八年底與崑南、王無邪和葉維廉等人合辦現代文學美術協會,先後出版純文學雜誌《新思潮》及《好望角》。一九五九開始為文學副刊《香港時報.淺水灣》撰稿,介紹和翻譯西方前衛文學。一九六一任台灣《筆匯》月刊香港代理人。一九六六年起參與編輯《南國電影》;其間亦曾任《四海周報》編輯。一九七三年移民加拿大,一九八三年始重新發表文章。與梁麗芳等人於一九八七年與友人共同創立加拿大華裔寫作人協會,歷任會長和理事等職。
一九六六至六七年間以筆名馬婁發表《十七嵗》、《藍色星期六》和《暮色蒼茫》等三本「四毫子小說」,另有文集《溫哥華寫眞》和《一指禪》等。
章節試閱
想起毛主席不亦快哉
去年第四期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社會科學戰線》最近才收到。翻開首頁,赫然出現這麼一個醒目標題:〈毛主席讀書生活紀實〉,是這一期的壓卷專稿。能稱為專稿,必然放在首頁;能放在首頁,自是份量極重的好文章。單是專稿兩個大字,已然吸引我的興趣,何況內容又是縷述毛主席的讀書生活,怎能不讀?一九七二年六月廿一日,長了一副梟雄相貌的尼克松訪問中國,行裝甫御,立刻趕去中南海晉謁毛主席。從電視上看到老態龍鍾的主席,呲牙咧嘴的總統,派頭活像大商行董事長的基辛格,以及中國政壇不倒翁周恩來。這幾位叱咤風雲的大人物竟能聚首一堂,的確史未曾有。更引起我的興趣和好奇的,卻是毛主席中南海的書房,線裝書排滿了整座書架,層層高疊,次序井然,原來主席居然也是大行家。現在才猛然省起,主席博覽群書,手不釋卷,藏書數量肯定不只這幾百本。如果像前輩吳魯芹那樣,將書房硬分成一齋二齋,主席的書房一定也設了很多分齋。一九七二年六月距今快十年,主席肥肥胖胖的硬朗身子,躺在水晶棺裡也躺了快六個年頭。作為中國人民一份子,我沒有理由會忘記他老人家。作為一介小民、愛書讀書之餘,又喜歡附庸風雅,學主席藏書批書的凡夫俗子。更令我懷念的,倒是主席的藏書。
〈毛主席讀書生活紀實〉寫得很好,也很精彩,一洗學術八股頹風。作者忻中文筆穩健,粗中帶細,雖說全文氣勢像風趣幽默的報告文學,刊在以學術研究標榜的《社會科學戰線》,未免格格不相入。不打緊,學術文章同樣可以輕鬆自如。這個晚上,我默默對自己說:先煮一壺朋友送來的一品茉莉香片,提提神,醒醒腦;要坐得四平八穩,還要目不斜視。趁夜闌人靜、無星無月,先讀一讀〈毛主席讀書生活紀實〉。平日夜讀,甚少茉莉相伴。今夜案頭無語,睡意全消。立刻記起文革初期,主席他老人家由賊眉賊眼的彪叔陪著,站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時,慢慢向天舉起的手勢,簡直像一位為信徒祝福的牧師。「他常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獨自坐在小油燈旁,不知疲倦地讀書學習。」這豈不是我自己的寫照麼?我也用過小油燈,後來又用過火水燈,還有一個時期用過大光燈,現在改用電燈。我決不敢和毛主席相比。在延安那一段艱苦歲月,那裡有電燈?住進中南海以後,大門口長駐汪東興的手下,來來往往,晉見的人又絡繹不絕。除了大門口,也許還要經過中門口,才可以看到主席書房的小門口。大中小門口都站著荷槍實彈的守衛,再用不著重溫一燈如豆的苦難生涯,燈火通明更不在話下。我這人平日讀書,學了一個毛主席的壞習慣,喜歡像脂硯批紅樓那樣,批語連篇。
我對這一段的批語直書如下:挑燈夜讀,豈不是我的寫照?我像毛主席,還是毛主席像我?主席生而有知,當明白是我像他。主席呀,你在天之靈的靈眼,總能洞悉乾坤,明察秋毫,不會那麼小家氣,說你像我是開罪了你。要是主席的未亡人仍坐鎮天安門,說毛主席像我這句話所擔當承受的罪名,也夠瞧的了。夜讀到底不是偉人專有的怪癖。古人無燈,就出了一個聚螢火求明的書蟲,窗下苦讀。夜讀成癖,實在無可厚非。古儒白天遊山玩水,吟詩作對,到了晚上,往往展讀以求補充。今不同古,但讀書人的興趣和習慣,千百年來竟積習成統。經過八小時工作,或閉門尋句,或抽煙微笑;在書堆裡追索自己的世界,探究自己的食糧。也許沉迷在老莊的天地尋獲佳句,也許像林語堂,抽著煙斗幽了自己一默。夜讀當然也有像毛主席那樣,是為了學習。但更廣泛的寒窗夜客,是為了窮年累月養成的習慣,改也改不了。我自己就有過這樣的經驗:夜讀容易入腦,容易領悟。曹雪芹那兩句「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如今隨時可以上口,有時還搖頭擺腦唸起來,在小輩面前裝腔作勢,就是靠長年夜讀記在腦裡的。說到主席他老人家的文章,豈敢不讀?老人家那五大卷選集,一直珍之藏之。有時放在枕邊,有時放在案頭。有時放在廁所,有時放在旅行袋。
說起廁,人人和廁有緣,不能一日無廁,除非流落撒哈拉。讀書人和廁,又結下不解緣。類似例子,古今中外,真是不勝枚舉。毛主席固然是偉大舵手,偉大領袖。正確點說,他更是讀書人。讀書人和廁既結下不解緣,是則主席也和廁結了不解緣。「就拿大便的幾分鐘來說,他都非常珍惜,從不白白地浪費掉,也都用來看書學習。一部重刻宋淳熙本《昭明文選》和其他的一些書刊,他就是利用大便的時間今天看一點,明天看一點,斷斷續續看完的。」利用上廁時間看書,沒有甚麼大不了,寒窗夜客十居其九學足毛主席,分秒必爭。從前的廁所,不像今天那麼講究,只有大城市的富人,才可以享受抽水馬桶。一般人家自備便桶,木製,上覆蓋。大解時,以痰盂盛物,然後傾倒洗淨;晚上放在街門邊,候人清理。鄉下的窮措大更慘,解手只好上茅廁。前一種即五十年代紅歌星李香蘭唱的〈夜來香〉,因為倒糞的零時開工,人都睡了,雖臭氣燻天,亦不易察覺。「夜來香」遺風流傳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才算絕跡。當時的香港,繁華鼎盛,高樓大廈連地起,西樓唐樓大樓小樓,一律改用水廁,「夜來香」遂唱不起來。倒不知延安時代的毛主席,用家廁呢還是茅廁?主席眉宇軒昂,高及六尺,蹲在盂上,還要讀厚厚的刻本《昭明文選》,未免太委屈他老人家了。
想起毛主席不亦快哉
去年第四期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社會科學戰線》最近才收到。翻開首頁,赫然出現這麼一個醒目標題:〈毛主席讀書生活紀實〉,是這一期的壓卷專稿。能稱為專稿,必然放在首頁;能放在首頁,自是份量極重的好文章。單是專稿兩個大字,已然吸引我的興趣,何況內容又是縷述毛主席的讀書生活,怎能不讀?一九七二年六月廿一日,長了一副梟雄相貌的尼克松訪問中國,行裝甫御,立刻趕去中南海晉謁毛主席。從電視上看到老態龍鍾的主席,呲牙咧嘴的總統,派頭活像大商行董事長的基辛格,以及中國政壇不倒翁周恩來。這幾位叱...
作者序
序
從《拉撒路》看盧因的四十年
〈拉撒路〉不但是本書的書名,也是本書開首的第一篇,盧因還是喜歡這個小說的。
多年前檢閱舊雜誌,曾經把《文壇》月刊從頭到尾翻了一遍,來到第178期,見目錄上有短篇小說〈拉撒路〉,作者「馬婁」,拉撒路是天主教新約聖經的人物,耶穌行奇跡令他死而復生;作者馬婁的名字卻是頭一次在《文壇》出現。馬上翻到那頁,於是看了一篇眼前一亮的小說。這小說,只看一遍不夠,必要專心仔細的再讀,方能豁然大悟,明白為何叫做「拉撒路」。小說看罷,心裡愉快,並非因為這是個罪人改邪歸正的故事,而是終於在文風保守的《文壇》,讀到一段新鮮漂亮的小說,當時就喜歡上作者的行文風格。
盧因在《文壇》發表了五個短篇,它們是〈拉撒路〉、〈暗層〉、〈少年牧師手記〉、〈生命的最低層〉和〈陰影〉,除了〈拉撒路〉,都收在2021年出版的小說集《颱風季》裡,為什麼不把〈拉撒路〉輯入呢?
現在想來,也許是盧因的故意,要把〈拉撒路〉留著,作為跟著出版的新書名字。
《颱風季》收錄了盧因1950至1960年代的作品共廿三篇,都是小說,《拉撒路》有作品廿五篇,除了小說,還有散文,或可歸類為散文化的小說,寫作年份從1960到1990年代末——〈拉撒路〉於1960年1月發表,作者執筆時還是1950年代哩——足足四十年,這本書從寫作年份到文類都較為複雜。
一本書收錄了作者四十年來的作品,固然是作者個人的精心安排,於讀者而言,卻方便了對作者創作生涯的審視,從而對作者的作品有更廣闊及更深入的認識。以《拉撒路》來說,書裡有五篇小說寫於1960年代,然後是二十篇寫於1980到1990年代的小說與散文,沒有一篇是1970年代的,為何有這十多年的空白,敢問這十多年作者何處去了,為何不寫?有機會應要問問。
寫於六十年代的五篇小說,應該是盧因對小說創作的發燒期,不但寫作的熱情高,而且喜歡嘗試不同的題材,〈拉撒路〉寫刑滿出獄的「我」在監獄裡度過的最後一個日夜,馬上就要恢復自由的「我」,腦袋裡想些什麼,紅丸、巴比通、白粉、牧師、醫生,獄官為他寫的職業介紹信?有趣的是,「我」在「命運、生活」這兩個詞語裡糾結的同時,又時刻想到獄警獄卒的「殖民的聲調、殖民地嗓子」;幫辦有人情味,但那是「殖民地產品」;抽著沙展送的紙煙,想到的卻是香煙裡有「殖民地味」,如此種種,莫不反映了作者對英國統治下的香港憤懣抑鬱的情懷。
同樣在小說裡滲入國族感情與身份迷惘的是〈異國夢〉,小說以第一人稱,寫我在北婆羅一個森林小鎮與一個土著少女的戀愛。盧因在小說裡詳細描寫了當地土著的生活風俗習慣,如鬥雞、篝火會、馬來男子對中國女子的慾望,土著女子對中國男子的仰慕等等,簡直可以作獵奇小說看。然而盧因想表達的不單單是個以悲劇告終的愛情故事,他要寫的是華人與馬來人的矛盾,即使我在北婆羅成長,是個血氣方剛的青年,又與馬來姑娘洛芝熱戀,但是仍會有「湖南的女孩子很多情,蘇州的女孩子很漂亮,上海的女孩子很會打情罵俏」的想像,我明白「我生長在北婆羅洲,中國是怎樣的,壓根兒不知道,也從未渴望認識中國的女孩子」,我只希望與洛芝在一起,「我只要求這些,此外,我對我的祖國又何所求呢?」。然而與當地人的格格不入,在我與當地土著兩雄爭美時更明顯,儘管我於此地生活,但我在當地人眼中始終是個異類。小說結尾寫我在船上遇到一個乘客,問我的目的地:「哪一個中國?台灣的?大陸的?」,而我是到香港去的,這就來到小說裡比較隱晦的主題:我是誰?
〈戀愛故事〉、〈黃風砂〉以香港為背景,前者是一個「命運的競技場上的失敗者」,電影看了一半,中途離場,在路上零思碎念,從電影到藝術到哲學到讓他失戀的女朋友都想了個遍;後者描寫低下層的艱苦:患肺癆的修路工人被判頭欺詐與拖欠、情同手足的工友的江湖義氣,雖然大家都沒有美好的明天。
與〈戀愛故事〉同樣寫於1960年的〈新口岸〉是盧因小說創作的另一種嘗試,寫女性的婚外情,丈夫是海員,遠在歐洲,而在澳門的妻子與葡萄牙青年如夢似幻的熱戀,盧因以他獨特的文筆,時虛時實的文字剪接與跳躍,讓小說呈現一片迷離的海市蜃樓景像。
盧因觸碰女性心理的小說還有〈春盡〉,寫作時間來到1986年,〈春盡〉的情節結構與人物書寫更為複雜,小說由「我」開始,擴展到不同女子的故事,每個角色各有聲音自有糾結,細碎的事件如水銀瀉地卻又盤繞交錯,最後作者把千絲萬縷一收,頭緒又回到「我」身上,這個帶有懸念的複調小說,與盧因早期的小說比較,差異頗大。
香港回歸前,不少人選擇移民,條件好的申請較容易,條件差的亦有門路,其中一種方法是結婚,多數是女子嫁到外國去。以盧因移居海外多年,必定見識不少這樣的婚姻,此所以有〈相親〉這一篇。小說裡要找老婆的是個住在加拿大的金山伯,沒讀過什麼書,身無長物,更別說有幾多房產物業在手了,然而他即將會得到一個從香港過來的新娘,這新娘本身有物業有女兒,只是聽說了金山伯在彼邦很有作為,決定飄洋過海以身相許。無疑這是個笑中有淚的小說,大概題材已夠沉重,盧因改用較輕快的筆調出之,讀來又是另一種感受。
如果盧因寫武俠小說,或者是加入武俠元素的歷史小說,大家怎麼看呢?這樣的實驗有〈醉倒〉與〈彈筑〉,又是另一道奇詭的文學風景。〈醉倒〉與〈彈筑〉要連著一起看,因為小說的主角是同一個人——荊軻。荊軻刺秦王的故事見於多種史書,事起於燕太子丹密謀刺秦,事結於荊軻刺秦失敗身死,這是不能改變的史實,然而從太子丹召見荊軻,到荊軻在秦王面前圖窮匕現,這中間卻有許多想像空間,稍加發揮即有無盡故事,例如史書記載荊軻出發前:「有所待,欲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荊軻在等人,可是太子丹一再催迫,無奈起程。荊軻等的是誰,一個隱世高人?作者問:如果等到了,去的是兩位高手,一擊而驚天下,止干戈,歷史將怎樣續寫呢?
盧因不寫假如刺秦成功會如何如何,而是以小說家身份,寫那位神秘人物,再把無限可能的聯想留給讀者。如果〈醉倒〉寫的是遺憾,〈彈筑〉寫的就是惆悵,一乘馬車,載著荊軻與高漸離,他們是高山流水惺惺相惜的知己,然而來到河邊,風蕭蕭兮易水寒,終須分手,是生離死別。小說寫高漸離與荊軻的相遇相知,最後是高漸離擊筑悲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小說結尾:「漸褪的暮色更像頭罩,慢慢罩住了無邊際的空間;從天那邊,展開半色淡彩,罩住了地這邊。無窮無盡,又好像難以形容的幽靈」幾句,如重石壓在人心頭。
《拉撒路》裡,有不少文章介乎小說與散文之間,以寫作年份看,都是盧因定居加拿大後寫的,往往也就從當地生活裡取材,〈閨房情趣〉、〈捉雲小記〉、〈松香〉、〈魚喪〉、〈市書〉、〈奇遇〉幾篇寫的都是父母兒女、夫妻朋友的日常,平常日子裡又有小驚喜小趣味,這幾篇文章的寫法,許定銘曾作介紹:「……盧因已走進了另一境界,小說創作走向散文化,無故事,只有片段……不單沒有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連對話也摒棄引號,混在段落裡隨意書寫,完全是: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老子就愛這樣!」(見許定銘〈看盧因表演「一指禪」,《香港文學醉一生一世》,頁176),看來盧因很喜歡這種寫法,而且自1980年代始,到寫於1998年,列為本書壓軸篇的〈情人佳節〉,都是這種看來隨意的流水行雲。
還可以指出的是,沿著本書從頭到尾讀下來——從作者廿多歲的作品到六十多歲的,可以清楚得見作者心境與文風的轉變,從青年時代悶雷似的憤懣不平,中年後轉而為戲謔嘲弄,到了1990年代步入黃金之秋,作者的文章已經寫得瀟灑自由,完全是豁然開朗雲淡風輕。
以讀者眼光看盧因,看法始終是:盧因是個多變、不羈的作家,從行文到取材都是。所以如果在這本書裡,忽然讀到一篇好像是海明威的,並不稀奇,我說的是〈費里莎蒼龍〉。蒼蒼茫茫的費里莎大河上,我與尼克逆流而上,在悲傷的故事裡穿梭,尼克總是有許多為什麼的問題,怎麼能夠一一解答呢,我說尼克,你慢慢自然會明白的。看,連語氣都似尼克的父親。盧因寫尼克,也許是向海明威致意,也許是他興之所至。
讀者如我,只要喜歡,自然會跟得上盧因作品裡的看似無心與寫意。
李洛霞
序
從《拉撒路》看盧因的四十年
〈拉撒路〉不但是本書的書名,也是本書開首的第一篇,盧因還是喜歡這個小說的。
多年前檢閱舊雜誌,曾經把《文壇》月刊從頭到尾翻了一遍,來到第178期,見目錄上有短篇小說〈拉撒路〉,作者「馬婁」,拉撒路是天主教新約聖經的人物,耶穌行奇跡令他死而復生;作者馬婁的名字卻是頭一次在《文壇》出現。馬上翻到那頁,於是看了一篇眼前一亮的小說。這小說,只看一遍不夠,必要專心仔細的再讀,方能豁然大悟,明白為何叫做「拉撒路」。小說看罷,心裡愉快,並非因為這是個罪人改邪歸正的故事,而是終於在文風...
目錄
序 從《拉撒路》看盧因的四十年 李洛霞
拉撒路
附錄:重生的印記——淺評短篇福音小說《拉撒路》 黎玉萍
戀愛故事
新口岸
黃風砂
異國夢
想起毛主席不亦快哉
閨房情趣
捉雲小記
松香
魚喪
一指禪
醉倒
彈筑
詩鬥
聽雪
春盡
奇遇
拙趣
市書
看女
嫁女
晴晚花甲
費里莎蒼龍
相親
情人佳節
序 從《拉撒路》看盧因的四十年 李洛霞
拉撒路
附錄:重生的印記——淺評短篇福音小說《拉撒路》 黎玉萍
戀愛故事
新口岸
黃風砂
異國夢
想起毛主席不亦快哉
閨房情趣
捉雲小記
松香
魚喪
一指禪
醉倒
彈筑
詩鬥
聽雪
春盡
奇遇
拙趣
市書
看女
嫁女
晴晚花甲
費里莎蒼龍
相親
情人佳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