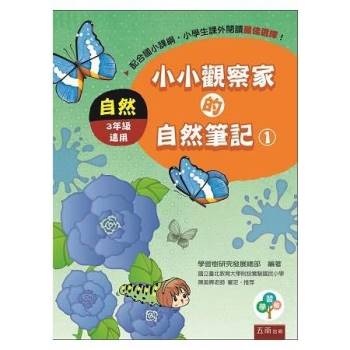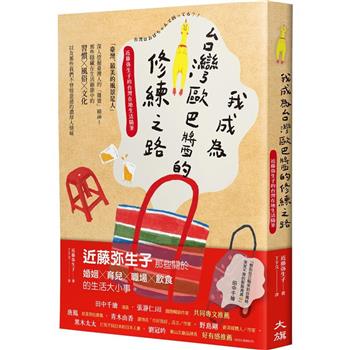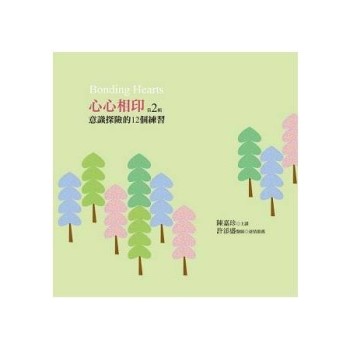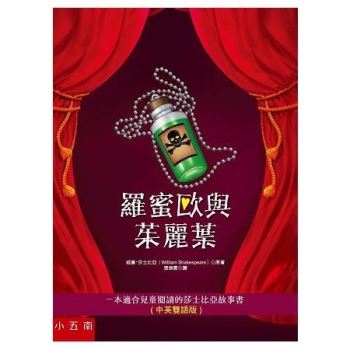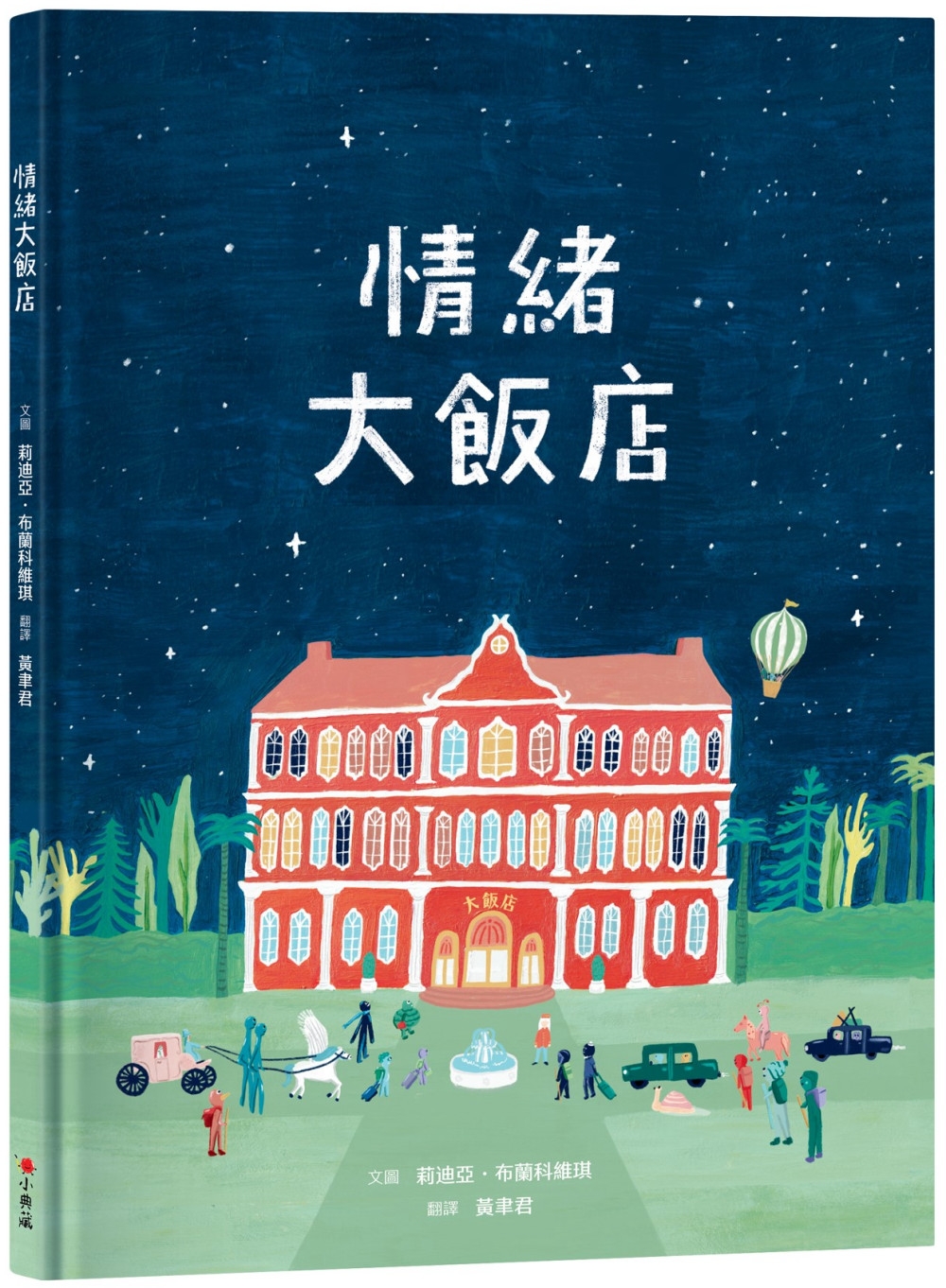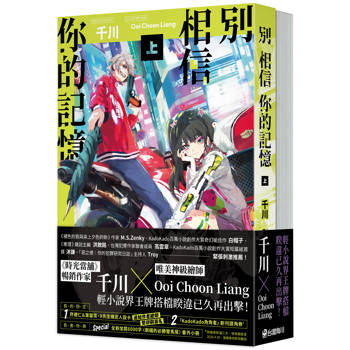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參差杪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360 |
二手中文書 |
$ 395 |
中文現代文學 |
$ 450 |
現代散文 |
$ 450 |
文學作品 |
$ 465 |
現代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參差杪
內容簡介
《參差杪》為香港小說家張婉雯散文結集。本書收錄的作品,其寫作年期橫跨兩個世紀,歷二十餘年,見證了時代之更迭。首章「動物的夢」寫貓、寫鼠,寫城市裡動物的生存空間,盡見作者對牠們的遺憾與補償;「口吻是小說家唯一的劍」以社會經驗漫談文學,以所讀所思引申聯想,慧眼獨具;「在自由的路上踽踽而行」以作者與父輩、師兄相處時光為重心——橫跨歲月,各篇互相參照,流露思念;「將殘的燈火」重新回憶過去的人和事,豐富的人物描寫,盡見小說的運筆;終章「在離散的時代裡她們尚有彼此」,回應當下所身處的時代,寄語完整。作者期望藉著散文書寫,重構記憶與生命、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種種連結。本書分成五個部分,包括青春的觀照、對故人的思念、社區生活的日常,和對文學的體會;以此構成作者的人生觀照,回應當下的變遷。在本書中,作者探索散文寫作的各種可能,包括散文在抒情、評論與記敘上的面貌;或強烈或淡雅的筆觸。作者希望建立紛紜而獨特的散文寫法,開拓本地散文寫作的風格。書中文章篇幅不一,故名「參差」;即使是枝葉末節,也寄望能如大樹樹椏伸向廣闊天空,故曰「杪」——盡見她感受生命的矛盾與反思,細緻豐富。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張婉雯
生於香港,喜歡寫作,關心動物。小說集《微塵記》獲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推薦獎;〈潤叔的新年〉獲第二十五屆聯合文學新人小說獎(中篇);〈明叔的一天〉獲第三十六屆中國時報文學評審獎 (短篇小說),另獲香港書獎、中文文學創作獎等。曾出版:《你在——校園貓的故事》(2020)、《那些貓們》(2019)、《微塵記》(2017)、《甜蜜蜜》(2004)、《極點》(與莫永雄合著)(1998)等。
張婉雯
生於香港,喜歡寫作,關心動物。小說集《微塵記》獲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推薦獎;〈潤叔的新年〉獲第二十五屆聯合文學新人小說獎(中篇);〈明叔的一天〉獲第三十六屆中國時報文學評審獎 (短篇小說),另獲香港書獎、中文文學創作獎等。曾出版:《你在——校園貓的故事》(2020)、《那些貓們》(2019)、《微塵記》(2017)、《甜蜜蜜》(2004)、《極點》(與莫永雄合著)(1998)等。
目錄
推薦序 樊善標
自序
第一章 動物的夢
照貓畫虎
貓族的瑪雅文明
老鼠列傳
那所中學的白老鼠
繁花
動物的夢
研討會後的微塵後記
第二章 口吻是小說家唯一的劍
雄辯的必要
口吻是小說家唯一的劍
爾有何貴爾有何堅
盛世過來人
無用之勇
整餅之道
中大的飲食日常
第三章 在自由的路上踽踽而行
叔叔與我
烏托邦中的迷子
在自由的路上踽踽而行
悼黃繼持老師
憶楊國榮師兄
Yours in struggle
洪葉落
當你凝視深淵時
第四章 將殘的燈火
父系歷史研究
叛逆的祖父
過客
在公園
中大泳池邊
娜庫沙的父親
將殘的燈火
雪地上的肩膀痛
陣痛
第五章 在離散的時代裡她們尚有彼此
樹
異鄉的跛子
師姐
廣島遺跡
患難
強人
明年今日
給我教過的男孩們
真理
過早的蒼老
在離散的時代裡她們尚有彼此
自序
第一章 動物的夢
照貓畫虎
貓族的瑪雅文明
老鼠列傳
那所中學的白老鼠
繁花
動物的夢
研討會後的微塵後記
第二章 口吻是小說家唯一的劍
雄辯的必要
口吻是小說家唯一的劍
爾有何貴爾有何堅
盛世過來人
無用之勇
整餅之道
中大的飲食日常
第三章 在自由的路上踽踽而行
叔叔與我
烏托邦中的迷子
在自由的路上踽踽而行
悼黃繼持老師
憶楊國榮師兄
Yours in struggle
洪葉落
當你凝視深淵時
第四章 將殘的燈火
父系歷史研究
叛逆的祖父
過客
在公園
中大泳池邊
娜庫沙的父親
將殘的燈火
雪地上的肩膀痛
陣痛
第五章 在離散的時代裡她們尚有彼此
樹
異鄉的跛子
師姐
廣島遺跡
患難
強人
明年今日
給我教過的男孩們
真理
過早的蒼老
在離散的時代裡她們尚有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