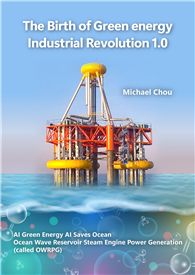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飲食魔幻錄(增訂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30 |
二手中文書 |
$ 540 |
飲食文學 |
$ 540 |
中文現代文學 |
$ 558 |
中文書 |
$ 558 |
現代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飲食魔幻錄(增訂版)
內容簡介
《飲食魔幻錄(增訂版)》結集了杜杜在《明報》專欄發表的短篇文章,增訂版新增兩篇文章,暢談飲食及菜色、由食物所衍生的想像和藝術,探討它們在日常生活與藝術世界中的角色。全書大量地引經據典,提及不少飲食相關的小說、散文,甚至附上一些小食譜。內容多樣又精彩豐富,插圖精美吸引。本書為香港文學館的香港文學經典復刻書系之一。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杜杜
江蘇揚州人。上海出生,香港長大,現居紐約。中學時就讀華仁書院,接受愛爾蘭耶穌會神父的天主教教育,思想背景深受其影響。其後在香港大學攻讀英國文學和比較文學。興趣是電影,立志做作家,最後主要從事教育工作,現已退休。其作品散見於香港報刊,結集作品有《瓶子集》(一九九五)、《非常飲食藝術》(一九九七)、《另類飲食的藝術》(一九九九)、《飲食與藝術別集》(二OO二)、《飲食調情》(二O一六)、《甜美的悠閒》(二O二一)等。
杜杜
江蘇揚州人。上海出生,香港長大,現居紐約。中學時就讀華仁書院,接受愛爾蘭耶穌會神父的天主教教育,思想背景深受其影響。其後在香港大學攻讀英國文學和比較文學。興趣是電影,立志做作家,最後主要從事教育工作,現已退休。其作品散見於香港報刊,結集作品有《瓶子集》(一九九五)、《非常飲食藝術》(一九九七)、《另類飲食的藝術》(一九九九)、《飲食與藝術別集》(二OO二)、《飲食調情》(二O一六)、《甜美的悠閒》(二O二一)等。
目錄
怪雞與龍蛋
夏日雞蛋幻想曲
奇異的果實
荒誕奇幻的飲食世界
靈異魔幻飛魚肉
仙境飲食奇觀
有靈性的鮭魚
罐頭的疑惑
牙齒狂想曲
牙齒的歡樂
嘴的聯想
腐臭神奇臭豆腐
可吃可玩的麵粉公仔
冬日年糕的祝福
樸素家鄉味 童年焦麵和西班牙炒麵包
蠶蛹與禾蟲
嬌俏輕盈的貝奧奇麵包
奪寶奇兵漢堡包
鴨子也升仙
歡樂賓治
名家論味精
素食者的無奈
食肉者的矛盾
危機重重的廚房
讀聊齋一嘗鬼味
乞丐的食物
吃的屈辱
浪漫的地痞小館
飲食的忘我境界
雞蛋的美學
飯桌的瓦解
無中生有鼠尾湯
愛物惜福說殘羹
神奇廚藝大觀
中產階級的晚飯
溫柔的牛油麵包
奇方妙食解相思
秋天的飯盒
羹調天下安(上)
羹調天下安(下)
杯子夢幻曲
檸檬茶與阿拉丁
夏日雞蛋幻想曲
奇異的果實
荒誕奇幻的飲食世界
靈異魔幻飛魚肉
仙境飲食奇觀
有靈性的鮭魚
罐頭的疑惑
牙齒狂想曲
牙齒的歡樂
嘴的聯想
腐臭神奇臭豆腐
可吃可玩的麵粉公仔
冬日年糕的祝福
樸素家鄉味 童年焦麵和西班牙炒麵包
蠶蛹與禾蟲
嬌俏輕盈的貝奧奇麵包
奪寶奇兵漢堡包
鴨子也升仙
歡樂賓治
名家論味精
素食者的無奈
食肉者的矛盾
危機重重的廚房
讀聊齋一嘗鬼味
乞丐的食物
吃的屈辱
浪漫的地痞小館
飲食的忘我境界
雞蛋的美學
飯桌的瓦解
無中生有鼠尾湯
愛物惜福說殘羹
神奇廚藝大觀
中產階級的晚飯
溫柔的牛油麵包
奇方妙食解相思
秋天的飯盒
羹調天下安(上)
羹調天下安(下)
杯子夢幻曲
檸檬茶與阿拉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