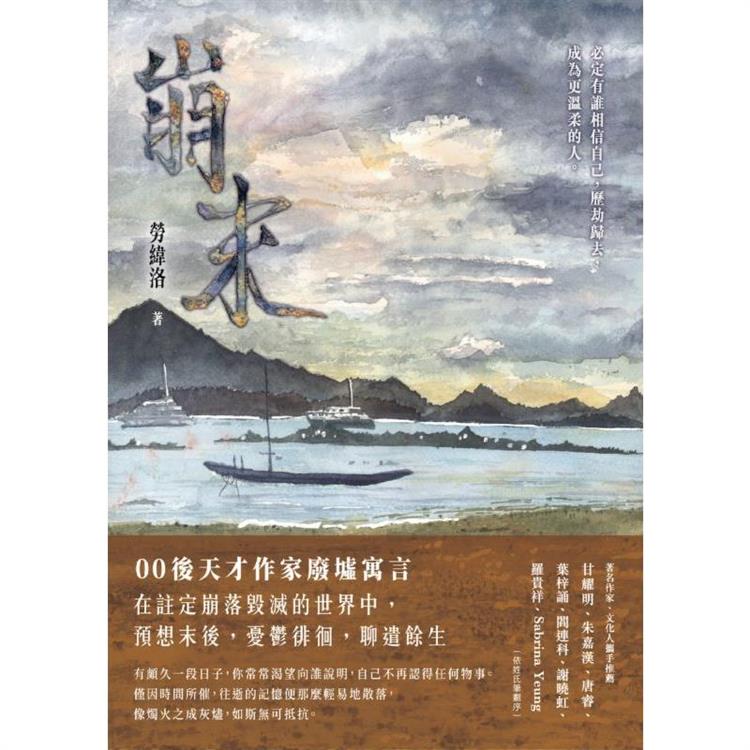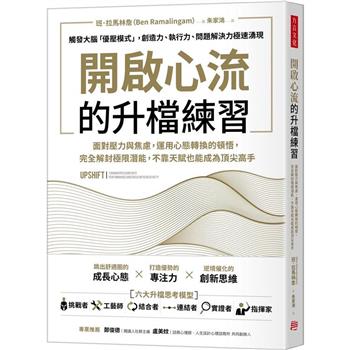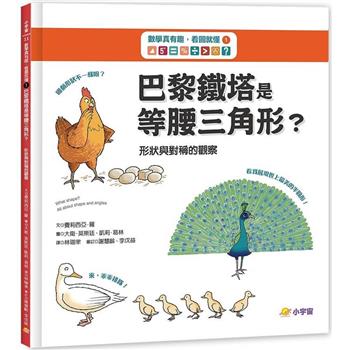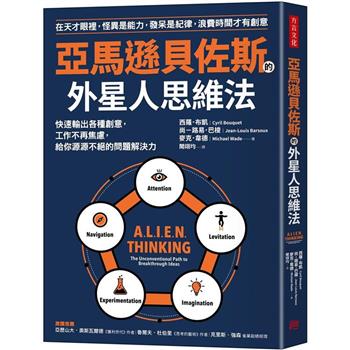第一部 神
當我醒來的時候,淵面幽暗,我感覺渾身疼痛,並暈眩。尚有記憶的最後一個景象,是這樣的:有整座斑橫的珊瑚山,光泡如水母,簇擁著一團巨大的白影,自極遠處,向我迴游而來。在一瞬刻裡,祂便靠近了我。抵著急流,我勉力睜眼,睹見了祂山壁般黑沉嶙峋,而無比龐然的背。我又睹見著祂腹間,波浪狀的表膚,上面有繁複廣鋪的眼瞼,有張有合,張開的如星辰,合起的如礁石。我於是,就那樣驚惶了許久。直至風暴終究漸漸地,離走於我的意識之際,我本欲開口,想要求問,祂是怎樣感受這片星空的,在這不可能更為恆遠的寂靜中。
或許,這樣的景象,早已發生過無數次了。只不過是,每次當我睡著,便會不自覺地忘記,忘得乾乾淨淨。不僅是這場相遇本身,我感覺自己,還會忘記更多的事情,我自己是誰,是從哪裡來的,這具身體的每一部分要怎 樣操作,諸如此類,我都將忘記。然後,當我再次醒來,我會挾帶著上一次睜開眼的時候,所看見的最後一個畫面,就好像剛誕生的嬰雛,在海的至深處,重新習認這個廣邈世界的一小角落,隨浪濤推擁,徐緩地浮近水面,長出四肢,仰頭指向繁星。
最初,總是在空氣沒那麼灼熱的時刻,我才會淋漓地,動用雙腳行上岸邊。有時,天上會有月光,間明或暗,我在牠底下晃搖身軀,將泥沙盡量甩落。有時,天會下雨,那就更方便一些,只需要坐在礁石上,任雨沖洗,一切即會簡潔得如在海中。我發現,若我躺在岸上,時間總是變得很短暫。但即便那樣,我會把握著夜晚,嘗試認識星座,將光度不一的天體,以無數種方法連起、區分,又再度連起來,那種動作,我感會,就像嘗試認識自己的前生那樣。
後來當我漸漸慣習了太陽,即使是白晝,有時也會在岸邊坐上一陣。只是那些時候,我總會覺得無趣,甚至是厭惡。因為,除了離得海洋更近,太陽,這顆星,與其他繁星毫無差別。但每當牠翻過山,照及海面,本來的星辰便要躲匿起來,再不容我所見。這使我漸漸覺得,太陽是一種絕黑的假象,牠掩蓋了天空的臉容。明明在夜裡,繁星再多、再璀璨,也遠遠少微於牠們之間,也不會破壞,那些深幽的間隙。牠們更為謙卑地眨亮,像是曉得,當自己的光穿越時間,傳抵這片海面時,牠們本身就早已消逝了。
從那陣,我也並沒真的想明白,如果牠們理解自己的短促,何以仍要這麼彆扭地,盡量顯得可見,且又如此赤裸而沉默,以供人說明。
我還會記得,在後來的世景,尚未潦草建成的最初時刻,我遇見了祂。那是災異即將到臨的日子,我沒再看過海,雨也沒有從天上降下,已經很久了。我直如屍體不動,癱臥在陰暗的石窟裡,感受風的方向,如此沉靜,以至於猜想自己,就是從那陣開始得了熱病。常常,我會滿眼昏花,那些僅有可見的景物,總是不受控制地,自動化開成燼。我感覺像失卻了晝夜,亦再難辨別,自己究竟是酣睡了,抑或醒著。
是一回,我從熱病的煎熬中起來,做了第一個夢:我離遠睹見一道人影,在水中行走,因為浪的緣故,我無法辨清他的容貌。不知為何,我很想向彼方探近身軀,逐漸傾斜著,只為把他看得,稍更廓清一些。直至,我感覺到水,就如此冰涼地漫過我頂,當有一束光箭劃過水面的聲音,我便知道,自己忽爾變成了那人。水中龐大的重力,一下子將我拽降,眼邊流過無數玻璃似的細小氣泡,莫名其妙地躁動,像圍牆、像風窩向內攏密,把我環繞,也使我感覺像流過了星塵。當中,我恍惚再一次看見了那白影,於是一瞬之間,我就被擊投在海的深淵裡。
不知過了多久,我確確切切地,看見了被浪潮沖上岸的,蒼白發漲的肉身。從彼遠處,橫經一大片沙漠,有一人朝我徐緩走來。我認得那身裝束,頭戴草冠、身披麻衣,在日曬之下像是透風那樣,綻映出琥珀色的雙眼,我總感覺,自己是認得他的。他來到我的跟前,忽以一種相類是跪拜的姿勢,俯伏在我死去多時的骸軀上,輕撫我額角那坨結滿鹽晶的髮,然後,吻住了的嘴唇。我並不能夠理解,那動作意味著甚麼,但看著時,我感到了哀傷。如果此般死滅,乃是我肉身的命,旱地上,我僅存的心,又該所向何方:在最起始,我便尋求,直至世界的末了。
傍晚,一細片暗紅色的雲,從遠空飄來。至雲趨近,漸漸像血潮那樣瑩亮,定住了風,祂雙足,便重新沾及了礁石。當冷硬的觸感,再度漫過胸膛上那道傷疤,前一次醒著的記憶,終於歸返於腦海之內。那時候,早已無法辨認任何物事,曾決意背向整個世界,緩拖著步伐,晃晃跌跌的步進,那沉黑地翻湧著,無際的浪裡。祂借了風,以供自己暫居,一邊沉降,一邊仰視著最後的星叢,彷彿在那更裡面,認出了自己。
也許是,天將要亮了。篝火漸微,暗影在映照裡,只剩餘一張無比模糊的臉容,嘴唇輕顫著,彷彿在喚呼祂的名字。然而昏聵,乃是成為神明的代價。故彼,祂轉頭望向身後,最荒遙的岸際,赫然目睹,那動作猶被永恆地剎定,祂自己靜止的肉身。從此以後,祂便長久說不出話來。
雨於是滂然降下;而時間,亦總已如此將我逮住。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崩末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95 |
現代小說 |
$ 495 |
文學作品 |
$ 495 |
中文現代文學 |
$ 511 |
中文書 |
$ 512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崩末
《崩末》為香港00後年輕作家勞緯洛最新長篇小說。
勞緯洛以詩意、冷僻、細膩的語言寫成一則關於時間與記憶的廢墟寓言,
以敘事建構「曼陀羅」般的環形迷宮,在注定散失、崩落、毀壞的世態裡,
想像末後的重逢。「直到最後一個相信救贖的人,
都因過於久遠的等待而徹底遺忘,且已死去之時,
救贖才會以無人知曉的方式,
靜穆地來臨。」勞緯洛以文學作為對救贖的預想,
對所愛之人給出的微小祈願與簡要應答。
《崩末》是他實踐其「餘生寫作」的一次重要嘗試。
本書為香港文學館的文藝越界叢書系列之一。
作者簡介:
勞緯洛
2001年生於香港,基督徒。現於香港浸會大學主修人文學系。2018年出版小說《卷施》。合著有《黑暗夜空擦亮暗黑隕石》、《樹心邊.新蒲崗》與《根莖葉花--花墟的記憶與想像》等。曾獲文學獎,包括第五屆「恒大中文文學獎」大專組冠軍與「二零二零年中文文學創作獎」文學評論組冠軍等。文學創作、文學評論及哲學評論散見「虛詞.無形」、《方圓:文學及文化專刊》、《Sample 樣本》、《微批 Paratext》、《字花》、「別字」、《明報》與《聯合文學》等。曾為港台電視清談節目《文學放得開》客席主持。曾與不同團體合作,舉辦多場不同主題系列講座、課程與讀書會。
章節試閱
第一部 神
當我醒來的時候,淵面幽暗,我感覺渾身疼痛,並暈眩。尚有記憶的最後一個景象,是這樣的:有整座斑橫的珊瑚山,光泡如水母,簇擁著一團巨大的白影,自極遠處,向我迴游而來。在一瞬刻裡,祂便靠近了我。抵著急流,我勉力睜眼,睹見了祂山壁般黑沉嶙峋,而無比龐然的背。我又睹見著祂腹間,波浪狀的表膚,上面有繁複廣鋪的眼瞼,有張有合,張開的如星辰,合起的如礁石。我於是,就那樣驚惶了許久。直至風暴終究漸漸地,離走於我的意識之際,我本欲開口,想要求問,祂是怎樣感受這片星空的,在這不可能更為恆遠的寂靜中。
或許...
當我醒來的時候,淵面幽暗,我感覺渾身疼痛,並暈眩。尚有記憶的最後一個景象,是這樣的:有整座斑橫的珊瑚山,光泡如水母,簇擁著一團巨大的白影,自極遠處,向我迴游而來。在一瞬刻裡,祂便靠近了我。抵著急流,我勉力睜眼,睹見了祂山壁般黑沉嶙峋,而無比龐然的背。我又睹見著祂腹間,波浪狀的表膚,上面有繁複廣鋪的眼瞼,有張有合,張開的如星辰,合起的如礁石。我於是,就那樣驚惶了許久。直至風暴終究漸漸地,離走於我的意識之際,我本欲開口,想要求問,祂是怎樣感受這片星空的,在這不可能更為恆遠的寂靜中。
或許...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名家推薦
推薦序 羅貴祥 解或不解《崩末》
推薦序 謝曉虹 一種史詩英雄的征(歸)途——讀勞緯洛的《崩末》
推薦序 葉梓誦 失眠之人
第一部 神
第二部 古老的索引
第三部 背海之罪
第四部 風景
跋 寫作的餘生
附錄 夢與馬
墮落
推薦序 羅貴祥 解或不解《崩末》
推薦序 謝曉虹 一種史詩英雄的征(歸)途——讀勞緯洛的《崩末》
推薦序 葉梓誦 失眠之人
第一部 神
第二部 古老的索引
第三部 背海之罪
第四部 風景
跋 寫作的餘生
附錄 夢與馬
墮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