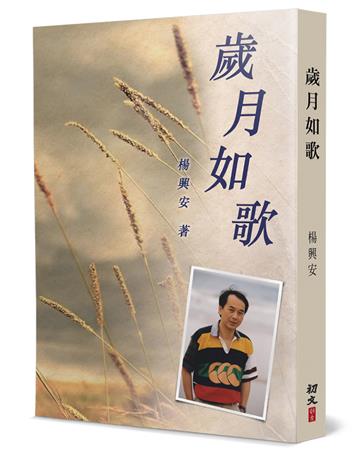在明報輕快的日子
能到《明報》任職,是我的榮幸,也可以說是一種緣分。此中緣由從何說起呢?該是讀金庸小說開始。
前緣
八十年代初離開電視編劇崗位後,創作力仍旺盛,計劃寫小說。為了打好基礎,要分析好小說作準備,於是拿最喜愛、最嫻熟的金庸小說來分析。花了半年公餘時間,寫就《金庸筆下世界》十章,還有腹稿十章未動筆。恰好當時創辦的「博益」出版社徵稿,在好友勸說下,周一郵寄投稿,周二便由當時「博益」負責人施祖賢先生致電約見,他說徹夜讀完我的文章,決定替我出版。真是喜出望外。《金庸筆下世界》不久出版,我郵寄一冊給金庸,可惜未見回音。
約半年後,當時台灣最大的出版社遠景出版社社長沈登恩到香港找我,希望我寫續篇。因尚有腹稿未寫,便一口答應下來,誰知過了年半仍未著一字,沈兄表現焦急,於是不斷送贈旗下出版的論金著專集給我讀。我也問心有愧,終於拋開雜務,於三年後寫成續篇。事有湊巧,我到書局買豹毛筆練習書法,巧遇金庸伉儷也在逛書局。想到何不把新作寄給金庸,請求在《明報》逐日刊出?於是選了兩章寄出,並說自己正修讀碩士。約過了一周,竟然接到金庸親自來電,他說要聘請秘書,問我有沒有意當任?這是天大喜訊,簡直是奇迹,當即訂約會面。
與當世大文豪見面,難掩內心興奮和忐忑不安,想不到談話的氣氛很好,後來金庸主動說出薪酬,寫在一張紙上給我看,問我是否同意。我輕鬆地看了一眼,微笑點頭表示同意。能追隨金庸工作是一種榮幸,還能計較薪酬嗎?其實,恐怕至今他仍不知道,這比我上次領薪的數字低了不少。但機構性質不同,也不能比較。金庸問我什麼時候可以上班?我說十五號吧?金庸問我是否忙,我說沒事,方便算薪金嘛。他說:「下星期一吧!」我立即同意。那天是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我成了明報的一分子。
與同事融和 相處愉快
當時我的職位是「社長室行政秘書」,與公司各部門類似輻射關係,每個部門都會聯繫,但亦非恆常接觸。初期老闆叫我和社長室新同事到各部門了解一下,大家對我們都很客氣,遇到一些知名已久的文化人,我們都表示仰慕,其中對名記者陳非和紫微楊印象最深刻。原來此前我好些刊於《明報》三千字特稿都是紫微楊選用的,我乘機道謝。陳非則向我們說了一些報界的掌故,非常動聽。
和明報同事共事,多是融洽和暢順愉快的,有些交情維繫至今,不過暗湧還是存在。某部門的頭頭,辦公室和寫字枱亂作一團,知道是社長室來的人則有點誠惶誠恐,好像見到御林軍。聽說此人對別人不賣賬,對下屬妄自尊大。這些聽到而難以碰到,亦恐怕是流言。好像我辭職不久,此人亦離職,在文化界消失。
磨練書信 習以致用
社長室的工作較有彈性。但我恆常的工作是要寫覆函,我撰稿再由社長修繕,滿意後才發出。初期金庸拿着我的信稿對我說:「語氣要謙虛些。」只因我認為金庸是成功人物,語氣便寫得堂皇冠冕,以為得體,原來還是要謙虛些。後來金庸又走來囑咐我:「字體要寫小些,」我隨即問原因,他說字體大,好像出告示給人家,這樣不好。隨即又說,一封信最好一張紙說完,這是他給我最初的指示。
由於當日經驗淺,學養不足。最初撰寫回函時都有欠得當之處,金庸便替我改稿,有時在旁還註明怎樣錯了,該寫什麼。我看到改稿,既汗顏慚愧,又感激,會整日惶恐不安,對自己深責,感到不能勝任。後來要求自己首先不能犯重複錯誤,再找離我日久的尺牘涉獵多讀。漸漸金庸改得少了,後期我感到寫得未必好,但他再沒有修改我的文字了。甚而在一些初稿上附夾寥寥數字「寫得很好。」,這便使我開心幾天。我衷心感謝金庸對我的包容,更感謝他對我的點撥,終身不忘。
當時國內開始接納金庸小說,引致許多讀者來信好奇詢問或表示意見,月中數量不少。記得我在職期間這類提問我都答得的當,記憶中金庸看後都沒有修改,都由他親署後寄出。
籌備報慶與社論專集
入職《明報》翌年剛好是明報三十周年報慶,籌備報慶不免一番工作,慶祝三十周年的標誌便是我設計的。此外籌備大型聚餐慶祝,最有意義的是本報友報的作家將聚首一堂,當為本港文化界的盛事,我亦期望見到許多心儀作家的風采。結果一番忙碌後,報慶當天暴風襲港,取消聚餐,真是大煞風景。
此外,我受命編彙《明報社論專集》為慶祝報慶項目之一,無前題囿限。我想到《詩經》三百篇恆久傳誦,《明報》三十年便來三個社論三百篇,共九百篇。第一輯內容有關香港,第二輯內容關於中國,第三輯論及世界大事、人物、各地風尚、習俗等等時事問題。可惜籌備八八九九,金庸突然取消此一計劃,不知原因,但極為可惜、可惜。
歷來《明報》社論逾萬篇,因工作關係我都要瀏覽,當然有精粗之別,雖然後來取消《社論集》計劃,但在過程中我卻獲益良多,可說一生難遇,猶如得睹武俠小說中武林秘笈。原來金庸的武俠小說是九陰真經,社論是九陽真經。《社論集》是極有價值的社會大學教材,是歷史文獻。從中有社會性常識、啟發性資料、世情得失事故的探討,使我增添學養,智慧大為開啟。其中一篇「自來皇帝,不喜太子」說出道理,至今印象猶深,內文輾轉說出的道理,令人拍案。真多謝金庸先生,給我這樣的機會修煉。
因報社的運作主要是晚上,早上便較清暇,期間每周我都有幾天到太古城健身室健身,再到北角報社上班。我是練氣不練力,非想骨肉橫生。健身後洗洗澡才上班,何等輕快?報社提供午飯,六人一桌,四菜一湯,到時便吃,吃完便走,連點菜也不用費神,何等瀟灑?那時剛好跟永憬法師學靜坐,飯後在房子把燈光關了,一片漆黑,一閉眼,再張開眼,準是過了半小時有多,再重新投入工作。生活這樣有規律,身心健康也。
結緣《明報月刊》
後來金庸差我到《明報月刊》幫忙,不久調職到《明報月刊》,我有點不高興,想到《明報》已非久留之地。在《月刊》認識到古德明,大家談得來。古兄是位較性烈的謙謙君子,外圓內方。他的中英文造詣均深厚,做事認真,曾為一言一語而到圖書館翻查半天。每期《月刊》出版後,他都掏腰包請編輯部同事午飯,大抵這是「古風」,想不到是他和我同一天辭職。
在《明月》工作沒有壓力,對我而言工作輕鬆。但過了不久,舉家批准移民海外,便離開明報。後來再回港,是另一個故事了。離開了《明報》,才體會到金庸為我的安排。因為他不知道我申請移民,而金庸自己也快將離開《明報》,便及早安排我到學術性較濃的《明報月刊》工作。如無事故,我可以安安穩穩輕輕鬆鬆工作至退休,有如給我一張長期飯票。我對金庸為我的費心,未宣於口,內心還是永遠銘謝。得幸金庸的知遇,使我生命中添上輕快、恆久眷念的彩筆。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歲月如歌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78 |
現代散文 |
$ 238 |
中文書 |
$ 243 |
現代散文 |
$ 243 |
中文現代文學 |
$ 243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歲月如歌
本書名為「歲月如歌」,實因無論內中談及的人物,還是社會現象,都是歲月如流的時代印記,皆可訴可歌。
正如李白所說「浮生若夢,為歡幾何」。
寄盼讀者翻卷之餘,更感悟歲月之無情與有情。
好評推薦:
「《歲月如歌》一書收錄了楊興安博士談文字、文化、文學、教育和歷史鈎沉等多篇文章。楊博士是興中會先烈楊衢雲先生的堂姪,他愛研究唐代傳奇,關心教育。《歲月如歌》是楊博士寫的一部書,也是他的人生點滴。他的作品是一座文史哲的寶山,進入這座寶山的讀者,當不會失望,一定不會空手而回。」
——曾紹樑
作者簡介:
楊興安
文學博士。專業研究唐代傳奇及小說,香港出生及成長。楊氏多年來從事文教工作,曾任職教學、報社、電視台及商業機構。八十年代任明報社長查良鏞秘書。九十年代任長江實業集團中文秘書。並於多所大學及香港各大機構職員培訓主講中文課程。期間接受報章、電台、電視台多次訪問。出席多次各地學術研討會。被邀約為主講嘉賓。
楊氏嗜愛藝文,八十年代開始寫作,早年獲博益小說徵文獎,出版多類型著作,包括《金庸小說十談》、《金庸小說與文學》、《現代書信》、《浪蕩散文》、小說《柳岸傳情》。舞台劇作《最佳禮物》與《無名碑》,均於香港公演多場。近著有《唐傳奇小說集》及散文《歲月如歌》。現為香港作家聯會永遠會員。
章節試閱
在明報輕快的日子
能到《明報》任職,是我的榮幸,也可以說是一種緣分。此中緣由從何說起呢?該是讀金庸小說開始。
前緣
八十年代初離開電視編劇崗位後,創作力仍旺盛,計劃寫小說。為了打好基礎,要分析好小說作準備,於是拿最喜愛、最嫻熟的金庸小說來分析。花了半年公餘時間,寫就《金庸筆下世界》十章,還有腹稿十章未動筆。恰好當時創辦的「博益」出版社徵稿,在好友勸說下,周一郵寄投稿,周二便由當時「博益」負責人施祖賢先生致電約見,他說徹夜讀完我的文章,決定替我出版。真是喜出望...
能到《明報》任職,是我的榮幸,也可以說是一種緣分。此中緣由從何說起呢?該是讀金庸小說開始。
前緣
八十年代初離開電視編劇崗位後,創作力仍旺盛,計劃寫小說。為了打好基礎,要分析好小說作準備,於是拿最喜愛、最嫻熟的金庸小說來分析。花了半年公餘時間,寫就《金庸筆下世界》十章,還有腹稿十章未動筆。恰好當時創辦的「博益」出版社徵稿,在好友勸說下,周一郵寄投稿,周二便由當時「博益」負責人施祖賢先生致電約見,他說徹夜讀完我的文章,決定替我出版。真是喜出望...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前言
時代的印記
本人先後出版了十多部著述,但散文只有二十年前的《浪蕩散文》。年前承文灼非兄、鄧傳鏘兄約稿,散文雜文寫多了,分別在雜誌及網頁刊出。今選出集而成冊,賦名《歲月如歌》。第一組「歲月」,收錄一些青少年時代及至遙遠童年的憶述。從中反映香港的演進和昔日的香港,那較貧窮和安逸的日子,令人懷緬。對今日港人,或更有感悟之處。其次是一些生活感受的散文,集中談論文士、文心和文化。未知今日在香港生活的讀者,是否能引起共鳴。
及談古今文人言行,其中其人文采事業,即未能驚天動地,...
時代的印記
本人先後出版了十多部著述,但散文只有二十年前的《浪蕩散文》。年前承文灼非兄、鄧傳鏘兄約稿,散文雜文寫多了,分別在雜誌及網頁刊出。今選出集而成冊,賦名《歲月如歌》。第一組「歲月」,收錄一些青少年時代及至遙遠童年的憶述。從中反映香港的演進和昔日的香港,那較貧窮和安逸的日子,令人懷緬。對今日港人,或更有感悟之處。其次是一些生活感受的散文,集中談論文士、文心和文化。未知今日在香港生活的讀者,是否能引起共鳴。
及談古今文人言行,其中其人文采事業,即未能驚天動地,...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歲月驕陽之無聲
矇朧歲月
身在福中
童年小露台
貧乏而富足的童年
香港戰後義學教育
無憂童年和小學會考
少年十五二十時
六十年代羅師寄宿生活
珍惜我們的中學年代
無償傳藝的書法大師
在明報輕快的日子
情醉紐西蘭
蠟燭
無言的眸子
清風偶遇
和我一起成長的家姊
輕風吹我心
王敬羲與南北極月刊
香港填詞人文學成就
中文要學書面語
梁羽生探索
文壇奇俠話倪匡
饒宗頤閒談高見
胡適白話文忽略文言
蔡元培...
矇朧歲月
身在福中
童年小露台
貧乏而富足的童年
香港戰後義學教育
無憂童年和小學會考
少年十五二十時
六十年代羅師寄宿生活
珍惜我們的中學年代
無償傳藝的書法大師
在明報輕快的日子
情醉紐西蘭
蠟燭
無言的眸子
清風偶遇
和我一起成長的家姊
輕風吹我心
王敬羲與南北極月刊
香港填詞人文學成就
中文要學書面語
梁羽生探索
文壇奇俠話倪匡
饒宗頤閒談高見
胡適白話文忽略文言
蔡元培...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