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棠
一、
打一開始,海棠就知道他是有家室的。
襯衫乾淨整齊,西裝頭,小肚腩,背部渾厚有肉,半框眼鏡後,一雙輕微浮腫的眼睛——怕是鸞鳳纏綿需索無度導致的腎虛吧。
反正,這是一個生活穩定有人伺候的男人。
未婚男子身上盤桓的青澀氣息和慌裡慌張,他沒有。
只有婚姻,有度有節的婚姻才能養出這樣的男人的體格和氣質。
未婚男子,不管如何穿山渡水千帆過盡,始終是男孩。
「在幹嘛呢?」他微信。
「查房。」
海棠拍了一張病房的照片發過去。
眼科醫院,少血腥惡病,相比於別的綜合醫院,簡單乾淨得多。
冬天一來,病房大多空著。
335房是唯一一個住滿人的。
一個六十歲的退休老太和她的女兒女婿。
三張小床之間,兩個床頭櫃,擺滿了東西。水果、手機充電器、吹風筒,以及幾支蒙牛優酸乳。
小夫妻三十出頭。
女婿很體貼,買早餐、午飯、水果,陪老太太做各項檢查。上午十點,做女兒的要麼還在賴床要麼在慢吞吞地化妝。
女人就這樣,仗著有人寵,有風使盡艃。有誰天生風風火火的呢?不過是無人可靠,凡事自己來,日久天長,不風火也不行了而已。
「媽,您要不要喝點優酪乳?」男人問老太。
老太朝海棠投來詢問的眼光。
「沒問題,可以喝的,阿姨。」海棠邊說邊給老太滴眼藥水,同時也看了那女婿一眼。眉清目秀清清爽爽的一個男子,身材保持得不錯,隔著襯衣仍舊依稀可見隆起的三角肌和胸大肌。 「謝謝宋醫生啊,辛苦了。」女婿對海棠點頭致意。
愛屋及烏吧。否則,哪個男人會如此殷勤地伺候起丈母娘來?
手機一震,微信來了——
「病房很熱鬧啊。」後面綴了個紅唇表情。
「是。三張床都住滿了。女兒女婿陪老太太做白內障手術。」海棠用的是陳述句,表面上不鹹不淡,事實上卻說得詳細。她不知道自己為何要如此詳細。
手機又震了,是個表情圖,一個簡筆劃小人兒,雙手舉著一個愛心,愛心裡幾個字:寶貝,我想你了。
這是他的慣用圖片。
事實上,他從未這麼說過,也從未喊過她的名字或是別的。
連昵稱也沒有。
叫老婆?不。他不會那麼蠢,蠢到給她不該有的希望和暗示。
叫寶貝?也不對。說不定那是他老婆的專寵。
直呼其名又顯得生分。
索性省了。
再親密,再你儂我儂耳鬢廝磨,在稱呼上也不過是「你」「我」而已。
換作從前,海棠會回復:我也想你。
但是那天,海棠沒有。
出門之後,她聽見女兒在洗手間裡喊女婿:
「寶寶,我不想出門,你看媽要吃什麼,打包回來好了。」
「腸粉吧。」老太太說。
女婿爽利地出門了。一個「寶寶」就把男人哄得屁顛屁顛鞍前馬後。
——換作我媽躺在這裡,他會來嗎?
永遠,不會——海棠心知肚明。
只有蠢貨才會對無望的事情滿懷希望。
刪掉對話方塊,把手機塞回白大褂的口袋裡。
口袋大,手機一墜到底。
空空蕩蕩。一如人生。
海棠二十八歲。是大家關心的剩女。
不少人明面上是關心,實際上是八卦。
生活本就無聊,不八卦一點別人的七葷八素簡直就活不下去了。背地裡嚼舌頭的人不少:該不會是有什麼毛病吧?要不怎麼會連個男朋友也沒有?
「八公八婆多得是,蟑螂老鼠滅絕了,這些人都還在的。管不了那麼多,隨他們說去!反正咱也沒什麼需要跟別人交代的!」閨蜜楊梅敷了一塊芝麻糊一樣的黑色面膜,慵懶地躺在沙發上,好言相勸。一個「咱」字用得,也算是用心良苦。可話背後到底也是輕薄的——一個女人,一把年紀還吊兒郎當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算什麼呢?
楊梅和海棠,當然不是「咱」。
楊梅所到之處向來熱鬧,男人們圍著她團團轉,像蜜蜂圍著花兒一樣。可她精明,知道女人青春易逝寶刀會老,在亂花漸欲迷人眼之際,狠下心來找定一個男人,過起了善男信女的生活。
海棠很少異性緣。二十出頭那一年,天橋上算命的大鬍子握住海棠的手,說:「感情線短,桃花弱,晚婚命格。還有一句不知當說不當說……」大鬍子神色凝重,略有遲疑。
「儘管說吧,師傅。」
不過糊口罷了,果真有道破天機的能耐,怕也不會在這天橋上風吹日曬騙飯吃吧。姑且聽之好了。
「雙鳥離飛之相,恐情路坎坷啊。」
嗨,坎坷就坎坷吧。來世為人,誰又能一帆風順呢。那時的海棠年輕氣盛,無所畏懼。
後來海棠再特意去了幾次天橋,卻再沒見到算命的大鬍子。茫茫人生,聚散皆無常,算得了別人命的人往往算不了自己。
「還是找個人吧,也別眼界太高啦,好歹冬天有人暖被窩,來大姨媽有人遞水送藥,下雨打雷有人抱一抱,碰上個蟑螂老鼠也有人出馬消滅,至於換燈修馬桶這類事情連物業服務都省了——全是男人一手搞定。」楊梅偶爾也會轉換話風,和別人一樣一口咬定海棠是因為心高氣傲才導致的孤身一人。
海棠不是孤身一人,卻和孤身一人沒什麼區別。認識數年,一年十二個月,見他的次數屈指可數,偶爾頭疼腦熱,卻依然形單影隻,自己料理自己。
誰此時孤獨,就永遠孤獨——誰的詩句?記不清了。反正獨來獨往慣了。
可有時候海棠覺得這樣也不賴。見慣了在婚姻裡煙薰火燎是非不斷的人,反覺得自己的日子過得清淨。
一朝嫁作他人婦,終日柴米油鹽醬醋茶裡泡著,如何能夠逃出生天?只好認真庸俗下去了。
今朝有酒今朝醉吧,何苦左奔右突執於前程?何況這前程於一個女人而言不過是一日三餐相夫教子罷了。
像父母一樣又如何?都是文學教授,算是才子佳人珠聯璧合,大半輩子下來,卻依然烽火連天爭戰不止。
「我是瞎了眼才看上你!」
「我他媽的才是倒了八輩子的大霉!」
兩個文學教授吵起架來一點都不文雅,和村夫野婦毫無二致。若硬要找出差別來,那就是媽媽自殺前好歹還會留下遺書。
「媽媽無法繼續了,請你們原諒我。媽媽犯的最大的錯誤是把你們帶到這個世界卻無法繼續陪伴你們。」
那一年,海棠十歲,哥哥海岸十四歲。
再後來的事,海棠忘了。海棠只記得一個人的身體裡原來有那麼多的血——媽媽割腕自殺。好在那天海棠發燒,請了病假提前回家,然後,媽媽被救了回來。
連死都肯,卻不肯活。
至於爸爸,鬍子拉渣,頭髮凌亂,眼窩深深塌陷,像一棵遭了颱風的老樹。
海棠不知道該同情誰。
媽媽撿回一條命之後,父母的交鋒變得少了,氣氛卻很壓抑。每個人都小心翼翼,避免踩雷。
後來的事,海棠忘了,只是她很早就知道——所謂日久天長,不過是忍罷了。把自己忍老,孩子忍大,把理想、激情、海闊天空忍成日復一日的死水微瀾。
忍是什麼?心頭上一把刀。
一把刀戳到心尖上,很多東西就滅了。
滅了之後,只剩生活。
也只有滅了之後,才能夠生活。
有些事情,無需別人教育,你自己就突然懂了。
但世上的事永遠如此:懂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勞燕分飛的人再多,也不妨礙每天都有人喜結連理。說到底,一生太長了,長得只能用很多的俗氣、煙火氣才能填滿。
「人活著,不都圖個圓圓滿滿麼?」——隔三岔五,小姨的電話就打過來,有時是在夜裡,有時是在白天——「你媽在你這個年紀,你都四歲了。」
一個女人,有男人,有兒女,就是圓滿——誰管它真假呢。假戲真做,做著做著,就慣了。
婚嫁一事,小姨比媽媽盯得緊。小姨知道,有些話,做父母的不好開口。即便開了口,也總是不得要領難抵主題。即便得了要領抵了主題,海棠也不見得真聽進去。
小姨是知道海棠的。
的確,好幾次,媽媽一張口,海棠差點脫口而出:你和我爸倒是順時應物了,那又如何?這輩子過得還不夠嗆?
話到嘴邊,還是咽了回去。都是女人,何苦如此殘忍?
燈光下,媽媽頭上新長出的一截白髮格外刺眼,染髮的速度已趕不上長白的速度了,黑白兩色,在她頭上竟分出了楚河漢界。
其實媽媽也沒說什麼過分的話,只是裝作不經意地說誰誰誰的兒子從國外回來,人不錯,家教也好,可以見一見。
見海棠不應,她好久才冒出一句:
「廣撒網,總能網到魚吧?」
海棠終於忍不住爆笑起來:「不愧是文學教授。」
「你別笑,話糙理不糙。」
媽媽邊說邊用手在圍裙上擦了擦,問:「幾點了?你爸說了回來吃飯的,到現在還不見人!」
「爸去哪了?」
「嗨,還不是那幫子詩友!寫來寫去都是些屁話!」
「媽,你年輕時不也寫過詩嗎?」
「誰年輕時不寫詩啊?」媽媽沒好氣地瞥了海棠一眼。
寫詩的媽媽想必也曾斑斕過吧——海棠想——可到底是枯了。
無數個夜裡,海棠值完班回家,見客廳的電視開著,媽媽坐在沙發上,瞌睡打得前傾後仰。
海棠上前輕輕地拍了拍她:「媽,進房睡吧。」
她迷迷糊糊的,睜開眼,盡是渾沌。不知今夕何夕。好久才緩過來說:「你也快去洗洗睡吧。」說完,轉身進房了。
萬籟俱寂。
爸爸在房裡鼾聲如雷。
海棠的心一陣苦澀。為媽媽,也為爸爸。兩個廝守了一輩子的人,真正擁有過對方麼?也許曾有過,可卻變得如此荒涼。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海棠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海棠
好評推薦:
「憑藉一支筆,讓心靈安靜,讓精神昂揚,讓生活豐富。讓自己面對未知的未來,有個永遠不會背棄的傾訴物件。佛花的這本《海棠》,既是她傾訴的結晶,也是一個成熟的作品,顯露了人生的幽深與回環。」——南翔
「我在這個集子中看到了一種可貴的文學品質,告解意識。離離合合、生生死死的人間故事,倘若缺少一種宗教精神的透視,講得再纏綿悱惻也只是『鴛鴦蝴蝶式』的小書,惟具備深切生命體驗,有哲思睿見,方能脫離兒女情長、才子佳人的窠臼。顯然,佛花做到了。《海棠》是不僅僅是一部小說集,她更是一個女人的成長史、心靈史。」——蔡益懷
「中文系出身的佛花,當然讀過乃至愛過張愛玲。乍一看,她的小說語言張揚淩厲。但她不像張愛玲那樣尖酸刻薄。相反,她的底色如此厚道溫情。她對筆下的人物投入了全部熱情,並毫不掩飾地熱烈讚美她們對真情真義的渴求。其實,追求尊嚴和恪守良知的哪裡是書中的她們?明明是賦予她們生命的佛花啊。」——湯奇雲
作者簡介:
佛花
文學碩士,深圳麥哲倫書吧創始人。貪戀世間一切美好事物,愛美貪吃嗜睡好玩,偶著文章。當過老師、記者、編輯。現為香港都會大學創意寫作專業全日制學生。小說、詩歌、評論發表於《北京文學》、《香港作家》、《山花》、《讀書》、《花城》、《詩林》、《特區文學》等刊物。出版有詩集《人間》。繪本《愛,從來就在那裡》亦將於今年八月面世。深信人生如夢,即便終究是空,也要認真歡喜一場。
章節試閱
海棠
一、
打一開始,海棠就知道他是有家室的。
襯衫乾淨整齊,西裝頭,小肚腩,背部渾厚有肉,半框眼鏡後,一雙輕微浮腫的眼睛——怕是鸞鳳纏綿需索無度導致的腎虛吧。
反正,這是一個生活穩定有人伺候的男人。
未婚男子身上盤桓的青澀氣息和慌裡慌張,他沒有。
只有婚姻,有度有節的婚姻才能養出這樣的男人的體格和氣質。
未婚男子,不管如何穿山渡水千帆過盡,始終是男孩。
「在幹嘛呢?」他微信。
「查房。」
海棠拍了一張病房的照片發過去。
眼科醫院,少血腥惡病,相比於別的綜合醫院,簡單乾淨得多。
冬天一來,病房大多空著。
33...
一、
打一開始,海棠就知道他是有家室的。
襯衫乾淨整齊,西裝頭,小肚腩,背部渾厚有肉,半框眼鏡後,一雙輕微浮腫的眼睛——怕是鸞鳳纏綿需索無度導致的腎虛吧。
反正,這是一個生活穩定有人伺候的男人。
未婚男子身上盤桓的青澀氣息和慌裡慌張,他沒有。
只有婚姻,有度有節的婚姻才能養出這樣的男人的體格和氣質。
未婚男子,不管如何穿山渡水千帆過盡,始終是男孩。
「在幹嘛呢?」他微信。
「查房。」
海棠拍了一張病房的照片發過去。
眼科醫院,少血腥惡病,相比於別的綜合醫院,簡單乾淨得多。
冬天一來,病房大多空著。
33...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我讀佛花與《海棠》
張愛玲曾將自己虛構的都市傳奇視作「流言」。「流言」當然就是關於都市男歡女愛的八卦故事。其實,無論是流言的製造者還是傳播者,他們都在虛妄地享受著流言敘述中所展示的見多識廣,以及由這種所謂的知識能力轉化而來的權力慾。因此,杜撰流言就成為張愛玲的寫作姿態,並體現了她的小說觀——從自己營造的「流言」中,呈現都市人家幽暗的人性風景。不過,情義的難求恰恰是她小說嘮叨的母題。
儘管讀著張愛玲小說長大的佛花,也在做著當代都市流言的記錄,但她的心態卻遠沒有張愛玲那麼超脫。可能是她沒有張氏的那貴族...
張愛玲曾將自己虛構的都市傳奇視作「流言」。「流言」當然就是關於都市男歡女愛的八卦故事。其實,無論是流言的製造者還是傳播者,他們都在虛妄地享受著流言敘述中所展示的見多識廣,以及由這種所謂的知識能力轉化而來的權力慾。因此,杜撰流言就成為張愛玲的寫作姿態,並體現了她的小說觀——從自己營造的「流言」中,呈現都市人家幽暗的人性風景。不過,情義的難求恰恰是她小說嘮叨的母題。
儘管讀著張愛玲小說長大的佛花,也在做著當代都市流言的記錄,但她的心態卻遠沒有張愛玲那麼超脫。可能是她沒有張氏的那貴族...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佛是一枝花/南翔
我讀佛花與《海棠》/湯奇雲
海棠
女船長
姐姐
鳳凰
後記 筆墨之下,千軍萬馬
創作談 眾生皆我
我讀佛花與《海棠》/湯奇雲
海棠
女船長
姐姐
鳳凰
後記 筆墨之下,千軍萬馬
創作談 眾生皆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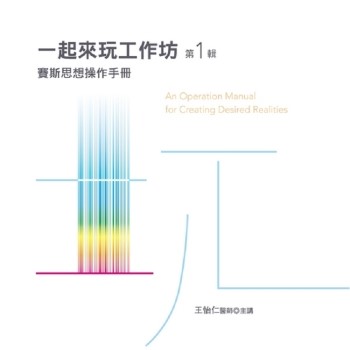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