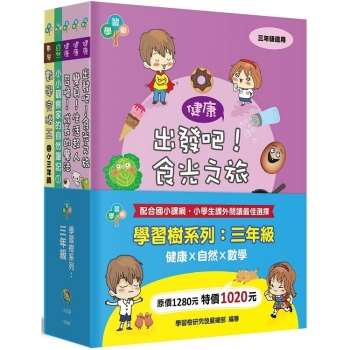北角光影與香港文學記憶
一 前記
我把潮黃了的《香港街道地方指南》從記憶的抽屜拿起來。
1989年通用圖書有限公司出版。封面照片居然有貝聿銘的銀竹指天,俯首笑對不遠的霍朗明(Noman Foster)的現代主義鋼筋和輪齒。這一年五月,啊,我記得。和半城的人我在街上走過。
把地圖攤開,我記得英皇道上叮叮而行電車。向西,它指向我和半城人的跫音。向東,它盛載過我十年記憶中春秧街市的生猛鮮活。我在北角住了十年,直到我被流放到清水灣為止──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我在鍵盤上敲出了「我記得」,但為何記憶只活在地圖?地圖上,一頁一葉,枯黃了的百福道、乾涸的天后廟道,我在此徘徊原來已有三千夜。還記得七姊妹道上的神話、陽光和寧靜,新光戲院與國貨公司門前車軌上的洶湧人聲。銀幕、琴行、書局,影影綽綽。記憶,為何活在地圖頁上移動的指頭?十年,剛好足夠十個指頭之所用。今年,我們都豎起雙手,左手往右數,右手往左數,數數指頭。不作前瞻,只敢回望。北角的光影,可以供香港文學回望嗎?
二 1934年:李育中〈維多利亞市北角〉
維多利亞市北角
蔚藍的水
比天的色更深更厚
倒像是一幅鋪闊的大毛毯
那毛毯上繡出鱗鱗紋跡
沒有船出港
那上面遂空着沒有花開
天呢卻編回幾朶
撕剩了棉絮
好像也舊了不十分白
對岸的山禿得怕人
這老翁彷彿一出世就沒有青髮似的
崢嶸的北角半山腰的翠青色
就比過路的電車不同
每個工人駕御的小車
小軌道滑走也吃力
雄偉的馬達吼得不停
要輾碎一切似地
把煤烟石屑潰散開去
十一月晴空下那麼好
游泳棚卻早已凋殘了
我在一間教會辦的英文書院完成中學教育。校長是正直慈懷的傳教士,我們一半的科目就由洋校長、校長夫人,和幾位充滿愛心遠來蠻荒的碧眼老師任教。學校覺得本地的教科書不夠好,特別為我們從澳洲訂購課本。我還記得,其中地理科的課本題名是《季候風亞洲》(Monsoon Asia)。記得其中一課講香港,地圖上標記了香港首都,是「維多利亞市」。嘿,同學說,哪來的首都?
讀李育中詩,維多利亞市就在眼前。李育中(1911-2013),生於香港,在港澳間受教育,三十年代曾任職香港工務局、中學教師等。1934年,香港忽然出現了幾份詩刊:《時代風景》、《詩頁》、《今日詩歌》,與李育中都有關係。李育中就以這首北角詩,為殖民地的維多利亞市留下記憶。
這維多利亞市的北方一角,水天一色的蔚藍。李育中詩的開篇兩行,給你一個山光水色的希望。但從第三行開始,山水自然就已異化為毛毯編繡工場,「波光鱗鱗」原來是毯上紋跡。天上雲朶卻是「撕剩了的棉絮/好像也舊了不十分白」。自然界在詩裏只帶來驚嚇──「秃得怕人」;「翠青」的山色,跳接上在路面行駛的綠漆電車。
三十年代的香港,在詩人眼中已是「山水告退,城市方滋」的變異時世。「現代性」以「輾碎一切」的力度,轟轟隆隆襲來。全詩的高潮,就在「馬達」吼叫不停,「把煤烟石屑潰散開去」的工業文明的「雄偉」中出現。今天揭開一頁頁香港歷史的神話傳說,還是漁帆點點,水白山青;城市好像是六、七十年代的業績。原來早在三十年代,詩人已感知,逝者如斯,凋殘的歲月無可挽回。
面對時代變遷,李育中的態度還是不難見到的。他雖然用上「雄偉」一詞來標誌「現代」,但他似乎沒被城市光影色誘而歡欣起舞。「那上面遂空着沒有花開」、雲「舊了不十分白」、每個工人「走也吃力」、「游泳棚」──是七姊妹泳棚吧?這是人與大自然相擁抱之所──「已凋殘了」;雖是輕輕道來,憑弔哀悼的餘韻還是迴盪不絕。
六十多年後,李育中接受梁秉鈞訪問。他回憶香港文壇說:「三○年代早期是本色較強,作家比較多土生生長,也與上海、廣州有聯繫,形成自己的力〔量〕。1937年後,外來的作家成為主力,帶動本土作者。」(梁秉鈞〈三、四○年代的香港文壇──李育中訪談錄〉)無論李育中是否有這分後見之明,他已在歲月中銘刻了他在維多利亞城的呼吸聲。「本土」之為「本土」,如此而已。
三 1957年:馬朗〈北角之夜〉
北角之夜
最後一列的電車落寞地駛過後
遠遠交叉路口的小紅燈熄了
但是一絮一絮濡濕了的凝固的霓虹
沾染了眼和眼之間朦朧的視覺
於是陷入一種紫水晶裏的沉醉
彷彿滿街飄盪着薄荷酒的溪流
而春野上一群小銀駒似地
散開了,零落急遽的舞孃們的纖足
登登聲踏破了那邊捲舌的夜歌
玄色在燈影裏慢慢成熟
每到這裏就像由咖啡座出來醺然徜徘
也一直像有她又斜垂下遮風的傘
素蓮似的手上傳來的餘溫
永遠是一切年輕時的夢重歸的角落
也永遠是追星逐月的春夜
所以疲倦卻又往復留連
已萬籟俱寂了
營營地是誰在說着連綿的話呀
我是從九龍南移到北角的新移民。我在九龍成長,小時候只會在農曆新年間拖着爸爸的手過海,到香港島往親戚家拜年。爸爸會告訴我,香港人比我們九龍人有禮貌,衣着比較光鮮,所以我要聽話、守規矩,不要失禮。當我成了新移民時,親戚們不知不覺都消失了。拜年的禮儀,隨父親老去了。於是,流落在異鄉的感覺很強烈。在國都和皇都戲院側,在馬寶道小販市場內,一路上都是聽不懂的呢喃。於是,我得用心睇、用力看。在電車上,紅燈好像特別喜歡我,常在我歸途等候;漸漸,我們有了交通,舒心地步入七姊妹的神話裏。或者,這不是馬朗看到的小紅燈,他看到遠遠交叉路口的小紅燈熄了。
馬朗(1933-),本名馬博良,原籍廣東中山,出身華僑家庭。四十年代在上海發表作品,與吳組光、張愛玲、紀弦、邵洵美等文壇中人都有往來。五十年代初移居香港,在1956年3月1日發表一篇宣言──〈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到我們的旗下來!〉;這是香港文學神話《文藝新潮》的發刊詞。
馬朗是推動香港現代主義運動的神話英雄。五十年前的一個夜晚,他在北角。和大批1949年後南來的文人一樣,他駐足於「小上海」這個僑置州郡。城市的聲色光影,在時間中漂浮,濡染了北角之夜。最後一列電車駛過後,「小紅燈熄了」,但霓虹光影卻在雨中,或者淚眼中,導引入迷離的超現實世界:與「紫水晶的沉醉」應和的是「滿街飄盪着薄荷酒的溪流」,再幻化成春野上四散奔馳的「小銀駒」,更又轉變成「舞孃們的纖足(下的銀色皮鞋)」。這個迷離世界中,還響起「登登聲」──是銀駒馳騁的蹄聲?還是舞孃們的銀鞋的步履聲?打斷了「那邊捲舌的夜歌」──操北方語言的。聲音的交響,光影的搖晃,交織貫通不同的時空。「春野」大概象徵了馬朗美好的舊記憶。然則歌聲舞影,究竟是眼前的景象,還是回憶中的聲響?在第三節出現的「素蓮似的手上傳來的餘溫」,更似是他記憶世界中的往事;沿此思路,當下的「北角」,隱然昔日「上海」的重像。馬朗從上海開展了他的文藝生命,這時流落於「小上海」的「北角」。今昔之間,疊映印合。第三節的「她」,會不會是他忘不了的她?是「年輕時的夢」?「連綿的話」是他腦海中響起的思念嗎?作者在第四節點出這是「年輕時的夢重歸的角落」:「北角」就是他「懷戀北地的角落」。在這裏,一切柔情記憶都湧現。誰在說話?不就是他自己向回憶說話嗎?這首詩給人一種哀怨的感覺,現實與記憶糾結成動人的詩境。
馬朗把田園景致鑲嵌在城市光影之間,使時空的交接更顯迷離惝恍。作為神話英雄的馬朗,正要在香港繼續他的夢想。就在年前,他揭竿吶喊:「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是鬥士的,請站起來,到我們的旗下來!」這一晚,他說:「永遠是一切年輕時的夢重歸的角落/也永遠是追星逐月的春夜」。北角於他,不是「信非吾土」的遺憾,而是「有夢相隨」。這個「現代主義」的夢,也就在此地延展連綿,薪火相傳。
四 1974年:也斯〈北角汽車渡海碼頭〉
北角汽車渡海碼頭
寒意深入我們的骨骼
整天在多塵的路上
推開奔馳的窗
只見城市的萬木無聲
一個下午做許多徒勞的差使
在柏油的街道找尋泥土
他的眼睛黑如煤屑
沉默在靜靜吐煙
對岸輪胎廠的火災
冒出漫天裊裊
眾人的煩躁化為黑雲
情感節省電力
我們歌唱的白日將一一熄去
親近海的肌膚
油污上有彩虹
高樓投影在上面
巍峩晃盪不定
沿碎玻璃的痕跡
走一段冷陽的路來到這裏
路牌指向銹色的空油罐
只有煙和焦膠的氣味
看不見熊熊的火
逼窄的天橋的庇蔭下
來自各方的車子在這裏待渡
我在九龍半島的西南一角長大。上大學以後,開始了每天的渡輪之旅。海霧中的汽笛聲,在記憶裏,只會醉人魂魄。迷津泊岸之際的搖晃,使人興奮莫名。追趕晚上最後的航班,在解纜水手叱喝聲踏上跳板,再靜看海面晃晃不息的霓虹。怎麼這就是我最深刻的碼頭記憶?也斯筆下的碼頭在東,我心底的津渡在西;直至我被北角收容,我自西徂東。
也斯(1948-2013),梁秉鈞,「是香港本土詩發展中的一位關鍵人物」。相信沒有人不同意黃燦然這個評斷。也斯詩之感人,不在激越的情緒,而是生活中的涵泳玩索。他從小學三年級遷來北角,在電車聲中成長。馬朗的「北角」,一定給他許多的啟迪,教他去關懷本土的風物。
他這首詩共有四節:第一節的「我們」是詩中的主要觀感者。為全詩定調的感覺是第一行的「寒意」二字,下接幾行後的「徒勞」,延續到第二節的是「煩躁」。但也斯沒有繼續鼓動這個心潮,而將之化為視象的「黑煙」。第三節所有情緒字眼都已退隱,由視象主導畫面。譬如說,以「晃盪不定」的「高樓投影」,替換了不安的感覺。在第四節也斯再從同一選擇軸上安排他的意象:「冷陽」、「銹色」、「煙和焦膠的氣味」,而不讓讀者親臨「熊熊的火」的現場。最後一行,也斯以「來自各方」的車子之「待渡」結束,既延展了「共濟」的情懷,也蘊蓄着「希望」的力量。
以寫景的技術而言,也斯掌握得非常純熟;即使從未踏足「北角碼頭」的讀者,也可以隨着也斯的車行見到香港東海岸碼頭一帶的景象:塵土飛揚的城市、沿岸的輪胎廠、裊裊黑煙、海上的油污、棄置的空油罐……。這是寫田園詩的力度寫非田園的城市。這當然來自細意和耐心,以及敏銳的觀察能力。
也斯的詩藝的表現,更在於「感覺」與「物象」如何結合。在詩人冷靜觀物姿態的表象下,其實不乏內心的騷動。好比「在柏油的街道找尋泥土」,是多麼令人失望的「徒勞的差使」!聲音本是生命力的表現,可是「我們」推窗所見,只感覺「城市的萬木無聲」;城市中的「萬木」,不是田園的「木」,不但毫無生氣,更暗瘂無聲。「眼睛黑如煤屑」的「他」,只會「沉默」,不外是「城市的萬木」之一;所吐的「煙」,就是「眾人的煩燥」。白日「熄滅」,不再帶來歌唱。浪漫的「海」加上浪漫的「彩虹」,原來是工業世界的油污。城市的象徵──雄偉巍峩的「高樓」,在海光倒影中顯現晃盪虛怯的真相。
也斯於現實的揭露和批判,其實緣自對城市的深情。詩中最後留下期盼──「待渡」,就是盼望那過渡到彼岸的一天。這首詩寫於1974年,香港還沒有所謂「九七大限」。彼岸,大概指人文精神所能彰顯之處。在天橋庇蔭下的「待渡」者,包括「來自各方」的城內人──不止北角居民。詩人期盼「我們」、「眾人」,以至城市中所有的「他」,都可以渡過苦海,達到彼岸。
五 後語
我與斜陽下的七姊妹同行,從健康東街、西街,走到電照街,看着姊妹們寧謐地石化;我穿越英皇道、馬寶道,一面聽琴、一面讀書,信步來到海風中叫賣聲響的北角碼頭,買一份晚報,與渡輪卸下來的每張臉孔同時呼吸每一口的海魚腥風……。從這一呼一吸開始,「北角」就是「我城」的喻體、喻依,也是喻旨。直到李育中為我響起雄偉的馬達、馬朗與我目送最後一列電車、也斯讓我坐在他的車子待渡;歲月燃燒海潮,把我指頭游走的地圖熏黃了。可幸,我還在呼吸不息。
回憶在在文學世界中,就是前瞻。
其實,响清水灣,時時清楚睇倒北角。
(2007年7月)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香港.文學:影與響的圖書 |
 |
香港.文學:影與響 作者:陳國球 出版社:練習文化實驗室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8-2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08 |
二手中文書 |
$ 277 |
現代小說 |
$ 277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308 |
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香港.文學:影與響
陳國球教授新作《香港‧文學:影與響》與前作《抒情中國論》、《香港的抒情史》一脈相承,全書無論是個人隨筆、學術文章抑或訪談對話,都旨在以情打通文學與人、文學與社會、文學與世界的關係。本書文章出入古今中西,借鏡他者異域,讓讀者能夠從中觀照當下的香港,文學的影與響,其實似遠實近。
作者簡介:
陳國球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文學講座教授、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總監。
曾任香港科技大學中國文學教授,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主任,加拿大雅博特大學東亞系、捷克查理大學東亞研究所、臺灣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臺灣政治大學中文系,以及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客座教授;東京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人。
著編有:《香港的抒情史》、《抒情之現代性》、《香港文學大系》(十二卷)、《抒情中國論》、《文學如何成為知識?──文學批評、文學研究與文學教育》、《情迷家國》、《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香港地區中國文學批評研究》。
TOP
章節試閱
北角光影與香港文學記憶
一 前記
我把潮黃了的《香港街道地方指南》從記憶的抽屜拿起來。
1989年通用圖書有限公司出版。封面照片居然有貝聿銘的銀竹指天,俯首笑對不遠的霍朗明(Noman Foster)的現代主義鋼筋和輪齒。這一年五月,啊,我記得。和半城的人我在街上走過。
把地圖攤開,我記得英皇道上叮叮而行電車。向西,它指向我和半城人的跫音。向東,它盛載過我十年記憶中春秧街市的生猛鮮活。我在北角住了十年,直到我被流放到清水灣為止──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我在鍵盤上敲出了「我記得」,但為何記憶只活在地圖...
一 前記
我把潮黃了的《香港街道地方指南》從記憶的抽屜拿起來。
1989年通用圖書有限公司出版。封面照片居然有貝聿銘的銀竹指天,俯首笑對不遠的霍朗明(Noman Foster)的現代主義鋼筋和輪齒。這一年五月,啊,我記得。和半城的人我在街上走過。
把地圖攤開,我記得英皇道上叮叮而行電車。向西,它指向我和半城人的跫音。向東,它盛載過我十年記憶中春秧街市的生猛鮮活。我在北角住了十年,直到我被流放到清水灣為止──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我在鍵盤上敲出了「我記得」,但為何記憶只活在地圖...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後記
眼前打印出來的文字校樣,猶如歲月皺褶的遺痕。在我的平凡生活中,文學無非是春誦夏弦的課業。然而,潮起潮落;文學其實是我生命中賴以撐持的眾木。以文學為專業,危機意識常來相伴;生活在文學中,卻是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文學香港於我的影與響,在數十年間,漸漸移向前景。想到要把這些蕪文雜記編集成書,是黎漢傑先生的主意。漢傑是我在香港科技大學講研究生課時的旁聽生,後來我知道他放棄大學修讀的專業,投身文學,不敢為他高興,卻深受感動。好幾年了,他一直熱心推動我整理那塗鴉式的非學術文稿,交...
眼前打印出來的文字校樣,猶如歲月皺褶的遺痕。在我的平凡生活中,文學無非是春誦夏弦的課業。然而,潮起潮落;文學其實是我生命中賴以撐持的眾木。以文學為專業,危機意識常來相伴;生活在文學中,卻是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文學香港於我的影與響,在數十年間,漸漸移向前景。想到要把這些蕪文雜記編集成書,是黎漢傑先生的主意。漢傑是我在香港科技大學講研究生課時的旁聽生,後來我知道他放棄大學修讀的專業,投身文學,不敢為他高興,卻深受感動。好幾年了,他一直熱心推動我整理那塗鴉式的非學術文稿,交...
»看全部
TOP
目錄
第一輯 歲華荏苒
1. 樹影間的大角嘴
2. 憶昔買書在香港——中學編
3. 北角光影與香港文學記憶
4. 感傷的教育
5. 我與文學史與胡適
6. 山移海動見平原:我眼中的平原君
7. 懷也斯,想香港文學
8. 一個文學教授的獨白
9. 家明與香港
10. 秋鶩眠於風
11. 懷人
第二輯 映雪囊螢
12. 我看陳滅的「我城景物略」——序陳智德《地文誌》
13. 歲月煙花——序鄭蕾《香港現代主義文學與思潮》
14. 文學史與文學教育——序潘步釗《給中學生閱讀的中國文學史》
15. 詩與真——讀《一般的黑夜一樣黎明》
16. 在倫敦遇上一九八...
1. 樹影間的大角嘴
2. 憶昔買書在香港——中學編
3. 北角光影與香港文學記憶
4. 感傷的教育
5. 我與文學史與胡適
6. 山移海動見平原:我眼中的平原君
7. 懷也斯,想香港文學
8. 一個文學教授的獨白
9. 家明與香港
10. 秋鶩眠於風
11. 懷人
第二輯 映雪囊螢
12. 我看陳滅的「我城景物略」——序陳智德《地文誌》
13. 歲月煙花——序鄭蕾《香港現代主義文學與思潮》
14. 文學史與文學教育——序潘步釗《給中學生閱讀的中國文學史》
15. 詩與真——讀《一般的黑夜一樣黎明》
16. 在倫敦遇上一九八...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陳國球
- 出版社: 練習文化實驗室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8-25 ISBN/ISSN:978988774768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40頁 開數:25
- 商品尺寸:長:210mm \ 寬:148mm \ 高:13mm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