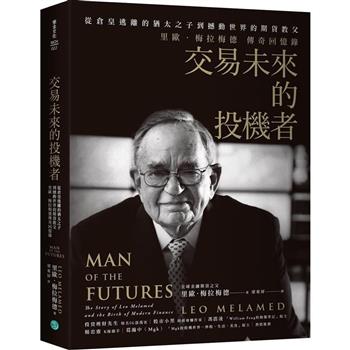1
黃仁逵 散步
約黃仁逵:找個話題,一起聊天。答:談天說地算不算話題。也可以啊。答:畫人思考,不以文字先行,亦不以文字終結。問:那我要準備什麼。答:有指引的談天說地,還算是談天說地嗎。於是在週日黃昏,隨意坐在面朝酒吧的公園樹下、花圃旁邊,挨得籬笆彎彎的,腳踏坑渠蓋,酒瓶、酒杯與煙灰缸放在鐵箱子上,鐵箱有一側接駁消防喉,以證明它不是桌。無所謂吧。他徐徐吐出一個個散開的白煙圈,煙盡了,便喝杯酒,喝一口說說畫,喝一口又說些電影,說音樂時酒吧傳來民謠的樂聲,他說寫作時我在想:六十歲到底是什麼概念,他六十歲了,一點老態都沒有。他說:「創作能醫百病。」又說:「你是否在做你最想做的那種人,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問他為何不許我預備。他答:預備了,訪問便變成你想印證自己的想法,這本身不好,是趕路和散步的分別。趕路要有目的地,而散步卻是沿途有很多東西看,走了很久很久也沒有到達原來想到的地方,但不重要,因為你看到的比原先預定的多很多。沿途不知會拾獲什麼,拾起再算。又不知有沒有用,可能這輩子都沒有用,不要緊。他說:散步是創作方法,未必最有效或最節省時間,但最好玩。
你說你四歲開始喜歡畫畫,我問。他吐一圈白煙,笑笑,所有人都在四歲開始喜歡畫畫,在還未接觸文字以前。只是後來美術老師教你一些繪畫技術,卻反過來磨滅了你的創作熱情,而文字則是從小學開始學習,技能人人都有,只是日後你決意要荒廢這技能的話,怪不得人。問他創作是否天份。不是,是思考形式,如果你的思考形式令你常常感到挫敗,動物性的本能會令你不再創作。又問創作是什麼。是每個人生來都有的,但後來有些人遺失了,有些人不知自己遺失了,又有些人覺得遺失了也無所謂,那就無,抵你無。我沒有遺失,四歲開始喜歡畫畫,現在仍很喜歡。
一隻貓從花圃竄出來,在酒吧門外徘徊,老闆立時拿出貓糧,放在地上,貓待老闆轉身回店,便低頭吃糧。他說:這貓等開飯,定時定候來,是街貓但有酒吧養。我說:貓毛是看得出的滑。貓多整潔,他說。很多很多鳥聲,從遮蔭的樹頂傳來,不一會又聽見二胡聲,從公園傳來,不時聽見酒吧傳來ukulele的樂聲,一群人圍着樂手拍掌唱民謠。
逗貓玩,貓不理我。這對街貓來說是好事,他說,喝半杯酒,又說回散步:總有些東西在吸引你的注意力,如果貓不出現,你不會留意貓,但你對貓沒有感覺也不會看見貓,你會看見別的。你的眼睛不是閉路電視,不會看來看去都是同一個畫面,即使在同一段路。又說起他的電影編劇工作。編劇有很多方向,他說,有時是商品考慮,為保持戲劇張力所以不斷放些事件進去,令電影不悶,這樣不好,因為有些作品的原意不是要娛樂你,而是要表述一些想法,所以令作品不悶是多餘的。貓還在吃,忽然兩隻狗走來,貓與狗對望,立時竄走,狗大搖大擺來到貓原本的位置,低頭吃貓糧。貓走了,我說。當然走,不是第一次做嘛,貓明白的,他說。這兩隻狗會咬貓嗎,我問。吃貓糧已經很不好啦,他答。
電影可以悶,書不可以。他天性不耐煩,寫不成長篇,也沒看過任何經典長篇小說,如《紅樓夢》,總是讀不下去,同時覺得沒看過經典不是罪惡。他在巴黎住了七年,也沒到過鐵塔。又來到加拿大難得一遇的博覽展門前,哥哥進去看,他堅持在門外等,哥哥非常生氣,覺得他不長進,他卻覺得沒什麼非看不可,而觀看過多卻會無法消化,浪費時間。他覺得讀很多書就會變成很好的文人是錯覺,到書店也不一定買書,反正買回家裏也是放幾年才看。甚至,他連畫展也少看。
問:那你曾不斷觀看嗎。答:是的,因為蠢,很短時間想學很多東西,多年後才發現這樣很蠢,因我只看見畫者消化經歷後的作品,可是令他想畫畫的那件事,以及畫者本身,其實遠遠比他的畫重要。同一件事發生在很多人面前,只有這人將這事變成畫,是因為這件事對他來說還不完整,是要這件事加上這個人再加上這幅畫才算完整。如果只看見畫卻不見動機,也看不見原來那件事,那你看來看去都是創作的單一面向。
矮樹後還藏着一盆貓糧,貓在吃,忽然又望見了狗,迅即逃離,狗施施然繞到樹後吃貓糧。這盆也給狗發現了,我說。狗真是狗,偵緝隊來的,他笑笑。他說自己一直在用很多蠢方法創作,但創作是好好玩的,這是初衷,如果創作不好玩,打死都不做。蠢也無所謂,真是好玩嘛。我問:會有一直創作但覺得創作不好玩的人嗎。大把。他答:有些人不服氣,不甘心,或騎虎難下,覺得自己讀藝術,無論如何都要做點東西出來,但不知道做什麼好。其實世上本無藝術家,只有嚮往與不嚮往做藝術家的人,而我是畫者。我說:有些人自稱作家。不用領牌的,他笑道,你自稱醫生或者黑社會就會被拘捕,自稱作家、藝術家,沒事的,不是刑事案,只是肉麻,你有幾藝術家?
他說創作對每個人來說都重要,是自我救贖,唯有通過創作才能完成自己,令自己心安理得地活着。我懷疑安全網對每個人來說才最重要,特別是在香港。他說如果安全網是供樓,都頗危險,有樓了,但你在屋內做什麼呢?吃杯麪。不如努力省錢來創作,至少你吃杯麪也知道自己為什麼在吃杯麪,總比供樓好。無敵海景吃杯麪,多戇居。危機感是可以恐嚇自己一世的,但你想過什麼日子,想做什麼人,你知道。
寫作也好玩。他說:但太多人把寫作放上神檯,令這件事嚇怕了自己,這無助於創作。如果寫作與你很親近,你就會覺得很好玩,寫成什麼樣子都無所謂了。像小孩一樣,玩遊戲是有輸有贏的,但小孩從來不介意輸贏,有得玩才最重要。是你的思維決定創作離你有多遠。他說:文章可以不獲獎,不刊出,沒有掌聲與讚賞。問:你想人讚嗎。他吐個煙圈,笑笑:如果讚你的是你很鄙視的人呢,你就真是要反省自己做錯什麼事而令這人覺得你好正了。給衰人愛上是很痛苦的,比詛咒更慘。問:你試過嗎。答:不知道。但你是什麼人就會吸引什麼人圍着你,如果圍着你的人給你很大壓力,又不懂欣賞好的價值觀,你換掉這群人吧,全部換掉。哈哈。創作的快樂在於自由自在,而自在比自由更重要。
夜色籠罩着整條街,樂聲愈來愈濃,有一句沒一句的談着,像散步,沒有目的,沒有終點。
二〇一五年四月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織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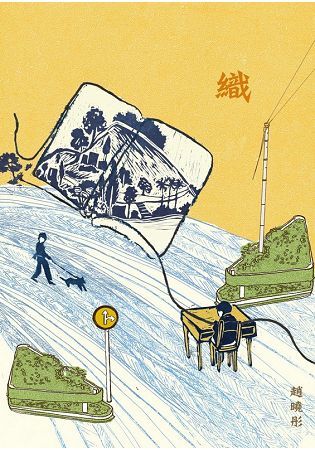 |
織 出版社:練習文化實驗室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6-23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08頁 / 13 x 19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織
黃仁逵、潘偉源、周耀輝、董啟章、李維怡、陳曉蕾、胡燕青……
一個個熟悉的名字,背後都有你與我不知道的故事。
本書收錄約三十位文藝工作者的訪談,其中包括詩人、小說家、學者、填詞人,等等。從貌似隨意的對話,我們可以發現他們背後的歷史、情感以及對文藝的理念,更讓我們走進他們的生命,在字裏行間,一起共喜同悲。
作者簡介:
趙曉彤
喜歡貓,討厭狗,喜歡散步,喜歡莊子,好奇未知,膚淺,三分鐘熱度,唯一長久的愛好是寫作。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曾任文學散步員、九龍城訪問員、編輯、記者、補習老師、廢青等職,曾獲青年文學獎新詩公開組冠軍、中文文學創作獎散文公開組優異,從小到大的夢想是吃飽睡足。
TOP
章節試閱
1
黃仁逵 散步
約黃仁逵:找個話題,一起聊天。答:談天說地算不算話題。也可以啊。答:畫人思考,不以文字先行,亦不以文字終結。問:那我要準備什麼。答:有指引的談天說地,還算是談天說地嗎。於是在週日黃昏,隨意坐在面朝酒吧的公園樹下、花圃旁邊,挨得籬笆彎彎的,腳踏坑渠蓋,酒瓶、酒杯與煙灰缸放在鐵箱子上,鐵箱有一側接駁消防喉,以證明它不是桌。無所謂吧。他徐徐吐出一個個散開的白煙圈,煙盡了,便喝杯酒,喝一口說說畫,喝一口又說些電影,說音樂時酒吧傳來民謠的樂聲,他說寫作時我在想:六十歲到底是什麼概念,他六十...
黃仁逵 散步
約黃仁逵:找個話題,一起聊天。答:談天說地算不算話題。也可以啊。答:畫人思考,不以文字先行,亦不以文字終結。問:那我要準備什麼。答:有指引的談天說地,還算是談天說地嗎。於是在週日黃昏,隨意坐在面朝酒吧的公園樹下、花圃旁邊,挨得籬笆彎彎的,腳踏坑渠蓋,酒瓶、酒杯與煙灰缸放在鐵箱子上,鐵箱有一側接駁消防喉,以證明它不是桌。無所謂吧。他徐徐吐出一個個散開的白煙圈,煙盡了,便喝杯酒,喝一口說說畫,喝一口又說些電影,說音樂時酒吧傳來民謠的樂聲,他說寫作時我在想:六十歲到底是什麼概念,他六十...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所有訪問都在《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刊登,謝謝主編關夢南,以及他的文學夢。
每次重讀舊稿,我都記得那場訪問(幾乎都是人生初見),以及我與我城所經歷。記得一次,情緒低落,在趕赴訪問的路上邊走邊哭,踏進商場,趕緊收起眼淚,收起那個軟弱與破碎的自己,快步來到約定的咖啡店。那時的我,與所有時刻的我,都記在稿件裏了,讀者看不見的,而每次讀稿,我總看見。
黃仁逵 散步
潘偉源 珍重
周耀輝 念念
潘國靈 頑石
廖偉棠 旺角
飲 江 燈下
韓麗珠 貓洞
董啟章 對照
李維怡 相處
陳曉蕾 好死
謝曉虹 幻吃
王...
每次重讀舊稿,我都記得那場訪問(幾乎都是人生初見),以及我與我城所經歷。記得一次,情緒低落,在趕赴訪問的路上邊走邊哭,踏進商場,趕緊收起眼淚,收起那個軟弱與破碎的自己,快步來到約定的咖啡店。那時的我,與所有時刻的我,都記在稿件裏了,讀者看不見的,而每次讀稿,我總看見。
黃仁逵 散步
潘偉源 珍重
周耀輝 念念
潘國靈 頑石
廖偉棠 旺角
飲 江 燈下
韓麗珠 貓洞
董啟章 對照
李維怡 相處
陳曉蕾 好死
謝曉虹 幻吃
王...
»看全部
TOP
目錄
黃仁逵 散步
潘偉源 珍重
周耀輝 念念
潘國靈 頑石
廖偉棠 旺角
飲 江 燈下
韓麗珠 貓洞
董啟章 對照
李維怡 相處
陳曉蕾 好死
謝曉虹 幻吃
王良和 魚咒
陳 慧 空間
盧勁馳 看見
呂永佳 公園
蔡珠兒 種地
可 洛 網癮
麥樹堅 束縛
羅貴祥 族群
黃燦然 翻譯
周漢輝 公屋
胡燕青 聖經
鄒文律 平衡
陳子謙 聽見
劉偉成 解鎖
吳美筠 種植
葉曉文 尋花
樊善標 阿愁
潘偉源 珍重
周耀輝 念念
潘國靈 頑石
廖偉棠 旺角
飲 江 燈下
韓麗珠 貓洞
董啟章 對照
李維怡 相處
陳曉蕾 好死
謝曉虹 幻吃
王良和 魚咒
陳 慧 空間
盧勁馳 看見
呂永佳 公園
蔡珠兒 種地
可 洛 網癮
麥樹堅 束縛
羅貴祥 族群
黃燦然 翻譯
周漢輝 公屋
胡燕青 聖經
鄒文律 平衡
陳子謙 聽見
劉偉成 解鎖
吳美筠 種植
葉曉文 尋花
樊善標 阿愁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趙曉彤
- 出版社: 練習文化實驗室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6-23 ISBN/ISSN:978988774776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08頁 開數:32
- 商品尺寸:長:190mm \ 寬:130mm \ 高:12mm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