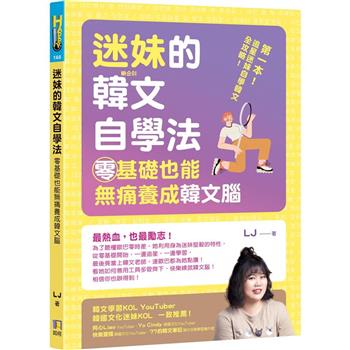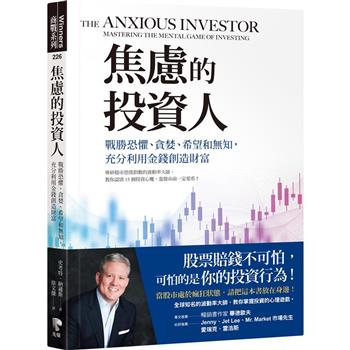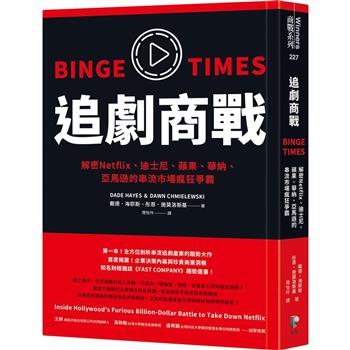舊日decent──讀伍淑賢《夜以繼日》後
樊善標
現在,即使在家裡喝奶茶或咖啡,我也緊張兮兮地記着不要把調匙泡在杯子裡,這完全是讀了伍淑賢專欄的後果。調匙放錯地方的無禮,她認為超過了接受的底線,但又自嘲地稱之為「勢利」(〈我的勢利〉)。另一篇沒有收入這本文集的〈失戀中途站〉同樣令我念念不忘。五十年代紅歌星Patti Page去世那陣子,伍淑賢在一家餐廳聽到不斷播放的I Went to Your Wedding、Tennessee Waltz等名曲,中間還夾着Engelbert Humperdinck的The Last Waltz、Tom Jones的Delilah、The Platters的Smoke Gets in Your Eyes,憑次序她就知道是飛利浦出品的Golden Oldies on CD,因為家裡也有一套,早聽熟了,而且感動過一位經歷人生轉折的朋友。
伍淑賢的喜惡帶着一種舊日的decent。因為不趨時而顯得時下難以企及,恰像小學老師為她所撰的嵌名聯:淑德取以處人,賢慧用以治學。(〈小學先生〉)這種感覺大概和先讀了她的小說分不開。九十年代初登在《素葉文學》的三篇〈父親〉,許迪鏘評為「揮灑自如,用一種疏離的筆法寫一家人緊密的親情」,近年的短篇,張楚勇特別欣賞「筆觸的沉著和細膩」,我都無異議,但更佩服的是中篇〈山上來的人〉。
〈山〉暗地裡以七十年代末的金禧中學事件為背景,不是要記錄一個社會運動的始末,或闡述其意義,而是借此寫幾個少女交疊分岔的成長軌跡。社會運動是他們偶然遇上的大事,對他們的命運、性格自有影響,但不是唯一的影響。各種因素交互纏結,無法一言以蔽之,我認定這就是人生實相的體悟了。小說有許多細節,但寫來疏朗爽快,如主角秀貞家境本已寒窘,支持她讀書的父親突然不告而去,「沒有人比媽媽更雀躍了。沒了爸絆手絆腳,媽讓我馬上去鞋廠打工。決定的那天是升上中三第二個星期。眼見新買的書簿,就要白白浪費掉」,緊接着的一段已是「媽媽很怕見到修女,叫我自己去跟校長說要退學」。作者幾乎筆不著紙,鮮見經營環環緊扣的因果鍊,也不輕易表白對角色的感受。既揮灑,又沉著,這是怎樣的一種境界。
從九十年代初讀〈父親〉到現在,和伍淑賢見面不過三次。最初是十多年前某個典禮,當時問她拿了一張名片,轉眼就丟失了。前年《山上來的人》小說集出版,獲得了香港文學館「香港文學季」2015年度的推薦獎,在頒獎禮上真正認識了伍淑賢,不久又邀她到香港中文大學談創作歷程。《山》收錄了伍淑賢三十多年來所作小說的大部份,加上張楚勇等的序、許迪鏘的編後記、伍淑賢演講時的自白,大概知道了她的一些背景。對喜歡的作者,當然想了解更多,於是又根據編後記的提示,在網上資料庫蒐集伍淑賢近幾年的報紙專欄雜文來看,這些專欄現在選錄成為這本《夜以繼日》。
香港專欄雜文的本質就是發表大大小小的意見。一群作者多則每天,少則每星期一、兩天,在報紙副刊固定的位置,以固定的篇幅,吐露他對生活見聞、本地社會、世界各地,甚至宇宙古今的意見。中外報紙副刊似乎很少以這樣的面貌出現,可是香港大概從六十年代以來,就以此為常態。九十年代中後期,連載小說在報紙上消失,專欄雜文依舊存在。魯迅在生時,有人稱他為「雜文專家」,香港專欄作者也不妨命名為「意見專家」。以雜為專當然是譏諷,「專家意見」和「意見專家」的顛倒,用意也如出一轍。旦旦而伐,「專家」的高見總有一天窮盡,然而讀者逐日追看,卻未必為了尖新見解、前沿知識。互聯網普及之前,雜文副刊提供了最平等的作者、讀者交往平台,儘管無法在版面上直接發言,讀者的反應仍能影響作者的去留。於是交朋友取代了載道、言志,成為專欄的慣常語調,「讀者」也逐漸變作「讀友」。孔子說交友之道貴乎友直、友諒、友多聞,但要勞煩聖人垂教,必然因為一般人少有這種上進心吧。這裡且不談直和諒,多聞如果欠缺趣味,恐怕不能讓讀者滿意,因此雖然隨着教育普及,出現了以專業標榜的專欄作家,如醫藥、法律、廣告,但大眾趣味仍是先決條件。
八、九十年代專欄雜文之盛,甚至觸動了學術界。一方面學院中人兼寫專欄蔚成風氣,另一方面好些學者力倡以專欄雜文作為香港文學的代表。後者與香港身份的自覺及危機密切相關,當時的想法在今天自可批評有各種不足,但嘗試提出另一種欣賞文學的標準,終究有積極意義。專欄的淺薄、粗糙、功利,與率真、敏捷、入世只是一線之隔,到最後也許仍得回到誰寫(作者才性)、誰讀(讀者口味)的老生常談。
《夜以繼日》的文章都是最近七、八年所寫,但讀來總有八十年代good old days的味道。那是香港經濟繁榮的好日子,不少土生或土長的五十後,從草根階層開始攀上中產,伍淑賢也屬於這一世代吧。現在「第二代香港人」的成功故事已經不是人皆受落了,讀到作者在「佔中」初起時,力言冷靜的重要(〈政局如夢如幻〉),或者認同作家阿城讚美香港的話:「香港的飯館裡大紅大綠大金大銀,語聲喧嘩,……香港人好鮮衣美食,不避中西,亦不貪言中華文化,……在內地已經消失的世俗精緻文化,香港都有,而且是活的」(〈世俗〉),都不禁捏一把汗。
然而伍淑賢並非僅僅理直氣壯地說她的道理。她介意泡在茶裡的調匙,卻不忘自嘲這種反應「勢利」,並想到自己「也一定有很多舉措讓某些人看不順眼」。她肯定規矩有助建設「文明」,令「社會秩序會暢順點,生活品質會精緻點,自己和別人也比較可愛」(〈我的勢利〉)。這種改良主義的想法,在八十年代知識分子中應該屬於主流。但沒有全盤否定建制不代表毫無質疑,例如她「慨歎我們一度以為香港已進入真正的meritocracy,即是不講出身,光講實力,就可以公平地闖天下。這一套我們曾經以為的金科玉律,隨着經濟走下坡,已徹底打破……年青人的起步點,是拉得越來越遠呢?還是社會分層根本一直如此,只是我太天真不察覺而已?」(〈人事關係〉)
說到更貼身的事情,例如超級市場變得高檔以吸引中產,作者自承十分高興,但也明白有些長者嫌貨品昂貴。不止這樣,大眾化的超市是公公婆婆消閒的去處,升格為只有英文名字的中產超市,有些人「或連店名也說不出,連話語權也失去」。不過作者設身處地,如果她是管理層,在商言商,也只會提高檔次。那麼,她問,「企業或資本主義究竟是為誰服務」?Edward Freeman的持份者理論(stakeholder theory)提出「資本主義要進展,必須真正滿足更廣闊持份者利益」,即不僅是股東和員工,還包括周邊其他人。但難以回答的是,這家超市「對那些公公婆婆有多大責任」。(〈超市變身〉)這些反思沒有試圖觸及資本主義體制的本質,但不要忘記,伍淑賢任職商界,她的反思最低限度是坦誠的。──據張楚勇說,伍淑賢在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期間,與港大畢業同學組織了一個論政團體,執筆撰寫了不少論政聲明,可惜我未有機會拜讀。──全書關於職場和關於其他的內容,其實無法截然分開,職業讓她得到某種觀看事物的位置,公餘興趣何嘗不是這樣?只是看那麼多或新或舊的書、電影、電視劇……算是公餘還是本業呢?
但我得再次補充,這和先讀了伍淑賢的小說密切相關。瀏覽這些專欄雜文,最初的樂趣是發現小說的原材料,例如〈放下〉寫一位年輕同事的父母,除了每人一個行李箱的日常用品,甚麼都丟掉,包括女兒的成績表、獎盃等,而且是趁女兒不在家時拋棄,以免子孩捨不得。這一家原來早寫進了短篇小說〈利安〉,女兒換作男身,成為主角。小說〈父親〉裡小小年紀的主角每天接父親下班、颱風來襲的日子,幫忙聯絡鄰居打麻將等,原來一一是作者親身經歷。(〈甜的中環〉、〈鮎魚與溫黛〉)更高興是找到與小說平行的另一些感受,我指的是像〈女校男sir〉記述參加中學母校四十周年的舊生活動,與老師重逢,兼憶起學生時代的趣事,笑談之間解開了許多少年時的謎,也得悉不止學生離校之後各有去向,老師也未必長守舊業。小說〈山上來的人〉從學生位置敘述成長過程中外界環境毫不留情的挑戰,〈女校男sir〉的收筆則說:「想起這些早期的老師,都把花樣年華分給學生,但我們的黃金歲月,卻鮮有他們份兒,到再見他們的時候,已太遲了。」
伍淑賢的小說冷靜克制,不動聲息,專欄卻放鬆得多,不怕直接道出感受和見解,但有時也施展一下小說筆法。〈麥記疑雲〉玩弄亦真亦幻的敘述,寫她與朋友在揚州看見一家麥當奴快餐店,標誌的顏色似乎不對,位置和裝潢也有問題,判斷是「A貨」。當過記者的朋友走到櫃枱前,直接問女伙計,「這店是真的嗎」,女伙計目無表情,反問「你認為真的店是怎樣的」。朋友一下子沒法回應,但也未釋疑。離開揚州那天,作者在那快餐店吃早點,食物質素找不出瑕疵,於是深感不論真假都無所謂了。臨走買了杯熱咖啡帶給朋友,「朋友一喝便說,這咖啡是真的!」但這代表作者的最後意見嗎?從伍淑賢小說處理細節的手法看,更像是存此一說,其實疑雲難消,餘音盪漾。
另一篇〈執著〉的敘述更有趣。作者首先表示:「常提醒自己別執著,別嘮叨,話說一遍就夠了,人家不聽就算,反正控制不到。不過言語不執著,並不表示已放下,我們的行為還可以十分執著。」按作文的「常法」,接着的事例不外乎支持或延伸此一主旨。文章引用的是一部紀錄片,拍攝日本三一一海嘯後,岩首縣村民原地重建家園。重建期間,破房子裡滿是泥漬,家具雜物亂作一團,親人遺體未知下落,但每一家都堅持在神壇上供一瓶鮮花,悼念新魂,作者讚歎這是「可敬的執著」。接着的一段,開始時說:「我們很多時驚人地執著而不自知。」事例則是前面提過的揚州旅程,那位朋友拿著熱咖啡,邊喝邊退房間、乘車上路、談電話,個多小時後,到達目的地,呷完最後一口,才把紙杯丟進垃圾桶。這一大段轉為簡述就不免走樣,只能畫蛇添足地補充:關鍵是作者想幫忙拿杯子,朋友執意不肯,要親手放進垃圾該去的地方。作者同樣讚歎:「她那份執著,我很感動。」
但這是怎樣一回事?兩個主題句和接著的事例都背道而馳,讀到事例後的總結,才突然發現主題句並不表達主題。作者一向認為不該執著,但世上就是有值得執着的事情;執著而不自知似乎是壞事,但有些不自知的執著令人感動。同樣的急轉來了兩次,就不是失手,而是結構了。
奇特的結構在全書中並不多見,伍淑賢不大追求敘述試驗,這毋寧該理解為她的創作觀甚至文藝觀──加意保存具體細節。上海的朋友邀請她回家吃飯,房子建於三十年代,是荷蘭建築師的手筆。伍淑賢特別記下這個細節:朋友帶她「到廚房看一塊內置熨衣板,不用時收在壁櫥,熨衣服時放下來」,這令她想起,張愛玲《小團圓》裡九莉的三姑楚娣嗜好是看房子,「有一次看了個極精緻的小公寓,只有一間房……櫥門背後裝着熨衣板,可以放下來,羨慕得不得了」。伍淑賢也讚美朋友家的熨衣板「帥極了」。總有張愛玲專家能夠把這細節說成《小團圓》的關鍵暗喻吧,我倒寧可相信張愛玲在〈燼餘錄〉所說的:「人生的所謂『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並願意伍淑賢也是這麼看。
《夜以繼日》最吸引我的正是作者對小說、漫畫、電影、電視劇等藝文作品的閒散評論。這些評論遍佈書中,不限於「藝文混醬」一輯。伍淑賢在大學主修比較文學。現在的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差不多,主要修練各式文化理論,伍淑賢的時代則讀俄國小說、德國小說、日本能劇、元明戲曲,加上一些專題比較,如中國戲曲對布萊希特的影響,上課都是討論作品(〈古早比較文學〉)。伍淑賢自謙作品讀得粗疏,但如此龐大的範圍,確也不可能用考訂的方式細究,或許就因此而培養出對細節片斷的敏感吧,例如她說,「上一代的日本導演,都擅長處理二人對談的文戲。《二人世界》裡最好看的,就是王海生和麗子邊喝茶喝酒、做家務,和在小食店邊幹活邊談的戲。婚姻和事業這些人生大事的決志,就在這些細碎的交談和種種思前想後之中醞釀完成。香港電影很少有好看而合乎庶民常態的對談戲,不是太誇張,就是太文藝,所以我們的交談戲都不耐看」(〈王海生〉)。
《二人世界》是木下惠介拍的電視劇,七十年代在無線電視播出,男女主角的名字譯作王海生和麗子。那年代我還不大懂得看愛情劇集,僅有的模糊印象是《佳偶天成》,恰巧也是木下惠介拍的。不管怎樣,伍淑賢注目的細節引起了我強烈的興趣:海生回鄉問務農的父親借錢做生意,也是在鄉下當農夫的大哥罵他自私。翌日父親私下答應借錢,海生趕火車回東京,在山路上遇見大哥。大哥態度溫和多了,承認是因為自卑,妒忌弟弟能夠長居東京。「兄弟二人邊走邊談,不覺走上一道橋,突然刮起風,背後一片參天大樹吹得東歪西倒,兩兄弟也吹得有點瑟縮。雖然那陣風極可能是人造的,不過我寧願信是真風,因為那場戲實在好看」(〈等雲等風〉)。
張楚勇在一篇論文裡引用了奧克肖特(Oakeshott)的一段話:「詩人不是在做以下三件事:首先去經歷一些情感,跟着就這些情感進行思索,最後尋找合適的方式把這些感受去達出來。詩人做的只是一件事:美的或詩意的想像。」張楚勇接着說:「伍淑賢看了論文手稿後,深表贊同。」我完全不知道奧克肖特,但偶然讀到美國史學大師雅克‧巴森(Jacques Barzun)一篇八十年代的舊文章〈高雅而枯燥的文化〉(Arthur Krystal編,陳榮彬譯《文化的衰頹》,臺北:橡實文化,2016),所說似乎和奧氏一線相通。巴森認為高雅文化在當前已失去涵養心智的作用,因為現代社會把評價藝術和人文作品的權力都委託了給專家。專家努力分析、解拆文化,建立各自的專業,但巴森指出,人腦還有另一種截然相反的運作方式──「直觀理解力」(intuitive understanding)。「直觀理解力」通過仔細觀察,嘗試掌握整體的特性,期間無法下明確的定義、歸納成簡約的原則、把事物代換成數值,因此「誰都無法輕易將理解結果傳達給別人,只能透過文字類比來引發聯想,也就是藉由意象來傳達。因此,對於理解的對象與其意義,是不可能達成普遍共識的」。巴森最後一句也許說得太盡,但這不就是伍淑賢寫小說的方法?那些具體的細節本身有豐富的意義,不僅是一些思想和理念。
原來伍淑賢的散文也有同樣的傾向,但未必是寫作方法,而是更底層的觀察、體會人和事的習慣:先不帶着建設宏大森嚴體系的目的蒐集材料,只是隨心看去,唯求自身受用,即使有意見要表達,也不刻意剪盡橫生的枝節。這種散文,既是粗放,也是任真,容易給人抓着破綻,批評不夠精緻深刻,但作者的性情涵養也流露無礙,像伍淑賢的decent和從容就讓我神往不已。
我是借伍淑賢來暗中為舊日的香港辯解嗎?其實,舊人舊事儘有一點都不decent的。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夜以繼日的圖書 |
 |
夜以繼日 作者:伍淑賢 出版社: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10-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52 |
中文書 |
$ 352 |
現代散文 |
$ 360 |
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夜以繼日
都說報紙只有一天生命,無論多喧鬧的新聞,到了第二天便成明日黃花,與廢紙無異。然則報紙副刊上的專欄文字,是不是也朝花夕萎,二十四小時之後便再無意義和價值?這端視乎作者的態度和深度。是書所收,都精選自伍淑賢在報章上的專欄,她自言「採多元題材兼切入現世」,這「多元題材」乃基於作者廣濶的閱歷,而「切入現世」,則出自她敏銳的觀察和思考。因而日常生活的紀錄、職場的見聞,以至往昔的片段回憶,莫不反映人情世態的現狀和變遷,由是開啟讀者自身經驗的回顧和反省。細言之,書分五章:「朝八晚八」寫職業生涯種種;「夜有所思」寫日常生活及自省;「遣興書懷」寫藝文閱讀;「山河故人」寫中華大地遊歷見聞;「明日黃花」寫往昔人事與人情。全書細節豐富,情意綿密,趣味盎然。
作者簡介:
伍淑賢,香港人,原籍廣東順德。從事公關及傳訊工作。早年小說散見《素葉文學》和《文化新潮》等,近年則發表於《字花》和台灣的《短篇小說》,隨筆多見諸報章。小說集《山上來的人》,2015年獲香港文學季推薦獎。
章節試閱
舊日decent──讀伍淑賢《夜以繼日》後
樊善標
現在,即使在家裡喝奶茶或咖啡,我也緊張兮兮地記着不要把調匙泡在杯子裡,這完全是讀了伍淑賢專欄的後果。調匙放錯地方的無禮,她認為超過了接受的底線,但又自嘲地稱之為「勢利」(〈我的勢利〉)。另一篇沒有收入這本文集的〈失戀中途站〉同樣令我念念不忘。五十年代紅歌星Patti Page去世那陣子,伍淑賢在一家餐廳聽到不斷播放的I Went to Your Wedding、Tennessee Waltz等名曲,中間還夾着Engelbert Humperdinck的The Last Waltz、Tom Jones的Delilah、The Platters的Smoke Gets in Your ...
樊善標
現在,即使在家裡喝奶茶或咖啡,我也緊張兮兮地記着不要把調匙泡在杯子裡,這完全是讀了伍淑賢專欄的後果。調匙放錯地方的無禮,她認為超過了接受的底線,但又自嘲地稱之為「勢利」(〈我的勢利〉)。另一篇沒有收入這本文集的〈失戀中途站〉同樣令我念念不忘。五十年代紅歌星Patti Page去世那陣子,伍淑賢在一家餐廳聽到不斷播放的I Went to Your Wedding、Tennessee Waltz等名曲,中間還夾着Engelbert Humperdinck的The Last Waltz、Tom Jones的Delilah、The Platters的Smoke Gets in Your ...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徘徊在夜與日之間/序 許迪鏘
舊日decent/讀後 樊善標
後記 伍淑賢
1 朝八晚八
另類暑期工/看領袖/十四億/人事關係/男少女多/氣節/解放美人魚/
騎呢見工/食物政治/湯碗裡的風波/鬥快去南極/老闆愛政治/盛事這行當/
樽頸/悼公關女將/那杯茶/老美/即日來回/我的勢利/斷人善根/
我知道的麥理覺/麥理覺二三事/灰飛煙滅/參觀巨鳥/我的桌面/
送、貪、買/名門之後/培訓百態/小熊小猴小丑/前輩
2 夜有所思
八國聯軍/書要怎樣教/咖啡店興亡/小孩不笨/去哪兒?/南洋三日/
大坑/醫館現代化/阿茂整...
舊日decent/讀後 樊善標
後記 伍淑賢
1 朝八晚八
另類暑期工/看領袖/十四億/人事關係/男少女多/氣節/解放美人魚/
騎呢見工/食物政治/湯碗裡的風波/鬥快去南極/老闆愛政治/盛事這行當/
樽頸/悼公關女將/那杯茶/老美/即日來回/我的勢利/斷人善根/
我知道的麥理覺/麥理覺二三事/灰飛煙滅/參觀巨鳥/我的桌面/
送、貪、買/名門之後/培訓百態/小熊小猴小丑/前輩
2 夜有所思
八國聯軍/書要怎樣教/咖啡店興亡/小孩不笨/去哪兒?/南洋三日/
大坑/醫館現代化/阿茂整...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