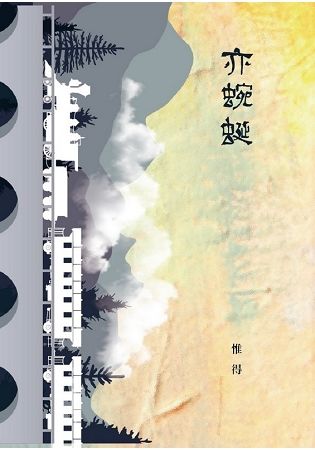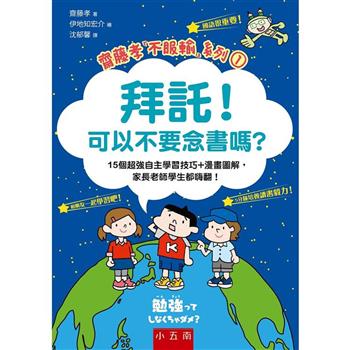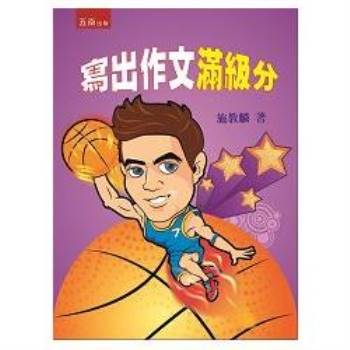惟得小說的主題,一直集中在家庭當中的關係糾葛。閲讀他的文字,你不會看到火紅激烈的思緒,但那淡淡的人情世故,總是在一般小說所謂矛盾衝突的臨界前終止。這種寫法,更像傳統中國短篇小說的散點透視,通過一段迂迴的情節,展現各人的心理幽微,誠如蔡益懷的推薦序所言:「頗有張愛玲手筆的神韻,實在是當代香港小說中難得的別致之作。」
小說摘要:
〈停電〉:
他們就這樣,你望我,我望你,望向窗口望向牆,又不約而同的望向電視機,熒光幕一片空白,他們也不把視線移開,好像要看出一個奇跡。
〈航機即將降落新加坡〉:
「詠新為甚麼要嫁人?我們三人在一起,不是很美滿嗎?」
〈清夜月〉:
日子真像賊,趁着人不在意,又把一些貴重的東西拿走。
〈長壽麪之味〉:
生命千瘡百孔,充滿鄙視、失望與冷落,只換得零碎的歡樂,惟有故事王國安全舒適。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亦蜿蜒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 218 |
小說 |
$ 261 |
現代小說 |
$ 261 |
中文現代文學 |
$ 290 |
中文書 |
$ 297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亦蜿蜒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惟得
散文及小說作者,也從事翻譯,現居加拿大。
一九七〇年代開始創作小說,多刊於《大拇指週報》,並任該刊書話版編輯。
一九八〇年代初為《香港時報》及《號外》撰寫專欄,一九八四年赴美求學,畢業於加州柏克萊大學,一九九〇年代重新寫作,文稿散見《明報》、《信報》、《蘋果日報》和香港電影資料館叢書,近年著作多發表於《香港文學》、《城市文藝》、《大頭菜文藝月刊》及《別字網志》,小說〈十八相送〉收錄於《香港短篇小說選二〇〇六—二〇〇七》(二〇一三年),小說〈長壽麪之味〉收錄於《香港短篇小說選二〇一三—二〇一四》(二〇一八年),著有短篇小說集《請坐》(二〇一四年,素葉出版社);散文集《字的華爾滋》(二〇一六年,練習文化實驗室有限公司出版社);電影散文集《戲謔麥加芬》(二〇一七年,文化工房)。
惟得
散文及小說作者,也從事翻譯,現居加拿大。
一九七〇年代開始創作小說,多刊於《大拇指週報》,並任該刊書話版編輯。
一九八〇年代初為《香港時報》及《號外》撰寫專欄,一九八四年赴美求學,畢業於加州柏克萊大學,一九九〇年代重新寫作,文稿散見《明報》、《信報》、《蘋果日報》和香港電影資料館叢書,近年著作多發表於《香港文學》、《城市文藝》、《大頭菜文藝月刊》及《別字網志》,小說〈十八相送〉收錄於《香港短篇小說選二〇〇六—二〇〇七》(二〇一三年),小說〈長壽麪之味〉收錄於《香港短篇小說選二〇一三—二〇一四》(二〇一八年),著有短篇小說集《請坐》(二〇一四年,素葉出版社);散文集《字的華爾滋》(二〇一六年,練習文化實驗室有限公司出版社);電影散文集《戲謔麥加芬》(二〇一七年,文化工房)。
目錄
遍閱人情 備嘗世味——惟得《亦婉蜒》 蔡益懷
1) 停電
2) 奇童志
3) 航機即將降落新加坡
4) 長壽麵之味
5) 人間網絡
6) 亦蜿蜒
7) 與森林合拍家庭照
8) 她從常德公寓出來
9) 清夜月
10) 四月原是一本很年輕的書
11) 未完
後記:還未五詳短篇小說
1) 停電
2) 奇童志
3) 航機即將降落新加坡
4) 長壽麵之味
5) 人間網絡
6) 亦蜿蜒
7) 與森林合拍家庭照
8) 她從常德公寓出來
9) 清夜月
10) 四月原是一本很年輕的書
11) 未完
後記:還未五詳短篇小說
序
序
遍閱人情 備嘗世味——惟得《亦蜿蜒》
蔡益懷
喝茶已經是香港人的標誌,就像情之所鍾刺在臂上的紋身,再也擦不掉。說是藝術,倒不及日本人的斟酌,發展了精雕細琢的茶道。粗枝大葉的一盅兩件,更似狼吞虎嚥,在點心紙上畫符般亂點鴛鴦,不過要補足滿漢全席的想望,羅通掃北之後,揚手喚侍應結賬,往往等待座位的時間,比實際上坐下來用點心的時間還要長,香港人並不介意,儀式就是生活情趣。
這是惟得君小說作品中的一段話。對香港市井文化風情有所認識的人,讀到這樣的文字,相信都不難意會,且不免莞爾一笑。在《亦蜿蜒》這本集子中,閃現閱世之功與睿智之光的妙語,隨處可見,可以說信手拈來都是這類閃閃發光的文字珠寶。由此也可管窺惟得小說的藝術風貌。
深明世故,諳熟人情,富於趣味,是中國小說的一大傳統。惟得君的作品,深得中國傳統小說的要領,對人情世故有精微的體察和表現,頗有張愛玲手筆的神韻,實在是當代香港小說中難得的別致之作。
這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閱世至深。作者擅長透過尋常生活,尤其是家庭倫理,透視人生百態,感悟生命的升沉與窮逹,以及人世間的種種況味。如〈人間網絡〉,透過強哥的職場生涯與夫妻生活,道出人生的困頓,尤其是人在中年的困厄。在異國他鄉求生,在職場上浮沉,在家庭生活中嗑碰的人,都不難產生感同身受的閱讀體驗。再如,〈航機即將降落新加坡〉寫到女兒遠嫁新加坡,父親反應異常,暗自哀號,以沙啞的喉音追問,女兒「為甚麼要嫁人?我們三人在一起,不是很美滿嗎?」,不捨之情,躍然紙上,真乃神來之筆。讀到此處,筆者亦為之愀然。本人一向認為,真正意義上的創作是心泉的外溢,是深厚的生活閱歷、人生經驗的自然流露,好的作家創作靠的是「氣」而不是「力」。可惜,時下一般人寫小說,大都像肥皂劇編劇,絞盡腦汁「度橋」,胡編亂造,整色整水。像這樣靠笨力、蠻力「度」出來的故事,縱使曲折離奇、荒誕不經,也終究是等而下之的次品。惟得的小說不一樣,憑閱世的內功揮筆,不編故事,以意領文、以氣運筆,描繪紛繁的世象,曲盡人心的幽微。他的筆下沒有甚麼波瀾壯闊的社會歷史場面,也沒有大悲大苦的悲情人生,相反都是尋常人家的尋常生活與心象,卻妙在能夠以小見大,以微見著。如〈與森林合拍家庭照〉、〈清夜月〉等,情節都十分簡單,透過一段路程串連一個故事或一番心緒。前者寫一家人追尋父輩的原木小屋,兜兜轉轉,始終沒能找到,最終發現「原木小屋更似海市蜃樓」。與其說他們尋找的是現實之物,不如說是一種心象,木屋只是一個象徵物而已。後者述說一對夫妻觀影回家途中因月亮而勾起的情思,「我們的月亮」是一個中心意象,見證着這對夫妻的情路歷程,但也考驗着他們的情緣——「日子真像賊,趁着人不在意,又把一些貴重的東西拿走。」夫妻二人的關係像已冷卻的麪,「需要重新加熱」。惟得的小說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展開,即以某種情意結為磁石,凝聚前世今生的種種事象與因緣。胸中有丘壑,筆底氣象萬千,作品自有不凡的品質。
其二,敍說精巧。惟得的小說深得現代小說的神髓,筆法路數多樣,不拘情節小說的俗套,顯然對各路小說技法都有師承。在他的筆下,可看到「祖師奶奶」的影子,也不難發現歐美現代小說,乃至拉美魔幻派筆法的基因,但他不是簡單的模仿、因襲,而是消化吸收,融滙貫通,將各種筆法內化為自己的技藝,最終自成一格。一般的情節小說像西方的油畫講究透視關係一樣,要求視角的統一,即講述故事時會將鏡頭放在某一個位置,如架在某個人物的頭頂,隨着其視點的移動而展開畫面,情節也循着一定的因果展開。惟得君的小說則不太一樣,以心理為發端,採用的是散點透視,像傳統的水墨一樣,隨胸中的情意而俯仰,不同角度的景象都可以共冶於一個畫面。他有上帝的全知視角,卻又沒有居高臨下的姿態與口脗,更無意指點江山,相反始終置身人世間,以人間的情懷洞察世情,叩問人心。他的視角游移不定,不受時空拘束,自然可以隨意點染。如〈亦蜿蜒〉,現實與心理相互涵蘊,打破時空關係,筆頭驅遣自如,給人一種印象派畫作的感覺,光與色彩的變化都帶着主觀意緒的因子。這個作品謂之印象派小說,大概也未為不可。當然,創作的本相不在於名目,得道的作家在乎的是創作本身的施展,通常不理會甚麼派別與名目。值得一提的是,惟得小說善於留白,隱而不露。如〈與森林合拍家庭照〉、〈清夜月〉,都有不俗的表現,話說七分,留下三分想像空間。再如〈長壽麪之味〉,藉一個壽宴講述何老太的人生,以及一個家庭的聚散,故事的結尾盡顯張力,也是韻味綿長。
小說是智慧與文字技藝的結晶,有千百種「說」法,沒有一成不變的公式或法寶,一千個作者就會有一千種言說的可能性和面貌,而大凡能夠「說」出自己的話,發出一己聲音的,必有可觀之處。惟得正是這類能用自己的方式創作的小說手藝人,他的作品深明世故、善體人情,飽蘊人生智識,無論從內容還是敍說風格來說,都別有風貌與品性,相信讀者自能領略到別樣的意趣。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於南山書房
遍閱人情 備嘗世味——惟得《亦蜿蜒》
蔡益懷
喝茶已經是香港人的標誌,就像情之所鍾刺在臂上的紋身,再也擦不掉。說是藝術,倒不及日本人的斟酌,發展了精雕細琢的茶道。粗枝大葉的一盅兩件,更似狼吞虎嚥,在點心紙上畫符般亂點鴛鴦,不過要補足滿漢全席的想望,羅通掃北之後,揚手喚侍應結賬,往往等待座位的時間,比實際上坐下來用點心的時間還要長,香港人並不介意,儀式就是生活情趣。
這是惟得君小說作品中的一段話。對香港市井文化風情有所認識的人,讀到這樣的文字,相信都不難意會,且不免莞爾一笑。在《亦蜿蜒》這本集子中,閃現閱世之功與睿智之光的妙語,隨處可見,可以說信手拈來都是這類閃閃發光的文字珠寶。由此也可管窺惟得小說的藝術風貌。
深明世故,諳熟人情,富於趣味,是中國小說的一大傳統。惟得君的作品,深得中國傳統小說的要領,對人情世故有精微的體察和表現,頗有張愛玲手筆的神韻,實在是當代香港小說中難得的別致之作。
這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閱世至深。作者擅長透過尋常生活,尤其是家庭倫理,透視人生百態,感悟生命的升沉與窮逹,以及人世間的種種況味。如〈人間網絡〉,透過強哥的職場生涯與夫妻生活,道出人生的困頓,尤其是人在中年的困厄。在異國他鄉求生,在職場上浮沉,在家庭生活中嗑碰的人,都不難產生感同身受的閱讀體驗。再如,〈航機即將降落新加坡〉寫到女兒遠嫁新加坡,父親反應異常,暗自哀號,以沙啞的喉音追問,女兒「為甚麼要嫁人?我們三人在一起,不是很美滿嗎?」,不捨之情,躍然紙上,真乃神來之筆。讀到此處,筆者亦為之愀然。本人一向認為,真正意義上的創作是心泉的外溢,是深厚的生活閱歷、人生經驗的自然流露,好的作家創作靠的是「氣」而不是「力」。可惜,時下一般人寫小說,大都像肥皂劇編劇,絞盡腦汁「度橋」,胡編亂造,整色整水。像這樣靠笨力、蠻力「度」出來的故事,縱使曲折離奇、荒誕不經,也終究是等而下之的次品。惟得的小說不一樣,憑閱世的內功揮筆,不編故事,以意領文、以氣運筆,描繪紛繁的世象,曲盡人心的幽微。他的筆下沒有甚麼波瀾壯闊的社會歷史場面,也沒有大悲大苦的悲情人生,相反都是尋常人家的尋常生活與心象,卻妙在能夠以小見大,以微見著。如〈與森林合拍家庭照〉、〈清夜月〉等,情節都十分簡單,透過一段路程串連一個故事或一番心緒。前者寫一家人追尋父輩的原木小屋,兜兜轉轉,始終沒能找到,最終發現「原木小屋更似海市蜃樓」。與其說他們尋找的是現實之物,不如說是一種心象,木屋只是一個象徵物而已。後者述說一對夫妻觀影回家途中因月亮而勾起的情思,「我們的月亮」是一個中心意象,見證着這對夫妻的情路歷程,但也考驗着他們的情緣——「日子真像賊,趁着人不在意,又把一些貴重的東西拿走。」夫妻二人的關係像已冷卻的麪,「需要重新加熱」。惟得的小說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展開,即以某種情意結為磁石,凝聚前世今生的種種事象與因緣。胸中有丘壑,筆底氣象萬千,作品自有不凡的品質。
其二,敍說精巧。惟得的小說深得現代小說的神髓,筆法路數多樣,不拘情節小說的俗套,顯然對各路小說技法都有師承。在他的筆下,可看到「祖師奶奶」的影子,也不難發現歐美現代小說,乃至拉美魔幻派筆法的基因,但他不是簡單的模仿、因襲,而是消化吸收,融滙貫通,將各種筆法內化為自己的技藝,最終自成一格。一般的情節小說像西方的油畫講究透視關係一樣,要求視角的統一,即講述故事時會將鏡頭放在某一個位置,如架在某個人物的頭頂,隨着其視點的移動而展開畫面,情節也循着一定的因果展開。惟得君的小說則不太一樣,以心理為發端,採用的是散點透視,像傳統的水墨一樣,隨胸中的情意而俯仰,不同角度的景象都可以共冶於一個畫面。他有上帝的全知視角,卻又沒有居高臨下的姿態與口脗,更無意指點江山,相反始終置身人世間,以人間的情懷洞察世情,叩問人心。他的視角游移不定,不受時空拘束,自然可以隨意點染。如〈亦蜿蜒〉,現實與心理相互涵蘊,打破時空關係,筆頭驅遣自如,給人一種印象派畫作的感覺,光與色彩的變化都帶着主觀意緒的因子。這個作品謂之印象派小說,大概也未為不可。當然,創作的本相不在於名目,得道的作家在乎的是創作本身的施展,通常不理會甚麼派別與名目。值得一提的是,惟得小說善於留白,隱而不露。如〈與森林合拍家庭照〉、〈清夜月〉,都有不俗的表現,話說七分,留下三分想像空間。再如〈長壽麪之味〉,藉一個壽宴講述何老太的人生,以及一個家庭的聚散,故事的結尾盡顯張力,也是韻味綿長。
小說是智慧與文字技藝的結晶,有千百種「說」法,沒有一成不變的公式或法寶,一千個作者就會有一千種言說的可能性和面貌,而大凡能夠「說」出自己的話,發出一己聲音的,必有可觀之處。惟得正是這類能用自己的方式創作的小說手藝人,他的作品深明世故、善體人情,飽蘊人生智識,無論從內容還是敍說風格來說,都別有風貌與品性,相信讀者自能領略到別樣的意趣。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於南山書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