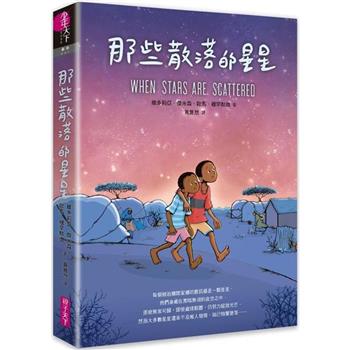「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
——張愛玲與香港的不解緣
蔡益懷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裏,誰知道甚麼是因,甚麼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
這是《傾城之戀》中的一段話,相信很多人都十分熟悉。這個小說敍述的是白流蘇的故事,不過,在我看來,這段話也道出了張愛玲本人的命運。一個女子在兵荒馬亂的時代,似乎注定把握不住自己的命運,而只能像浮萍一樣隨波飄流。
一九三九年,十九歲的張愛玲來到香港,入讀港大文學院,也從此跟香港結下不解之緣。她原本是要到倫敦大學升學,卻因為歐戰無法成行,改讀港大。她在香港學習與生活的時間並不長,只有三個年頭。一九四一年,香港淪陷,又一次改變了張愛玲的人生走向。一九四二年夏天,她中斷學業,回到上海,開始走上寫作之路。
張愛玲離開香港,心並沒有因此而遠離這個小島,相反從上海回望香港。她在散文〈到底是上海人〉中這樣寫到︰
我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包括《沉香屑》、《一爐香》、《二爐香》、《茉莉香片》、《心經》、《琉璃瓦》、《封鎖》、《傾城之戀》七篇。寫它的時候,無時無刻不想到上海人,因為我是試着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的。
她是一個冷峻的觀察者,用上海人的視角審視、觀察着香港,也記錄了她的所見所聞,她見證了一座城巿的傾覆。
在她的筆下,有說不盡的蒼涼故事,像上面提到的小說都不同程度地述及香港的風情,而最直觀又集中的描述則莫過於散文〈燼餘錄〉。這是張愛玲離開香港多年後,對戰時歲月種種「趣事」的回憶。下面,就讓我們來選讀一些片段吧。
一個炸彈掉在我們宿舍的隔壁,舍監不得不督促大家避下山去。在急難中蘇雷珈並沒忘記把她最顯煥的衣服整理起來,雖經許多有見識的人苦口婆心地勸阻,她還是在炮火下將那隻累贅的大皮箱設法搬運下山。蘇雷珈加入防禦工作,在紅十字會分所充當臨時看護,穿着赤銅地綠壽字的織錦緞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雖覺可惜,也還是值得的,那一身伶俐的裝束給了她空前的自信心,不然,她不會同那些男護士混得那麼好。同他們一起吃苦,擔風險,開玩笑,她漸漸慣了,話也多了,人也幹練了。戰爭對於她是很難得的教育。
………
同學裏只有炎櫻膽大,冒死上城去看電影——看的是五彩卡通——回宿舍後又獨自在樓上洗澡,流彈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還在盆裏從容地潑水唱歌,舍監聽見歌聲,大大地發怒了。她的不在乎仿佛是對眾人的恐怖的一種諷嘲。
上面這一段文字真實記錄了戰事初期港大學生的「生趣」事。張愛玲並不是一個愛看熱鬧的人,相反,她是一個洞明世事的觀察者,冷靜得有幾分冷酷與無情,她不動聲色地勾勒着亂世的人生素描。看看她筆下的一個教授之死。
我們得到了歷史教授佛朗士被槍殺的消息——是他們自己人打死的。像其他的英國人一般,他被征入伍。那天他在黃昏後回到軍營裏去,大約是在思索着一些甚麼,沒聽見哨兵的吆喝,哨兵就放了槍。
佛朗士是一個豁達的人,徹底地中國化,中國字寫得不錯(就是不大知道筆劃的先後),愛喝酒,曾經和中國教授們一同遊廣州,到一個名聲不大好的尼庵裏去看小尼姑。他在人煙稀少處造有三幢房屋,一幢專門養豬。家裏不裝電燈自來水,因為不贊成物質文明。汽車倒有一輛,破舊不堪,是給僕歐買菜趕集用的。
他有孩子似的肉紅臉,瓷藍眼睛,伸出來的圓下巴,頭髮已經稀了,頸上繫一塊黯敗的藍字寧綢作為領帶。上課的時候他抽煙抽得像煙囪。儘管說話,嘴唇上永遠險伶伶地吊着一支香煙,蹺板似的一上一下,可是再也不會落下來。煙蒂子他順手向窗外一甩,從女學生蓬鬆的鬈髮上飛過,很有着火的危險。
他研究歷史很有獨到的見地。官樣文字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顯得十分滑稽,我們從他那裏得到一點歷史的親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觀,可以從他那裏學到的還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死了——最無名目的死。第一,算不了為國捐軀。即使是「光榮殉國」,又怎樣?他對於英國的殖民地政策沒有多大同情,但也看得很隨便,也許因為世界上的傻事不止那一件。每逢志願兵操演,他總是拖長了聲音通知我們:「下禮拜一不能同你們見面了,孩子們,我要去練武功。」想不到「練武功」竟送了他的命——一個好先生,一個好人。人類的浪費……
張愛玲冷眼看世界,淡然地述說別人的故事,同時也冷峻地剖白自己,對自己的自私毫不偽飾掩藏。
有一個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蝕爛症。痛苦到了極點,面部表情反倒近於狂喜……眼睛半睜半閉,嘴拉開了仿佛仿佛癢絲絲抓撈不着地微笑着。整夜地叫喚:「姑娘啊!姑娘啊!」悠長地,顫抖地,有腔有調。我不理。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我恨這個人,因為他在那裏受磨難,終於一房間的病人都醒過來了。他們看不過去,齊聲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來,陰沉地站在他牀前,問道:「要甚麼?」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繪他點東西,不拘甚麼都行。我告訴他廚房裏沒有開水,又走開了。他嘆口氣,靜了一會,又叫起來,叫不動了,還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
這人死的那天我們大家都歡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時候,我們將他的後事交給有經驗的職業看護,自己縮到廚房裏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爐小麪包,味道頗像中國酒釀餅。雞在叫,又是一個凍白的早晨。我們這些自私的人若無其事地活下去了。
這就是張愛玲,以近乎冷血的筆調塗抺出一幅戰時的香江畫卷,展示出亂世景象,也透視出人世的荒謬與蒼涼。她是清醒的,因為她看清了生命的本相︰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道,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裏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人都是孤獨的。
張愛玲通過文字留下來的戰時殘卷,已經成了香港歷史記憶的一部份。今天,當我們走進港大校園,漫步在陸佑堂、儀禮堂、梅堂的山徑之間,仍然可以想像一個來自上海的女生,特立獨行的神情。
張愛玲一生在香港停留了三次,第二度來港是在一九五二年。她向香港大學申請復學獲得批准,於當年七月經廣州抵達香港,入住女青年會埋首寫作,並未再入港大復學。在此期間,她開始為香港「美國新聞處」翻譯《老人與海》、《愛默生選集》、《美國七大小說家》(部份)等書,及創作長篇小說《秧歌》、《赤地之戀》。一九五三年,深居簡出的她認識了紅學專家宋淇及夫人鄺文美,結為知交。當時宋淇一家居住在北角繼園街輝濃臺,張愛玲就託他們在附近的英皇道租了一間斗室。宋淇在〈私語張愛玲〉中寫道:
這房間陳設異常簡陋,最妙的是連作家必備的書桌也沒有,以致她只能拘束地在牀側的小几上寫稿。說她家徒四壁並非過甚其詞。她一直認為身外之物都是累贅,妨礙一個人生活的自由。
宋淇的兒子宋以朗後來也曾回憶說,「當時我家在繼園街大斜路轉角第一幢,家裏工人常下山送飯到張愛玲家」。當年的北角有「小上海」之稱,張愛玲居住於此想必也留下了不少足跡。她那張叉腰昂首的經典相片(見圖),就是拍攝於街角一間叫「蘭心」的照相館,這也算是她在北角留下的永久記憶吧。她非常滿意這張相片,曾說:「我很喜歡圓臉。下世投胎,假如不能太美,我願意有張圓臉。」她後來再光顧蘭心,回來時又說︰「最好照相拍得像自己,又比自己好看一點。」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張愛玲搭乘「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赴美國。
一九六一至六二年,張愛玲第三度來港,為電懋電影公司編寫《紅樓夢》、《南北一家親》等劇本。這次居港,前後不過半年,住在花墟道斗室,返美前到宋淇位於豪宅區加多利山的居所借宿兩星期。
這就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奇女子」張愛玲,與香港的不解因緣。一場戰爭改變了她的人生走向,也讓她對香港有了刻骨銘心的記憶。她屬於上海,也屬於香港,而且成了香港一個永久的傳奇。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客棧倒影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18 |
現代散文 |
$ 261 |
現代散文 |
$ 261 |
中文現代文學 |
$ 290 |
中文書 |
$ 297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客棧倒影
本書所收的文字,似乎都與行旅有些許關連,雖非有意為之,倒應合了某種冥冥的安排……文中固然承載了種種見聞,是真實經歷與經驗的記錄,但一進入文字之中,這些都不再是現實本身,相反只是投映在文字之湖的倒影。
——蔡益懷〈羈旅人生的倒影〉
本書文字均環繞作者生活所得的所思所感。筆端在自傳、遊歷,寫人,感懷之際,往往流露出作者的至情至性。小書共分四個部分:輯一【都巿田園】,是居港歲月的點滴留影,份量不多,但也是人生不同階段的真實見聞與心言;輯二【人在天涯】,是旅途見聞,記錄過往一些行蹤,雖說類近遊記,但所記必有所寄慨,與自身不可分割;輯三【與你同在】,懷人記事,師友親朋,所寫必為作者尊崇欣賞,所言也必出於自家心田;輯四【天地見證】,是一組見聞錄,從當年四川地震災區的第一現場採寫回來,不是報導而是見證,當年以筆名見刊於《明報》,權當以文字的形式獻上的一炷清香,為死者也為生者。
作者簡介:
蔡益懷
筆名許南山、南山,文學博士,作家、文學評論家,著作有︰小說集《前塵風月》、《情網》、《隨風而逝》、《裸舞》、《東行電車》,文學論文集《港人敘事》、《想像香港的方法》、《拂去心鏡的塵埃》、《本土內外》,文藝學專著《小說,開門》、《妙筆生花》等。
著作曾獲豐子愷散文獎、香港出版雙年獎等。
章節試閱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
——張愛玲與香港的不解緣
蔡益懷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裏,誰知道甚麼是因,甚麼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
這是《傾城之戀》中的一段話,相信很多人都十分熟悉。這個小說敍述的是白流蘇的故事,不過,在我看來,這段話也道出了張愛玲本人的命運。一個女子在兵荒馬亂的時代,似乎注定把握不住自己的命運,而只能像浮萍一樣隨波飄流。
一九三九年,十九歲的張愛玲來到香港,入讀港大文學院,也從此跟香港結下不解之緣。她原本是要到倫敦大學升學,卻...
——張愛玲與香港的不解緣
蔡益懷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裏,誰知道甚麼是因,甚麼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
這是《傾城之戀》中的一段話,相信很多人都十分熟悉。這個小說敍述的是白流蘇的故事,不過,在我看來,這段話也道出了張愛玲本人的命運。一個女子在兵荒馬亂的時代,似乎注定把握不住自己的命運,而只能像浮萍一樣隨波飄流。
一九三九年,十九歲的張愛玲來到香港,入讀港大文學院,也從此跟香港結下不解之緣。她原本是要到倫敦大學升學,卻...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羈旅人生的倒影
﹙代序﹚
這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文學寫作以來,我都沒有在散文方面怎麼用力,時間精力主要耗在小說、評論上。不過,時不時還是會隨性寫下一些散章,記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久而久之積累下一些篇什。去年,得文友鼓勵,整理了其中一部份,輯成此書。這些都是近十數年的文字,早年的只收了〈客棧倒影〉這一篇。沒有將所有的散文都整理成册,說來也是貪方便,一則近年的文字有電子檔,從電腦裏找出來,稍加編輯即可;二則早年的文字都散見於不同的報刊,搜集、輯校需時,一時難以顧及,也就捨難取...
﹙代序﹚
這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文學寫作以來,我都沒有在散文方面怎麼用力,時間精力主要耗在小說、評論上。不過,時不時還是會隨性寫下一些散章,記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久而久之積累下一些篇什。去年,得文友鼓勵,整理了其中一部份,輯成此書。這些都是近十數年的文字,早年的只收了〈客棧倒影〉這一篇。沒有將所有的散文都整理成册,說來也是貪方便,一則近年的文字有電子檔,從電腦裏找出來,稍加編輯即可;二則早年的文字都散見於不同的報刊,搜集、輯校需時,一時難以顧及,也就捨難取...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羈旅人生的倒影
輯一都巿田園
我的都市田園﹙二章﹚
水星街十八號
回家的路悠長悠長
跑步,為生命充電
探尋沙羅洞
登獅子山
西貢郊遊記
嶼南懷古
赤柱灣畔聽海濤
輯二人在天涯
客棧倒影
回首一方净土
花蓮夜雨
平遙人家
大漠魂
武夷神思
長汀,我帶不走的繾綣
泉南佛國處處道場
面對堅硬的高牆,讓我們輕盈如飛鳥
沐著長白山的清風起跑
狄更斯伴我遊倫敦
倫敦的小巷
那天,我登上了科隆大教堂
輯三與你同在
省港路上的遐思
師道
不拘理法自成格
他走得真是瀟灑
說說曾老總的固執
她如春風般溫煦
...
輯一都巿田園
我的都市田園﹙二章﹚
水星街十八號
回家的路悠長悠長
跑步,為生命充電
探尋沙羅洞
登獅子山
西貢郊遊記
嶼南懷古
赤柱灣畔聽海濤
輯二人在天涯
客棧倒影
回首一方净土
花蓮夜雨
平遙人家
大漠魂
武夷神思
長汀,我帶不走的繾綣
泉南佛國處處道場
面對堅硬的高牆,讓我們輕盈如飛鳥
沐著長白山的清風起跑
狄更斯伴我遊倫敦
倫敦的小巷
那天,我登上了科隆大教堂
輯三與你同在
省港路上的遐思
師道
不拘理法自成格
他走得真是瀟灑
說說曾老總的固執
她如春風般溫煦
...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