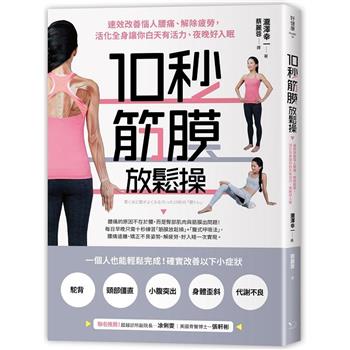夜語心燈,拈花微笑,煥發自性光輝,照見自身,也溫暖人心。
中國古代有源遠流長的詩話傳統,文人學士談文說藝,寓學理於閒談中,隻言片語,微言大義,內容豐富多采,形式活潑多樣,蔚為大觀。本書作者於創作、著述、編輯之餘,以現代視角、今人筆法,隨事生說,積累了若干藝文心得感言,大有上承古風續寫現代詩話的意味。此書共收錄八十多篇藝文小品,為作者近十年間的隨筆精選。全書分兩輯,「藝文絮語」與「編後漫筆」,前者為求道心得與創作雜感,其中不乏對文化文學現象的現實回應;後者為文學雜誌的編後寄語,記錄了不同年代與社會時期的所思所想。二者各有側重,特點為一,都於隨性輕快的漫話中閃現卓識與洞見。
文如其人,集中小品乃作者為人為學為文的心跡墨痕,所言所語皆不虛誑,一如作者所說︰此中有真言。
以心印心,心心相印,但願文友都能從這本小書中領受到作者的幽幽文心、拳拳盛意。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南山夜語:藝文隨筆集(精裝)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31 |
中國古典文學 |
$ 277 |
國學總論 |
$ 277 |
中文現代文學 |
$ 308 |
中文書 |
$ 315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南山夜語:藝文隨筆集(精裝)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蔡益懷
蔡益懷(常用筆名南山、許南山),暨南大學文藝學博士,作家、文學評論人, 八十年代開始從事文學創作與評論,結集出版的著作有——小說集︰《前塵風月》(香港︰獲益,1994)、《情網》(同上,1998)、《隨風而逝》(同上,1999)、《裸舞——蔡益懷小說選》(台灣︰釀出版,2011)、《東行電車》(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15);散文集︰《客棧倒影》(香港︰初文出版社 2017);文論集︰《港人敍事》(香港作家協會,2001)、《想像香港的方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2005)、《拂去心鏡的塵埃》(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本土內外——文學文化評論集》(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15);學術專著︰《小說,開門》(香港︰天地圖書 2015)、《妙筆生花——中文寫作+名篇導讀》(香港︰練習文化,2016)
蔡益懷
蔡益懷(常用筆名南山、許南山),暨南大學文藝學博士,作家、文學評論人, 八十年代開始從事文學創作與評論,結集出版的著作有——小說集︰《前塵風月》(香港︰獲益,1994)、《情網》(同上,1998)、《隨風而逝》(同上,1999)、《裸舞——蔡益懷小說選》(台灣︰釀出版,2011)、《東行電車》(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15);散文集︰《客棧倒影》(香港︰初文出版社 2017);文論集︰《港人敍事》(香港作家協會,2001)、《想像香港的方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2005)、《拂去心鏡的塵埃》(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本土內外——文學文化評論集》(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15);學術專著︰《小說,開門》(香港︰天地圖書 2015)、《妙筆生花——中文寫作+名篇導讀》(香港︰練習文化,2016)
目錄
這支筆有價,不賣﹙代序﹚
藝文絮語
現實堅硬如冰,讓我們輕盈如飛鳥
為何文學如何文學
作家的心向着弱者
詩是通靈的文字
孤獨,是詩人的必修課
現代人為甚麼缺失詩情
詩人的天職是還鄉
詩人的血應該是熱的
詩的辯證法
功夫在詩外
外師造化 中得心源
別叫我詩人
因文字之名
陪金庸「捱鬥」
我寫,故我在
說說創作力
為伊消得人憔悴
我的生命詩學
被虛構的人
半是修女,半是蕩婦
理解梵高
潛水鐘與蝴蝶
居於斯 愛於斯
神秘的原創力
如有神助
「九龍皇帝」的精神
聽從內心的指引
如此詩人,如此涼薄
為生命讓路
生命的頌歌
情與愛的心聲
一本高品位的作家論著
讀羅貴祥《游文異種》
《徐訏作品評論集》讀後
故事的力量
紀念王敬羲
人面桃花,人是物非
文人多大話?
認同與反思
甘做一名文學的義工
編後漫筆
文人修的是來世
叩問曹禺「一生的苦悶」
最是一年春好處
歸去,呼吸一口純淨的空氣
小說聖手的「斷魂槍」
隱而不露即藝術
為甚麼是契訶夫
因簡單而純粹而強大
為文學病象把一下脈
詩人都是懷鄉的人
文字有靈,文學有價
香港,何其小又何其大
拒絕虛假,這就是答案
從文字轉換想到文化的裂痕
文學需要一團火
講述地道的香港故事
碎片化時代文心不能碎
茶餐廳裏的編委會
文學的熱情與信仰
寫作,可創造一個世界
文學的綠洲與福地
香港,一座故事的城
文學,紥根於生活的土壤
我們對文學仍懷有信心
文學需要包容
北極村星空下的懷想
從一個被遮蔽的作家說起
回歸原鄉的書寫
文學新世代 創作生力軍
美因河畔的回眸
以文學的名義吹響集結號
香港需要一個文學館
為有源頭活水來
俠骨文心寫春秋
文學應該回應現實的訴求
把握「為人生」的價值尺度
詩歌療治我們心靈的傷痛
還寫作一點真誠
冬日的文學暖流
打開心靈世界的窗口
文學的薪火傳承
厚實的文字記錄
風骨的文學
傾聽內心的聲音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讓文學回到生活中來
後記︰此中有真言
藝文絮語
現實堅硬如冰,讓我們輕盈如飛鳥
為何文學如何文學
作家的心向着弱者
詩是通靈的文字
孤獨,是詩人的必修課
現代人為甚麼缺失詩情
詩人的天職是還鄉
詩人的血應該是熱的
詩的辯證法
功夫在詩外
外師造化 中得心源
別叫我詩人
因文字之名
陪金庸「捱鬥」
我寫,故我在
說說創作力
為伊消得人憔悴
我的生命詩學
被虛構的人
半是修女,半是蕩婦
理解梵高
潛水鐘與蝴蝶
居於斯 愛於斯
神秘的原創力
如有神助
「九龍皇帝」的精神
聽從內心的指引
如此詩人,如此涼薄
為生命讓路
生命的頌歌
情與愛的心聲
一本高品位的作家論著
讀羅貴祥《游文異種》
《徐訏作品評論集》讀後
故事的力量
紀念王敬羲
人面桃花,人是物非
文人多大話?
認同與反思
甘做一名文學的義工
編後漫筆
文人修的是來世
叩問曹禺「一生的苦悶」
最是一年春好處
歸去,呼吸一口純淨的空氣
小說聖手的「斷魂槍」
隱而不露即藝術
為甚麼是契訶夫
因簡單而純粹而強大
為文學病象把一下脈
詩人都是懷鄉的人
文字有靈,文學有價
香港,何其小又何其大
拒絕虛假,這就是答案
從文字轉換想到文化的裂痕
文學需要一團火
講述地道的香港故事
碎片化時代文心不能碎
茶餐廳裏的編委會
文學的熱情與信仰
寫作,可創造一個世界
文學的綠洲與福地
香港,一座故事的城
文學,紥根於生活的土壤
我們對文學仍懷有信心
文學需要包容
北極村星空下的懷想
從一個被遮蔽的作家說起
回歸原鄉的書寫
文學新世代 創作生力軍
美因河畔的回眸
以文學的名義吹響集結號
香港需要一個文學館
為有源頭活水來
俠骨文心寫春秋
文學應該回應現實的訴求
把握「為人生」的價值尺度
詩歌療治我們心靈的傷痛
還寫作一點真誠
冬日的文學暖流
打開心靈世界的窗口
文學的薪火傳承
厚實的文字記錄
風骨的文學
傾聽內心的聲音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讓文學回到生活中來
後記︰此中有真言
序
代序
這支筆有價,不賣
我有一管禿筆,說來也沒甚麼特別,用了幾十年,真的是又破又殘,不值錢。
雖然如此,倒還沒想過閒置、丟棄,更沒想過用它來換錢。畢竟用開用慣,有幾分感情,或許也有幾分敝帚自珍的驕矜。
此日,夜來幽夢,有東家財主的家奴登門,說要買我這支筆。我幾乎啞然失笑。幸好沒笑,不然夢就醒了。
奴者說,他的東家看好我這支筆,要我幫他寫點錦繡文章。
我認識這個東家,方圓百里千里無人不知,富甲一方,最近又起了一座新紅樓,富麗奢華之極。真是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誰人不知何人不曉?鄰里過客無不驚嘆豔羨它的堂皇,自然也有不少墨客騷人爭相賦詩贊頌。
奴者直言,主人對那些吹捧文章都不放眼內,倒是看中你這支筆管所流出的文字。
我說,哈哈,這支筆鄙陋之極,何堪大用?
奴者以為我吊高來賣,說無非是酬勞,錢不是問題。
聽此一言,我的興致倒來了,於是應答,如此說來,倒是真想知道你的主子出價幾何。
奴者直截了當,你開個價。
他大概以為我心動了,天下哪有嫌錢腥的人?我說,我的這支筆很貴哦。
奴者又問,時下最高稿酬如何計算。我告之行情,對方曰,嗨,這算甚麼,給你十倍的潤筆費又如何?此事敲定了!
我說,慢,這可不是錢的問題。對方瞠目,欲知為何。我說,我太了解你家主人的為人,恕我直言,為富不仁,横行霸道,姦淫搶掠,無惡不作,豈是我所能效力之流?
奴者道,我懂你的意思,也尊重你的想法,但我家主人並不是要你給他寫頌歌,只是要你講一點正面的話,不要只是聽那些負面的說法。寫文章,不過觀點與角度,你只看負面的,無異盯着地面的狗屎。樹大有枯枝,一點敗葉都沒有那才奇怪呢。你只要往好的一面看,到處都光鮮亮麗、金光燦爛。說一點好聽的話,何難之有?再說,你看,我家主人發家致富,天下人誰不驚嘆,我家的門面是全世界最輝煌的,我家的高樓是全世界最壯觀的,我家的……
罷罷罷,我連聲制止,我知道你家有許多的威名,冠絕全球,家財多到足以一俊遮百醜,全世界的人都買你們的怕,好吧?奴者自豪地說,可不是!
我說,我懂,你家甚麼都不缺,就缺一個好名聲,對吧?
他悻悻不語。
我說,請回吧。
他心有不甘,說難道有如此豐厚的酬勞都不考慮?他環視一番我的破屋,又道,何必讓自己活得像個苦行僧呢?
我說,我也愛財,但取之有道。
他又說,你不再考慮一番?韓愈還有諛墓的文字,李白有也擦鞋的時候!再說,文章還是小事,投到我主人幕下,何愁沒有你的榮華富貴?
啊,確實吸引,難為了你這位說客。我說,待我問過這支筆。
話音剛落,倏然一管修長的筆亢然直立眼前,雖非七尺男兒,卻也傲然挺立,有點男兒氣。我的這管筆自號毛穎,所以我平時也以穎兄稱之。我說兄臺伴我多年,此君言語,你也聽見,然與不然,憑你一句話。穎兄曰,伴君多年,讀的都是聖賢書,寫的都是肺腑言,胸中墨都是肝膽汁,豈能胡謅荒唐言,做一些顛倒是非、指鹿為馬的文章?罷了!罷了!
我說,聽到了吧?穎兄不答應。
筆是筆,你是你,難道你管不住自己的筆?奴者面有慍色,以為我在戲弄他。
我說,此筆就是我的心,穎兄就是我的手足,我們是一體的,分不開。
奴者知道我態度決絕,懊惱地說,真是怪人,不食人間煙火!別敬酒不吃吃罰酒,小心惹禍上身!
毛穎聽此言,當即正顏厲色,就要發作雄辯滔滔痛斥狗奴才。
我嘴笨木訥,不擅言辭,但知穎兄的急才,文思敏捷,出口成章。這麼多年,我能夠寫一點可堪一讀的文章,也全靠他的墨水。我是名副其實百無一用的人,倒是他遍閱古今中外經史百家,算是一個讀書人。所以他一開口就會滿口伯夷叔齊、箕子微子,仲尼孟柯太史公,掉起書包來,連我都頂佢唔順,再加上是個牛脾子,包硬頸,輕易惹不得。我止住他,穎兄,時候不早,才剛完成了一篇長文,你我都累了,再說我聽日還要上早班,還是就此打住吧。
我轉頭對來者說,我知你家老爺是惡人,不過我也是一個怪脾氣的人。恕我不敬,請回,不送!
奴才走了。留下一句,戇居佬!
哈哈,穎兄與我相視而笑。我說,還是仁兄知我心。毛穎說,還是老兄最愛惜我這管禿筆。
相伴幾十年,誰不知道大家的脾性?又是一番調笑。
嘻嘻哈哈,夢醒,我再好好端視案頭的筆,普普通通,真是物如其人,平凡至極,鄙陋不堪,實在不是甚麼大材,如說有甚麼特別,不過就是有點怪癖,不做富貴夢,只是安於喝一杯小酒,說一點人話,着實一瓶一缽足矣嗰隻。
仰觀夜空,浩浩星河,都是我景仰的人物,響噹噹、硬梆梆,哪有那些貪生怕死,只求眼前富貴之徒的影子?
此心已決,這支筆雖不值錢,但有價,不賣!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於南山書房
這支筆有價,不賣
我有一管禿筆,說來也沒甚麼特別,用了幾十年,真的是又破又殘,不值錢。
雖然如此,倒還沒想過閒置、丟棄,更沒想過用它來換錢。畢竟用開用慣,有幾分感情,或許也有幾分敝帚自珍的驕矜。
此日,夜來幽夢,有東家財主的家奴登門,說要買我這支筆。我幾乎啞然失笑。幸好沒笑,不然夢就醒了。
奴者說,他的東家看好我這支筆,要我幫他寫點錦繡文章。
我認識這個東家,方圓百里千里無人不知,富甲一方,最近又起了一座新紅樓,富麗奢華之極。真是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誰人不知何人不曉?鄰里過客無不驚嘆豔羨它的堂皇,自然也有不少墨客騷人爭相賦詩贊頌。
奴者直言,主人對那些吹捧文章都不放眼內,倒是看中你這支筆管所流出的文字。
我說,哈哈,這支筆鄙陋之極,何堪大用?
奴者以為我吊高來賣,說無非是酬勞,錢不是問題。
聽此一言,我的興致倒來了,於是應答,如此說來,倒是真想知道你的主子出價幾何。
奴者直截了當,你開個價。
他大概以為我心動了,天下哪有嫌錢腥的人?我說,我的這支筆很貴哦。
奴者又問,時下最高稿酬如何計算。我告之行情,對方曰,嗨,這算甚麼,給你十倍的潤筆費又如何?此事敲定了!
我說,慢,這可不是錢的問題。對方瞠目,欲知為何。我說,我太了解你家主人的為人,恕我直言,為富不仁,横行霸道,姦淫搶掠,無惡不作,豈是我所能效力之流?
奴者道,我懂你的意思,也尊重你的想法,但我家主人並不是要你給他寫頌歌,只是要你講一點正面的話,不要只是聽那些負面的說法。寫文章,不過觀點與角度,你只看負面的,無異盯着地面的狗屎。樹大有枯枝,一點敗葉都沒有那才奇怪呢。你只要往好的一面看,到處都光鮮亮麗、金光燦爛。說一點好聽的話,何難之有?再說,你看,我家主人發家致富,天下人誰不驚嘆,我家的門面是全世界最輝煌的,我家的高樓是全世界最壯觀的,我家的……
罷罷罷,我連聲制止,我知道你家有許多的威名,冠絕全球,家財多到足以一俊遮百醜,全世界的人都買你們的怕,好吧?奴者自豪地說,可不是!
我說,我懂,你家甚麼都不缺,就缺一個好名聲,對吧?
他悻悻不語。
我說,請回吧。
他心有不甘,說難道有如此豐厚的酬勞都不考慮?他環視一番我的破屋,又道,何必讓自己活得像個苦行僧呢?
我說,我也愛財,但取之有道。
他又說,你不再考慮一番?韓愈還有諛墓的文字,李白有也擦鞋的時候!再說,文章還是小事,投到我主人幕下,何愁沒有你的榮華富貴?
啊,確實吸引,難為了你這位說客。我說,待我問過這支筆。
話音剛落,倏然一管修長的筆亢然直立眼前,雖非七尺男兒,卻也傲然挺立,有點男兒氣。我的這管筆自號毛穎,所以我平時也以穎兄稱之。我說兄臺伴我多年,此君言語,你也聽見,然與不然,憑你一句話。穎兄曰,伴君多年,讀的都是聖賢書,寫的都是肺腑言,胸中墨都是肝膽汁,豈能胡謅荒唐言,做一些顛倒是非、指鹿為馬的文章?罷了!罷了!
我說,聽到了吧?穎兄不答應。
筆是筆,你是你,難道你管不住自己的筆?奴者面有慍色,以為我在戲弄他。
我說,此筆就是我的心,穎兄就是我的手足,我們是一體的,分不開。
奴者知道我態度決絕,懊惱地說,真是怪人,不食人間煙火!別敬酒不吃吃罰酒,小心惹禍上身!
毛穎聽此言,當即正顏厲色,就要發作雄辯滔滔痛斥狗奴才。
我嘴笨木訥,不擅言辭,但知穎兄的急才,文思敏捷,出口成章。這麼多年,我能夠寫一點可堪一讀的文章,也全靠他的墨水。我是名副其實百無一用的人,倒是他遍閱古今中外經史百家,算是一個讀書人。所以他一開口就會滿口伯夷叔齊、箕子微子,仲尼孟柯太史公,掉起書包來,連我都頂佢唔順,再加上是個牛脾子,包硬頸,輕易惹不得。我止住他,穎兄,時候不早,才剛完成了一篇長文,你我都累了,再說我聽日還要上早班,還是就此打住吧。
我轉頭對來者說,我知你家老爺是惡人,不過我也是一個怪脾氣的人。恕我不敬,請回,不送!
奴才走了。留下一句,戇居佬!
哈哈,穎兄與我相視而笑。我說,還是仁兄知我心。毛穎說,還是老兄最愛惜我這管禿筆。
相伴幾十年,誰不知道大家的脾性?又是一番調笑。
嘻嘻哈哈,夢醒,我再好好端視案頭的筆,普普通通,真是物如其人,平凡至極,鄙陋不堪,實在不是甚麼大材,如說有甚麼特別,不過就是有點怪癖,不做富貴夢,只是安於喝一杯小酒,說一點人話,着實一瓶一缽足矣嗰隻。
仰觀夜空,浩浩星河,都是我景仰的人物,響噹噹、硬梆梆,哪有那些貪生怕死,只求眼前富貴之徒的影子?
此心已決,這支筆雖不值錢,但有價,不賣!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於南山書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