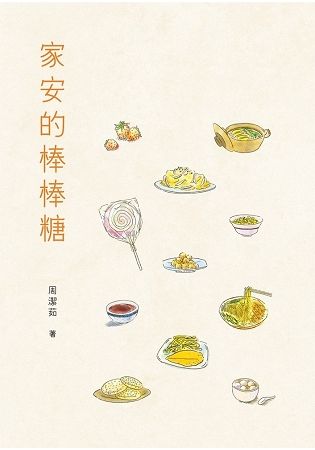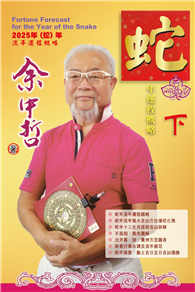在香港做一個文學編輯
二十多年前了,我知道一個電影,《香港朝九晚五》,電影我肯定是沒看過,據說是限制級,這個片名倒一直記到現在,實在是太深刻了對於那個時代的我來講,原來香港人是九點上班五點下班的呀?我那個時候在一個機關上班,朝幾晚幾不是記得很清晰了,只知道冬天起床的時候天色還是漆黑的,夏天無限漫長,單位班車下來,生無可戀的瞬間。
我沒有想到的是我到了四十歲,又回到了這個坐班的狀態,而且在香港。果然是朝九,然而晚六,而且要打卡。加上我住沙田,出版社在北角,來回三個小時車程成為常態,我這個個人的電影就演成了朝七晚八。
看過一個中國內地文學編輯的日常,一切從中午開始,午後他還抽管煙,喝口茶,坐到沙發上。
一個香港文學編輯一天的開始,一定是早上五點四十五分,精確到秒,鬧鐘都不需要,七點前出門搭巴士,下了巴士買早餐,有時候是凱施餅店的碎蛋沙拉麪包,有時候是唐記包點的油煎鍋貼三隻不要醋,有時候巴士司機發揮超常,八點半不到就飛到了北角,於是彎入巴士站前那間潮州粉麪店,要一碗牛肚麪配鮮炸魚皮,豪氣啊,絕對能夠撐到下午一點,午飯的飯點。
上午九點前是一定要坐在桌前的了,看稿,當然是看稿,各種看,一個字都不能看漏了。四十歲才開始做編輯,恨不相逢未嫁時。不過也還好,也只是四十歲,有的作家剛剛開始寫作。
上班第一天,看見老主編一個小本子,每個來稿都手工登記,也真是驚到咬自己。每條稿的處置也都用紅筆劃過,做了註釋,這樣的小本子,放在桌面上的就有十多本。服氣。也只有在香港,也只發生在香港,一個三四十年歷程的編輯部。
三年前我與一個美國出版社有過一個關於英文寫作以及香港的討論,那也是我剛剛回來開始寫作的第一年,我的觀察是從外部進入的,美國式的,有的細節又是對的:
很多閱讀者不知道自己應該讀甚麽,所有閱讀的指導都是利欲熏心的,讀者與出版公司不再互相信任,因為每一個人都在說假話,說誇張的話。這一點也體現在編輯與作者之間的關係上。我在與你們的文字編輯溝通的時候發現她在每一個她認為有疑慮的地方都做了記號,然後逐條詢問,她使用了這個建立一個證據的方法,去為她的讀者們負責,她對她的讀者太過於負責,導致的結果就是我得一個一個地去解釋那些問題,直到給到真正清晰明白的答案。甚至修改會製造問題的單詞。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是欣喜的,我從一九九一年開始發表第一個作品,到二千年停筆,這個期間,我發現編輯們已經不大會改你的稿了,並不是因為你的作品真正就是像一個大師那樣完美,一個字都動不了,而是大家都沒有這個改稿子的意願和習慣了。我從一些年長的中國作家那裏聽說,他們年輕的時候還會有一些改稿會,大家聚集在一起,看看山水,談談文學,改改稿子。這樣的心和格式,在我開始寫作的時候,就沒有了。有中國人情味的東西都沒有能夠得到傳承。甚至現在的一些年輕編輯,勢利,粗魯,沒有禮貌也沒有信用。編輯這個身份的品德底線已經沒有了,就沒有辦法再去談人性,良心。一個時代的墮落是從嘲弄詩人開始的,一份文學刊物的墮落也是從嘲弄自己的作者開始的。我停留在香港,大概也是因為香港最後還保留了一些傳統的美好的東西,而且香港一直在很努力地保護着這些東西。香港作家們的架構可能都是散鬆的,因為沒有一個人混來混去,大家都要謀自己的生,以寫作之外的方式。寫作成為了真正乾凈的一件事情。
如今我也開始做編輯,再看當年的這段話,竟然有些唏噓。我當然不會推翻我說過的話,只是到了自己做編輯,才真正意識到做編輯的不易。做過專業作家,再來做專職編輯,這種體會,真是珍貴。我想起我的作家時代,我的編輯斯繼東跟我說的話,「作為編輯應該始終相信好小說的無數種可能。作家可以偏執,編輯不可以。」
吃完單位統一訂的盒飯,桌上趴了十五分鐘以後,上班,繼續看稿。
在我這裏,每個來稿當然也是要登記,有的東西是一定會被傳承下來的,但是肯定是用電腦。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家安的棒棒糖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40 |
二手中文書 |
$ 185 |
現代散文 |
$ 221 |
現代小說 |
$ 246 |
中文書 |
$ 252 |
中文現代文學 |
$ 25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家安的棒棒糖
女作家周潔茹最新散文作品集,《記憶中的食物》,《現在地》及《在香港寫作》。作為一個從內地漂泊到美國,又回到香港定居的寫作者,周潔茹筆下的生活五味雜陳。書中記述與故人重逢,追憶往事和愛情,周潔茹以文學審美的視角,觀望自己的生活軌跡,飽含豐富的女性私人化體驗。她品嘗親情、友情、愛情與文學創作帶來的幸福與甜蜜,悲傷與苦澀,世情萬象、人情冷暖都在生活細節中一一展現。
作者簡介:
周潔茹
江蘇常州人,中國七零後代表作家之一。
有長篇小說《小妖的網》、《中國娃娃》、《島上薔薇》;小說集《我們幹點甚麽吧》、《你疼嗎》、《到香港去》;隨筆集《天使有了欲望》、《我當我是去流浪》、《一個人的朋友圈》等。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居香港,《香港文學》執行總編輯。
TOP
章節試閱
在香港做一個文學編輯
二十多年前了,我知道一個電影,《香港朝九晚五》,電影我肯定是沒看過,據說是限制級,這個片名倒一直記到現在,實在是太深刻了對於那個時代的我來講,原來香港人是九點上班五點下班的呀?我那個時候在一個機關上班,朝幾晚幾不是記得很清晰了,只知道冬天起床的時候天色還是漆黑的,夏天無限漫長,單位班車下來,生無可戀的瞬間。
我沒有想到的是我到了四十歲,又回到了這個坐班的狀態,而且在香港。果然是朝九,然而晚六,而且要打卡。加上我住沙田,出版社在北角,來回三個小時車程成為常態,我這個個人的電影就...
二十多年前了,我知道一個電影,《香港朝九晚五》,電影我肯定是沒看過,據說是限制級,這個片名倒一直記到現在,實在是太深刻了對於那個時代的我來講,原來香港人是九點上班五點下班的呀?我那個時候在一個機關上班,朝幾晚幾不是記得很清晰了,只知道冬天起床的時候天色還是漆黑的,夏天無限漫長,單位班車下來,生無可戀的瞬間。
我沒有想到的是我到了四十歲,又回到了這個坐班的狀態,而且在香港。果然是朝九,然而晚六,而且要打卡。加上我住沙田,出版社在北角,來回三個小時車程成為常態,我這個個人的電影就...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家安的棒棒糖
我至今無法忘懷
在臺北的日子
我坐在車上吃棒棒糖
後來睡着了
那支棒棒糖卻不見了
我還記得旅店窗外的
那隻蜜蜂
翅膀沾滿了閃亮的金粉
它柔軟而圓的肚子
還記得在海邊的麥當勞
牆壁都塗滿了
貝殼與海浪
彷彿在沙灘上
我還在想着
那枝棒棒糖的下落
是否在臺北
某個專屬於糖果的地方
我至今無法忘懷
在臺北的日子
我坐在車上吃棒棒糖
後來睡着了
那支棒棒糖卻不見了
我還記得旅店窗外的
那隻蜜蜂
翅膀沾滿了閃亮的金粉
它柔軟而圓的肚子
還記得在海邊的麥當勞
牆壁都塗滿了
貝殼與海浪
彷彿在沙灘上
我還在想着
那枝棒棒糖的下落
是否在臺北
某個專屬於糖果的地方
TOP
目錄
一,記憶中的食物
家安的棒棒糖
洋蔥炒蛋
凍咖啡
炒青菜
涼茶
煲仔飯
薑蔥雞和素丸子
拉麪
沒有牛肉麪
餃子
香料
蛋糕
土豆沙拉
味噌湯
野草莓
炸魚薯條
越南粉
湯圓店
大麻糕
醬油拌飯
素麪
冰磚
早飯
米飯餅
燉蛋雞湯
米粉餅
泡飯
豆腐
鍋貼
棒冰
三絲魚卷
魚片乾
冒菜
酒
葡萄酒
冰凍啤酒
二,現在地
烏溪沙
利安邨的空姐
利安邨的瘋子
九龍灣
馬鐵
馬鞍山
未圓湖
香港的人
香港服務
大圍有個火鍋店
我有兩條路
三,在香港寫作
在香港寫小說
我當我是去流浪
對於寫作我還能做點甚麼
島上
在香港
我們的香港
在香港做一個文學編輯
家安的棒棒糖
洋蔥炒蛋
凍咖啡
炒青菜
涼茶
煲仔飯
薑蔥雞和素丸子
拉麪
沒有牛肉麪
餃子
香料
蛋糕
土豆沙拉
味噌湯
野草莓
炸魚薯條
越南粉
湯圓店
大麻糕
醬油拌飯
素麪
冰磚
早飯
米飯餅
燉蛋雞湯
米粉餅
泡飯
豆腐
鍋貼
棒冰
三絲魚卷
魚片乾
冒菜
酒
葡萄酒
冰凍啤酒
二,現在地
烏溪沙
利安邨的空姐
利安邨的瘋子
九龍灣
馬鐵
馬鞍山
未圓湖
香港的人
香港服務
大圍有個火鍋店
我有兩條路
三,在香港寫作
在香港寫小說
我當我是去流浪
對於寫作我還能做點甚麼
島上
在香港
我們的香港
在香港做一個文學編輯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周潔茹
- 出版社: 初文 出版日期:2018-08-10 ISBN/ISSN:978988786678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08頁 開數:32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