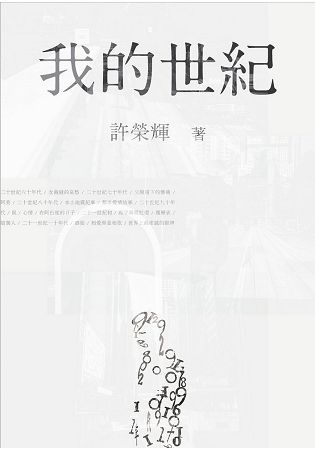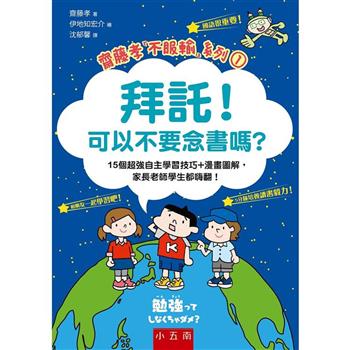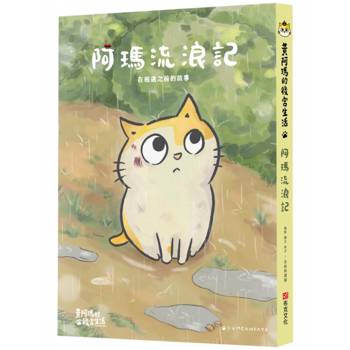現實是一個無限多面的錐體,我們所居住的這個城市也不例外,有各種面相,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面貌和風景,作出千差萬別的解說、詮釋。《我的世紀》就是許榮輝從個人的經歷出發,以個人的視角,對香港這個都市的平民生活與時代變遷所作的個體敘述。作者以真實的筆觸,勾勒一幅幅歷史畫面,一如香港社會的「老照片」,展現出自六十年代以降不同時期的社會風貌與歷史嬗變。這部飽含舊時記憶與情感體驗的作品集,無疑是一部個人的「香港史」。作者不求對幾十年來的社會狀況、時代風雲作全景式的反映,只是以個人的眼光,作零散的、片斷的呈現,且作出個體的旁述。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個工廠女工勞碌、疲憊的身影,也可以看到一個社會在時代變局中的迷茫、焦慮與無力感。
蔡益懷
作者簡介:
許榮輝
曾在香港新聞界長期擔任新聞翻譯工作,作品入選劉以鬯先生主編的《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
章節試閱
女裁縫的哀愁
一、
我要說的故事,背景是這樣的: 那時(我說的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樓房是低矮的,像我居住的這個地區,大多也就是七、八層吧。至於唐樓,四、五層的就很普遍了。 一般人家的日子過得很簡單,單從街景就可以看出個眉目來了。別說那些隨處可見的報紙檔,就是在街頭擺了個只賣香煙的攤檔,也可以搵兩餐了。
煙仔檔鎮日聚集着一群飛仔,窮極無聊,看到有哪個路過的細路,總愛做個像要打人的動作,撩一撩來打發無聊,看到對方露出驚怕的樣子,就會得意地大笑起來。 這種笑聲更可怕,嚇得細路跑得更快了。
那時,一般人的教育程度很低,甚至可以說,文盲很多。
寫信佬在街道某個避風的角落擺了個檔口,也可搵兩餐。經常,在黃昏的斜陽下,看到一個婦女坐在他跟前的一張小椅上,抽抽噎噎地說些甚麼,應該是無限的心事吧!寫信佬只管埋頭落筆,待信寫成後,以木然的神情,淡然的語調,把內容唸了一遍給她聽,她一一默默地點着頭。
這個時候她極度哀傷的情緒已經平復,她也知道,一切哀傷到了紙上都已變得很平淡,指望別人代入她的傷感,哪有可能?
有一次,我聽到寫信佬問一名婦女,還有甚麼要說的嗎?婦人就重覆了一遍她的傷心事。寫信佬以憐憫的語氣對她說:「人一出世,就注定是痛苦的了,誰沒有一肚子的辛酸?把所有這一切都寫給遠方的親人知道,徒增他們的牽掛,而毫無幫助。」
婦女含着淚點頭,感謝寫信佬把信寫得淡然的苦心。
那時,女人的美容,哪有現在五花八門的化妝技術,高級的護膚品?當街總可以看到口裏咬着一根線的女人,以熟練的技巧,為愛美的師奶刮臉。
在暖洋洋的冬日,坐在椅子上曬着陽光的師奶,一想到刮臉後的容光煥發,在臉被刮得緊繃的時候,仍不忘綻出笑容。
娛樂也簡單。電視機是專屬較富裕人家的東西,電影院很遙遠。公園裏的遊樂設施不多。我們孩子,最喜歡的去處之一是巷仔裏的理髮店。
周末的理髮店總是有着很多小孩子,一玩起捉迷藏,就把理髮的正經事忘了。
店裏還會有一大堆漫畫書,雖然已被孩子們翻得破破爛爛,畢竟是至愛,要是新添的,必成搶手貨,輪到自己時,已變得跟破破爛爛的舊書沒有分別,但仍然讀得津津有味。
理髮師傅都是馬迷。因為賽馬大多在周末舉行,周末就成了他們最繁忙的日子。他們馬不停蹄地為孩子們理髮,馬場上的賽馬也為他們馬不停蹄,帶來叫他們或悲或喜的賽果。
賽馬評述員透過收音機為他們直播,那種講馬時,語速逐步加快,最後聲嘶力竭的藝術,成了後來的傳統,是繪聲繪影的典範。
我依然記得,在評述得最起勁最緊張的時候,師傅的頭部都傾向收音機那邊去,就像向日葵傾向太陽,即使某個孩子突然尖叫並且哭了起來,他還是不理會,充其量暫時停下手,要聽到有了賽果才安心。
這是像每週的賽事,都要上演的,差別就看那個孩子遭殃罷了。因為,就算技藝再高超的師傅,因為整個心思都撲到聽馬上,剪髮器把孩子的頭髮纏住了還不知道,繼續向上推,自然要叫孩子痛得叫了起來。
賽馬日讓師傅們的周末過得很忙碌,也很容易過。賽馬日理所應當是他們最驚喜,最失望,最興奮,最沮喪的一天。
通常,他們把辛苦掙來的錢的一部份送給了馬會,但他們覺得值得,因為這樣,漫長、平淡的人生才似乎有了點起伏。那是平庸、卻也算相對穩定的時代,師傅大多數會維持這樣簡單的生活,直至他們退休,因為他們都覺得這樣的生活方式適合他們。或者,要說有甚麼其他原因,或許是他們被困在小巷裏,與外間的發展已嚴重脫節,除了這份工,也難以到別處,過別樣的生活了。
只有到了某個時候,比如,包圍着它們的低矮樓房重建了,理髮店所處的陋巷消失了,他們自然也無法維持他們的日子了。
我所認識的好多孩子,因為自小就受到熏陶,長大後也喜歡賽馬。他們後來各自走向自己的人生路,有的得意,有的失意。
市面上最熱鬧的,莫過於我家居住樓房對面的那家酒樓了。
因了這家酒樓,我從小就明白,不論多貧窮的社會,總有吃得起的人,他們把酒樓擠得滿滿的。那時的侍者,賣點心不是用車仔推着,而是把各式點心放在一個四四方方的托盤裏,用皮帶繫着,掛在脖子上,在客人中間穿梭叫賣。
侍者雖然辛苦,卻可營造一種氣氛。那時,我已經上學了。上學時,酒樓就已是一片喧囂,市聲活靈活現呈現眼前。酒樓裏的座位裝不下食客,侍應會把餐枱放到外面的行人道上。
反正那個時候的車輛不像現在這麼多,並不太受影響。早晨茶客品茗,吃點心,看報紙,自得其樂。
放學時,又看到酒樓坐滿了吃午飯的食客了。在我看來,那個時候所有的熱鬧場面,都是在酒樓表現出來的。
我家窮,雖是近在咫尺,那酒樓卻又恍如另一個世界了。
我作了這樣的開場白,無非是想說:那個時候,在我熟悉的這個地區,再野的人,過的也不過是很簡單的生活方式。
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故事,也就留下了這種簡單生活方式的印記。
女裁縫的哀愁
一、
我要說的故事,背景是這樣的: 那時(我說的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樓房是低矮的,像我居住的這個地區,大多也就是七、八層吧。至於唐樓,四、五層的就很普遍了。 一般人家的日子過得很簡單,單從街景就可以看出個眉目來了。別說那些隨處可見的報紙檔,就是在街頭擺了個只賣香煙的攤檔,也可以搵兩餐了。
煙仔檔鎮日聚集着一群飛仔,窮極無聊,看到有哪個路過的細路,總愛做個像要打人的動作,撩一撩來打發無聊,看到對方露出驚怕的樣子,就會得意地大笑起來。 這種笑聲更可怕,嚇得細路跑得更快了。
那時,一般人的教...
作者序
香港社會變遷的個體旁注
——許榮輝《我的世紀》閱讀報告
蔡益懷
窮困、勞碌、疲憊、迷茫、焦慮……這是這本作品集的關鍵詞。
現實是一個無限多面的錐體,我們所居住的這個城市也不例外,有各種面相,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面貌和風景,作出千差萬別的解說、詮釋。《我的世紀》就是許榮輝從個人的經歷出發,以個人的視角,對香港這個都市的平民生活與時代變遷所作的個體敍述。作者以真實的筆觸,勾勒一幅幅歷史畫面,一如香港社會的「老照片」,展現出自六十年代以降不同時期的社會風貌與歷史嬗變。這部飽含舊時記憶與情感體驗的作品集,無疑是一部個人的「香港史」。作者不求對幾十年來的社會狀況、時代風雲作全景式的反映,只是以個人的眼光,作零散的、片斷的呈現,且作出個體的旁述。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個工廠女工勞碌、疲憊的身影,也可以看到一個社會在時代變局中的迷茫、焦慮與無力感。
作為一個曾經在社會的底層掙扎過的作家,許榮輝始終以一種在地的情懷,審視、回望香港的社會現實與人情世態,他的心是貼近弱者的。他的文字接地氣,有人間氣息,全無高高在上的「精英」意識,也無自命不凡的「自大」鼻息。這樣的作家,不顯山不露水,一向為我所尊重與欣賞。他沉潛於現實生活之中,靜默地觀察與思考,且對尋常人生作出個人化的表述。一如他在〈心情〉中所透露的創作心迹,在生命的沉澱物中發掘故事,提煉主題,紀錄曾經發生過的平凡小事,「最重要的是留下一點記憶」。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許氏的心性與創作路向了,他志在寫「一個真實的故事,一段小小的成長故事,小人物有血有淚的瑣事。」
通觀整個作品集,有兩大主調特別顯明,一是弱勢社群的悲歌,二是時代變遷的反芻。
一、弱勢社群的悲歌
紀錄六七十年代勞工苦況,是許榮輝小說的一大主題,也是他在香港文學創作群體中獨樹一幟的標誌性特色。也許正是得益於艱難歲月的人生經歷,許氏的創作一直保持着一種可貴的品質,即正視人間疾苦。所謂「文窮而後工」,大凡有出息的文學人,往往是承受過生活磨難的人,如狄更斯,如老舍。苦難淬礪了他們的心性,讓他們更有同情心,讓他們獨具慧眼,能夠從尋常人生中發現風景,寫出感人的故事。苦難,成了他們創作的壓艙石。在許榮輝的作品中,我也看到了這樣一些特質。
在描寫勞工生活的小說中,我特別欣賞〈父親遺下的傷痛〉和〈阿美〉這兩個作品。前者記錄老一輩的艱辛,讓人看到一個母親所承受的人生傷痛。後者則直接反映勞工密集工業時代的工人苦況,如作品中所言︰「生活在那個年代,捱生捱死的低下階層人,有種命若螞蟻的絕望感。一個人捱生捱死,唔憂做,但也只不過是搵兩餐,其他的就統統別指望了。」這個作品如實描述出工廠流水線的景況︰「那時的工廠大廈,就為這種勞工密集工業而設計和建造,每層樓的面積很大,一排一排的生產線緊緊地擠着,一眼望去,幾乎是一望無際的密密麻麻的年輕女工在低頭苦幹,叫人想到了螞蟻的勞作。」這些作品與其說是「創作」,不說如是紀錄,是活生生的見證。作者以文字的形式為自己留下一份生命的備份,同時也為香港的時代風雲、社會嬗變,作出個體的備注。
這就是文學,來自於生活,來自於真切的生活體驗。文學就是生活的話說多了,成了老生常談,容易讓人麻木,甚至反感。然而,如果你真正領會了文學的本質,就會相信,離開了生活,文學甚麼都不是。空有華美文字而無生命體驗的文學,只是一件沒有肉身與靈魂的金鏤玉衣。當然,只有生活同樣是不夠的。生活的原礦還需要經過提煉,轉化成含有人生思考的經驗,才具備文學值。文學寫作就是「去蔽」,拂去表層的塵埃,讓生活的本相得以呈現,讓讀者看清生活的本來面目,看到人的天性與真實的生存狀況。許榮輝的作品就做到了這點,他讓我們看到了生活的真相。在他的筆下,有兩個人物形象都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其一是母親,其二是阿美。
母親是全書中着墨最多的人物,除〈父親遺下的傷痛〉外,〈鼠〉與〈心情〉等作品,都對母親形象有不同程度的記敍與刻寫。通過這些作品,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刻苦耐勞,又善良隱忍的女性形象。她只是「這座都市一名廉價勞工」,且看她在餅廠工作的情景︰「機器像水庫決堤的堤壩,餅乾像瀉下的洪水,女工們終日與機器角力着,拼命把流瀉下來的餅乾裝進餅桶裏,但她們總是被洪水淹沒。即使是在寒冬,也是汗流浹背,很辛苦,但無數歲月就這樣悄悄流逝。」餅廠結業,她又進入大工廠,辛苦工作幾十年,直到工廠北遷,被社會所抛棄。她的一生似乎只有兩個字「痛苦」,「以前工作得太辛苦,就是痛苦了」,「以前的痛苦,造成了今天的病痛。從痛苦走向另一個痛苦,構成了一個人生。這是母親的人生。」這位母親固然只是一名普通的女工,但又豈是平凡如草芥的一員,她就是老一代移民、底層勞工的縮影,是艱難歲月苦難母親的象徵。
阿美是另一類打工女的象徵,從她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代女工的生存處境。她在電子廠做科文,也許是沉淪下潦,又奮發無力的緣故吧,「整個人都顯得太隨便了,太無所謂了,隨便得叫人一下子感到她沒有甚麼可珍貴的東西」。她的臉「是疲累的,因為疲累而蒼白。又因為希望憑着一支煙而把滿臉的疲累支撑起來,滿臉的肌肉反而扭曲了。這種因為疲累而失控的肌肉,讓人一眼就看出了精神上一種徹底的崩潰。要命的是,這張面孔的主人,似乎對自己精神上的崩潰無所謂,或是恐怕已習以為常了,一個女子的氣質就蕩然無存了」。這無疑是許許多多工廠妹精神面貌的寫真。作者透過這個形象,表現出六七十年代打工仔的共同命運,家貧,早早投身社會,失去接受教育的機會而苟活着。他們過着昏天黑地的日子,身心交瘁,滿目都是叫人難受的昏暗。他們工作勞累、生活刻板,但仍然努力掙扎着,不少人則力求上進讀夜校。「她們知道她們身處深坑,她們必須趁着年輕還有氣力的時候,努力爬出來。但有多少人真的能夠爬得出來呢?最多的人也許爬到一半,就又跌到了坑底。」這就是他們的相同之處,無論如何的努力,總是無法擺脫困境。盡管如此,他們還是沒有放棄對生活的最後一點希冀,正如阿美所說︰「我總不信我的命運會那麼差吧!」
〈阿美〉這個作品如一份社會檔案,真實紀錄了一代打工仔的苦況,讓人們看到一個時代的集體迷失,着實是香港當代文學中難得的紀實力作。值得一提的是,文學不是生活經驗的簡單複寫,而是經過作家的心靈容器發酵過,以個人的透鏡審視折射出來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許榮輝筆下的場景畫面都染上了個人的情感色彩,有着一層舊時歲月的蒼桑色調。正是這種個人經驗,為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增添了個人的痕跡。
二、時代變遷的反芻
文學有不同的面向,除了探視個體的生命狀態,揭示人的生存處境,也面向社會歷史,作出反思與批判。八十年代以降,香港社會發生了一系列改變歷史進程的巨變,回歸、政改等等事件接踵而至,產生一波又一波的震盪。作為一個有社會意識、勤於思辨的作家,許榮輝自然也把目光投向時代風雲、社會演變,且作出他個人的觀察、判斷、言說。在這個集子中,〈本土地震紀事〉、〈心情〉、〈在阿巴度的日子〉等篇章,都一定程度反映出他個人的歷史意識,從中不難感受到他的在地情結與追問質詢精神。這些作品反映出香港社會的迷茫與焦慮,自然也探測到這個城市的變化,「味道變了,不是以往那種味道。原有的味道被外來的味道入侵了」,進而質問「一切都變得我不熟悉了,那個我熟悉的本城到哪裏去了呢?」
歷史書寫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和路徑,如長江大河式的宏大敍事,或家族回憶的私密記述。許榮輝無意於寫大歷史,對社會歷史變局作全方位的掃描和展示,相反只是通過個體的體驗,對社會變遷作出吉光片羽的折射式點染。應該看到,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界一直存在一種「重大題材癖」,追求一種高、大、全的歷史書寫,幾至形成文學的「厚重拜物教」,流行緊扣重大歷史事件作機械反映、食而不化的創作風尚。我對這類創作習氣,一向是頗為抗拒的,在我看來,作家之於現實的關係,全然有別於政治家、歷史學家,並不是以「政治正確」或意識型態的標準,來進行是非判斷;也不是以歷史年表式的書寫,來羅列史實。作家始終是以一種人道的準則,審視社會、觀察人生、叩問靈魂,他們的本事是以一種悲憫之心觀照現實,撫慰蒼生。所以,不管多麼重大的事件,一落到作家筆下就不再是以新聞筆調作粗線條的報導,而是始終以個體生命的價值和尊嚴為標尺,展開人性的反思、追問、衡量、評說。面對現實,正視歷史,這才是文學的創作的本質。許榮輝的創作正體現了這樣的特質,他始終透過個人的經驗,對社會現象作人性透視,且加以思辨質詢。他不求全,不貪大,但卻為大歷史作個人的旁述與補白。
〈本土地震紀事〉以隱喻的方式指涉現實政治,對八十年代香港社會的惶惑疑慮加以荒誕化表現。故事記述本城八十年代初的一場災難——地震,言說其深遠影響。那最初的沉悶轟響,導致人心惶惶,且成為日後社會發展根本巨變的源頭。本城人因這場地震而出現集體癔症,不少人選擇了棄城,爭相求購「地震屋」,如此等等。隨着時光的推移,本城人頓悟了這場「地震」的後果,「每個本城人心中都有一條可以勾起他無限回憶的街道,一個可以看到美麗海景的碼頭……都消失了」;「這比起一場真正的地震,把一切都摧毀了,更加徹底。」這個作品以曲筆言說現實,不直接對真實的歷史事件作出描繪與評述,反倒在表達上取得更大的自由度和迴旋空間,可以無罣無礙地將話說透,言語似乎也更具穿透力。
在許榮輝的文學作品中,〈心情〉可說是一篇我城人生的隨想錄,以「他」一個正在寫作歷史劇本的人為敍述者,對幾十年滄桑歲月、社會演變,作出片斷式的回顧與反芻,意在拼貼出一幅歷史長卷。故事從「他」隨母親由羅湖到香港第一天寫起,展現駁雜的內容,流露紛繁的意緒,母親、女皇雕像、工廠女工、「黃皮狗」鎮壓示威、拖着大包小包擠火車過關到國內寄包裹、老人凌晨四五點到診所輪街診……種種畫面、場景,如走馬燈般閃現,記憶與思緒紛至沓來,其中百感交雜的「心情」可想而知。作者通過這個作品,傾注出對這個城市的思考與過往歲月的緬懷,「女工們的疲累一直是這都市繁華的象徵」,「我們曾經有過這樣可愛而純樸的日子。都失去了嗎?」而其中最多的寄慨,當是對滄海桑田社會變遷的感喟,「畢竟是大都會,只要人一走了神,就變得一切都陌生了」;「歷史是成年人開的一個大玩笑,已被無數謊言掩蓋,歷史很大程度上是胡謅的,沒有人能找到完全的真相,我們何不在那血迹斑斑的史迹裏,也胡謅出一個娛樂人的故事來?」
〈在阿巴度的日子〉也是一篇有份量的作品,文中由奇風異俗生發聯想,借題發揮,不乏讓人意會的妙喻。故事中的阿細是一位新聞工作者,被派到外國採訪,在異域他鄉的阿巴度體驗到文化的差異,這讓他想到自己的家鄉,自然彼此參照作出對比。他一抵達阿巴度就發現一個現象,不斷有人向他派單張,上面寫着︰雞蛋是好的。他對此當然抱有戒心,並產生疑問,這座都市是否語言偽術很發達,那簡單的一句話是否暗藏了很多細節。阿細是帶着恐懼來到阿巴度的,因為他的家鄉城市愈來愈不堪,「他厭惡家鄉的語言偽術」。他由「雞蛋是好的」,聯想到「教改是好的」。兩句話相互對照形成思辨的張力,發人深思,真乃精妙之筆。
此外,〈鼠〉也同樣是別具意趣之作。故事中的滿大姨是從異域歸來的華僑,由於少小離家到南洋謀生,被異族文化所同化,觀念與行為都與眾不同。她穿「奇裝異服」,哼唱「We are the world」,性格開朗,但她似乎把心留在了異域,忘了帶回來,融入新生活的速度很慢,因而給一個傳統家庭帶來不小的衝擊。最讓「我們家」無法忍受的是,滿大姨居然買回一隻老鼠,當寵物來養。這不僅給妹妹一家帶來恐慌,讓一家人不得安寧,還惹來隣里的側目。作者透過這個故事,表現出一個奇女子堅不可摧的自信,同時也表達出如下思想,「人生為甚麼會有這麼多困境了,有的是有意製造的,有的卻是莫名其妙產生的,雖然都會引起人的痛苦、驚恐,本質上是不是一樣?」「一個人要是真的有追求,即使生命的火花熄滅了,也可以重燃。」
許榮輝就是以這樣的方式講述着他的香港故事。他除了回述個人的經歷,表現弱勢群體的悲涼人生之外,還以隱喻、隨想等方式回望歷史,反思社會的變遷。這些年來人們言說香港當年時,似乎只流於一句空洞口號「獅子山精神」,倒是這些故事的細節肌理成了一種時代圖騰的紋路,而一個個的畫面、場景則成了那一個抽象概念的鮮明注腳。
許氏不是一個太着意於經營故事「橋段」的作家,但他是一個從心出發的寫作人。他從尋常人生出發,憶述、記錄他所經歷過的歲月,從中發現意蘊,且加以反芻。事實上,他還是一個思辨型的作家。
在這批作品中,一直有一個「我」的存在。「我」是這個城市芸芸眾生中的一員,不起眼,但有自己的視角。他注視、觀看、思考、判斷,有疑惑,也有無奈。
也許,這就是許許多多小市民的共同心緒吧?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於南山書房
香港社會變遷的個體旁注
——許榮輝《我的世紀》閱讀報告
蔡益懷
窮困、勞碌、疲憊、迷茫、焦慮……這是這本作品集的關鍵詞。
現實是一個無限多面的錐體,我們所居住的這個城市也不例外,有各種面相,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面貌和風景,作出千差萬別的解說、詮釋。《我的世紀》就是許榮輝從個人的經歷出發,以個人的視角,對香港這個都市的平民生活與時代變遷所作的個體敍述。作者以真實的筆觸,勾勒一幅幅歷史畫面,一如香港社會的「老照片」,展現出自六十年代以降不同時期的社會風貌與歷史嬗變。這部飽含舊時記憶與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