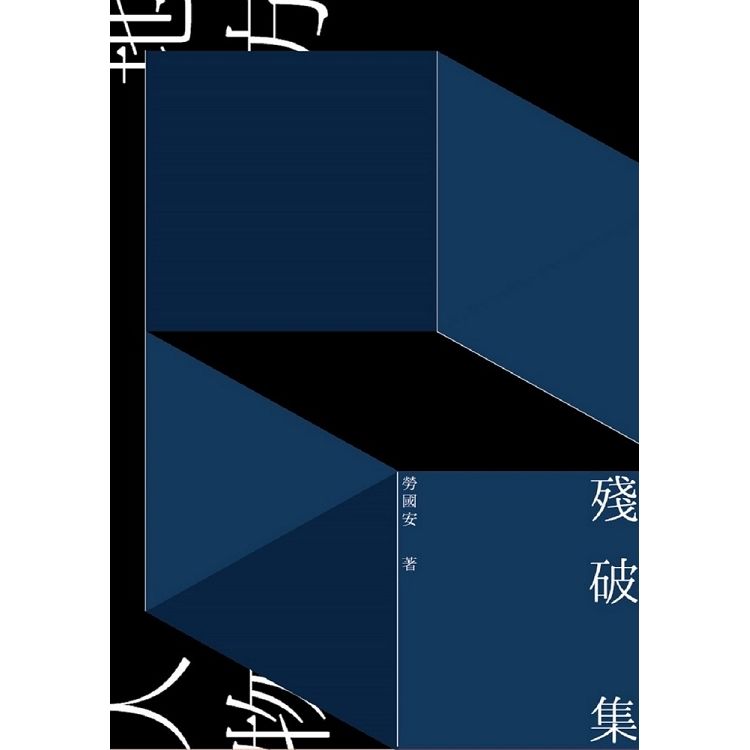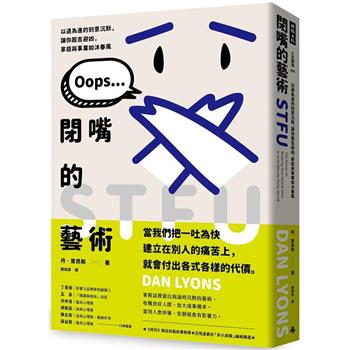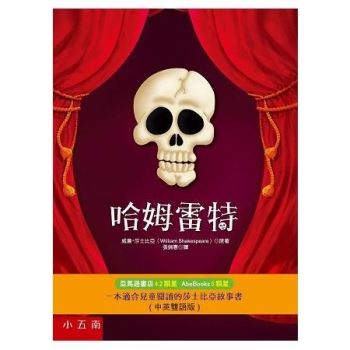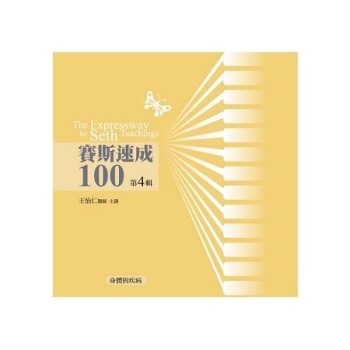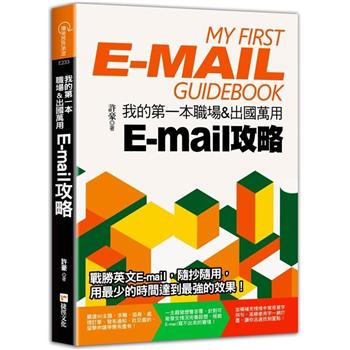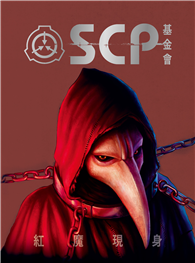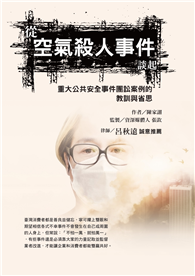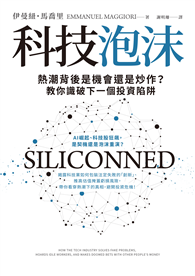蒙太奇的意思,是把事情的過程先選擇性剪成斷片,然後選擇性接合。
事情發生過程的時間和空間,都可以剪成斷片,又都可以接合起來。
蒙太奇享有時間和空間的極大自由,可以忽東忽西,忽今忽古。
而小說的傳統寫法,囿於一時一地一事的情節發展連貫性,不輕易剪成斷片,礙難接受忽東忽西,對待時空的態度偏於僵化。
《殘破集》用蒙太奇一改這種傳統手法,使小說的時空形態變化多端。
林樹勛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殘破集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91 |
小說 |
$ 229 |
現代散文 |
$ 229 |
中文現代文學 |
$ 255 |
中文書 |
$ 261 |
小說 |
$ 261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殘破集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勞國安
自2003年開始積極發表作品,曾發表於《文學世紀》、《香港文學》、《城市文藝》、《字花》、《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小說風》、《80’S Renaissance》、《新少年雙月刊》和《百家文學雜誌》等。
本書收錄自2009年至2017年創作的16篇小說,全部均曾公開發表,更是作者第一本小說集。
勞國安
自2003年開始積極發表作品,曾發表於《文學世紀》、《香港文學》、《城市文藝》、《字花》、《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小說風》、《80’S Renaissance》、《新少年雙月刊》和《百家文學雜誌》等。
本書收錄自2009年至2017年創作的16篇小說,全部均曾公開發表,更是作者第一本小說集。
目錄
序
人物篇
莫先生的審慎魅力
黑暗派對羅密歐與茱麗葉
寫給某科學院的一份報告
對話
沒有星光的晚上
手汗會
理想伴侶
逃
現代教育
老懵懂
像你這樣的一個女子
地方篇
重建前後
黃禍
鬧市中的森林
長者請坐
人物篇
莫先生的審慎魅力
黑暗派對羅密歐與茱麗葉
寫給某科學院的一份報告
對話
沒有星光的晚上
手汗會
理想伴侶
逃
現代教育
老懵懂
像你這樣的一個女子
地方篇
重建前後
黃禍
鬧市中的森林
長者請坐
序
序
二〇〇三年,我的第一篇小說刊於《文學世紀》,之後作品陸續出現在《香港文學月刊》、《城市文藝》、《字花》及《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其中的《小說風》、《80's Renaissance》、《新少年雙月刊》和《百家文學雜誌》因為得不到政府資助或銷量不理想而相繼停刊。雖然投稿的地方愈來愈少,但染上寫小說這「惡習」後便不能自拔,所以縱使刊登率比以前低都惟有一直寫下去。
寫了十多年小說,累積了不少故事,這個夏天終於有空整理舊作,經過一番挑選和修改後終於將作品結集成書。
《殘破集》收錄了我自二〇〇九年至二〇一七年創作的十六篇小說。這些小說展現了我的人生觀,現實往往比想像中殘酷,人生亦充滿缺憾,甚至支離破碎……
二〇一七年九月
推薦序
一本蒙太奇小說
林樹勛
《殘破集》不妨說是一本蒙太奇小說。十幾個短篇中,很多是用電影的蒙太奇手法寫成的。我想單單談一下這本小說的蒙太奇手法。
一 用蒙太奇解除了傳統手法對時空的束縛,創造出小說時空的新氣象
蒙太奇的意思,是把事情的過程先選擇性剪成斷片,然後選擇性接合。事情發生過程的時間和空間,都可以剪成斷片,又都可以接合起來。蒙太奇享有時間和空間的極大自由,可以忽東忽西,忽今忽古。而小說的傳統寫法,囿於一時一地一事的情節發展連貫性,不輕易剪成斷片,礙難接受忽東忽西,對待時空的態度偏於僵化。《殘破集》用蒙太奇一改這種傳統手法,使小說的時空形態變化多端。
〈羅密歐與茱麗葉〉是寫一對青年男女戀愛的短篇小說。這類短篇,用傳統的手法,通常是專注於情節連續性的發展,從頭一寫到尾,兩點一直線,不作他顧,時空較為短窄單調。作者另闢蹊徑,用蒙太奇手法來寫。他把小說的大門打開,向時空開放。把電梯從11樓下降至地面歷程的兩分鐘時間,切割成十五個斷片,通過心理活動的描寫,各個斷片講述不同時間和不同地點的故事內容,分隔接合(即有分隔的接合)起來,成為一個完整的戀愛故事。在小小的方寸電梯空間裏,在短短的電梯下降兩分鐘時間內,收納了兩個青年人戀愛過程的許多日日夜夜,造訪了留下他們羅曼司腳印的許多商場舞廳。小說中的方寸地,小說中的兩分鐘,真可謂非同小可!和以傳統方法寫成的小說比較起來,這篇小說的時空感,顯然豐富得多。
〈寫給某科學院的一份報告〉,則給人以另一種時空感覺。這個短篇,寫父母溺愛兒女的社會現象造成嚴重後遺症,致令兒童普遍缺乏自立能力。故事發生的空間,是一個很大的與世隔絕的實驗倉,時間共一個星期,倉裏住着十個自小被父母溺愛慣了的香港男女少年。他們不會自己煮飯炒菜燒開水;平時網上遊戲成癮,有人因為倉裏不能上網,變成像癮君子一樣涕淚漣洏;號稱資優的學生,竟然連穿鞋時綁鞋繩都不會;有人連輕便的勞動都不願做,怕流汗,怕辛苦,出現王子病公主病;……等等,多不勝數。小說的主旨是要盡可能充份反映那數不盡的後遺症。如果用傳統寫法,把各種各樣的後遺症連續不斷的寫下去,就難免成為沒有盡頭的流水帳,讀起來會喘不過氣。而作者用蒙太奇的手法,化整為零,把整個一星期時間分割成若干個斷片來寫,既分隔又連接。在小說的時間道路上,分隔處是涼亭,連接處是新的一程起點。眼睛在涼亭歇一下腳,然後興致依然,繼續走進被溺愛慣了的港童世界,看那一幅幅發人深省的畫面。化整為零的結果,時間不再是冗長,全程一路青山綠水,不沉悶,零壓逼,輕鬆愉快。
〈對話〉、〈現代教育〉、〈像你這樣的一個女子〉、〈重建前後〉、〈長者請坐〉等篇,也都採用蒙太奇的手法,掙脫了傳統手法的束縛,為作品帶來多姿多彩的時空新氣象。
講蒙太奇突破時空局限性的好處,並非要一概抹殺傳統寫法。一般來說,連續性寫法更有利於營造情節,更有利於塑造人物形象,那是抹殺不了的。
二 用蒙太奇創造形象化的新意思
〈對話〉講一個婚宴上發生的故事。它用蒙太奇手法,把婚宴過程切割成八個斷片。每個斷片紀錄了不同的在場人士的對話。很自然,對話的內容都是關於婚姻的。當中有的夫婦一方埋怨另一方的缺點,有的甚至竟然因此當場吵到要離婚。最後一個斷片,席間的徒弟柏拉圖提出「甚麼是婚姻」的問題請教老師。蘇格拉底叫他先到森林去選一棵最好的樹材帶回來作聖誕樹,然後答覆他。徒弟依照吩咐,到森林裏選了一棵樹材帶了回來。老師問:「這就是最好的嗎?」這時徒弟才發覺樹材原本是有點枯黃的,只好如實答道:「當初我以為是最好的。」老師終於給了他答案:「這就是婚姻。」讀者掩卷一思量,當然不禁拍案叫絕。一個內蘊豐富又深刻的關於婚姻的新意思,剎那出現。這個新意思,以藝術的形象揭示:結婚雙方當初都認定對方是最好的,但後來才發現對方原來都是有缺點的,這就是婚姻。
創造形象化的新意思,是蒙太奇手法的靈魂。有人把這種新意思的出現,比喻為蒙太奇的化學反應效果。像化學反應一樣,從被切割成的一個個斷片中,一下子出現新的生成物。不是甲加乙等於兩者之和,而是甲乙化合生成丙。丙是一種全新的東西。這是蒙太奇手法的神奇效應。我們也可以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理解這種效應。在蒙太奇小說裏,每一斷片都是一個意象。我們每個人的潛意識大世界裏頭,儲存了萬千百年來遠祖的無數經驗意象,也儲存了自我個體的大量經驗意象。蒙太奇斷片意象一進入讀者的意識系統,就能夠把舊有的相關經驗意象激活。激活了的經驗意象,又去激活更多的經驗意象,聯類遞進,生成意思,於是一個新意思誕生。
《殘破集》的多篇蒙太奇小說,大多都有新意思創造出來。〈對話〉之外,還有〈寫給某科學院的一份報告〉、〈現代教育〉等篇,新意思都能一針見血,而且形象豐富。
三 一篇獨特的蒙太奇小說
〈長者請坐〉雖然毛病明顯,但是其蒙太奇手法頗具匠心,頗為獨特。
蒙太奇雖然擁有對時空的無限自由,但是在小說創作的實際運作中,因循者眾,創新者寡,獨特的難得一見。這個短篇居然在小說中創作出一種倒向的時間來。小說講的是瑞寧街一條小巷子的變化歷程。不因循自然時序,也不守舊成規。不是依照起步、興旺、全盛、衰落的原本進程來寫,而是倒過來寫。這種倒向的時間,有動態,有聲音,一步步、一天天,向着從前回頭走,看得見,聽得到。這是寫實的小說,不是甚麼科幻小說。時間是現實的。現實的時間,在小說裏居然回頭走,很是罕見,非常獨特!
更難能可貴的是,這種回頭走的時間形態,為蒙太奇所催生的新意思,帶來了形象化的藝術效果。小說裏的時間,是從「第九十八天」開始回頭走,逐日逐日的走,一直走到從前的「第一天」。小巷子的衰落、全盛、興旺、起步,情景歷歷在目。走到「第一天」,我們終於親眼看見,一個後來叫做陳伯的人正在開始為那條小巷子做第一個開荒牛,做繁榮昌盛的開荒牛。蒙太奇所創作的回頭走時間形態,催生出了一個新意思。這個新意思表明,社會今天的繁榮,同長者在其昨天的貢獻不可分。這個新意思,就活在回頭走的時間形態裏。回頭走的時間形態,體現了這個新意思。新意思形象生動,看得見,聽得到。在這裏,回頭走的時間是形式,新意思是內容。形式與內容,完美結合,相得益彰。
我還想點讚一下題目。〈長者請坐〉,題意實在太豐富了!讀完小說之後,對長者,你怎麼得不尊敬?怎麼能不關懷?怎麼會不讓座?……
二〇〇三年,我的第一篇小說刊於《文學世紀》,之後作品陸續出現在《香港文學月刊》、《城市文藝》、《字花》及《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其中的《小說風》、《80's Renaissance》、《新少年雙月刊》和《百家文學雜誌》因為得不到政府資助或銷量不理想而相繼停刊。雖然投稿的地方愈來愈少,但染上寫小說這「惡習」後便不能自拔,所以縱使刊登率比以前低都惟有一直寫下去。
寫了十多年小說,累積了不少故事,這個夏天終於有空整理舊作,經過一番挑選和修改後終於將作品結集成書。
《殘破集》收錄了我自二〇〇九年至二〇一七年創作的十六篇小說。這些小說展現了我的人生觀,現實往往比想像中殘酷,人生亦充滿缺憾,甚至支離破碎……
二〇一七年九月
推薦序
一本蒙太奇小說
林樹勛
《殘破集》不妨說是一本蒙太奇小說。十幾個短篇中,很多是用電影的蒙太奇手法寫成的。我想單單談一下這本小說的蒙太奇手法。
一 用蒙太奇解除了傳統手法對時空的束縛,創造出小說時空的新氣象
蒙太奇的意思,是把事情的過程先選擇性剪成斷片,然後選擇性接合。事情發生過程的時間和空間,都可以剪成斷片,又都可以接合起來。蒙太奇享有時間和空間的極大自由,可以忽東忽西,忽今忽古。而小說的傳統寫法,囿於一時一地一事的情節發展連貫性,不輕易剪成斷片,礙難接受忽東忽西,對待時空的態度偏於僵化。《殘破集》用蒙太奇一改這種傳統手法,使小說的時空形態變化多端。
〈羅密歐與茱麗葉〉是寫一對青年男女戀愛的短篇小說。這類短篇,用傳統的手法,通常是專注於情節連續性的發展,從頭一寫到尾,兩點一直線,不作他顧,時空較為短窄單調。作者另闢蹊徑,用蒙太奇手法來寫。他把小說的大門打開,向時空開放。把電梯從11樓下降至地面歷程的兩分鐘時間,切割成十五個斷片,通過心理活動的描寫,各個斷片講述不同時間和不同地點的故事內容,分隔接合(即有分隔的接合)起來,成為一個完整的戀愛故事。在小小的方寸電梯空間裏,在短短的電梯下降兩分鐘時間內,收納了兩個青年人戀愛過程的許多日日夜夜,造訪了留下他們羅曼司腳印的許多商場舞廳。小說中的方寸地,小說中的兩分鐘,真可謂非同小可!和以傳統方法寫成的小說比較起來,這篇小說的時空感,顯然豐富得多。
〈寫給某科學院的一份報告〉,則給人以另一種時空感覺。這個短篇,寫父母溺愛兒女的社會現象造成嚴重後遺症,致令兒童普遍缺乏自立能力。故事發生的空間,是一個很大的與世隔絕的實驗倉,時間共一個星期,倉裏住着十個自小被父母溺愛慣了的香港男女少年。他們不會自己煮飯炒菜燒開水;平時網上遊戲成癮,有人因為倉裏不能上網,變成像癮君子一樣涕淚漣洏;號稱資優的學生,竟然連穿鞋時綁鞋繩都不會;有人連輕便的勞動都不願做,怕流汗,怕辛苦,出現王子病公主病;……等等,多不勝數。小說的主旨是要盡可能充份反映那數不盡的後遺症。如果用傳統寫法,把各種各樣的後遺症連續不斷的寫下去,就難免成為沒有盡頭的流水帳,讀起來會喘不過氣。而作者用蒙太奇的手法,化整為零,把整個一星期時間分割成若干個斷片來寫,既分隔又連接。在小說的時間道路上,分隔處是涼亭,連接處是新的一程起點。眼睛在涼亭歇一下腳,然後興致依然,繼續走進被溺愛慣了的港童世界,看那一幅幅發人深省的畫面。化整為零的結果,時間不再是冗長,全程一路青山綠水,不沉悶,零壓逼,輕鬆愉快。
〈對話〉、〈現代教育〉、〈像你這樣的一個女子〉、〈重建前後〉、〈長者請坐〉等篇,也都採用蒙太奇的手法,掙脫了傳統手法的束縛,為作品帶來多姿多彩的時空新氣象。
講蒙太奇突破時空局限性的好處,並非要一概抹殺傳統寫法。一般來說,連續性寫法更有利於營造情節,更有利於塑造人物形象,那是抹殺不了的。
二 用蒙太奇創造形象化的新意思
〈對話〉講一個婚宴上發生的故事。它用蒙太奇手法,把婚宴過程切割成八個斷片。每個斷片紀錄了不同的在場人士的對話。很自然,對話的內容都是關於婚姻的。當中有的夫婦一方埋怨另一方的缺點,有的甚至竟然因此當場吵到要離婚。最後一個斷片,席間的徒弟柏拉圖提出「甚麼是婚姻」的問題請教老師。蘇格拉底叫他先到森林去選一棵最好的樹材帶回來作聖誕樹,然後答覆他。徒弟依照吩咐,到森林裏選了一棵樹材帶了回來。老師問:「這就是最好的嗎?」這時徒弟才發覺樹材原本是有點枯黃的,只好如實答道:「當初我以為是最好的。」老師終於給了他答案:「這就是婚姻。」讀者掩卷一思量,當然不禁拍案叫絕。一個內蘊豐富又深刻的關於婚姻的新意思,剎那出現。這個新意思,以藝術的形象揭示:結婚雙方當初都認定對方是最好的,但後來才發現對方原來都是有缺點的,這就是婚姻。
創造形象化的新意思,是蒙太奇手法的靈魂。有人把這種新意思的出現,比喻為蒙太奇的化學反應效果。像化學反應一樣,從被切割成的一個個斷片中,一下子出現新的生成物。不是甲加乙等於兩者之和,而是甲乙化合生成丙。丙是一種全新的東西。這是蒙太奇手法的神奇效應。我們也可以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理解這種效應。在蒙太奇小說裏,每一斷片都是一個意象。我們每個人的潛意識大世界裏頭,儲存了萬千百年來遠祖的無數經驗意象,也儲存了自我個體的大量經驗意象。蒙太奇斷片意象一進入讀者的意識系統,就能夠把舊有的相關經驗意象激活。激活了的經驗意象,又去激活更多的經驗意象,聯類遞進,生成意思,於是一個新意思誕生。
《殘破集》的多篇蒙太奇小說,大多都有新意思創造出來。〈對話〉之外,還有〈寫給某科學院的一份報告〉、〈現代教育〉等篇,新意思都能一針見血,而且形象豐富。
三 一篇獨特的蒙太奇小說
〈長者請坐〉雖然毛病明顯,但是其蒙太奇手法頗具匠心,頗為獨特。
蒙太奇雖然擁有對時空的無限自由,但是在小說創作的實際運作中,因循者眾,創新者寡,獨特的難得一見。這個短篇居然在小說中創作出一種倒向的時間來。小說講的是瑞寧街一條小巷子的變化歷程。不因循自然時序,也不守舊成規。不是依照起步、興旺、全盛、衰落的原本進程來寫,而是倒過來寫。這種倒向的時間,有動態,有聲音,一步步、一天天,向着從前回頭走,看得見,聽得到。這是寫實的小說,不是甚麼科幻小說。時間是現實的。現實的時間,在小說裏居然回頭走,很是罕見,非常獨特!
更難能可貴的是,這種回頭走的時間形態,為蒙太奇所催生的新意思,帶來了形象化的藝術效果。小說裏的時間,是從「第九十八天」開始回頭走,逐日逐日的走,一直走到從前的「第一天」。小巷子的衰落、全盛、興旺、起步,情景歷歷在目。走到「第一天」,我們終於親眼看見,一個後來叫做陳伯的人正在開始為那條小巷子做第一個開荒牛,做繁榮昌盛的開荒牛。蒙太奇所創作的回頭走時間形態,催生出了一個新意思。這個新意思表明,社會今天的繁榮,同長者在其昨天的貢獻不可分。這個新意思,就活在回頭走的時間形態裏。回頭走的時間形態,體現了這個新意思。新意思形象生動,看得見,聽得到。在這裏,回頭走的時間是形式,新意思是內容。形式與內容,完美結合,相得益彰。
我還想點讚一下題目。〈長者請坐〉,題意實在太豐富了!讀完小說之後,對長者,你怎麼得不尊敬?怎麼能不關懷?怎麼會不讓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