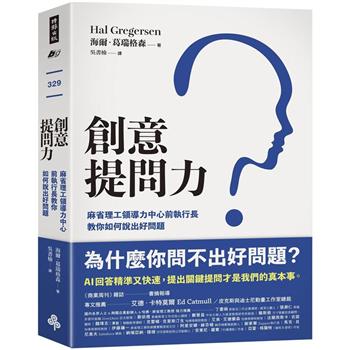今天我們的時代病了,病得變了型、病得支離破碎。以前熟悉的人、事和物全都變得陌生,怒火焚燒全城,城市的人惶恐終日,卻又走投無路。
我們今天的時代病,不過是歷史的循環,不同時代的作家──蕭紅、張愛玲、陳之藩、陳染等,他們都一一受過感染。
蕭紅和張愛玲的時代病,是源自家庭對她們女性身分的傷害,兩者都逃離了家的封鎖,成為了「出走的娜拉」,然而兒童時受傷後留下的痂痕,卻深殖內心,令她們日後的文學創作,充滿悲涼荒蕪的意象和情懷。
陳之藩的「時代病」是源於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中國發生的政權轉移,他對當時的執政者不存寄望,對抗爭者的方向更是擔憂不已,他嘆道:「時局如此荒涼,時代如此落寞;世人如此魯莽,吾道如此艱難。」這一句話中的無盡感嘆,在今天、在城中,似乎對每一個人都適用。
陳染的「時代病」反映了個人主義者面對「社會化」的困局,她是社會中的「差異者」,不希望被成規同化,只好遁入小說中,裝瘋扮癲,以精神病的面罩逃避壓迫。她更認為,和她同病相憐的人彼彼皆是,所以稱這一個病為「世紀末流行病」。
作者簡介:
潘傑
自幼受大舅父薰陶,喜愛文學,成年後從商,擁雙MBA,退任前曾任跨國公司亞太區營運長。近十年重新學習文史,分别在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完成文學碩士課程,現為香港大學博士候選人,研究香港近代史。人生下半塲的希望是,繼續研究香港文學及歷史的有趣課題,發掘這一個偉大城市的風光面貌。
章節試閱
失重練習
手機指模認證失效
畫面一再出現
手機是否被調換
或是我
已經無法被辨認
溫度比想像中冷
在窗的右下角
畫一艘帆船
懸掛了聖地牙哥的夕陽
旅程仍然繼續
高速公路奔馳的聲音
是下一站的揭幕
穿梭十五小時的時差
第一句說的
是晚安
還是早安
聖莫尼卡的天使
離不開這片無盡的海
天使 停在遊樂場的招牌上
收集週末歡樂
海浪一個一個打了褶
笑聲在沙灘擱淺
由很遠的童年沖上岸
從前的家近海
捏到手中的歡樂
遍布整座海灘
站在平交道的交錯點
等候或延遲
上一站與下一站的距離
太多空歡喜的練習
小朋友玩膩了捉迷藏
最後玩了一輩子
你還好嘛?
相隔二十多年
為甚麼我長高了
與金門橋的距離 沒有絲毫拉近
加州的陽光沒有曬進來
風很大
但願把面容 吹得更散
讓剝落的自己 永遠陪在你身邊
叮叮聲剛巧經過
我們站在三藩市的馬路旁邊
調校相機倒數
不知甚麼時候 討厭朱古力太甜
五 四 三 二 到 一
閃光很刺眼
溫度比想像中暖
懸掛了吐露港的早晨
巴士在高速公路奔馳
行李很重
全是香港的濕氣
失重練習
手機指模認證失效
畫面一再出現
手機是否被調換
或是我
已經無法被辨認
溫度比想像中冷
在窗的右下角
畫一艘帆船
懸掛了聖地牙哥的夕陽
旅程仍然繼續
高速公路奔馳的聲音
是下一站的揭幕
穿梭十五小時的時差
第一句說的
是晚安
還是早安
聖莫尼卡的天使
離不開這片無盡的海
天使 停在遊樂場的招牌上
收集週末歡樂
海浪一個一個打了褶
笑聲在沙灘擱淺
由很遠的童年沖上岸
從前的家近海
捏到手中的歡樂
遍布整座海灘
站在平交道的交錯點
等候或延遲
上一站與下一站的距離
太多空歡喜的練習
小朋友玩膩了捉迷藏
最後玩了一輩子...
作者序
〈以失重承受世界的沉重——試讀《失重練習》〉
陳穎怡
文滴請我為詩集作序,我問問完稿日期就答應了,覺得是一段青蔥的緣份。八年前我們的詩作同被收錄一本合集,新書發佈會當天她坐我旁邊,竟穿上款式一樣的鞋子,閑談之下發現購自同一小店,這有趣的巧合叫我記得這個女生。這麼多年,文滴一直是個清新的人,簡單、直爽,與她相處感覺自然。
《失重練習》取同名詩作為題,然而細讀之下,發現它不只是詩人作品選集而已,這些詩作的脈絡的確與「失重」有關,頗為耐人尋味。而我有興趣了解的是,作為詩人的第一本詩集,文滴交出「失重」這帶有距離感的字眼作為命題,概括一段詩意煥發的詩光,預示在抒情之餘,更伴隨情感的反芻。
失重
「失重」是怎樣的狀態?四輯欄目的名字給讀者溫馨提示:「羽破」、「落棉」、「銀絮」也是輕不着地,而「浮石」告訴你,就是石頭在那個時空裏也是懸浮虛置的,《失重練習》一再呈現那個變動不居的世界、難以篤定的心境。
同名詩作〈失重練習〉以日常生活中「失重」情境,兩地時空的切換,表現一種你和我在長途飛行後,甫抵達異地所體驗的錯置感:
溫度比想像中冷
在窗的右下角
畫一艘帆船
懸掛了聖地牙哥的夕陽
旅程仍然繼續
高速公路奔馳的聲音
是下一站的揭幕
穿梭十五小時的時差
第一句說的
是晚安
還是早安
有別一般書寫旅程的切入點,詩人注視抵達的狀態,長途旅程的時差,令旅人並置於出發地與目的地的時空,感覺身處的當下並不確切。「第一句說的/是晚安/還是早安」呼應着首段定調的「或是我/已經無法辨認」一句,不知所屬、隱隱然的悸動與恍惚,才是本質。
及後異國風光與回憶來回跳接:「聖地牙哥」、「聖莫尼卡」、「金門橋」、「加州的陽光」、「三藩市的馬路」——詩中這些旅程的內容被掏空了,餘下地標名字,未有寄託具體情感。詩集中其餘詩作處理異地記憶時,往往戛然而止:「把我壓倒在紐卡素的大樹下/與樹根纏繞」(〈口袋裏沒有我的名字〉)、「有多遼闊/有多像紐卡素/抬頭看見藍白怎樣登對」(〈折翼的魚兒〉)、「就這樣依傍在阿里山的雲海/懸浮於二千尺的掛牽」(〈無添加〉)……只有全集最後三首較為具體抒發旅程見聞所感,可見旅遊勝景,是詩人常用的意象,而旅程卻並非她的母題。風景的跳接,令閱讀起來無法投入特定處境,遊走沒有重心,呼應着詩人希望呈現的狀態。
旅程,只是詩人的練習,一種失重的練習。話說回來,為甚麼一個清新的女生視「失重」為練習?試讀〈失重練習〉詩末:
叮叮聲剛巧經過
我們站在三藩市的馬路旁邊
調校相機倒數
不知甚麼時候 討厭朱古力太甜
五 四 三 二 到 一
閃光很刺眼
溫度比想像中暖
懸掛了吐露港的早晨
巴士在高速公路奔馳
行李很重
全是香港的濕氣
這段寫詩人在街頭與友人拍照留念,並以此幕跳接回到香港的當下。回來時「溫度比想像中暖」呼應了前段剛抵達時「溫度比想像中冷」,無論在哪裏,亦感覺身在異境,自己的預想與現實的表現總有出入,說的是溫度,卻透視一種格格不入的突兀感。失重的旅程尚可帶來片刻快樂的閃念,回來卻是「行李很重/全是香港的濕氣」。「香港的濕氣」指香港帶來的沉重感,「行李」和「濕氣」分別強調這種沉重感如何揮之不去、又如何無處不在。「失重」與「沉重」,在詩人筆下關係密不可分。有時「失重」是一種回應沉重的練習、有時則是沉重造成的反應。
在沉重中失重
愈對世界充滿盼望、理想,愈會為光怪陸離的現實感到沉重。詩人的沉重來自她的家園——香港,跟書寫旅程時快與略相比,寫到香港時總是娓娓道來,慢而具體道出關切與迷惘。其中〈香港.漂白〉最為全面表達城市生活的沉重,亦深刻表現詩人活在其中的掙扎與自救。
鬧鐘在響
全城在說話
夾在火車堆中
電視在說新聞
電話在說是非
粗口在說女生
遊戲機在說過關
我對着麪包說了句早晨
下一站是紅磡
多了一個尖東
我絆倒了
是幾頭紅磚
被裝修工人拆卸
雙眼通紅流下了幾塊顏色
在地上
來到轉角
才驟覺自己走着
忘了最近長出了腿
從前
我懂得飛
坐上這公園的鞦韆
便能長出翅膀
[……]
為甚麼
你樓下的士多變大了
好像改了名字
是Apm嘛?
找不到水泡餅
就撕下這雙手
左手抱着右手
圈成水泡自救
忽然聽到金幣跌下的聲音
走了一步 多了一聲
頭上生出一棵發條樹
每天準時上鏈
每晚準時停步
為何果實沒半點發大
曾灶財褪色了的塗鴉
香港從此漂成白色
像我一樣
抹走過去
已認不出
那回家
那更漂白的路
〈香港.漂白〉
開首以喧囂帶出城市的印象,這種喧囂除了吵鬧,詩中以不同人、物同樣急着說三道四,表現一種巨大的紛擾。聽覺的紛擾尚且能以「對着麪包說了句早晨」刻意看淡,城市巨大而急促的改變,卻難以視而不見。「下一站是紅磡/多了一個尖東/我絆倒了/是幾頭紅磚/被裝修工人拆卸」多一個車站,對一般人而言更便捷,詩人看見的,是迎新背後的棄舊,拆去的紅磚代表舊事物,沒有人會為它們發聲。舊事物的消逝,流下的淚化成人們不能解讀的「幾塊顏色」,悲傷在這個惟發展是尚的社會來得不合時宜。
消逝何以悲傷?「為甚麼/你樓下的士多變大了/好像改了名字/是Apm嘛?」這些舊事物充滿人情味與成長記憶,曾經是我們過去的一部份,如今「變大」、「改了名字」改頭換面成了大型購物廣場,只為容得下消費與交易,不需要記憶、消滅了人情。詩末提及曾灶財的塗鴉,具個性的毛筆大字,一度寫入香港人的社區印象,更被設計師推崇,墨寶更曾在蘇富比拍賣,現實中政府與承建商卻用油漆覆蓋大字——「香港從此漂成白色」連幾個大字也容不下、以制度、官僚主義凌駕個人的社會,難以叫人產生歸屬感「已認不出/那回家/那更漂白的路」。
看着生活的地方漸漸去掉個性與記憶,只有刻板的制度留下來,活着遂變得麻木——「來到轉角/才驟覺自己走着/忘了最近長出了腿」、「頭上生出一棵發條樹/每天準時上鏈/每晚準時停步/為何果實沒半點發大」沉重的現實會吃人,吃掉自我意識。詩集中不少詩作關注的「失重」,歸根究柢是對失去自我的恐懼與掙扎——「鐵路蕩失/我們失去目的地」(〈劃出來的日常〉)、「我推開了僅餘的出口/跑進一座座高樓/乖乖接受電腦激光治療/擊退熱誠與憧憬」(〈亡命之途〉)、「回到那年/我們沒有重組/成為另一個自己」(〈夢.游失語〉)、「遠處吹起沙塵暴/我被捲入重疊時區/劃破了飄盪的汽球」(〈末日殘存者〉)、「差一點/我們與這些棉絮/一起飄到藍色的盡頭」(〈如棉絮飛〉)。
特別的是,儘管「失重」是由「沉重」起,除了〈香港.漂白〉和〈劏出來的日常〉比較具體書寫沉重的處境,其餘詩作中「沉重」不是以曖昧的姿態出現,就是完全缺席,如是有較大的空間演繹「失重」的狀態,彷彿「失重」是詩人尚可自適的舞臺。以兩首詩的「失重」表現為例:
路軌轉彎的時候
剛巧錯過了電車
禮頓道的上空特別寬闊
一群白鴿於美麗中
放任飛翔
口袋裏沒有我的名字
卻找到一趟熟悉的筆跡
藏在發黃的信封裏
似乎遺失了甚麼
無法核實的身份
我是誰的 親愛的
冰冷的面孔在斑馬線交叉跌碰
我站在路中心
黑夜躋身綠色小巴
向我訴說向前衝的輝煌
又翻了翻口袋
朋友的笑臉依舊
卻貼上太多陌生的標點符號
攜着永固的友誼一併吐出
沒有咀嚼也沒有消化
房間的衣服
給我一件又一件的掛起
或許褶痕與你的皺眉太相似
帶點稚氣
〈口袋裏沒有我的名字〉
一個人
浮在牀上
抬頭往上望
手風車仍在想飛嗎?
天空卻把我困住
太陽沒有被按着
手指頭點來了一下光
空氣開始咬到濃濃的味道
黑影長高了
陪伴着這顆光
右面的方格
把風框進來
頭髮亂了
有點像你
[……]
腳板下的
整座廢紙
想摺成紙鶴飛走吧
或是想念着大海……
船
我還依稀記得
是這樣的摺
不過
再不懂游過維多利亞港
現在
我喜歡浮
〈一個人.浮〉
〈口袋裏沒有我的名字〉開首是一幅禮頓道速寫,當中看見美麗「一群白鴿於美麗中/放任飛翔」,也看見錯失「路軌轉彎的時候/剛巧錯過了電車」,不過情景的描述與線索太少,僅帶出氛圍,並沒有要經營畫面的意思。下一段即開展主題,在這樣的氣氛下,詩人憶起往事,似曾相識,「似乎遺失了甚麼/無法核實的身份/我是誰的 親愛的」但回憶也是虛無,過去的關係在當下若即若離。第三段是前兩段的組合,同樣是一幅城市風景的速寫,過渡至與朋友重聚的陌生感。詩人一貫集中呈現「失重感」的作風,言及人際關係的疏離,她不是要反思友誼或情感維繫,焦點仍是那個內在的世界,探問那種存在的突兀感,猶如自己回憶的局外人。
〈一個人.浮〉更是集中呈現孤立而失重的狀態,語調平靜,沒有刻意渲染不安與傷感。詩人在自己的房間展開聯想「手風車仍在想飛嗎?」、「整座廢紙/想摺成紙鶴飛走吧/或是想念着大海……」把擁抱自由與理想的渴望投射到無語的死物之上,說出自己的無能為力;不但理想遙遠「黑影長高了/陪伴着這顆光/右面的方格/把風框進來」甚至有失去主體性之虞,像「黑影」只能「陪伴」、「風」也被房間的空格「框進來」。「失重」的痕跡一個一個加起來,好像很無望,然而詩末告訴你,「不過/再不懂游過維多利亞港/現在/我喜歡浮」,泳渡大海需要力氣,「再不懂游過」指面對香港(「維多利亞港」)目前的現實或沒有逆轉的能力,而「喜歡浮」是作者在這個充滿無力感的世代,保持樂觀、隨遇而安的個人選擇。詩,未嘗不是詩人「浮」的表現,一種「浮」的藝術,使自己不致沉溺。
浮於影像與記憶
詩,如何讓詩人浮於世?〈失重練習〉最後一段,詩人着意描述馬路邊拍攝過程,「五 四 五 二 到 一/ 閃光很刺眼/溫度比想像中暖/懸掛了吐露港的早晨」描述聲音、記錄細節、甚至提及倒數期間的閃念,是全詩最美最有畫面感的時空跳接,明朗之中又有種說不出的惘然,突出了定格當下的意圖。
與「攝影」相關的意象,一再於詩集出現:「聽說攝影是一場減法的美學/一覽無遺的風景/每個轉角的曲線/怎樣將你放大縮小/框在菲林紙上/卻沒法減去你」(《睡前服》)、「攝影只是一場告別儀式/每場黑白交替/我們都在失去/樹根依舊牢牢扣緊/茂盛的樹林/飛散於斧頭之間」(《花密語》)、「菲林沖曬下/地平線要如何承受一幀夕陽/快門按下一剎/是否就能擁有一格的你/笑容帶點粗糙/是感傷的質感」(《薄荷黑夜》) 、「無添加你的氧分/好讓我喪失重量/就這樣依傍在阿里山的雲海/懸浮於二千尺的掛牽/趕上清晨最漆黑的光芒/於遊人快門的一瞬間/成最閃耀的襯托」(〈無添加〉)、「從此定格於懷舊小店/攝成照片/放到梅田的長空/一滑而過的玻璃反射/剩下多少光芒/仍在等候黑夜」(〈梅花色變〉)。攝影可以保存影像,而保存影像也就可以珍藏記憶,對詩人而言,記憶有若生命中美好的光源:
每天發生的事又多又繁複,可是,我們沒可能到電器店裏,選購更多特大容量的記憶卡,去盛載不斷增加的文件夾。最後,我們只好自動刪除某些認為不再重要的片段或回憶。當你某天回想,它已漸漸變得褪色和暗啞……
世界上最奇妙的事情,就這樣發生了。不多於一毫米的厚度,卻能夠將很多無法回到挽回的片段,變成永恆。相片是一份最寶貴的禮物。有些感覺,翻一翻,就這樣儲藏下來。即使發黃了,它讓我肯定,我倆,是確實的存在過。
記得該書的主編讓詩人在不同問題中挑選一道或多道回應,作為簡介,文滴只選了一題——「有沒有想過,自己的腦海裏,究竟存在多少記憶體?」整篇短序也遍佈記憶的痕跡,記憶於她的意義,可以力抗時間的流逝,保存美麗的回憶。如此一來,除了在沉重的現實中存有快樂的憑據,保存對詩人而言,更是帶有美感的藝術,詩中「攝影」除了以意象出現,也可以視為創作的隱喻。
太陽悄悄的
從窗邊凝聚每顆光
塵埃四處浮遊
貓咪瞇起了雙眼
近乎靜止的狀態
像我倆曾經學懂
將櫻花凝固的美學
細看你的睫毛
緊緊黏住了燭臺折射的光芒
從指尖滑過你的鼻樑
發現蘿蔔蛋糕的甜味
只可積聚於最淺薄的一層
轉身躲進耳朵的每段彎路
傾聽南丫島風鈴輕奏的私語
僅化作雨點擱淺在窗邊的一角
手縫間拉扯着迷途的幼沙
流失的步伐
卻流連在維他玻璃樽的瓶口
傾瀉了整年盛憂的夕陽
留來溫暖你的雙手
[……]
〈如 約在花見〉
寫記憶中的場景,先不記流動的人事,沒有時序也排除外界的干擾,感覺空靈,以文字重現影像,實踐一種「凝固的美學」。然後小心翼翼,收集每一個細節,力求還原記憶的全貌,讓人重尋過去。「細看你的睫毛/緊緊黏住了燭臺折射的光芒/從指尖滑過你的鼻樑/發現蘿蔔蛋糕的甜味/只可積聚於最淺薄的一層/轉身躲進耳朵的每段彎路/傾聽南丫島風鈴輕奏的私語」從空闊的畫面,聚焦至戀人的臉,進一步凝視,凝視所表露的愛慕更從視覺擴及嗅、聽、觸覺,細膩描寫戀人之間的眷戀與依偎。詩集中第三、四輯的作品,有不少情詩,直接以「你」為書寫對象,而詩人的愛情,在「失重」的旋律下,有種「相忘於江湖」的味道,大概愛情的小溫馨,可以令人暫時脫身於不太可愛的現實吧。這點因篇幅所限,留待讀者細細品味。
從前在《秋螢》、《聲韻詩刊》讀到文滴的詩,只讀出清新的愛情小品,如今讀畢《失重練習》,發現那不只是一部青春紀事,詩作之間若隱若現一個更宏觀的脈絡:旅程的掠影、成長的碰撞、愛情的嚮往、理想的追逐……背後都有一座城市的身影。在城市急促轉變下,詩人反覆叩問自身的存在感,深刻的表現這一代青年人的掙扎,留下時代的寫照。
〈以失重承受世界的沉重——試讀《失重練習》〉
陳穎怡
文滴請我為詩集作序,我問問完稿日期就答應了,覺得是一段青蔥的緣份。八年前我們的詩作同被收錄一本合集,新書發佈會當天她坐我旁邊,竟穿上款式一樣的鞋子,閑談之下發現購自同一小店,這有趣的巧合叫我記得這個女生。這麼多年,文滴一直是個清新的人,簡單、直爽,與她相處感覺自然。
《失重練習》取同名詩作為題,然而細讀之下,發現它不只是詩人作品選集而已,這些詩作的脈絡的確與「失重」有關,頗為耐人尋味。而我有興趣了解的是,作為詩人的第一本詩集,文滴交出「失重」...
目錄
目錄
輯一:羽破
失重練習
劏出來的日常
一個人‧浮
亡命之途
口袋裏沒有我的名字
香港.漂白
夢.游失語
旋渦的音調
輯二:落棉
末日殘存者
沉睡的顏色
折翼的魚兒
粉紅雨點
趁時間還在午睡
睡前服
輯三:銀絮
好時辰
崩裂的圖案
如果你可以不這麼甜
如果我們還有時間
如 約在花見
如棉絮飛
快.樂
掛念是這樣的氣息
無添加
輯四:浮石
花密語
花瓶
春之告白
梅花色變
薄荷黑夜
靈感外帶
目錄
輯一:羽破
失重練習
劏出來的日常
一個人‧浮
亡命之途
口袋裏沒有我的名字
香港.漂白
夢.游失語
旋渦的音調
輯二:落棉
末日殘存者
沉睡的顏色
折翼的魚兒
粉紅雨點
趁時間還在午睡
睡前服
輯三:銀絮
好時辰
崩裂的圖案
如果你可以不這麼甜
如果我們還有時間
如 約在花見
如棉絮飛
快.樂
掛念是這樣的氣息
無添加
輯四:浮石
花密語
花瓶
春之告白
梅花色變
薄荷黑夜
靈感外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