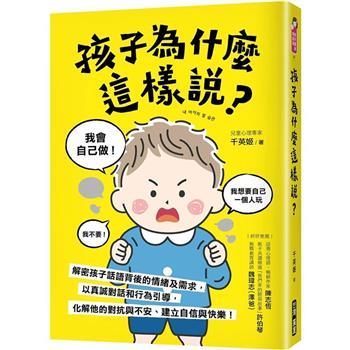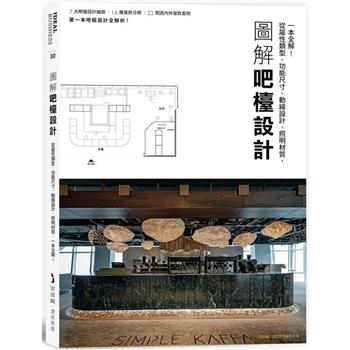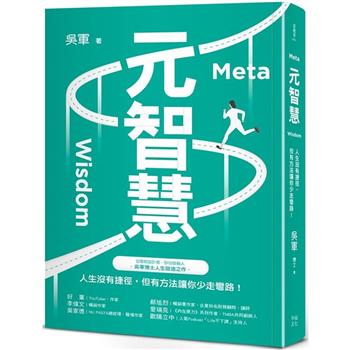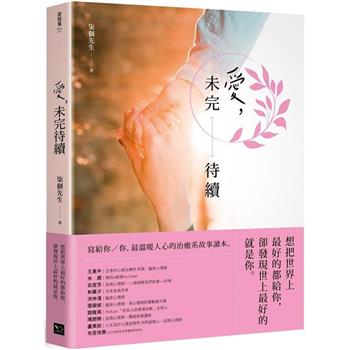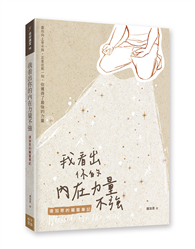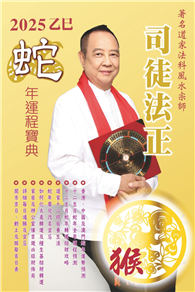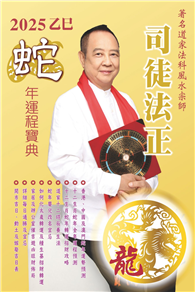長廊的短調
總有一次,一天裏總有一次他聽見長廊上響起一連串高跟鞋的腳步聲,聲音裏出現一個女人苗條的背影,慢慢走過長廊,一步響起一聲,一聲聲遠去,腳步變得低沉,背影變得縮小,暗淡,而隱没。他知道她走進了長廊盡頭右邊的寫字樓。他想她一定在那裏工作,不知是速記還是打字員,但他肯定不會是低薪職員,因為她看來不似。她決不會像他一個入息百餘元的小職員。假如像他,一個月的勞動只能換來身上一件大樓,不要說生活上其他開支了。而她每天穿上的旗袍都不同,相同的只是旗袍下面露出的雙腿,一雙尼龍絲襪緊緊包裹著的總是那麼小巧但均勻,所以腳步又是那麼小巧但均匀,聽起來像一種配合節拍的音樂,他愛聽。
音樂現在是奏完了,儘管没有指揮棒在空氣中一劃而放下,然後白髮的音樂家向臺下一鞠躬,身子站起,帶起了熱烈的掌聲。但他確實知道今天的音樂是完結了,只有等待明天同樣的時刻,當牆上的鐘擺擺動了十響。這是一個舊鐘,一個不宜於放置在現代化寫字樓牆上的舊鐘。老闆保存它,卻有他的理由。他說:舊鐘是他戰前父親買下的,寫字樓開幕那天就有它,永遠就要有它,因為它一息尚存也不放棄工作,正象徵這間公司服務的宗旨與精神。
老闆說甚麼也有理,為了他是老闆。他說:如果你不是我的鄉親,我早就掃把你,你在這裏一無是處。這點他也很難否認。他是一個身體短小瘦弱的人,粗重的工作不能做。他也不識英文,不能叫他寫一封信,甚至叫他照樣打一封也不行,即使叫他去派,也一樣派錯。
我真是無用,他自己也不否認,搖搖頭,牆上的鐘擺,以及頭頂電風扇的旋轉,轉得很慢,很清楚印下四條轉動的影子,吹下的風不涼,涼風卻是不需要的,今天是熱天,但仍舊是冬日,只是這裏地方大窗子小,光線和空氣都不足夠,而又没有安裝冷氣機,相信這一座十三層大廈一百多間寫字樓只有這裏没有冷氣。老闆真孤寒!
老闆習慣在十點半鐘回來。他看鐘,看門邊出現的身影知道準是老闆。他是寫字樓唯一表示歡迎老闆的僱員,他向他鞠躬,短小的身材顯得更短小,不只老闆懒得看他一眼,連簡單的一聲早晨也不回應,只顧啣著一根四寸長的雪茄經過女秘書小桌上的打字機走進他自己的辦公室。然後女秘書戴上足二百度的近視眼鏡,拿著一本册子跟著他走進去,很久才走出來。有時一面推開門一面在吃吃笑。他想:誰知道他們在裏面幹甚麼?外面呢,每個人知道老闆回來了,就裝成忙碌的樣子,使他也忙碌起來。
以致他走開了坐著向著門外長廊的位置,不知她何時下班,以及怎樣走過長廊。有一次他看見一個短小肥胖的男人跟她在一起,看來他是她的老闆也長得像他的老闆,但她仍舊裝著高視闊步,似乎看不起他似的一直走過,另一次他看見一個年青白臉的男人陪她一起,男人裝著一副殷勤,她每走一步也作勢要扶她,無奈她仍舊是老樣子,不管你是年輕還是年長,上司還是下屬,她同樣懶得管。向天空微仰的鼻子是高傲的,他只看見一次,在他故意提早下班那天,偶然跟她一起擠進了電梯,站在她旁邊。他矮小的身材要抬起頭才看進她的鼻孔,自己的鼻孔卻嗅到她身上髮上的芬芳,叫他想起世界上各大都市
之夜。
香港之夜早來,六點鐘天就開始暗下了,兩座大廈之間拖長了一條鉛灰色,當中没有一朵白天裏輕巧的雲塊,也没有一顆比夜更早來的星。他在狹長天空下走過。一天的工作完結了,搬動椅子,收拾桌子,掃地,熄燈,鎖門這一切都遺留在身後。他從大廈横門走入長巷而轉出了電車路。電車裏面有燈光了,車站的月臺也閃著一盞紅燈,像一顆星。電車在星前停下,不算太擠,他不難鑽進了三等。没有空位,他只有站著,在兩個站著的乘客之間。窗外的窗櫥在眼前向後走過,隨著車輪在軌道上轉動以及叮叮響起的叮嚀。一個女人站在窗櫥前面看裏面的春裝,他覺得背影很熟識,於是想起她。
她現在已經回到家?還不像他正在回家?或是像他剛下了車,胡思亂想地走出電車站,看不見一輛汽車駛過來,幾乎碰倒了他,吃一驚一步跳進了騎樓底,走過一間一間四層樓屋子的騎樓底,直到一個熟識的門口前面才停下。走上木樓梯,很黑,梯級狹窄而傾斜,陌生人走著很容易跌倒,他記得第一次走上就幾乎滑下,幸而連忙一手握住一條朽壞的扶手。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他老去,屋子也老去,應該把它拆下而改建另一座高大的新樓,像附近别的舊樓一樣。但他忽然又想到:假如有一天真的拆下,他搬到甚麼地方去呢?他每月付三十元租金的牀位相信在任何新樓也租不到,那麼,還是不拆好了。他滿足於屬於他的牀位。
因為雖然佔有的空間狹小,只容他一個人躺直身子,就是一張棉被也載不起,他一翻身被子就掉到地面去了,地面没有人掃,被子拖得很骯髒,又有甚麼辦法呢?誰叫你請不起工人,自己同時懶惰,一離開寫字樓就甚麼也不想工作。但牀位總是他的,他有時躺下或坐著,像現在坐著脱下永不擦一次的黑皮鞋。而且,牀位空氣充足,有兩扇窗,一在前一在後。
後面的窗打開,這邊的窗永遠開著,那邊的窗永遠關著。那是浴室,不止一次他看見玻璃窗前印下一個女人赤裸的身影,不知是燈光影響還是本來就是如此:身影並不美,不是太胖就是太瘦,腰圍與胸圍的比例絕不恰當,使他無法由影子而聯想到白天長廊上響起的背影。但他喜歡看,有時就為了等待一個影子的出現而躺在牀上倒著身子睜著眼睛,一夜不睡。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長廊的短調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91 |
中文書 |
$ 191 |
小說 |
$ 247 |
文史哲 |
$ 261 |
現代小說 |
$ 261 |
小說 |
$ 261 |
文學作品 |
$ 261 |
中文現代文學 |
$ 261 |
Literature & Fiction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長廊的短調
梓人是香港一名少人提及的傑出小說作家,尤其精於短篇。他是和崑南、盧因、蔡炎培等,都是從一九五〇年代成長的文藝青年。他的作品散見刊於《中學生》、《文藝季》、《文壇》、《文藝沙龍》、《好望角》等文藝刊物。而發表在《好望角》第二期的《長廊的短調》後來更多次入選各香港小說選集,儼然其著名的作品。是次整理出版的作品,除了有早期的作品,更有投稿海外刊物《蕉風》的小說,以及後來寫於《文壇》、《香港文學》的篇章,讓讀者一次過見證作者各個創作階段的風格轉變。
作者簡介:
梓人
原名錢梓祥,祖籍廣東三水,一九三六年在香港出生。聖約瑟中學畢業,聯合書院外文系肄業。
五十年代開始寫作,發表在《星島日報,學生園地》、《中國學生周報》、《人人文學》、《海淵》、《大學生話》、《蕉風》、《好望角》,後來尤其在《文壇》上發表了不少短篇。
短篇小說在六十年代結集為《四個夏天》及《離情》兩書。其著名短篇〈長廊的短調〉更多次入選各香港小說選集。
章節試閱
長廊的短調
總有一次,一天裏總有一次他聽見長廊上響起一連串高跟鞋的腳步聲,聲音裏出現一個女人苗條的背影,慢慢走過長廊,一步響起一聲,一聲聲遠去,腳步變得低沉,背影變得縮小,暗淡,而隱没。他知道她走進了長廊盡頭右邊的寫字樓。他想她一定在那裏工作,不知是速記還是打字員,但他肯定不會是低薪職員,因為她看來不似。她決不會像他一個入息百餘元的小職員。假如像他,一個月的勞動只能換來身上一件大樓,不要說生活上其他開支了。而她每天穿上的旗袍都不同,相同的只是旗袍下面露出的雙腿,一雙尼龍絲襪緊緊包裹著的總是那麼小巧但...
總有一次,一天裏總有一次他聽見長廊上響起一連串高跟鞋的腳步聲,聲音裏出現一個女人苗條的背影,慢慢走過長廊,一步響起一聲,一聲聲遠去,腳步變得低沉,背影變得縮小,暗淡,而隱没。他知道她走進了長廊盡頭右邊的寫字樓。他想她一定在那裏工作,不知是速記還是打字員,但他肯定不會是低薪職員,因為她看來不似。她決不會像他一個入息百餘元的小職員。假如像他,一個月的勞動只能換來身上一件大樓,不要說生活上其他開支了。而她每天穿上的旗袍都不同,相同的只是旗袍下面露出的雙腿,一雙尼龍絲襪緊緊包裹著的總是那麼小巧但...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從短篇〈一天〉和〈長廊的短調〉——
看梓人早期作品的文字魅力和詩意風格
馮偉才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與文友編選的《香港短篇小說選(五十至六十年代)》,其中一篇是梓人的〈長廊的短調〉,如今已成為六十年代香港短篇小說的代表作之一。當年沒考慮加入作者介紹,所以對梓人的背景沒有深究,也沒有向他同年代的人打聽。後來,研究香港文學的人多了,對梓人比較詳細的資料也陸續出現,才對他了解多一點。簡單的說,他在五、六十年代時是文藝青年,多投搞於美援刊物《中國學生周報》,《海瀾》等。後來在律師樓工作,就寫得比較少了。(...
看梓人早期作品的文字魅力和詩意風格
馮偉才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與文友編選的《香港短篇小說選(五十至六十年代)》,其中一篇是梓人的〈長廊的短調〉,如今已成為六十年代香港短篇小說的代表作之一。當年沒考慮加入作者介紹,所以對梓人的背景沒有深究,也沒有向他同年代的人打聽。後來,研究香港文學的人多了,對梓人比較詳細的資料也陸續出現,才對他了解多一點。簡單的說,他在五、六十年代時是文藝青年,多投搞於美援刊物《中國學生周報》,《海瀾》等。後來在律師樓工作,就寫得比較少了。(...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目錄
寂寞的秋日
一間屋子的故事
一天
神父口中的故事
遺書
阿紅的命運
小寶寶出生前後
歧路
長廊的短調
醉時醒後
野馬
砰
寂寞的秋日
一間屋子的故事
一天
神父口中的故事
遺書
阿紅的命運
小寶寶出生前後
歧路
長廊的短調
醉時醒後
野馬
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