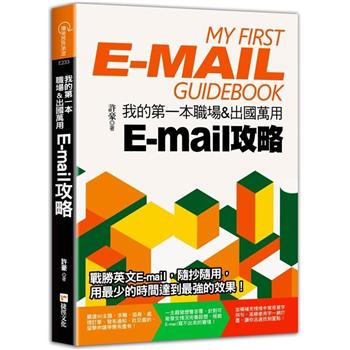這幾年,大概一月一篇在報紙寫文章,戰戰兢兢,唯恐有失。副刊的文藝版面已經那麼稀罕,寫不好就更浪費僅有的空間。
常常覺得香港臥虎藏龍,只是高人大概不願給報紙的方寸所囿,也不輕易隨便出手。但報紙副刊既未完全式微,還是需要有人來寫的。一個城市能有幾份好的副刊,有助維持其人文氣息,引發思考與討論。最初便想,若能填補空檔,在這位置出力,總算沒白費所學。
我慶幸一早發現自己不是個才華洋溢的人,比較適合寫評論。這絕無貶低評論的意思,但可以有所依傍地說自己的話,猶如有中生有,感覺份外安穩。平日興趣既然是讀書和看電影,能為文學和電影寫文章,簡直是福份。
這令我想到「眼光」一詞。跟常識相反,與折射無關,眼才是光的來源,烱烱如電筒一般,在漆黑之中,照遍視線所及之物,逐一將之變得明白起來。厲害的人都有這種眼光,或因其性情,或以其學問,更可能是因為情理兼備,照見人所不能見。如果他是作家,便能寫出好的書;如果他是導演,就會拍出精彩的電影。但具備這種眼光和洞見的人,畢竟只屬少數。自己沒眼光也不要緊,評論和引介,有時就像拍拍正在夜深趕路的人,然後把手向上一指,提示他們頭上的一片天空,原來點點發亮。若能如此,最少沒把書和電影白看,只是眼光光。
寫了幾年,發現學識只限我每月寫一至兩篇,要急也急不來,便繼續慢慢看,慢慢寫。這就連到書題《積風集》了。是二○○五年得悉可升讀研究院的那個晚上。下午收到取錄通知,因為有人退出,多了個空位,才有頂替的機會。一方面當然欣慰,前路的悵惘暫時告一段落,不用再等待獎學金的消息了,也不用上網找工作謀後路了。但很奇怪,另一方面又有種說不出的鬱悶。總覺得僥倖得逞,好像騙了誰似的,心裡一直不舒服。
只記得那晚回家後看電視直至深宵,雖然我討厭看電視。三時許吧,家人都睡了,便拿著電話靜靜走出家門,打電話給我最敬重的老師佘汝豐先生,他通常清早才睡。家住井字形屋邨,撥了號碼,便憑欄對著天井,用另一邊的耳朵聽著零星的鐵柵開閤,都沒留神是有人夜歸,還是大風吹過搖醒鐵柵。電話接通,勉力壓抑聲線的顫震,跟老師說了情況。他回答的聲音低沉得很,字字入心: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讀書是一生一世的。」
已忘了那次通話如何收結。但從此,莊子這句話於我就特別深刻。那明明是荀子的真積力久則入,孟子的盈科後進,負翼要積風。弔詭的是,天地之間,風偏偏最不願暫留,一去無蹤。這也真如學習,總不知多少留下,多少流走;不肯定在面前吹過的風,最後會遺下幾多痕跡。
這書可算是積風的寫照。第一和二部是書話,分為「這裏的書」和「那裏的書」。第三部「發光的電影」,寫的多是不止在螢幕發光,更在心中發光的電影。書中文章有幾篇寫在《信報》和《字花》,其餘全都寫在《明報》〈星期日生活〉。我感謝曾經合作的所有編輯,尤其是〈星期日生活〉的主編黎佩芬小姐,至今素未謀面,卻一直對我充滿信任,容許我在這求快求新的社會氣氛底下,寫了那麼多舊戲舊書。
去年三月,樊善標老師問我有否出書之意,那時回答說,自覺寫得還未夠好,多寫一年再算。碰巧今年三月,有天午膳後回校,收到校務處同事通知,剛才有出版社打電話找我。本以為是銷售課本的宣傳,後來才知道是花千樹的編輯小姐,說因在網上找不到我的聯絡,才打電話到學校來。希望這書沒辜負原來的期望。重讀舊文,選出比較滿意的五十篇,略加增塗修訂,主要是刪去廢話,補寫和重寫未足之處。
感謝曾為這書落力的人,包括為我在封面題字的萬偉良老師、畫封面的區華欣、校對的陳以璇,以及編輯葉海旋先生和羅海珊小姐。感激我的親人、朋友和師長。積風的過程,少不免有心急或沮喪的時候,我慶幸遇過那麼多好老師,有時拍拍我的膊頭,叫我要抬頭看得更高更遠;有時如星,教我近距離見識那耀眼的光芒。是為序。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積風集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積風集
榮獲2015年第十三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
「風之積也不厚,其負大翼也無力。」幾年來讀書看戲,總離不開莊子這句話。
本書為作者郭梓祺的專欄結集。第一和二部為書話,分為「這裏的書」和「那裏的書」。第三部「發光的電影」,寫的多是不止在螢幕發光,更在心中發光的電影。書中文章有幾篇寫在《信報》和《字花》,其餘全都寫在《明報》〈星期日生活〉。
作者簡介:
郭梓祺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文學士、英文系哲學碩士,現為中學教師。
TOP
作者序
這幾年,大概一月一篇在報紙寫文章,戰戰兢兢,唯恐有失。副刊的文藝版面已經那麼稀罕,寫不好就更浪費僅有的空間。
常常覺得香港臥虎藏龍,只是高人大概不願給報紙的方寸所囿,也不輕易隨便出手。但報紙副刊既未完全式微,還是需要有人來寫的。一個城市能有幾份好的副刊,有助維持其人文氣息,引發思考與討論。最初便想,若能填補空檔,在這位置出力,總算沒白費所學。
我慶幸一早發現自己不是個才華洋溢的人,比較適合寫評論。這絕無貶低評論的意思,但可以有所依傍地說自己的話,猶如有中生有,感覺份外安穩。平日興趣既然是讀書和看...
常常覺得香港臥虎藏龍,只是高人大概不願給報紙的方寸所囿,也不輕易隨便出手。但報紙副刊既未完全式微,還是需要有人來寫的。一個城市能有幾份好的副刊,有助維持其人文氣息,引發思考與討論。最初便想,若能填補空檔,在這位置出力,總算沒白費所學。
我慶幸一早發現自己不是個才華洋溢的人,比較適合寫評論。這絕無貶低評論的意思,但可以有所依傍地說自己的話,猶如有中生有,感覺份外安穩。平日興趣既然是讀書和看...
»看全部
TOP
目錄
自序 i
一.這裏的書
劉教授的為己之學
趙廣超的詩意
假作真時真亦假
鳥兒輕輕在歌唱
今之視昔
重投朱注
詩人的信
紀念陳之藩先生
酒神的反襯
《蘇東坡傳》的兩個中譯
驚睡覺,笑呵呵,林語堂與蘇東坡
雞鳴不已
稱職的狐狸
陳義略高也無妨
人和書的蹇途
老人與樹
二.那裏的書
苦難與神話
從沙林傑到訃文
如果人不用吃飯
《一九八四》以外
廣島白描
不太難的喬哀斯,更容易的普魯斯特
信與不信的尺牘往還
卡夫卡的地鼠
聽,莎士比亞在說話
遷就福克納
你也不可以是宮本武藏
斑...
一.這裏的書
劉教授的為己之學
趙廣超的詩意
假作真時真亦假
鳥兒輕輕在歌唱
今之視昔
重投朱注
詩人的信
紀念陳之藩先生
酒神的反襯
《蘇東坡傳》的兩個中譯
驚睡覺,笑呵呵,林語堂與蘇東坡
雞鳴不已
稱職的狐狸
陳義略高也無妨
人和書的蹇途
老人與樹
二.那裏的書
苦難與神話
從沙林傑到訃文
如果人不用吃飯
《一九八四》以外
廣島白描
不太難的喬哀斯,更容易的普魯斯特
信與不信的尺牘往還
卡夫卡的地鼠
聽,莎士比亞在說話
遷就福克納
你也不可以是宮本武藏
斑...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郭梓祺
- 出版社: 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6-25 ISBN/ISSN:9789888042876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56頁 開數:寬15 X高21(公分)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