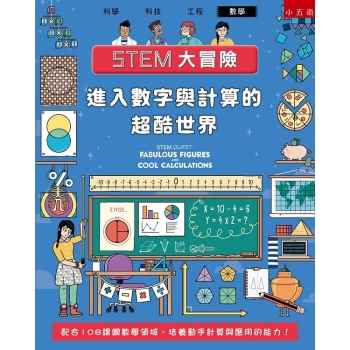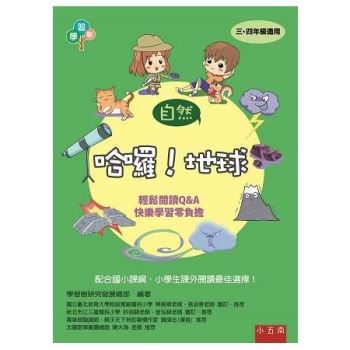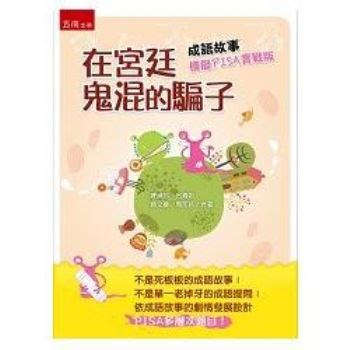兩個悲劇
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名氣很大,戲劇電影不斷為之宣傳。他有一個名叫授的五世孫,他的故事,比之乃祖奇詭得多,但是一點名氣也沒有。
這位授王有一個王弟,名叫豫,很想繼哥哥做越王,可是授王有四個兒子,等着接位,輪不到他。於是用傳統的老法子,向哥哥進讒,説四個侄兒的壞話,不外有的不成材,有的有謀皇篡位的企圖等等,授王聽信了,四個兒子,殺了三個,第四個不殺了,即使壞話説盡,也置之不理,好歹要留着他接位做越王。
把自己的兒子殺光,中外的昏君、暴君,大概百中揀不出一個會如此。
然而第四個終覺岌岌可危,不如先下手為強,奮然起兵圍王宮,把父親殺了,授王臨終時大徹大悟,嘆曰:「悔不聽豫弟之言!」
雨果説過:最兇殘的野獸,也愛護它的子女。人一做了國王之類,這個原理竟不適用,連最兇殘的野獸都不如。不過這是特例,一般還是有舐犢之情的。即如這位授王,第四個兒子還是不肯殺,加以愛護了,終於死在他手裏。
令人戰慄的是他的大徹大悟之言。意即悔不曾把第四個兒子也殺了。倘真如此,那麼就殺得乾乾淨淨。真能這樣嗎?不免懷疑。這樣的悲劇,比之《哈姆雷特》還要悲劇些。父子之情,原是高尚的感情,為了維護權力,在讒言煽動之下,不得不殺三個兒子,留下一個,雖然沒有殺,但有一句話,仍有欲得之而甘心的強烈意願。
悲劇的精神是在乎把有價值的東西活活地撕成粉碎給人看,父子之情是有崇高價值的,這裏終算粉碎得徹底了。連殺三個還不足悲,留下第四個,像在黑暗中現出了一絲閃光,似乎可以沖淡悲劇氣氛了,可以挽救這高尚感情,不致徹底粉碎。孰知不然!波濤又起,兒子反過來殺父親,這一反覆,自屬合情合理,因為父親已殺了三個兒子,有甚麼理由不會殺第四個?於是反擊,結果是使得最後剩餘的一點父子情也蕩然無存,尤其是遺言後悔沒有殺光,悲劇達到飽和的地步,毀滅得無可收拾。
另一個要輪到晉武帝司馬炎,篡魏立晉在他手裏完成,是事實上的開國之君。他有二十六個兒子,大多兩三歲即夭折,只留第二個兒子晉惠帝,偏偏是個半白癡,明知他做君主不能勝任,但是仍舊要傳位給他。(突出的故事是:「何不食肉糜?」在一定標準下不少太子是半白癡,不置論。)這一代不行,或者生個孫子成材吧?可是所娶的賈妃又不生育,任她去偷漢也無用,而且悍妒異常。那麼妾侍可以生育一個吧?但有孕的妾侍,又被賈妃擲戟刺腹而死。司馬炎用盡心機,在這件事上掙扎了很久,把自己的愛妾賜給兒子,終算生了一個孫子,有點頭角,便立為皇孫。司馬炎死時,皇孫還小,而半白癡必須即位做皇帝,眼看這個新立的司馬氏天下:大亂將起,然而這時要嚥最後一口氣了。
司馬炎無疑有愛子之情,可悲的是,他之所愛,是落空的,一個半白癡,比劉阿斗還差得遠,但又不得不愛他,把那種有價值的東西活生生地、無可奈何地自甘沉入明知絕路的深潭裏,同樣也是粉碎了。
自稱奉天承運的九五之尊,這個寶座多麼莊嚴,最愚蠢的皇帝,也不會自毀莊嚴,儘管是一個空架子,但是一個半白癡坐了上去,這個寶座還有甚麼莊嚴?晉室朝廷,還成甚麼樣子?司馬炎是早已預見到的,苦在心裏。寶座即使是虚偽,也還有它至高無上的現實價值,是唯我獨尊的至善至美的東西,在司馬炎以至整個統治階級眼裏當如此,然而坐上來的竟是個半白癡,豈非代表了惡?卻又不能不接受。在美、善與惡的矛盾中,美、善已為惡所屈服。一日,司馬炎在凌雲台宴羣臣,有個大臣,借着酒醉走到司馬炎身前,想説幾句話,臨時又説不出了,攀着司馬炎的御座説:「可惜啊!這個寶座!」即是反映了這個想法。司馬炎似有所覺,但只得説:「呀!你真醉了嗎?」在無可奈何中,各有悲哀。
天下是司馬氏的,寶座不傳給這個半白癡,難道傳給異姓嗎?悲劇的根源在這裏。正如越王授的悲劇一樣,那隻寶座一定要傳給兒子,留下一個不殺,反遭了毒手。司馬炎眼睜睜地讓半白癡去坐江山。越王授臨死,悔恨無已;司馬炎臨死,則陷入無可奈何的悲哀中。套一句《哈姆雷特》的劇詞,越王授會説:「殺還是不殺,這是一個問題。」司馬炎會説:「傳還是不傳,這是一個問題。」他們糾結在這樣的矛盾中。
這一類悲劇,歷史上不少。不過這兩齣是很突出的,關鍵全在於封建寶座。無怪有人説:「歷史是個大悲劇」。為甚麼如此?這裏也許是答案。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小說
深宵豔遇記(節選)
茶餐廳這時雖然靜靜的,在門口可嚷起了一大陣嘈聲,周詩的太太,碰到了趙華生的媳婦趙師奶和她的丈夫阿明,因為剛才這位趙師奶還到周太那兒去過,昨天看好的房子,打算今天就搬去,可是現在又在這兒見着了,就拉開了話。
「啊呀!周太,怎麼這樣巧,又碰到了。」趙師奶笑着説,還趕緊介紹了阿明,「這是我先生。看,這孩子才十個月,多胖啊!」
周太手裏正抱着那最小的孩子,腿上傍着一個,大聲笑起來,説:
「孩子多了,真麻煩!趙師奶,你才是個子孫太太哩!」
「哈哈哈哈!」趙師奶也大笑了,「阿明,周太真是一個好人,我們一見面就談得來,哪兒去找這樣的房東呢?看啊!這孩子多討人歡喜,那小手,熱粉圑一樣,阿明,你摸摸他呀!」
周太把孩子湊上去,阿明摸摸孩子的小手,冷冰冰的,説:
「真是熱粉圑一樣。」
兩個女人又大笑,連茶餐廳裏面也聽得見。
「周太的先生,是編劇本的,在電影公司裏,真是好文墨,」趙師奶説,「周太,你説今晚不回去,現在怕就是到周先生那兒去吧?」
「是啊!」周太點點頭,笑着説,「就在這大廈上面,十八樓,上去坐一會吧!」
「可不是又巧了?」趙師奶説,「我們也到十八樓,表妹就住在A座,正要去找她搬家。」
「哦!真是巧!這不是有緣了?哈哈!一同上去吧!」三個人就一同走,周太還不斷説,「你們只管搬去就是了,我那女工已經認得你了,屋子已經打掃好,進門出門,就按鈴,我還有一枝鑰匙,剛才找了好一會沒找到,過兩天找到了,再給你表妹好了。」
「不要緊,按鈴開鬥,有甚麼不方便呢?周太,你總要費心多照顧她一下才好哩!」
他們到了十八樓。可是周詩已經下樓,打旁邊一架電梯走了出來,到萬國茶餐廳去了。周太站在門口,說:
「請進來坐一會。」
「不打擾了,改日再見吧!我們就在那邊。」阿明指着A座説。
「有甚麼關係?真是。」周太推着趙師奶,「大家見見面,我先生最喜歡朋友,見了面就熟了,他就是忙,我們做這一行的,你們不知道,他那股忙勁兒呀,……」
話還沒有説完,女工把門開了。三個人走進去。可是沒見周詩,女工説他剛出去,阿明夫婦也沒坐,讚了幾句屋子寬敞,又説陳設得好,周太很高興,還想再拉幾句,趙師奶卻説要走了。
「女人總是這樣,好像很怕陌生的樣子,我這人就是不這樣。」周師奶對阿明説,「你坐了,你太太也坐了。」
但是阿明也説要趕快去辦事,搬家也有些麻煩,下次再到府上去拜望吧!
夫婦倆辭出之後,周太才問女工,周先生到哪兒去了,女工説不知道,周太沒再説話。女工卻想給周詩解釋幾句:
「周太,周先生其實沒甚麼,你發那麼大的脾氣,也虧他好性子,你還不相信我,我這麼大一把年紀了,跟你們的叔叔做了這多年。」
「你哪兒知道呢?」周太説,「他們男人,花樣多,你是老實人,怎麼懂?」
那女工看她這樣,也就罷了。
「我問你。」周太奶着孩子,忽然説。
「還問甚麼呢?説了你又不信。」
「不是這件事。那A座住着的是甚麼人?」
「A座?斜對面那一家?」
「是啊!你知道嗎?」
「哦!聽説是個舞女大班,以前,常常有舞女進出,忙得很,近來倒不大有。」
周太的臉立刻變青,幾乎跳了起來,暗想糟了,甚麼表妹表妹,怕就是做舞女的,那趙師奶説話又來得,倒也有點兒可疑,也許不是正經人。可是房子已經租出去了,她不還價,付定又付得多,今早上一下子付了上期①,説先付三個月就是三個月。不要是來搗亂的,鬧得你頭痛,要退他們租,就要你退回雙倍的錢,那不是糟了?
「你説的話可是真的?」周太問。
「啊呀!周太,我甚麼話你也不信,這還騙你做甚麼呢?」
周太連忙拉開奶頭,放下孩子,衝到大門口,又急急回轉身打開袋子,把早上收的錢拿出來,開門飛跑了出去。孩子在沙發上張開嘴大哭,她也不管。
周太走到A座,來開門的是一個中年男人,這人就是老方,老方聽説是找趙師奶的,就叫阿明太太走出來。
「有事你們談,請裏面坐,我要出去一會。少陪少陪。」老方説完,就忽忽忙忙下樓。趙華生剛才來過後,已經先下去了。
周太走了過去,先定了定神,正想開口,趙師奶早拉着麥梅過來,説:
「這就是表妹,南洋才回來的。」
麥梅叫她一聲周太,還説,「請坐呀!」接着一跳,就跳了開去。周太渾身冷了一半,只見她穿着低胸衫、牛仔褲,頭髮像一個大馬尾巴,在後面掃來掃去,十七八歲,亂塗着脂粉,真有些妖形怪狀,哪像是正經人家的女孩子?這還用説?不是舞女,還會是甚麼?周太沉下了臉,沒有做聲。
阿明夫婦倆你看看我,我望望你,覺得有點甚麼不對了。周太卻繃起笑臉來,笑得怪難看,説:
「真是對不起,我怎麼説呢?説了怕有些難為情。」
「有甚麼事呀?周太。」趙師奶説,她又睜大了眼望望阿明。
「説了你們可不要見怪。」
「有甚麼關係呢?我們算是熟人了。」趙師奶説。
「按理呢,這樣做是不該的,」周太説,「我也明白,不過要請你們原諒,剛才我先生打電話來,你們一走,他就來了電話,説他的妹妹明天就要回來了,想不到這樣快,這間房本是留給她住的,可是我又答應了你們,真叫我為難,這怎麼辦呢?」
趙師奶和阿明的臉,也早繃直了。阿梅斟了茶遞過來,恭恭敬敬地送到周太手裏。趙師奶説:
「周太的意思想怎樣呢?我們是付了三個月上期的,連價也沒有還。」
「就是這話呀!我想還是退了租,照規矩,那就要退雙倍,可叫我怎麼好?」
趙師奶看她樣子誠懇,就説:
「這當然也化不來,我們既然租定了,倒不如給你姑小姐另外去租一間,也是一樣付房租,我們又不願再去麻煩了,錢倒是小事。」
「唉!就是這點不好,我們那位姑小姐,最喜歡住那個房間。我多賠呢,也賠不起,你們知道的,出租一間房子,就是想減輕一點負擔,經濟寛裕了也不必這樣找麻煩的。」
「這倒不必客氣。」趙師奶説,「不管怎樣,我們不想退!」
「我們不想退!」阿明也説。
正説着,麥梅提着箱子走出來,守在旁邊,樓下的收音機正在放送牛仔舞樂曲,她就合着拍子,必剝剝剝的響起指頭來,還扭着身子,轉來轉去,很得意的樣子。周太看了一眼,咽了口唾沫,眼珠子打了一個轉,說:
「退是一定要退。」
「沒有這道理的,我們都已準備好了。」趙師奶着急起來。
----------------------------------------
①「上期」,廣東市井話,凡每期須付的款,期頭就付的,就叫上期。租金先付後住,即上期租。
詩詞
閒書四絕
(一)萬千事物説新生,語到雌黃處便驚。
重定左聯榜一甲,須推魯迅與江青。
(二)列寧當日掌紅旗,歧見不嫌高爾基。
覆轍難明生死外,中華今為夜郎悲。
(三)為覺胸中奇氣少,方謀鞭底響雷多。
夫人買盡宣城紙,字屬塗鴉又奈何。
(四)大荒路上作先驅,未入牛欄不丈夫。
忍恥包羞逢際會,當頭迎取臭漿糊。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高旅卷的圖書 |
 |
高旅卷 出版社:天地圖書 出版日期:2016-04-0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628頁 / 17 x 23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608 |
社會人文 |
$ 616 |
文學作品 |
$ 616 |
中文現代文學 |
$ 686 |
Literature & Fiction |
$ 725 |
中文書 |
$ 725 |
現代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高旅卷
本書是香港著名老作家高旅的文學選集,內容分為:散文、小說、詩詞及附錄,編者在作者數百萬字作品中選輯了他最有成就的四個部份,並附有高旅自傳、高旅作品表及有關作者的資料和評論。
作者簡介:
高旅(1918-1997),江蘇常熟人,北平民國大學肄業。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歷任滬、渝、湘、桂各大報記者、編輯、主筆等職。為戰地記者時,曾受重傷瀕危。勝利後任上海《申報》特派員,旋受聘到港任香港《文匯報》主筆。間有文藝活動,撰有長篇歷史小說《杜秋娘》等,膾炙人口。
1966年因抗拒「文革」擲筆十三年,1981年重又執筆,撰雜文《持故小集》,長篇歷史小說《玉葉冠》、《金屑酒》、《氣吞萬里如虎行》等,現代小說有長篇《春霧深深》、《野山毛桃》等。近作有長篇歷史小說《元宮爭艷記》、《巨像高雲北雁飛》,並續作《持故小集》雜文。作者對中國傳統文化,見解新穎,文筆老辣,暢然說理,幽默諷刺處無不雋永,為文壇所重。
TOP
章節試閱
兩個悲劇
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名氣很大,戲劇電影不斷為之宣傳。他有一個名叫授的五世孫,他的故事,比之乃祖奇詭得多,但是一點名氣也沒有。
這位授王有一個王弟,名叫豫,很想繼哥哥做越王,可是授王有四個兒子,等着接位,輪不到他。於是用傳統的老法子,向哥哥進讒,説四個侄兒的壞話,不外有的不成材,有的有謀皇篡位的企圖等等,授王聽信了,四個兒子,殺了三個,第四個不殺了,即使壞話説盡,也置之不理,好歹要留着他接位做越王。
把自己的兒子殺光,中外的昏君、暴君,大概百中揀不出一個會如此。
然而第四個終覺岌岌可危,...
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名氣很大,戲劇電影不斷為之宣傳。他有一個名叫授的五世孫,他的故事,比之乃祖奇詭得多,但是一點名氣也沒有。
這位授王有一個王弟,名叫豫,很想繼哥哥做越王,可是授王有四個兒子,等着接位,輪不到他。於是用傳統的老法子,向哥哥進讒,説四個侄兒的壞話,不外有的不成材,有的有謀皇篡位的企圖等等,授王聽信了,四個兒子,殺了三個,第四個不殺了,即使壞話説盡,也置之不理,好歹要留着他接位做越王。
把自己的兒子殺光,中外的昏君、暴君,大概百中揀不出一個會如此。
然而第四個終覺岌岌可危,...
»看全部
TOP
推薦序
導讀:豈有風雨故人懷,萬版《秋娘》入夢來──高旅的雜文、小説、詩歌 羅琅(節錄)
高旅雜文
在散文方面,聶紺弩最讃譽的是高旅的雜文集《持故小集》,他説:「持故好,博學卓識,有知堂風味,但知堂抄書多勝他,海内以博學知名者為錢鍾書,他只識文藝,你比他天地闊,總之讀書多,記性好,其用無窮。」又説:「很耐尋味,讀時常不忍釋卷,故為勤進。」他又指出:〈唐代貶官〉、〈孫行者不能代取經〉等文,似可以多寫,易寫、易發表,且無人能達此水準。
文革狂飆肆虐神州大地,四人幫作惡多端,他作為一個正直的左派文化人,憤而於一九六...
高旅雜文
在散文方面,聶紺弩最讃譽的是高旅的雜文集《持故小集》,他説:「持故好,博學卓識,有知堂風味,但知堂抄書多勝他,海内以博學知名者為錢鍾書,他只識文藝,你比他天地闊,總之讀書多,記性好,其用無窮。」又説:「很耐尋味,讀時常不忍釋卷,故為勤進。」他又指出:〈唐代貶官〉、〈孫行者不能代取經〉等文,似可以多寫,易寫、易發表,且無人能達此水準。
文革狂飆肆虐神州大地,四人幫作惡多端,他作為一個正直的左派文化人,憤而於一九六...
»看全部
TOP
目錄
導讀:豈有風雨故人懷,萬版《秋娘》入夢來──高旅的雜文、小説、詩歌 羅琅 11
散文
唐代的貶官 28
混沌病 33
刑法瑣談 37
從八股文説起 41
活拆華清宮 45
龍的故事 50
律例與事實各歸各 54
為時代作證 57
雞鳴狗盜之外 61
想起了嚴復和劉師培 65
孫行者不能代取經 68
聞廣播《過秦論》有感 72
要財要命之類 76
揚雄的答案 80
文天祥高郵遇俠 84
兩個悲劇 88
曹丕的空話 92
從于墓説開去 96
王夫之的「迂論」 100
永樂大帝 104
擬葉公子張對話 107
人焉瘦哉──觀人篇...
散文
唐代的貶官 28
混沌病 33
刑法瑣談 37
從八股文説起 41
活拆華清宮 45
龍的故事 50
律例與事實各歸各 54
為時代作證 57
雞鳴狗盜之外 61
想起了嚴復和劉師培 65
孫行者不能代取經 68
聞廣播《過秦論》有感 72
要財要命之類 76
揚雄的答案 80
文天祥高郵遇俠 84
兩個悲劇 88
曹丕的空話 92
從于墓説開去 96
王夫之的「迂論」 100
永樂大帝 104
擬葉公子張對話 107
人焉瘦哉──觀人篇...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高旅
- 出版社: 天地圖書 出版日期:2016-04-01 ISBN/ISSN:978988825700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628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