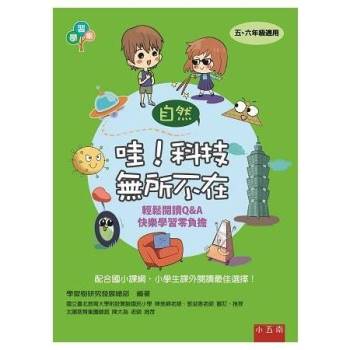2015年第十三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積風集》續作
「風之積也不厚,其負大翼也無力。」幾年來讀書看戲,總離不開莊子這句話。本書郭梓祺《積風集》續集。除書話和影評以外,另有數篇遊記和訪問。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積風二集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積風二集
內容簡介
目錄
馮睎乾序 i
自序 iv
書與電影
真正的閱讀——余英時與陳寅恪
遺民寄托——重讀《清初人選清初詩彙考》
《石語》與點將錄
蚌病成珠——重讀《七綴集》
苦中作樂——重讀楊絳
輕逸與深情——讀《宋淇傳奇》
剛健與超越——讀《美與狂》
也說《十七帖》
另一種中日關係——讀《茶事遍路》
低低低低的——悼周夢蝶
莊重的小說——重讀《紅格子酒舖》
像我這樣的一個導演——看陳果《我城》
漫漶幽埋,煙消雲散——讀《地文誌》
出游從容《魚之樂》
孰不可忍
博物館與帕慕克
希尼的小詩
從果戈里的〈鼻子〉說起
求真——奧威爾的散文
奧威爾是告密者?
改編之難——《大亨小傳》
改編之視野——《審判》的笑聲
星星之火
盲打誤撞,義不容情
神探魔探兩不分
瞬間看地球
瞬間看浪潮
地方和人
烏普薩拉
艾美利亞
伊斯坦堡
現代文人古典美——訪王穎苑
《少帥》真幻——訪宋以朗與馮睎乾
自序 iv
書與電影
真正的閱讀——余英時與陳寅恪
遺民寄托——重讀《清初人選清初詩彙考》
《石語》與點將錄
蚌病成珠——重讀《七綴集》
苦中作樂——重讀楊絳
輕逸與深情——讀《宋淇傳奇》
剛健與超越——讀《美與狂》
也說《十七帖》
另一種中日關係——讀《茶事遍路》
低低低低的——悼周夢蝶
莊重的小說——重讀《紅格子酒舖》
像我這樣的一個導演——看陳果《我城》
漫漶幽埋,煙消雲散——讀《地文誌》
出游從容《魚之樂》
孰不可忍
博物館與帕慕克
希尼的小詩
從果戈里的〈鼻子〉說起
求真——奧威爾的散文
奧威爾是告密者?
改編之難——《大亨小傳》
改編之視野——《審判》的笑聲
星星之火
盲打誤撞,義不容情
神探魔探兩不分
瞬間看地球
瞬間看浪潮
地方和人
烏普薩拉
艾美利亞
伊斯坦堡
現代文人古典美——訪王穎苑
《少帥》真幻——訪宋以朗與馮睎乾
序
序
如《積風集》自序所言,書題源出莊子的「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十年前某深夜,從電話聽佘汝豐老師引此勸勉,至今未敢或忘。風繼續吹,繼續積,繼續讀書看戲寫文章,乃有二集。
《積風集》出版後,家人之珍重最使我慚愧。父親是船長,家姐說,他把我送他的書放在密實袋才拿回船,讀後覺得內容艱難,會把不懂的字抄下查字典。在外國的母親想法有時跟我不算接近,收到了書,還是由衷高興起來。
我也把書送給有份把我養大的姑媽姑丈,書他們未必會看,但正如他們總把我旅行寄來的明信片過膠貼牆,他們就把書安放在組合櫃中。姑媽說,隔鄰住了一個聰明但頑皮的小妹妹,有時會過來坐坐吃東西。姑媽曾拿出那本《積風集》,跟小妹妹說,寫書這個人,以前跟你一樣大,就是住在這裏的,所以要聽話。據說那小妹妹竟因此覺得很厲害。
我出生後六年多,一直住在彩雲邨那十一樓的單位,想起來,很多東西都是從識字不多的姑媽身上耳濡目染。看見跛子不要大聲說「跛」,免人聽了難堪;隧道有盲公彈琵琶,她給我零錢放進他的鐵罐,也提醒不要太大力,有聲,他知道有人給錢便可。諸如此類,都是體貼入微多於規行矩步。雖然偶爾也發現,她會欺騙我,譬如有天我放在廚房的黃色三輪車無故失蹤,她便攤攤手說,給賊佬偷去,沒有了。我就很遲才醒覺,那麼辛苦潛進來,不會笨到只偷玩具,應該是嫌阻地方而給她丟掉。但到今天,只要一起在家吃飯,姑媽還是會特定買條大魚蒸給我,怕我平時少吃,不夠營養。她則總是最遲才碰那條魚。
忘了最初識字是在何時,深刻的倒是升了教會小學後,要學背主禱文。姑媽總在差不多播《歡樂今宵》的時間,帶我到晾着衫的騎樓,開張枱仔,打開手冊,逐一讀出那些異常生僻的文字——畢竟她最着緊的,多是何時拜山和賀誕;我對賀誕晚上長輩在酒樓壇前擲杯和競投花燈,則尤為神往。風吹過,頭上衣服搖晃,黑影幢幢,外面的電視有聲,我分心,她也分心,而且晚了自然想睡,但還是一句一句捱下去:「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遇到不懂的字,她會進去問我那時在讀中學的堂兄,他可能在專心看電視,印象中多是愛理不理。姑媽走開時,我總被面前狹長的廁所盡處,一個用尼龍網吊在水箱旁的籃球吸引,好像從來無人拿下,只一直如太陽高高掛着,封塵。我現在雖非教徒,卻仍能一字不漏背出主禱文,倒好奇那時姑媽不懂的是哪幾個字,忘了我究竟是怎樣學會的,更不知那籃球的下落。但因並無在禮堂被罰的記憶,應是不久後半推半就便背過去了。
要為第二本書寫序,一想就是上面這些畫面。對曾為我的教育出力的親人而言,讀書識字最大的意義,或許不是求真,而是脫貧,日後可以多吃魚,少吃苦。我不肯定這想法是卑微抑或崇高,但至少我從來知道,讀書識字,往往予人指望:在這艱難的世界,那大抵是條舒坦的路。他們當時一定沒料到我可讀大學,寫文章,把自己的書送給他們。現在,我終可在麻將枱上跟這幾位高手勉強較量,而只要他們想找原子筆而我碰巧又有,他們總習慣笑哈哈說:「吖果然係讀書人。」
就這樣成了讀書人。也無庸迴避吧,書既然真有幸讀過些,遇有好的,能力所及,應令更多人知道;世界已夠不公平,好東西更沒理由一路沉沒。寫文章,都是將不一定要跌在我身上的知識、想法和喜悅攤分開去,盡了力也就無憾。
除跟《積風集》一樣有書話和影評,《積風二集》另有數篇遊記和訪問。我從來覺得,旅行的時候在閱讀,閱讀的時候在旅行,而且總有人在,都是積學儲寶,大開眼界,故不妨結集一處。重讀舊文,發現有時顧此失彼,廢話太多,都增刪重寫,希望書會更像樣。
我要感謝為書編校和作序的馮睎乾先生。跟他相識不久,卻是傾蓋如故,能請這位我佩服的讀書人幫忙,深感榮幸。他曾提醒我不要一味仰視世界,也要有平視和俯視的時候,我覺得切中要害,常因此想着如何長進。
感謝《明報》〈星期日生活〉主編黎佩芬小姐。至今仍素未謀面,她卻對我一直信任。我慶幸這十多年來香港有這份富心思的副刊,能偶爾參與其中,是生活樂事。感謝長期售賣《積風集》的序言書室。感謝曾為這書落力的人,包括再度為我在封面題字的萬偉良老師,畫封面的區華欣。感謝花千樹出版社的葉海旋先生和周凱敏小姐。書中若有訛誤,掃葉未淨,責任在我。
是我幸運,生平竟遇到那麼多對我有恩的師友,所有勸勉指點,都在心中。
是為序。
如《積風集》自序所言,書題源出莊子的「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十年前某深夜,從電話聽佘汝豐老師引此勸勉,至今未敢或忘。風繼續吹,繼續積,繼續讀書看戲寫文章,乃有二集。
《積風集》出版後,家人之珍重最使我慚愧。父親是船長,家姐說,他把我送他的書放在密實袋才拿回船,讀後覺得內容艱難,會把不懂的字抄下查字典。在外國的母親想法有時跟我不算接近,收到了書,還是由衷高興起來。
我也把書送給有份把我養大的姑媽姑丈,書他們未必會看,但正如他們總把我旅行寄來的明信片過膠貼牆,他們就把書安放在組合櫃中。姑媽說,隔鄰住了一個聰明但頑皮的小妹妹,有時會過來坐坐吃東西。姑媽曾拿出那本《積風集》,跟小妹妹說,寫書這個人,以前跟你一樣大,就是住在這裏的,所以要聽話。據說那小妹妹竟因此覺得很厲害。
我出生後六年多,一直住在彩雲邨那十一樓的單位,想起來,很多東西都是從識字不多的姑媽身上耳濡目染。看見跛子不要大聲說「跛」,免人聽了難堪;隧道有盲公彈琵琶,她給我零錢放進他的鐵罐,也提醒不要太大力,有聲,他知道有人給錢便可。諸如此類,都是體貼入微多於規行矩步。雖然偶爾也發現,她會欺騙我,譬如有天我放在廚房的黃色三輪車無故失蹤,她便攤攤手說,給賊佬偷去,沒有了。我就很遲才醒覺,那麼辛苦潛進來,不會笨到只偷玩具,應該是嫌阻地方而給她丟掉。但到今天,只要一起在家吃飯,姑媽還是會特定買條大魚蒸給我,怕我平時少吃,不夠營養。她則總是最遲才碰那條魚。
忘了最初識字是在何時,深刻的倒是升了教會小學後,要學背主禱文。姑媽總在差不多播《歡樂今宵》的時間,帶我到晾着衫的騎樓,開張枱仔,打開手冊,逐一讀出那些異常生僻的文字——畢竟她最着緊的,多是何時拜山和賀誕;我對賀誕晚上長輩在酒樓壇前擲杯和競投花燈,則尤為神往。風吹過,頭上衣服搖晃,黑影幢幢,外面的電視有聲,我分心,她也分心,而且晚了自然想睡,但還是一句一句捱下去:「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遇到不懂的字,她會進去問我那時在讀中學的堂兄,他可能在專心看電視,印象中多是愛理不理。姑媽走開時,我總被面前狹長的廁所盡處,一個用尼龍網吊在水箱旁的籃球吸引,好像從來無人拿下,只一直如太陽高高掛着,封塵。我現在雖非教徒,卻仍能一字不漏背出主禱文,倒好奇那時姑媽不懂的是哪幾個字,忘了我究竟是怎樣學會的,更不知那籃球的下落。但因並無在禮堂被罰的記憶,應是不久後半推半就便背過去了。
要為第二本書寫序,一想就是上面這些畫面。對曾為我的教育出力的親人而言,讀書識字最大的意義,或許不是求真,而是脫貧,日後可以多吃魚,少吃苦。我不肯定這想法是卑微抑或崇高,但至少我從來知道,讀書識字,往往予人指望:在這艱難的世界,那大抵是條舒坦的路。他們當時一定沒料到我可讀大學,寫文章,把自己的書送給他們。現在,我終可在麻將枱上跟這幾位高手勉強較量,而只要他們想找原子筆而我碰巧又有,他們總習慣笑哈哈說:「吖果然係讀書人。」
就這樣成了讀書人。也無庸迴避吧,書既然真有幸讀過些,遇有好的,能力所及,應令更多人知道;世界已夠不公平,好東西更沒理由一路沉沒。寫文章,都是將不一定要跌在我身上的知識、想法和喜悅攤分開去,盡了力也就無憾。
除跟《積風集》一樣有書話和影評,《積風二集》另有數篇遊記和訪問。我從來覺得,旅行的時候在閱讀,閱讀的時候在旅行,而且總有人在,都是積學儲寶,大開眼界,故不妨結集一處。重讀舊文,發現有時顧此失彼,廢話太多,都增刪重寫,希望書會更像樣。
我要感謝為書編校和作序的馮睎乾先生。跟他相識不久,卻是傾蓋如故,能請這位我佩服的讀書人幫忙,深感榮幸。他曾提醒我不要一味仰視世界,也要有平視和俯視的時候,我覺得切中要害,常因此想着如何長進。
感謝《明報》〈星期日生活〉主編黎佩芬小姐。至今仍素未謀面,她卻對我一直信任。我慶幸這十多年來香港有這份富心思的副刊,能偶爾參與其中,是生活樂事。感謝長期售賣《積風集》的序言書室。感謝曾為這書落力的人,包括再度為我在封面題字的萬偉良老師,畫封面的區華欣。感謝花千樹出版社的葉海旋先生和周凱敏小姐。書中若有訛誤,掃葉未淨,責任在我。
是我幸運,生平竟遇到那麼多對我有恩的師友,所有勸勉指點,都在心中。
是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