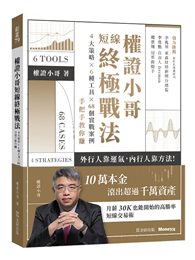塞西將軍當選埃及總統,軍人再次掌控國家。「茉莉花革命」血已流,卻似乎未開花結果。作者陳婉容新作《茉莉花開──中東革命與民主路》剖析中東大局以及這場革命的走向。中東革命,人民得廣場?是否能得天下?
陳婉容親身採訪二零一三年伊朗大選,見證當權者如何鋪路欽定接班人,這次「假普選」與「篩選」看似遙遠,卻令人聯想到香港當前處境。
以色列二零一二年狂轟猛炸加沙地帶,巴勒斯坦人死傷枕藉。不對等的所謂自衛戰爭,是何等邪惡的人才會容許?
伊斯蘭世界看似遙不可及,然而近世的民主社會發展,卻是普世人民彼此扣連的命運,若一般人要認識當前世界大局,學生要認識全球化,不得不閱讀這片茉莉花革命後的中東烽火大地。此書堪為當前國際政治的專業讀物,當中透過報告文學、政治學、法律學等深入淺出對比香港與中東,也是通識科的優良參考書。
作者以其政治學專長分析中東局勢,幫助讀者了解國際政治遊戲規則,深淺出分析入以巴衝突,以及西方與中東的恩怨,從中反思香港政局。
全書分為三章:第一章談中東大局,第二章談茉莉花革命、流亡者及中東少數民族,第三章把中東與國際民主經驗扣連到香港。全書均以趣味及與串連到香港相關社會問題,以吸引香港讀者,引發共鳴;附錄則為中東旅行經歷。旁徵博引政治學、歷史、學者觀點、學術著作等。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茉莉花開:中東革命與民主路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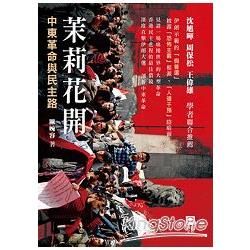 |
茉莉花開-中東革命與民主路 出版日期:2014-09-11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00 |
Others |
電子書 |
$ 144 |
社會科學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 308 |
中文書 |
$ 308 |
社會 |
$ 315 |
社會人文 |
$ 315 |
政治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茉莉花開:中東革命與民主路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陳婉容
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倫敦大學法律學系畢業。現職獨立記者,二零一三年隻身採訪伊朗總統大選,為多份報章寫下詡實見聞與報道。長文多見於《明報星期日生活》、《主場新聞》、《The Glocal》等,文章主要為中東與國際議題評論,但也寫香港及中國政治,書評、影評和劇評。自十多歲起,背著背包跑過近七、八十個國家,但仍然心繫中東這片土地,一次又一次的重新踏足,但永遠都發掘到新的面向。
曾經評論的主題包括:以巴衝突、埃及政變、伊朗核談判、伊朗二零一三總統大選、敘利亞內戰、黎巴嫩派系衝突、新疆問題、台灣社運等。中東以外,也對後殖理論和身份、國族等議題有濃厚興趣。在攻讀法律時曾修習國際法及國際人權法,寫過人道干預、轉型正義、義戰與難民等議題。
博客名為「The Catcher in the Rye」,因為我總覺得沙林傑筆下主角的孤寂與叛逆很像我:「我要做個麥田捕手。我知道那很瘋狂,但這是我所真正想要做的事。」
Facebook專頁:陳婉容 Sherry (www.facebook.com/sherrychanyy)
博客:The Catcher in the Rye(sherrychan.net)
陳婉容
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倫敦大學法律學系畢業。現職獨立記者,二零一三年隻身採訪伊朗總統大選,為多份報章寫下詡實見聞與報道。長文多見於《明報星期日生活》、《主場新聞》、《The Glocal》等,文章主要為中東與國際議題評論,但也寫香港及中國政治,書評、影評和劇評。自十多歲起,背著背包跑過近七、八十個國家,但仍然心繫中東這片土地,一次又一次的重新踏足,但永遠都發掘到新的面向。
曾經評論的主題包括:以巴衝突、埃及政變、伊朗核談判、伊朗二零一三總統大選、敘利亞內戰、黎巴嫩派系衝突、新疆問題、台灣社運等。中東以外,也對後殖理論和身份、國族等議題有濃厚興趣。在攻讀法律時曾修習國際法及國際人權法,寫過人道干預、轉型正義、義戰與難民等議題。
博客名為「The Catcher in the Rye」,因為我總覺得沙林傑筆下主角的孤寂與叛逆很像我:「我要做個麥田捕手。我知道那很瘋狂,但這是我所真正想要做的事。」
Facebook專頁:陳婉容 Sherry (www.facebook.com/sherrychanyy)
博客:The Catcher in the Rye(sherrychan.net)
目錄
代序
沈旭暉
周 澄
自序
導言 張翠容
第一章 生命凋零 茉莉花開 亡者、革命者、難民的故事
埃及政變──不斷重複的廣場革命
伊斯蘭主義與憲政民主──埃及與茉莉花的凋零
一無所有的生命──談難民人權與人道干預
難民營的秩序與哀愁──等待回家的中東難民
戰爭與救援市場學──誰拿走了你的捐款?
中東邊界的共同想像──從黎巴嫩與敘利亞說起
我們所知道的恐怖主義
無根的遊牧者──庫爾德族的建國夢與流浪
第二章 在沙漠栽種自由花──中東角力與民主之路
伊朗式選舉的啟示
伊朗式普選是如何煉成
借鏡伊朗式普選
伊朗大選採訪紀實
地下水道那麻木的鱷魚──伊朗流亡者之詩
雙子塔是布殊家族搖錢樹?──國家權力另類致富之道
這是最壞的年代──從《從帝國廢墟中崛起》說起
「最愛克林頓」──再思美國的軍事干預
以巴衝突:反錫安主義等於反猶?
以色列與自衛戰爭
《追擊拉登行動》──美國反恐十年小結
沉默的抵抗 巴勒斯坦入聯以後
若曼德拉是英雄,阿拉法特呢?
第三章 民主同途──從國際經驗看香港社會
俄羅斯維穩三步曲
第一部:培植極右翼支持政府
第二部:高壓手段
第三部:利用反恐打壓異己
讀《獨裁者的進化》
法律與人性尊嚴——讀《斷臂上的花朵》
We are “Hongkongners”? 本土香港──誰想像的共同體
窮罪
沒有英雄的年代
從次文化論少數族裔
中國最頭痛的問題──新疆的「巴勒斯坦化」?
附錄
烽火大地行紀──凝視中東的人與土地
沈旭暉
周 澄
自序
導言 張翠容
第一章 生命凋零 茉莉花開 亡者、革命者、難民的故事
埃及政變──不斷重複的廣場革命
伊斯蘭主義與憲政民主──埃及與茉莉花的凋零
一無所有的生命──談難民人權與人道干預
難民營的秩序與哀愁──等待回家的中東難民
戰爭與救援市場學──誰拿走了你的捐款?
中東邊界的共同想像──從黎巴嫩與敘利亞說起
我們所知道的恐怖主義
無根的遊牧者──庫爾德族的建國夢與流浪
第二章 在沙漠栽種自由花──中東角力與民主之路
伊朗式選舉的啟示
伊朗式普選是如何煉成
借鏡伊朗式普選
伊朗大選採訪紀實
地下水道那麻木的鱷魚──伊朗流亡者之詩
雙子塔是布殊家族搖錢樹?──國家權力另類致富之道
這是最壞的年代──從《從帝國廢墟中崛起》說起
「最愛克林頓」──再思美國的軍事干預
以巴衝突:反錫安主義等於反猶?
以色列與自衛戰爭
《追擊拉登行動》──美國反恐十年小結
沉默的抵抗 巴勒斯坦入聯以後
若曼德拉是英雄,阿拉法特呢?
第三章 民主同途──從國際經驗看香港社會
俄羅斯維穩三步曲
第一部:培植極右翼支持政府
第二部:高壓手段
第三部:利用反恐打壓異己
讀《獨裁者的進化》
法律與人性尊嚴——讀《斷臂上的花朵》
We are “Hongkongners”? 本土香港──誰想像的共同體
窮罪
沒有英雄的年代
從次文化論少數族裔
中國最頭痛的問題──新疆的「巴勒斯坦化」?
附錄
烽火大地行紀──凝視中東的人與土地
序
序一
為甚麼我們要認識俄羅斯和伊朗……
沈旭暉
陳婉容在大學時期是我的學生,後來再聽到她的名字,是在報章讀到她的文章,當時儼如一個年輕版張翠容。後來她的身份又成為了「南韓駐港領事館外交部國際政治研究員」,和我做訪問。後來又發現,她寫的國際關係評論愈來愈多,而且大都是關於一般人忽略的第三世界;再後來還知道,她打算到海外進修,如無意外,大概很快成行。
其實,這樣的生活,放在其他地方,可說是平常不過。但當我們生活的時空名叫「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她的人生選項,卻顯得卓立獨行。無論是哪個世代,這裡都習慣了朝九晚六的辦公室工作為常規,任何走出溫室的決定,都彷彿驚世駭俗,「讀國際研究來做甚麼」,也就成了比「為甚麼要讀書」更理直氣壯的「人生智慧」。陳婉容走到今天,卻證明了路是人走出來的,為大眾帶來國際視野不等於沒有市場,不呆在同一個辦公室也不等於三餐不繼。這樣的訊息,比主旋律的成功故事更發人深省。
更重要的是,本書收錄的文章,並非為了國際而國際,並不「離地」,反而對香港有很大參考價值。例如普京在俄羅斯的維穩方式,「伊朗式民主」的設計和智慧,我們都似曾相識,一般人卻說不出背後的所以然。要是沒有相應的國際視野,就是要為身旁的「在地」議題把脈,也容易斷錯症。我們在學院常有比較政治課,但真的能做到比較政治的人卻寥寥可數,反映這條路是孤獨的。無論陳婉容要成為戰地記者、還是更在意為港人提供通識智慧,都希望她能堅持下去,為我城的國際研究再放異采。
序二
闖蕩世界的渴望
周澄
話說這一篇短短的序,拖延了兩三個月也未能動筆。期間婉容當然追殺不懈,我也老實地答她,「除了愛慕之情,我實在想不到要寫甚麼啊……」。素以霸氣迫人為名的婉容,聽罷當然不收貨。但我知道,婉容等了一等,還是要把這空出的一頁留給我,無非是為了感銘彼此的情誼。
知道陳婉容這個大名,是在中大讀書的時候。她比我早畢業,讀書時我們並不相識,只是在某些友儕圈子聞說過她頗為高傲,僅此而已。當時偶然接觸到她的文字,莫名地感到投緣,但知道她是名校高材生,又經常周遊列國,自覺是兩個世界的人,所以未有高攀。一如對窗的鄰人,偶爾暗瞥觀照,不求妄越距離。
大學時代,一直忙於各樣學生組織與社運參與,基本上沒有甚麼閒錢去遠行,名副其實就是一條「窮港燦」。但儘管如此,從小愛看世界歷史故事、外國電影電視的我,從來都沒有忘卻闖蕩世界的渴望。作為一些人口中的「左膠」,我也對戰爭與殖民歷史斑駁的發展中國家格外有興趣。畢業後,因此把心一橫,去了菲律賓為一間非政府組織工作。本來計劃是留一年,但工作期間有點不盡如意,留了半年就決定回港,從新計劃自己的路向。回港前,我不知為何,竟然鼓起勇氣,透過facebook給婉容寫了一個不長不短的訊息。客套話當然有,但大家都竟然分享了一些當時對理想、對位置的困惑。如今看來,那些互勉點到即止,我當時沒有想過之後會和婉容成了密友,由國際時事本土議題、人生志向旅行大計到女生之間的私密八卦無話不談。
自小喜歡收到朋友在路上寄出的明信片勝於一式一樣的手信,但誠如前述的原因,我一直是收件人遠多於有機會寄予朋友。那時還未熟稔,厚著臉皮請婉容寄明信片給自己,她的旅途閱歷與流麗的筆跡徒添重量。因此,到我也開始不時獨自遠行的時候,我也沒有忘記在路上給她寫明信片。一次,我大意答謝她啟發我有更多勇氣去跨越未知的疆界,後來她割愛將她在格魯吉亞買回來的史太林叔叔珍藏明信片寄給我,其中一句是「其實你也影響了我很多」。她常說,在認識我之前,她很討厭處女座,因為處女座不論男女,都無一例外是尖酸挑剔、斤斤計較的完美主義者。但她說,我的完美主義卻是待人以寬,偏偏執著挑剔自己、鑽牛角尖,忽視自己的優點。
知道婉容將過去的文章重編出書,著實為她高興。推薦的話也不用我說了,讀者自會知曉。假若到我將來也獨立著作成書之時,也必定有一版留給她。(不過屆時,希望她不會像我一樣拖延吧,哈哈。)
自序
自由的狐狸
哲學家伯林(Isaiah Berlin)說過,知識分子有兩種,一種是狐狸,一種是刺蝟。古希臘寓言有云「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the fox knows many things, but the hedgehog knows one big thing)—所謂術業有專攻,要做好學問,似乎必然要做刺蝟;但人亦貴自知,如果天生就是狐狸,對甚麼事情都好奇心過了頭,沒有辦法心無旁騖地鑽研一件事情,那麼,當一隻稱職的狐狸,也許就是我之所能做到最好的事了。讀書時期以為自己一目十行過目不忘的本領很了不起,長大了就自知其實沒有甚麼驚天動地的才華,才能甚多但學不見得有專精,要將勤補拙又受天生慵懶性格所限,所以且行且書,在紙上流浪的生活,倒也快活。能夠攀越自己的限制自是強人,然而做自己所喜歡的事情,而且用心地做,心懷純粹不計後果地做,也不見得是軟弱吧。
這本小書就是我當一隻狐狸的思考筆記。這些年來,反覆從一道邊界跑到另一道邊界,從一本書翻到另一本書,重重複複幾乎完全沒有計劃的積累,原來畢竟有所造就,那些見聞與知識,在某種時刻竟有機會連結起來,成就我不曾想像的事。一年半以前,從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無心插柳地栽進寫字生涯的我,絕對想像不到在短短五百多天之後,第一本著作就會出版,而主題正是我心所繫的中東,一片在他人眼中神秘甚至野蠻的大地。
收到出版社邀約後,我嘗試在中東的瘋狂與喧鬧之中抽離,整理我關於伊斯蘭世界政局的評論文章與記事。這才驟覺書寫伊斯蘭世界,從來不是容易的事。大學時代,我重重複複的讀了薩依德(Edward Waefie Said)的著作,記得他在《遮蔽的伊斯蘭:西方媒體眼中的穆斯林世界》(Covering Islam,「Covering」一字是歧義,兼有「報道」及「遮蔽」之意)裡說過:「沒有任何一種宗教或文化群體會像伊斯蘭教一樣,被斬釘截鐵地認定將對西方文明造成威脅。」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加上九一一以降主流媒體的渲染,又為這種成見多添了幾分怖慄想像。
二零一一年「茉莉花革命」震動了整個世界,讓人重新思考伊斯蘭主義(political Islam)與憲政民主結合的可能;兩年後埃及再次變天,初始萌芽的民主政體又似被推翻,歷史到底還是沒有終結。然而這一場革命終於叫世人體認,所謂伊斯蘭世界的同質性不過是想像的產物,這片土地有原教旨主義者,有心向民主自由的革命分子,有提倡政教分離的世俗主義者,也有人相信政教合一或大阿拉伯主義,才是伊斯蘭世界對抗新殖民主義的利器。這片被稱為烽火大地的土地如同世界縮影,值得我們花更多心力去觀察和關注。
第三波民主化從一九七四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起,把半個地球捲進了走向民主的道路之上;既然連許多「專家」—正如薩依德說,太多「專家」喜歡就伊斯蘭議題說話,但那些人根本不了解伊斯蘭世界—眼中永遠不會接受民主的中東,也在茉莉花革命中迎向了民主化,香港一定不會是例外。過去十五年來,香港一直處於政制改革爭議的風口浪尖上,社會抗爭一場接一場,反對派分分合合,一片混沌。從脫殖到尋找身分認同,以至嘗試從這種半民主的曖昧不明狀態走往真正的民主,香港要走的路,其實跟許多普世經驗互為鏡像。所謂國際,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遙不可及,那麼事不關己。
普世經驗互為鏡像
茉莉花革命從北非始席捲阿拉伯世界,然而當中有成有敗;敘利亞從此陷入內戰,利比亞在內亂後成為了人道干預的對象,埃及似乎成功,但及後又證實根基不穩,突尼西亞偶有騷亂但似乎又在慢慢建立民主政制。成敗的因素的除了是這些國家各自的歷史發展階段,迥異的文化、經濟脈絡,公民社會成熟程度的分別,還有政府在威權轉型向民主之時的種種政策。從埃及的例子,我們或許可以理解所謂堅實的民主願景,還有茁壯的公民社會,對於穩定的政體轉型有何意義;從南非的例子,我們可以思考,香港如果有全民制訂憲法的機會,應該用怎樣的政治哲學邏輯去制定憲法。這些都是跟現今香港時局息息相關的議題。在彼方,俄羅斯威權政府控制新聞自由、鏟除異己、鐵腕鎮壓分離主義地區,但俄羅斯國民卻又似乎保有了一定的自由,我們或許可以從此窺視所謂假民主的危險性。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如果不去深入理解,香港人對於別人所擁有的民主自由再羨慕再嚮往,都不免廉價。
然而伊斯蘭世界的複雜,也許不是我這個如霧水般短暫勾留的旅人能夠理解的。我懷著對古文明與亞伯拉罕三教發源地的嚮往,懷著為伊斯蘭平反的目標踏足他們的世界,又讀了許多書和論文去寫一篇又一篇煞有介事的評論。然而我畢竟是個與他們的歷史與生活割裂的局外人,唯有提醒自己,至少要保持文字的純粹與理性,哪怕文字有多麼拙劣,仍誠實地記下所見所聞。我從來覺得自己是個無可救藥的世界主義者,認同東亞學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那套國族主義建構論,然而坐在敘利亞難民面前,聽他們述說無家無國的苦難;聽庫爾德人、巴勒斯坦人說為民族犧牲在所不惜,卻驟覺我或許不過是個天真的左派,忽略了國家民族的正當性,甚或是應然性。現實與書本的距離比我想像中更遙遠,然而就是這樣的,反覆建立論證再推翻重構的過程,佐證了一個人走上千萬里路的意義。
隻身採訪伊朗大選
二零一三年六月,我在炙熱的伊朗隻身採訪總統大選。高考時代因為想當記者,放棄了法律系,畢業後卻沒有投身傳媒工作。結果第一次當記者就是在萬里之外的,封閉的伊朗,不止語言不通,伊朗政府對新聞工作者的厭惡與壓制也是惡名昭著。行前兩天還在處理學業,耐不住跟好友訴說準備不足的擔憂,他說的話卻成了推動我前行的力量:「橫衝直撞不怕死的勇氣,就是你最好的特質。」於是戰戰競競的接下任務,懷著幾乎是莽撞的拼死的勇氣,以另一種身分重返這個美麗的國度。
魯哈尼勝選當晚,我在街上央求的士司機送我去德黑蘭城西的Valiasr Square。旅館老闆擔心我,跑出來替我跟司機溝通。上街慶祝的車輛已經擠滿了往Valiasr的主要道路,沒有司機願意在路上擠上數個小時。我在旁邊雙手合什,彎下身子說:「拜託,請你給我開個價錢,我真的要去。」司機聽不懂英語,但大抵還是聽到了我語氣中的央求意味。最後成交,十二萬伊朗里爾。我跳上車,跟旅館老闆穆薩維先生說再見。他看著我關上車門,在車窗旁細細叮囑:多晚回來都好,旅館前台有人會給你開門。萬事小心,別往人群裡鑽。
我始終沒有坐著這的士到Valiasr Square。半途不到,車子就在街上塞了近四十五分鐘。我走下車拍攝隨意在街上就跳起土耳其舞的男生,一個伊朗家庭熱情地請我上車跟他們同行,我給的士司機付了錢就跳上他們的車,於是少女Marzi和她的家人就成為了我的採訪翻譯。他們知道我來採訪,更是興奮莫名,一直對車外的其他人高呼:「我們車裡有個記者!」其他人聽見都湧到車窗旁,舉起手中的海報或標語要求我拍他們。我們一路隨著伊朗吵嚷的流行音樂舞動,看人們不時鑽上車頂,跟隨其他慶祝民眾高呼:「伊朗萬歲,釋放穆薩維!」我鼻子隱隱的發酸:一次勝利並沒有讓伊朗人忘記四年前的傷痛。成千上萬的慶祝民眾裡只有我一個外國女子,在人群中跟他們一起慶祝難得的一次勝利。縱在異鄉為異客,但我和伊朗人民對於民主、幸福與自由的追求,豈能說不是同樣。這世界的命運,比我們想像中的,更要緊緊相連。
那一晚,我在慶祝氣氛熾烈的街上採訪拍照,回到旅館天色已將明。回程途上,伊朗朋友的車子在開闊的高速通道上奔馳,晚風把我的頭髮吹亂,一絲一絲的纏在我的臉上脖子上。車裡大家在一夜狂歡後都沉默起來,我轉頭望向車窗外。夜色迷茫,山下鄉郊燈火零落,然而極目遠望,地平線上太陽的微光已經把黑夜盡處的天空薰染成一片美麗的,層層疊疊的藍。我在想,這個國家的命運說不上可以一夕改變,但唯有希望令人有在困境中不斷掙扎的堅韌。那就足夠。
我沒有為自己留影記下這個夜晚,也許所有記憶都會隨時間逐漸流逝。但我相信我走過的路,聽過的故事,為他人的幸福與痛苦曾有過的觸動,都會在某一個暗夜裡,穿透重重疊疊的或許庸常不已的日子,回至眼前。在往後的時日,皆如黑夜裡倏然而至的,耀眼的光芒,一切想像終歸能夠成真的見證。
做個自由人
我在美國作家梭羅的名著《湖濱散記》中,讀過這麼一個源自波斯的故事。「我在設拉子的酋長薩迪的《薔薇園》裡讀到:『他們詢問一位智者:至高無上的神創造了許多高大成蔭的名樹,但卻沒有一棵被稱為azad,或自由,只有柏樹例外,但是柏樹卻又不結果子,這其中有何奧秘嗎?』他回答說:凡樹皆有其相應的果實和特定的季節,適時則枝繁葉茂,鮮花盛開,逆時則枝葉枯敗,百花凋謝;柏樹與此不同,它永遠茂盛;azads,或宗教獨立者,就屬於這種特性—你的心不要放在流轉不居的事上;因為Dijlah,或底格里斯河,在哈里發部落絕種以後,仍將流過巴格達:如果你的手上富有,那麼要像棗樹一樣大方;但是如果你甚麼都給不起,那麼就像柏樹一樣,做一個azad,或自由人。」
每當有人問及是甚麼把我推出家門走向世界,我總是說,那些基因早就在血液裡,是我無法背逆的。放棄了物質生活的穩定,卻尋回精神生活的堅實,最少是一場公平的交換。說不斷的流離是為了追尋真相還是自我實現,都是後設的目標罷了。然而走過了千萬里路,山翻越了一個又一個,卻總念及一個我稱為家鄉的東亞小島,一個既擠擁又喧鬧,毫不可愛的城市。我總相信國際經驗有其可堪借鏡與觀照之處,我們的命運,這個世界的命運,早已緊緊相扣,只是我們毫不自知。如此就更相信所做一切,在我心愛的香港走向民主自由的路上,可能還是可以作出一點微小至極,但或是不可有缺的貢獻。
本書的文章,大部分出自我在《明報》星期日生活一個月或一篇或兩篇的供稿,有些來自《主場新聞》和其他刊物,經重新校訂後收錄。也有從未發表的文章,令這本書結構更緊密更完整。非常感謝《明報星期日生活》編輯黎佩芬小姐,香港的報章版面如此珍貴,黎小姐卻總是放心地把版面交給我,寫冷門至極的國際與正義議題,從不曾過問內容與觀點,也不曾刪減我的稿件。這種自由與信任,在今日的香港,尤其教人珍惜。
感謝為我撰寫導言的張翠容小姐、序言的沈旭暉教授。張小姐的作品為香港人擴闊了對於世界與新聞工作的想像;沈教授則令國際關係這門看似遙遠的學科變得平易近人。各種時代的刻痕如戰爭或恐怖主義都自有理性因由,唯有知識可以破除迷障,唯有人文關懷能戰勝恐懼。有他們為拙作撰序是莫大榮幸。也感謝為我寫友情序的周澄小姐。我們是無所不談的好朋友,也是互相鼓勵,激發進步的同儕。
也有許多在這條路上一直幫扶鼓勵的朋友,感激之情筆舌難宣,唯願你們知道我從遠方寄出的明信片,就是我難以啟齒的一點心意,特別感謝我的才女好友何雪瑩小姐。最後必須感謝父母家人與親愛的人,給了我自由。這本書,是自由的土壤上,開出的小花。
再漫長的旅途也有終站。混亂卻又同時無比澄明的行旅時日告終,我回到熟悉的香港,睡在熟悉的床上,過熟悉的生活。然而卻總忘不了如浮光掠過的每張真誠的笑臉,在異鄉偶遇一夕長談時,在桌上氤氳四溢的甘甜果茶,清真寺肅穆禱聲劃破清晨寧靜的時刻,沙漠夜空上的一挑叫人想起一千零一夜的阿拉伯之月。有時我痛恨自己的文字過分拙劣,無法描述我心裡曾有過的無以言說的觸動。也許我能夠做的,只是謙卑真誠地紀錄我的見聞與感受。其餘種種,請滄海世界,為我作證。
導言
民主漫長路
張翠容
近年,有一位年輕女生勤於筆耕,而且題材廣泛,從論政香江到國際大事,既有觀點也有角度。或許你未必同意她,但一定會對她的流暢文字,以及她的思考能力,留下印象。
陳婉容,我們一直沒有機會認識見面,過去我也只是偶爾在報刊上見過她的名字,直至她邀請我為她這本書寫序,我才認真閱讀她的文章。
在閱讀過程中,內心不無感動,怎麼香港還有這樣一位年輕人,如此熱愛文字和國際事務,並努力不懈,一邊遊走,一邊觀察,她很用心地在國際脈絡中,回看香港這個我們一起擁有的城市。
現在,她把這幾年散見於各報刊網路的文章,結集成書,名為《茉莉花開—中東革命與民主路》。
原來,我們有著對中東地區的共同感情。不過,由於這本書是以不同報刊文章結集,既觸碰中東地區,也談論其他地方和民族的民主爭扎,亦有書評,難免有點失焦。因此,我希望補充一下,茉莉花開之後的中東國家,民主轉型的難題。
當二零一零年年底突尼西亞爆發茉莉花革命,原本以為是茉莉花開,結果變成潘朵拉盒子,世俗與宗教之間,又或宗教派系之中互相傾軌,民主轉型陷於困局。
例如埃及,一開始進入民主的轉型期,走了一、兩步便威權回歸,陷入報復與仇殺,究竟哪裡出了錯?這令我們不得不思索,在轉型期中所出現的陷阱,埃及人民於一一年借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之勢,也發動了一場浩浩蕩蕩的抗爭行動,推翻超過半世紀的軍人獨裁統治,開拓通往民主之路,令整個國際社會為之觸目。歷史給予了埃及一個機遇,可惜這個機遇到目前為止,不僅沒有開花結果,反之有走回頭路之勢。
一直把持埃及政治的埃及軍方,於一三年中推翻來自穆斯林兄弟會的民選總統穆爾西後,繼續追殺兄弟會成員,而法庭其後還宣判了五百二十九名兄弟會成員死刑,為人類歷史首例,使人吃驚。
當埃及軍方頭目塞西將軍宣布參與總統大選,出奇地他深受不少民眾支持。我於一二年再度往埃及採訪時,發覺老百姓面對不停的示威抗議和社會爭拗,早生厭倦。有一位退休教師更坦言告訴我,他們不是追求民主,民主,是外界對他們的期許,但他們只希望生活好過一點。他相信唯有軍方才可為社會帶來安定,他支持軍方回歸。
我聽後,實不無傷感。埃及民主轉型運轉不過來,人們心生疑惑,壞民主是否不如好權威?
這令我想到,當年美國革命之父富蘭克林在結束制憲會議後,有美國老百姓問他:我們現在是共和國還是君主國?富蘭克林回說:當然是一個共和國,如果你們可以保住它的話。
民主漫漫長路,保得住它必須避免掉進轉型陷阱。甚麼叫轉型陷阱?這意指在民主轉型過程中,很容易讓既得利益者擋住去路,無法讓民主進一步深化。
在中東地區,埃及和其他後革命的中東國家,現在所面對的民主改革轉型死結,因為當中還夾著宗教因素和地緣政治,令死結更難解開。
我以此作為婉容這本書一個引子。我期待這位年輕女生,將來有更深刻的觀察,與我們分享。
(張翠容為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
為甚麼我們要認識俄羅斯和伊朗……
沈旭暉
陳婉容在大學時期是我的學生,後來再聽到她的名字,是在報章讀到她的文章,當時儼如一個年輕版張翠容。後來她的身份又成為了「南韓駐港領事館外交部國際政治研究員」,和我做訪問。後來又發現,她寫的國際關係評論愈來愈多,而且大都是關於一般人忽略的第三世界;再後來還知道,她打算到海外進修,如無意外,大概很快成行。
其實,這樣的生活,放在其他地方,可說是平常不過。但當我們生活的時空名叫「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她的人生選項,卻顯得卓立獨行。無論是哪個世代,這裡都習慣了朝九晚六的辦公室工作為常規,任何走出溫室的決定,都彷彿驚世駭俗,「讀國際研究來做甚麼」,也就成了比「為甚麼要讀書」更理直氣壯的「人生智慧」。陳婉容走到今天,卻證明了路是人走出來的,為大眾帶來國際視野不等於沒有市場,不呆在同一個辦公室也不等於三餐不繼。這樣的訊息,比主旋律的成功故事更發人深省。
更重要的是,本書收錄的文章,並非為了國際而國際,並不「離地」,反而對香港有很大參考價值。例如普京在俄羅斯的維穩方式,「伊朗式民主」的設計和智慧,我們都似曾相識,一般人卻說不出背後的所以然。要是沒有相應的國際視野,就是要為身旁的「在地」議題把脈,也容易斷錯症。我們在學院常有比較政治課,但真的能做到比較政治的人卻寥寥可數,反映這條路是孤獨的。無論陳婉容要成為戰地記者、還是更在意為港人提供通識智慧,都希望她能堅持下去,為我城的國際研究再放異采。
(沈旭暉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序二
闖蕩世界的渴望
周澄
話說這一篇短短的序,拖延了兩三個月也未能動筆。期間婉容當然追殺不懈,我也老實地答她,「除了愛慕之情,我實在想不到要寫甚麼啊……」。素以霸氣迫人為名的婉容,聽罷當然不收貨。但我知道,婉容等了一等,還是要把這空出的一頁留給我,無非是為了感銘彼此的情誼。
知道陳婉容這個大名,是在中大讀書的時候。她比我早畢業,讀書時我們並不相識,只是在某些友儕圈子聞說過她頗為高傲,僅此而已。當時偶然接觸到她的文字,莫名地感到投緣,但知道她是名校高材生,又經常周遊列國,自覺是兩個世界的人,所以未有高攀。一如對窗的鄰人,偶爾暗瞥觀照,不求妄越距離。
大學時代,一直忙於各樣學生組織與社運參與,基本上沒有甚麼閒錢去遠行,名副其實就是一條「窮港燦」。但儘管如此,從小愛看世界歷史故事、外國電影電視的我,從來都沒有忘卻闖蕩世界的渴望。作為一些人口中的「左膠」,我也對戰爭與殖民歷史斑駁的發展中國家格外有興趣。畢業後,因此把心一橫,去了菲律賓為一間非政府組織工作。本來計劃是留一年,但工作期間有點不盡如意,留了半年就決定回港,從新計劃自己的路向。回港前,我不知為何,竟然鼓起勇氣,透過facebook給婉容寫了一個不長不短的訊息。客套話當然有,但大家都竟然分享了一些當時對理想、對位置的困惑。如今看來,那些互勉點到即止,我當時沒有想過之後會和婉容成了密友,由國際時事本土議題、人生志向旅行大計到女生之間的私密八卦無話不談。
自小喜歡收到朋友在路上寄出的明信片勝於一式一樣的手信,但誠如前述的原因,我一直是收件人遠多於有機會寄予朋友。那時還未熟稔,厚著臉皮請婉容寄明信片給自己,她的旅途閱歷與流麗的筆跡徒添重量。因此,到我也開始不時獨自遠行的時候,我也沒有忘記在路上給她寫明信片。一次,我大意答謝她啟發我有更多勇氣去跨越未知的疆界,後來她割愛將她在格魯吉亞買回來的史太林叔叔珍藏明信片寄給我,其中一句是「其實你也影響了我很多」。她常說,在認識我之前,她很討厭處女座,因為處女座不論男女,都無一例外是尖酸挑剔、斤斤計較的完美主義者。但她說,我的完美主義卻是待人以寬,偏偏執著挑剔自己、鑽牛角尖,忽視自己的優點。
知道婉容將過去的文章重編出書,著實為她高興。推薦的話也不用我說了,讀者自會知曉。假若到我將來也獨立著作成書之時,也必定有一版留給她。(不過屆時,希望她不會像我一樣拖延吧,哈哈。)
自序
自由的狐狸
哲學家伯林(Isaiah Berlin)說過,知識分子有兩種,一種是狐狸,一種是刺蝟。古希臘寓言有云「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the fox knows many things, but the hedgehog knows one big thing)—所謂術業有專攻,要做好學問,似乎必然要做刺蝟;但人亦貴自知,如果天生就是狐狸,對甚麼事情都好奇心過了頭,沒有辦法心無旁騖地鑽研一件事情,那麼,當一隻稱職的狐狸,也許就是我之所能做到最好的事了。讀書時期以為自己一目十行過目不忘的本領很了不起,長大了就自知其實沒有甚麼驚天動地的才華,才能甚多但學不見得有專精,要將勤補拙又受天生慵懶性格所限,所以且行且書,在紙上流浪的生活,倒也快活。能夠攀越自己的限制自是強人,然而做自己所喜歡的事情,而且用心地做,心懷純粹不計後果地做,也不見得是軟弱吧。
這本小書就是我當一隻狐狸的思考筆記。這些年來,反覆從一道邊界跑到另一道邊界,從一本書翻到另一本書,重重複複幾乎完全沒有計劃的積累,原來畢竟有所造就,那些見聞與知識,在某種時刻竟有機會連結起來,成就我不曾想像的事。一年半以前,從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無心插柳地栽進寫字生涯的我,絕對想像不到在短短五百多天之後,第一本著作就會出版,而主題正是我心所繫的中東,一片在他人眼中神秘甚至野蠻的大地。
收到出版社邀約後,我嘗試在中東的瘋狂與喧鬧之中抽離,整理我關於伊斯蘭世界政局的評論文章與記事。這才驟覺書寫伊斯蘭世界,從來不是容易的事。大學時代,我重重複複的讀了薩依德(Edward Waefie Said)的著作,記得他在《遮蔽的伊斯蘭:西方媒體眼中的穆斯林世界》(Covering Islam,「Covering」一字是歧義,兼有「報道」及「遮蔽」之意)裡說過:「沒有任何一種宗教或文化群體會像伊斯蘭教一樣,被斬釘截鐵地認定將對西方文明造成威脅。」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加上九一一以降主流媒體的渲染,又為這種成見多添了幾分怖慄想像。
二零一一年「茉莉花革命」震動了整個世界,讓人重新思考伊斯蘭主義(political Islam)與憲政民主結合的可能;兩年後埃及再次變天,初始萌芽的民主政體又似被推翻,歷史到底還是沒有終結。然而這一場革命終於叫世人體認,所謂伊斯蘭世界的同質性不過是想像的產物,這片土地有原教旨主義者,有心向民主自由的革命分子,有提倡政教分離的世俗主義者,也有人相信政教合一或大阿拉伯主義,才是伊斯蘭世界對抗新殖民主義的利器。這片被稱為烽火大地的土地如同世界縮影,值得我們花更多心力去觀察和關注。
第三波民主化從一九七四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起,把半個地球捲進了走向民主的道路之上;既然連許多「專家」—正如薩依德說,太多「專家」喜歡就伊斯蘭議題說話,但那些人根本不了解伊斯蘭世界—眼中永遠不會接受民主的中東,也在茉莉花革命中迎向了民主化,香港一定不會是例外。過去十五年來,香港一直處於政制改革爭議的風口浪尖上,社會抗爭一場接一場,反對派分分合合,一片混沌。從脫殖到尋找身分認同,以至嘗試從這種半民主的曖昧不明狀態走往真正的民主,香港要走的路,其實跟許多普世經驗互為鏡像。所謂國際,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遙不可及,那麼事不關己。
普世經驗互為鏡像
茉莉花革命從北非始席捲阿拉伯世界,然而當中有成有敗;敘利亞從此陷入內戰,利比亞在內亂後成為了人道干預的對象,埃及似乎成功,但及後又證實根基不穩,突尼西亞偶有騷亂但似乎又在慢慢建立民主政制。成敗的因素的除了是這些國家各自的歷史發展階段,迥異的文化、經濟脈絡,公民社會成熟程度的分別,還有政府在威權轉型向民主之時的種種政策。從埃及的例子,我們或許可以理解所謂堅實的民主願景,還有茁壯的公民社會,對於穩定的政體轉型有何意義;從南非的例子,我們可以思考,香港如果有全民制訂憲法的機會,應該用怎樣的政治哲學邏輯去制定憲法。這些都是跟現今香港時局息息相關的議題。在彼方,俄羅斯威權政府控制新聞自由、鏟除異己、鐵腕鎮壓分離主義地區,但俄羅斯國民卻又似乎保有了一定的自由,我們或許可以從此窺視所謂假民主的危險性。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如果不去深入理解,香港人對於別人所擁有的民主自由再羨慕再嚮往,都不免廉價。
然而伊斯蘭世界的複雜,也許不是我這個如霧水般短暫勾留的旅人能夠理解的。我懷著對古文明與亞伯拉罕三教發源地的嚮往,懷著為伊斯蘭平反的目標踏足他們的世界,又讀了許多書和論文去寫一篇又一篇煞有介事的評論。然而我畢竟是個與他們的歷史與生活割裂的局外人,唯有提醒自己,至少要保持文字的純粹與理性,哪怕文字有多麼拙劣,仍誠實地記下所見所聞。我從來覺得自己是個無可救藥的世界主義者,認同東亞學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那套國族主義建構論,然而坐在敘利亞難民面前,聽他們述說無家無國的苦難;聽庫爾德人、巴勒斯坦人說為民族犧牲在所不惜,卻驟覺我或許不過是個天真的左派,忽略了國家民族的正當性,甚或是應然性。現實與書本的距離比我想像中更遙遠,然而就是這樣的,反覆建立論證再推翻重構的過程,佐證了一個人走上千萬里路的意義。
隻身採訪伊朗大選
二零一三年六月,我在炙熱的伊朗隻身採訪總統大選。高考時代因為想當記者,放棄了法律系,畢業後卻沒有投身傳媒工作。結果第一次當記者就是在萬里之外的,封閉的伊朗,不止語言不通,伊朗政府對新聞工作者的厭惡與壓制也是惡名昭著。行前兩天還在處理學業,耐不住跟好友訴說準備不足的擔憂,他說的話卻成了推動我前行的力量:「橫衝直撞不怕死的勇氣,就是你最好的特質。」於是戰戰競競的接下任務,懷著幾乎是莽撞的拼死的勇氣,以另一種身分重返這個美麗的國度。
魯哈尼勝選當晚,我在街上央求的士司機送我去德黑蘭城西的Valiasr Square。旅館老闆擔心我,跑出來替我跟司機溝通。上街慶祝的車輛已經擠滿了往Valiasr的主要道路,沒有司機願意在路上擠上數個小時。我在旁邊雙手合什,彎下身子說:「拜託,請你給我開個價錢,我真的要去。」司機聽不懂英語,但大抵還是聽到了我語氣中的央求意味。最後成交,十二萬伊朗里爾。我跳上車,跟旅館老闆穆薩維先生說再見。他看著我關上車門,在車窗旁細細叮囑:多晚回來都好,旅館前台有人會給你開門。萬事小心,別往人群裡鑽。
我始終沒有坐著這的士到Valiasr Square。半途不到,車子就在街上塞了近四十五分鐘。我走下車拍攝隨意在街上就跳起土耳其舞的男生,一個伊朗家庭熱情地請我上車跟他們同行,我給的士司機付了錢就跳上他們的車,於是少女Marzi和她的家人就成為了我的採訪翻譯。他們知道我來採訪,更是興奮莫名,一直對車外的其他人高呼:「我們車裡有個記者!」其他人聽見都湧到車窗旁,舉起手中的海報或標語要求我拍他們。我們一路隨著伊朗吵嚷的流行音樂舞動,看人們不時鑽上車頂,跟隨其他慶祝民眾高呼:「伊朗萬歲,釋放穆薩維!」我鼻子隱隱的發酸:一次勝利並沒有讓伊朗人忘記四年前的傷痛。成千上萬的慶祝民眾裡只有我一個外國女子,在人群中跟他們一起慶祝難得的一次勝利。縱在異鄉為異客,但我和伊朗人民對於民主、幸福與自由的追求,豈能說不是同樣。這世界的命運,比我們想像中的,更要緊緊相連。
那一晚,我在慶祝氣氛熾烈的街上採訪拍照,回到旅館天色已將明。回程途上,伊朗朋友的車子在開闊的高速通道上奔馳,晚風把我的頭髮吹亂,一絲一絲的纏在我的臉上脖子上。車裡大家在一夜狂歡後都沉默起來,我轉頭望向車窗外。夜色迷茫,山下鄉郊燈火零落,然而極目遠望,地平線上太陽的微光已經把黑夜盡處的天空薰染成一片美麗的,層層疊疊的藍。我在想,這個國家的命運說不上可以一夕改變,但唯有希望令人有在困境中不斷掙扎的堅韌。那就足夠。
我沒有為自己留影記下這個夜晚,也許所有記憶都會隨時間逐漸流逝。但我相信我走過的路,聽過的故事,為他人的幸福與痛苦曾有過的觸動,都會在某一個暗夜裡,穿透重重疊疊的或許庸常不已的日子,回至眼前。在往後的時日,皆如黑夜裡倏然而至的,耀眼的光芒,一切想像終歸能夠成真的見證。
做個自由人
我在美國作家梭羅的名著《湖濱散記》中,讀過這麼一個源自波斯的故事。「我在設拉子的酋長薩迪的《薔薇園》裡讀到:『他們詢問一位智者:至高無上的神創造了許多高大成蔭的名樹,但卻沒有一棵被稱為azad,或自由,只有柏樹例外,但是柏樹卻又不結果子,這其中有何奧秘嗎?』他回答說:凡樹皆有其相應的果實和特定的季節,適時則枝繁葉茂,鮮花盛開,逆時則枝葉枯敗,百花凋謝;柏樹與此不同,它永遠茂盛;azads,或宗教獨立者,就屬於這種特性—你的心不要放在流轉不居的事上;因為Dijlah,或底格里斯河,在哈里發部落絕種以後,仍將流過巴格達:如果你的手上富有,那麼要像棗樹一樣大方;但是如果你甚麼都給不起,那麼就像柏樹一樣,做一個azad,或自由人。」
每當有人問及是甚麼把我推出家門走向世界,我總是說,那些基因早就在血液裡,是我無法背逆的。放棄了物質生活的穩定,卻尋回精神生活的堅實,最少是一場公平的交換。說不斷的流離是為了追尋真相還是自我實現,都是後設的目標罷了。然而走過了千萬里路,山翻越了一個又一個,卻總念及一個我稱為家鄉的東亞小島,一個既擠擁又喧鬧,毫不可愛的城市。我總相信國際經驗有其可堪借鏡與觀照之處,我們的命運,這個世界的命運,早已緊緊相扣,只是我們毫不自知。如此就更相信所做一切,在我心愛的香港走向民主自由的路上,可能還是可以作出一點微小至極,但或是不可有缺的貢獻。
本書的文章,大部分出自我在《明報》星期日生活一個月或一篇或兩篇的供稿,有些來自《主場新聞》和其他刊物,經重新校訂後收錄。也有從未發表的文章,令這本書結構更緊密更完整。非常感謝《明報星期日生活》編輯黎佩芬小姐,香港的報章版面如此珍貴,黎小姐卻總是放心地把版面交給我,寫冷門至極的國際與正義議題,從不曾過問內容與觀點,也不曾刪減我的稿件。這種自由與信任,在今日的香港,尤其教人珍惜。
感謝為我撰寫導言的張翠容小姐、序言的沈旭暉教授。張小姐的作品為香港人擴闊了對於世界與新聞工作的想像;沈教授則令國際關係這門看似遙遠的學科變得平易近人。各種時代的刻痕如戰爭或恐怖主義都自有理性因由,唯有知識可以破除迷障,唯有人文關懷能戰勝恐懼。有他們為拙作撰序是莫大榮幸。也感謝為我寫友情序的周澄小姐。我們是無所不談的好朋友,也是互相鼓勵,激發進步的同儕。
也有許多在這條路上一直幫扶鼓勵的朋友,感激之情筆舌難宣,唯願你們知道我從遠方寄出的明信片,就是我難以啟齒的一點心意,特別感謝我的才女好友何雪瑩小姐。最後必須感謝父母家人與親愛的人,給了我自由。這本書,是自由的土壤上,開出的小花。
再漫長的旅途也有終站。混亂卻又同時無比澄明的行旅時日告終,我回到熟悉的香港,睡在熟悉的床上,過熟悉的生活。然而卻總忘不了如浮光掠過的每張真誠的笑臉,在異鄉偶遇一夕長談時,在桌上氤氳四溢的甘甜果茶,清真寺肅穆禱聲劃破清晨寧靜的時刻,沙漠夜空上的一挑叫人想起一千零一夜的阿拉伯之月。有時我痛恨自己的文字過分拙劣,無法描述我心裡曾有過的無以言說的觸動。也許我能夠做的,只是謙卑真誠地紀錄我的見聞與感受。其餘種種,請滄海世界,為我作證。
導言
民主漫長路
張翠容
近年,有一位年輕女生勤於筆耕,而且題材廣泛,從論政香江到國際大事,既有觀點也有角度。或許你未必同意她,但一定會對她的流暢文字,以及她的思考能力,留下印象。
陳婉容,我們一直沒有機會認識見面,過去我也只是偶爾在報刊上見過她的名字,直至她邀請我為她這本書寫序,我才認真閱讀她的文章。
在閱讀過程中,內心不無感動,怎麼香港還有這樣一位年輕人,如此熱愛文字和國際事務,並努力不懈,一邊遊走,一邊觀察,她很用心地在國際脈絡中,回看香港這個我們一起擁有的城市。
現在,她把這幾年散見於各報刊網路的文章,結集成書,名為《茉莉花開—中東革命與民主路》。
原來,我們有著對中東地區的共同感情。不過,由於這本書是以不同報刊文章結集,既觸碰中東地區,也談論其他地方和民族的民主爭扎,亦有書評,難免有點失焦。因此,我希望補充一下,茉莉花開之後的中東國家,民主轉型的難題。
當二零一零年年底突尼西亞爆發茉莉花革命,原本以為是茉莉花開,結果變成潘朵拉盒子,世俗與宗教之間,又或宗教派系之中互相傾軌,民主轉型陷於困局。
例如埃及,一開始進入民主的轉型期,走了一、兩步便威權回歸,陷入報復與仇殺,究竟哪裡出了錯?這令我們不得不思索,在轉型期中所出現的陷阱,埃及人民於一一年借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之勢,也發動了一場浩浩蕩蕩的抗爭行動,推翻超過半世紀的軍人獨裁統治,開拓通往民主之路,令整個國際社會為之觸目。歷史給予了埃及一個機遇,可惜這個機遇到目前為止,不僅沒有開花結果,反之有走回頭路之勢。
一直把持埃及政治的埃及軍方,於一三年中推翻來自穆斯林兄弟會的民選總統穆爾西後,繼續追殺兄弟會成員,而法庭其後還宣判了五百二十九名兄弟會成員死刑,為人類歷史首例,使人吃驚。
當埃及軍方頭目塞西將軍宣布參與總統大選,出奇地他深受不少民眾支持。我於一二年再度往埃及採訪時,發覺老百姓面對不停的示威抗議和社會爭拗,早生厭倦。有一位退休教師更坦言告訴我,他們不是追求民主,民主,是外界對他們的期許,但他們只希望生活好過一點。他相信唯有軍方才可為社會帶來安定,他支持軍方回歸。
我聽後,實不無傷感。埃及民主轉型運轉不過來,人們心生疑惑,壞民主是否不如好權威?
這令我想到,當年美國革命之父富蘭克林在結束制憲會議後,有美國老百姓問他:我們現在是共和國還是君主國?富蘭克林回說:當然是一個共和國,如果你們可以保住它的話。
民主漫漫長路,保得住它必須避免掉進轉型陷阱。甚麼叫轉型陷阱?這意指在民主轉型過程中,很容易讓既得利益者擋住去路,無法讓民主進一步深化。
在中東地區,埃及和其他後革命的中東國家,現在所面對的民主改革轉型死結,因為當中還夾著宗教因素和地緣政治,令死結更難解開。
我以此作為婉容這本書一個引子。我期待這位年輕女生,將來有更深刻的觀察,與我們分享。
(張翠容為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