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浮生
在他口中,童年一片慘淡。
那時怎會知道,命運是以怎樣的形式,影響一個人。
從呱呱墜地,到睜開雙眼。
你見浮生,你是浮生。
一、伊始
降世的嬰孩,十有八九要啼哭。睜開眼睛,看到的風景迥異。
智慧混沌未開,所有朦朧的念頭形成於孩提的記憶。
忘了昨天午飯的味道,卻能記起兒時一頓美味的色澤;翻查通訊錄才能想起誰的名字,卻能對著舊照片如數家珍地報出他們的糗事;在K T V 裡吼叫著半生不熟的流行歌曲,卻搜不到往昔銘記的第一支旋律。
小時候啊,活得最不經意,不知昨日不問明天,卻悠悠然地成為一個烙印。它映照今後的成長,種下深深的情結。
彷彿人的所有天賦稟性都是與生俱來的,帶著萬變不離其宗的個人色彩,一直扎向生命盡頭。也有人說,童年的富有或貧窮、熱鬧或孤獨,都在潛移默化地催逼出獨特的個性。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二日,香港北岸,灣仔。
一個嬰孩降生在一幢五六層高的宅子裡。六個兄弟姐妹、兩個傭人,還有一個已經癱瘓了的外婆。
他是張國榮,剛降生時取名為張發忠,在家中排行老十。老三、老四和老九很小的時候就夭折了。九哥恰恰是死於九月十二日,許多人說,發忠應該是老九轉世來的。
這麼多子嗣,張家算是人丁興旺。這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香港,實在是稀鬆平常。
如果想得到足夠多的嬌寵,要麼你是獨生子,要麼排行老幺。張國榮是後者,卻是個孤獨的老幺。
有兄弟姐妹總是好的,學齡前便有人做伴,可以結夥對抗父母,手拉手肩並肩為“一丘之貉”。但大姐和二姐最投機,五姐和六姐年齡相當,七哥和八哥在一起。張國榮跟頭上的八哥就相差八歲,大姐大他十八歲之多,在年齡層上已是孤立無援了。
“以前的樓房面積都較大,平時都很寧靜。就算很多客人來了,我自己一個人在房裡,他們都不知道。但我也不會大吵大鬧說沒大人陪我玩。這算是無聲的抗議吧。”張國榮說。
寂寞與否,應該是童年的第一意識。對於貧富家世,其實並無太多概念。
要是非論起貧富來,張國榮算是幸運的。他從小就能享受中產階級的生活質量,沒有經歷食不果腹的痛苦。
父親張活海是洋服店的老闆,白手興家創業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香港中環旺舖地段,經營的是荷里活潮流服裝。“張活海”三個字繡在大招牌上,就是讓顧客趨之若鶩的理由。
一次,荷里活著名演員加利.格蘭來到張活海的店裡,要定製兩件名貴的上衣,其中一件必須用頂級羊絨製成,還要求在四十八小時內趕製出來,連料子帶工錢一共兩千多港幣。兩天後,張活海捧著縫製好的兩件衣服來到加利.格蘭入住的酒店。待穿上後,張活海問他是否滿意,加利表示非常滿意。這時,張活海放心地從口袋裡掏出四百港幣,坦言由於頂級羊絨缺貨,用的是次級羊絨。本打算如果他不滿意,就把收了的錢全數退還。加利很開心,認為張活海是個“誠實的商人”,允諾他回去後會多介紹顧客登門。於是,就有了馬龍.白蘭度、威廉.荷頓等荷里活巨星的接踵而至。
按張國榮的話說,父親是一個極其有生意頭腦的商人。
名聲遠揚,加之張活海賣的衣服都是荷里活最流行的時尚款,眾多明星相繼光顧。順理成章地,這家洋服店成為服裝界和演藝界的紐帶。張國榮日後便完成了這樣的跨界 ── 學的是紡織,搞的是演藝。
家庭環境未必直接決定個性,卻影響著一個孩子的品位。遠離經濟核心的地段會孕育出“鄉非殺馬特”(內地網絡用語,指鄉村非主流),暴發戶的子嗣也迷戀穿金戴銀。作為一個洋服店老闆的孩子,所接觸的時尚文化,當然是最前沿的。見得多了,氣質也能被熏陶得優雅,張國榮的審美觀就是這樣一點點形成的。他幫父親送貨的那段日子,目睹了香港繁華的淺水灣,腦海裡就浮現了開著跑車在街上兜風的畫面。這頗有文藝格調的幻想,在日後也成為現實。
“我見過很多氣質優雅的人,自那開始便嚮往生活上的享受。”
“Tailor King”是張活海的綽號,翻譯過來就是裁縫之王,但張國榮對此嗤之以鼻,覺得好土,像外國人似的。
他和父親的關係並不親近。如果換到現世,他足以和無數人“拚爹”,還是個有錢、有名望、有手藝的爹,但他們父子的情感是缺失的,這對一個孩子而言是無法補救的。張活海工作忙碌,一年到頭除了節假日很少回家。
張國榮成名後,曾經這樣回憶道:“很多人都認為,我小時候不跟爸爸媽媽一起住是不大可能的事。但偏偏碰巧就這麼有可能發生在你們熟悉的我的身上。現在我說這些可以用過去時了,可能就沒有那種心酸,沒有那種不開心了,但現在提起來心裡還是好像有根刺,其實現在都人到中年了,就不應該太在意自己的過去了。”
父母在中環的店舖有兩層樓,他們住在樓下,樓上是工廠,這樣的安排是為了管理工人做工,卻也犧牲掉了陪孩子成長的樂趣。
“那時的大人都不太關心孩子的心理。或者我沒那麼幸運吧!總之我爸媽不太理我們心裡在想甚麼,或者他們也沒那麼開通。那時父母說甚麼,孩子都要照做,當時也沒甚麼禁止虐待兒童的機構可以投訴,我並不是說父母虐待我們。小孩子給媽媽打其實是一種好事,但我連被打的機會都沒有,更不用渴望星期天我爸爸帶我去花園照相了。”
那一年,張國榮六歲,讀一年級。當時的他已經生得非常漂亮,一雙大眼睛,嘴唇紅紅的,看著跟個洋娃娃似的。他來到爸爸的辦公室,碰到幾個伯伯和叔叔。面對這麼漂亮的小朋友,長輩們心生憐愛,不禁問道:“仔仔,爸爸有沒有請你飲茶?”
“飲茶”與其說是飲食習慣,莫不如稱之為一種相處形式。在北方人看來,那意境應該是閒散放鬆的,滿滿的溫情氛圍。
這對他們父子當然不可能。所以,張國榮回答了一句很怪的話:“我們不認識。”
事後回想起來,張國榮已經記不清父親對這話作了何種反應,大概是沒有反應。如果有一絲一毫的慍怒,小朋友都會竊喜地記在心裡 ── 畢竟這代表父親在乎他啊。
直到後來,張活海對兒子的態度都沒有太多改變。那個年代流行到游泳池游泳,張活海酷愛游泳,是冬聲冬泳團的團長。那個時代的香港,游泳池並不多,張國榮經常和用人各花兩毛錢到西環的一個游泳池游泳。有一天,他們不巧在石階上碰見了張活海和他的一眾朋友,張活海看到自己的兒子就好像看到好朋友的兒子一樣,摸了摸他的頭,然後塞給他一大把錢。張國榮只能把這錢移交給傭人,不知如何是好。
父子關係的親疏,對孩子的心理影響極大。張活海卻成了張國榮心裡的反面教材,提到父親,他反覆用到的詞是“自私”。
即便關係疏離,張國榮對父親除了隱隱的恨意外,也有尊重和愛。他說,父親對他的愛是無條件的,只是這愛不知如何表達,也不想學會表達。
零星的記憶裡,父親曾經給他買過新衣服,也帶著他到唱片店買唱片,讓他享受自己喜歡的音樂。
所以,張國榮曾這樣說:“父母對孩子的影響會是一生一世,我今日的事業,是父親間接的激勵,甚至我家中各兄弟姊妹的婚姻也受到父親的影響,包括我自己在內。”
又愛又怨。
二、女人
在誤拍三級片《紅樓春上春》時,已有人評價張國榮跟賈寶玉是極為相似的,天生尤物,風華絕代,命運都是一樣的大起大落。賈寶玉的一生是離不開女人的,胭脂濃香如影隨形,這一點跟張國榮大相徑庭。
自幼開始,家裡三個年長的女性就鋪陳出了三段命運,搖曳於塵世,各自孤獨。
張國榮的母親潘玉瑤很早就跟張活海結婚了,幫忙打理一些日常的瑣事,然後就生了“一窩孩子”。張家有兩房人,另一房並無所出。
潘玉瑤的心裡是極不平衡的,年輕的時候曾經向張活海索要家用,卻遭到一口回絕。另一房姨太太也不是好惹的主兒,兩女共侍一夫,爭風吃醋是肯定的。因為慪氣,繼母甚至拿尿淋過張國榮。
張活海在感情上並不是個安分的人,用張國榮的話說,就是“頗中意女人”,拈花惹草,招蜂引蝶。他經常到尖沙咀的半島酒店租房,約一些美麗的女士聊天。潘玉瑤為此鬱鬱寡歡,甚至找來私家偵探調查張活海。夫妻感情的不斷惡化,興許令她覺得嫁錯了人;加之工作忙碌,嗷嗷待哺的子女反而顯得累贅,更別論甚麼母愛了。
有一張舊照,是張國榮五歲時和母親一起拍的 ── 張國榮坐在汽車上,傻笑著目視前方。潘玉瑤在一邊站著,雙手交疊,一隻胳膊倚在車上,盯著鏡頭。微捲的頭髮垂在後頸,大花旗袍裹著豐腴的身材。母子之間並沒有任何親密的動作和眼神的交流,更像是一對陌生人。
在張國榮看來,母親也是自私的,程度遠勝於父親。張國榮長大之後,母子兩個在寶豐大廈一起住,那個時候就已經覺得合不來,更像是一對普通朋友,保持有禮有節的關係。出於孝道,張國榮在經濟上一直支援母親。
張國榮三十二歲那年,母親已經年邁。他把母親接到自己住的來帕路斯海濱的公寓。在傳統家庭中,老母親和兒子的相處,就算不親昵成怎樣,至少也是溫和放鬆的,偶爾拌拌嘴也再平常不過。但潘玉瑤還會小心翼翼地問:“能不能借用一下洗手間啊?”
也許兩個人都試圖付出努力,但錯過了最好的時機。到了這樣的年紀,已經不想再費力挽回甚麼。即便跟母親相處的時日遠比跟父親的多出許多,張國榮卻說,母親對他的愛是有條件的,不同於父親。如果今時今日他不是有所成就的張國榮,這段母子關係怕是會變成另外的樣子了。
淡漠的親情,給張國榮的心理投下了一層陰影,致使他對婚姻關係極其不信任。“如果相愛,沒有這一紙婚姻證明書,一樣可以過得很好;如果要分手,有這一紙婚約也改變不了甚麼。”
他最喜歡的舅舅結婚了,張國榮看著舅母嫁過來,在宴席上號啕大哭,拚命地用手去抓舅母,肝腸寸斷的樣子讓長輩們不知所措。
親情的缺失究竟能造就甚麼?它至少會是一根刺,永遠扎在心裡。所謂原諒,遙遙無期。
當滿世界都在歌頌母愛的時候,總會有一些形單影隻的孩子,擁抱著無助的童年。
在那棟老房子裡,還有一個女人。她跟張家並無親緣關係,在張國榮看來卻是家裡的一份子。她是傭人,叫六姐。
二○一一年,許鞍華執導,葉德嫻、劉德華主演的《桃姐》上映。影片講述了一對勝過母子關係的主僕情。桃姐是Roger 的傭人,把他從小拉扯大。成年後的Roger 待桃姐如生母,一直照顧她養老,直到最後天人永隔。影片引起轟動之時,張國榮已經離去八年,如果他能坐在電影院裡看到這部片子,一定會淚流滿面。他的性格是感性而寬厚的,何況這故事本就是他自身的寫照。
慈愛溫厚的雙臂攬他入懷,陪他一起玩耍,看著他在游泳池裡嬉戲……如果沒有六姐,張國榮的童年幾乎會徹底暗淡。她在張國榮的生命裡出現了三十四年,看他成長、揚名。當初,張國榮想走演藝道路,由子承父業的“中環十二少”轉戰歌壇,遭到了家裡的強烈反對。在這個關頭,是六姐偷偷地給他經濟上的支持,鼓勵他走自己想走的路。
“六姐的地位恍如歌曲Monica (張國榮成名曲)中的主角,她對我噓寒問暖,把我從小帶大,是健康又愉快的工人。這位工人在我心目中已經不是工人,地位已超越我母親,我非常珍惜六姐,我覺得親密情人失去後可以再找,但如果她突然消失,我指的是百年歸老,我會非常傷心,她是我一生之中對我最好的一個女人。”
對生命的美好領悟,緣於記事之初給你溫熱的人。
跟大多數孩子一樣,童年記憶裡至少會有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你曾以為她出生時便是那個樣子,以佝僂的形態存在。你不理解她在絮叨些甚麼,也不知道她為甚麼行走不靈光,她就是那麼尷尬地活著。
張國榮的外婆六十歲就癱了,平時有用人服侍,伺候她梳洗、飲食。雖然從小就跟外婆一起住,但他們只是“最熟悉的陌生人”罷了。
外婆是個孤獨的老人,很少說話,坐在紫藤椅上,看著孫輩們吵吵鬧鬧,很少有機會看女兒女婿一眼,只知道他們很忙。
外婆的去世,讓張國榮終生難忘。
小學一年級,張國榮放學回家,來接他的照舊是六姐。“十仔,一會兒回家別害怕啊,外婆睡著了。”六姐說。張國榮一頭霧水,仰著臉問六姐說:“甚麼叫睡著了?”六姐愣了一下,語塞了,拉著張國榮的小手繼續走。回到家裡的時候,表哥表姐們全都來了,親戚們匯聚一堂,痛哭流涕。
表哥走過來,說:“十仔,再來看一眼外婆。”
外婆是坐在藤椅上死去的,嘴巴微微張開,腦袋栽歪到一側,皮膚已經呈黑紫色。哭聲在周圍此起彼伏,張國榮盯著外婆的臉,直到有人來七手八腳地收斂,大人們也顧不得哭,跟著一起忙活起來,趕去殯儀館。
這是張國榮第一次感受到神秘的死亡。
眾人的淚水是看得見的,素黑的衣裝是看得見的,安詳的遺體是看得見的,唯有生老病死的深厚意義,需要漫長的時間去體味。
屋子裡少了一個人,這是最直觀的感知。擺弄一下藤椅,薄薄的灰,坐在上面的老人不見了。
身為幼者,當你降臨人間,許多家人都老了,甚至已經垂垂暮矣。
潘玉瑤,張國榮的母親,一個委委屈屈的正房,在不幸的婚姻裡終其一生。她的市儈、無奈與冷漠,碎片式的形象,拼拼湊湊也拼不出“母親”二字。可曾有那麼一時,她願意坐下來,一針一綫地為兒子縫補衣服,看他穿在身上,露出帶有成就感的笑意;可曾有那麼一時,凝望著鏡中白髮,知道大去之期不遠,拉著兒子健碩的臂膀,囑託人生不易?她的心事,已無人知曉。
六姐,漂泊一生沒有定所。在她尚未老去的時候,哺育過這個特別的孩子。情同母子,有些東西卻終究不可代替。她和張國榮,都有各自的孤獨。
外婆,去世如存在一般靜默。所有人都會離開,只是大多數人不是傳奇。在去世前一秒鐘,頭腦裡一幕幕的畫面,將是怎樣的苦樂,又有多少道不出的厭倦、訴不盡的流連?
俱往矣。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張國榮:不如我們從頭來過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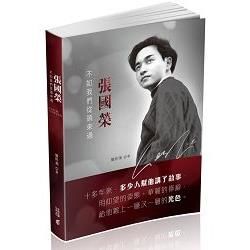 |
張國榮:不如我們從頭來過 作者:關熙潮 出版社: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10-14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89 |
二手中文書 |
$ 360 |
中文書 |
$ 360 |
影視寫真 |
$ 360 |
傳記 |
$ 450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張國榮:不如我們從頭來過
他,不是一夜成名的速食明星,跟所有普通人一般,在荊棘中摸爬滾打,跌跌撞撞地走過青春的迷途。
他,身著浴袍,腳穿拖鞋,唱:“我就是我,是顏色不一樣的煙火;天空海闊,要做最堅強的泡沫。”
他,是十二少,是寧采臣,是擁有白金唱片銷量的巨星,是享譽海內外的當紅偶像。
十多年來,多少人幫他講了故事,用仰望的姿態、華麗的修辭,給他鍍上一層又一層的光色,使他越發遙不可及。
本書講述張國榮從童年時代,到結緣音樂、初涉影視,再到歌壇影壇鑄就輝煌,最後隕落的一段傳奇。作者試圖全面地展示張國榮的一生,從他的成長、生活、音樂、電影以及他的導演夢出發,觸碰到張國榮在榮耀背後所不為人知的內心孤獨與情感掙扎,讓讀者了解更為真實、完整的張國榮。
作者簡介:
關熙潮
1987年生,作家。自2006年從事傳媒行業以來,擔任多家衛視娛樂節目導演,參與影視劇創作十餘部。
新浪微博:@關熙潮
TOP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浮生
在他口中,童年一片慘淡。
那時怎會知道,命運是以怎樣的形式,影響一個人。
從呱呱墜地,到睜開雙眼。
你見浮生,你是浮生。
一、伊始
降世的嬰孩,十有八九要啼哭。睜開眼睛,看到的風景迥異。
智慧混沌未開,所有朦朧的念頭形成於孩提的記憶。
忘了昨天午飯的味道,卻能記起兒時一頓美味的色澤;翻查通訊錄才能想起誰的名字,卻能對著舊照片如數家珍地報出他們的糗事;在K T V 裡吼叫著半生不熟的流行歌曲,卻搜不到往昔銘記的第一支旋律。
小時候啊,活得最不經意,不知昨日不問明天,卻悠悠然地成為一個烙印。...
在他口中,童年一片慘淡。
那時怎會知道,命運是以怎樣的形式,影響一個人。
從呱呱墜地,到睜開雙眼。
你見浮生,你是浮生。
一、伊始
降世的嬰孩,十有八九要啼哭。睜開眼睛,看到的風景迥異。
智慧混沌未開,所有朦朧的念頭形成於孩提的記憶。
忘了昨天午飯的味道,卻能記起兒時一頓美味的色澤;翻查通訊錄才能想起誰的名字,卻能對著舊照片如數家珍地報出他們的糗事;在K T V 裡吼叫著半生不熟的流行歌曲,卻搜不到往昔銘記的第一支旋律。
小時候啊,活得最不經意,不知昨日不問明天,卻悠悠然地成為一個烙印。...
»看全部
TOP
目錄
Chapter 1 浮生
伊始 女人 手足 早熟 浮生
Chapter 2 來者
新路 觸礁 奈何 相印 戀曲 來者
Chapter 3 風起
轉機 並進 緣分 情路 風起
Chapter 4 光華
高歌 揚威 猛進 爭霸 光華
Chapter 5 五年
白色 涅槃 轉生 虞姬 五年
Chapter 6 還夢
天王 寵愛 自我 春光 還夢
Chapter 7 天時
尾站 掠影 理想 熱情 天時
Chapter 8 煙滅
絕唱 偷心 異度 紀念 煙滅
附錄
張國榮人生大事記
張國榮唱片年表
張國榮參演電影表
伊始 女人 手足 早熟 浮生
Chapter 2 來者
新路 觸礁 奈何 相印 戀曲 來者
Chapter 3 風起
轉機 並進 緣分 情路 風起
Chapter 4 光華
高歌 揚威 猛進 爭霸 光華
Chapter 5 五年
白色 涅槃 轉生 虞姬 五年
Chapter 6 還夢
天王 寵愛 自我 春光 還夢
Chapter 7 天時
尾站 掠影 理想 熱情 天時
Chapter 8 煙滅
絕唱 偷心 異度 紀念 煙滅
附錄
張國榮人生大事記
張國榮唱片年表
張國榮參演電影表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關熙潮
- 出版社: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10-14 ISBN/ISSN:978988828499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56頁
- 商品尺寸:長:168mm \ 寬:230mm \ 高:18mm
- 類別: 中文書> 生活風格> 影視寫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