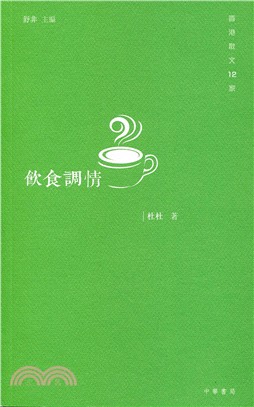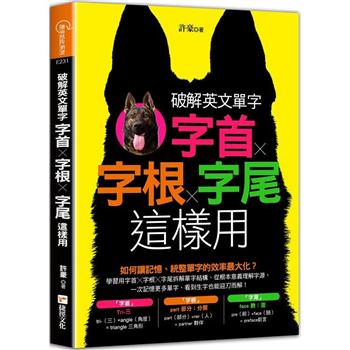非常加料記
周末和老伴共上紐約法拉盛茶樓,喝喝菊普,吃點雞扎鳳爪甚麼的,一邊和老伴閒話家常,也就算是一個節目了。這一個週末在飲茶之際點了一碗蠔豉排骨粥。點心阿嬸問我:「要唔要葱同埋胡椒粉?」我答曰:「乜都要。」這一碗粥吃呀吃的,吃了一條曲曲折折銀光閃閃的兩吋長鐵絲出來。我當下並沒有大驚小怪,還暗自好笑:這下子可應了自己剛才說過的那句話。待穿黑禮服的部長經過我的桌子,我才叫他停下告訴他:「以後應該注意一些。」部長道歉一聲,把點心卡上這碗粥的價錢勾掉。
中國人在異鄉做生意謀生,本來就不容易。我也不願意因這事而驚動四方,但作適可而止的處理便算了。這一向報紙和傳媒專尋中國飯館的不是,一下子說衛生設備欠佳,一下子又推出考證,結論中國菜的成分最有礙健康。話說回頭,一般的中國飯館清潔處理比較不認真。我吃飯吃麵吃出了鐵絲刷的碎片也不是第一次。記憶中在香港吃館子也不時有類似的情況出現,在醫院的飯堂吃豬扒飯吃出了小曱甴,在長洲的小飯店吃湯吃出了一大堆浮着的黑芝麻—那是螞蟻的浮屍。那時候人比較年輕,性格也隨便,因此都不放在心上。人家吃炸雞是吃出了老鼠頭來呢。
博懵伎倆
都說上館子吃東西最無謂的事情就是和侍應鬧意見,不成個體統。好便罷,不好也不宜發作,萬一沉不住氣吵了嘴,最明智的做法是以後不再光顧。那些自以為花錢大爺的顧客,在飯館子坐下來阿支阿咗,要了調羹又要叉子,芥辣來了又說沒有浙醋,把人家弄得火了,自會暗中對付出氣,結果吃虧的還是自己。
在食物中作非常加料之舉,動機可分多種。有的是為了吃免費餐,因此自動加料。在Victor/Victoria(1982)一片中,潦倒的女歌手肚子餓得無法忍受,便照樣上巴黎一流的飯館子進餐,待吃得七七八八之際,便放出一隻預早帶備的曱甴,然後大呼小叫一番,藉此博懵。但是終於上得山多遇着虎,博懵伎倆再施,被人識破,也就受了一頓教訓。
加料也可以因為要報仇。描述美國黑奴歷史的電視片集Roots(1977)裏面,有一雙黑白朋友的故事。小白人女孩和家中的小黑奴兩小無猜、情同姊妹。但是長大了之後因為身份種族不同而產生了矛盾衝突,女白人把女黑奴害得雞毛鴨血。女白人老了之後一次在路途上遇見舊日的女黑奴,拿出主子的身份命她拿一杯水來。女黑奴把一杯水送上,卻暗中吐了好大的一口唾沫,妥妥當當地和在清水之中。女白人若無其事骨嘟骨嘟地甘之如飴喝進肚子裏去,女黑奴只在一旁冷冷地觀看:今天你總算小規模地栽在我手上了。
暗箭難防
正是明槍易擋,暗箭難防。出來行走江湖的,結怨太多,免不了在吃鮑參翅肚之際也順便吃了一些唾沫之類的不明物體,還渾然不覺。老外有句老話:你不知道的事情傷害不了你。話可不是這麼講。廣東人的「死咗都唔知點解」倒是比較有警惕作用。
非常加料寫得最精彩的一段是在楚門.卡波提(Truman Capote)的短篇小說《花之屋》(The House of Flowers, 1950)裏面。故事描述太子港的美麗小妓女奧提莉愛上了山區青年,決定從良。只可惜青年的祖母是個女巫式的老婦,不時在暗中偷窺奧提莉小夫妻做愛,又對奧提莉諸般虐待。有一次還把一隻貓的頭切下來放在奧提莉的籃子內,企圖向她落蠱。奧提莉拈住了貓的耳朵,把貓頭提起,丟入灶頭的湯鍋裏面。當日午餐之後老太婆吃得舔嘴咂舌,還不住地誇獎奧提莉的湯煮得特別美味。
翌日早上,奧提莉又在籃中發現一條青綠小蛇。奧提莉一不做二不休,便把青蛇剁成肉末,放入鍋中熬成一鍋濃羹。之後每天的花樣層出不窮:炸蜘蛛、炒蜥蜴、煮鵟肉。
老太婆吃得起勁,並一邊問奧提莉:「你看來不舒服呢。你吃得那麼少。為何不嚐嚐這好湯?」
奧提莉回道:「因為我不想我的湯中有鵟肉,麵包裏有蜘蛛,又或者肉羹中有蛇。我對這一類東西沒有胃口。」
加鹽加醋
老太婆一下子會意過來,立時靜脈腫脹、舌頭麻木。她搖搖擺擺地站立起來,卻又倒下,天黑之前便一命嗚呼,歸西去矣。
如此大規模的加料行動,只可以算是小說中的大話。但是在真實的人生裏面,總免不了會碰上各式各樣有意無意主動或被動的加料事件。倒不一定是加在食物之中。言語之中也照樣可以加鹽加醋,扭曲事實,改變真相;非得有機警的舌頭,方可辨出事情的本味,免於加料之禍害。
魔幻糖漿
飲食本來就是魔幻的過程,從一粒種子埋在土中,發芽,吸收日月精華,雨露滋潤,成長為樹,結出果子,吃進人的腹中,再化成精神血氣,使一切有趣有益的藝術文化政治活動,得以繼續、增進、發展,那真是一環緊扣一環而又不停地變化變形的自然奇觀、歷史寫照。
神奇巧克力
家中常備現成的川貝露、枇杷膏,還有那一瓶瓶自己醃製的四季桔、蜜糖檸檬、酒浸紅草莓、橄欖油大蒜,都顏色明艷精神奕奕地排列在廚櫃之內,看看也心安理得,彷彿傷風頭痛、喉嚨紅腫、睡眠不足等等日常肉體上的磨難,皆可以從那些瓶子裏找到消解的魔法。肉體一旦輕鬆愉快,沒有了後顧之憂,便可以勇往直前尋求靈魂的滿足和幸福去了。
《百年孤獨》(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1967)這本魔幻寫實小說裏面的飲食描述,也具有魔幻的品質。書中的尼卡諾爾.雷依納神父一心想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教堂,於是手托小銅盤四出化緣,奈何收集的錢連幾扇門都造不起。他靈機一動,在廣場做露天彌撒,召集了半個鎮子的人,然後宣佈:「現在讓我們來親眼看看那無可辯駁的例證,證明上帝有無限的神力。」做彌撒時輔祭小夥子給他端來一杯冒煙的巧克力。神父一口氣喝下,然後從袖管裏抽出塊手帕擦嘴唇,伸開兩臂,閉上雙眼。於是神父竟然離地升起了十二厘米。這一下子可叫人心服口服。一個月來他四處表演巧克力升騰絕技,很快便籌足款項,教堂也就順利地開工,興建大吉。
瑞典皇家學院在一九八二年頒授諾貝爾文學獎給加西亞.馬奎斯,宣稱《百年孤獨》「匯集了不可思議的奇蹟和最純粹的現實生活」。在這神父升騰的片段裏,神父離地升騰是「不可思議的奇蹟」,那杯熱巧克力卻是「最純粹的現實生活」。如果神父服的是仙丹靈藥,那他的升騰則純是幻想,沒有對比也沒有張力。但他喝的是家常熱巧克力,因此反而替魔幻的升騰加添了一層寫實的意味,使那魔幻更加可以相信。而神父的離地升起了「十二厘米」,也具有新聞報道的準確性。
魔幻奇蹟
《百年孤獨》的英譯由Gregory Rabassa執筆,是公認的佳譯,連加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自己也十分大方地承認英譯的文本比原著更強而有力,但是很奇怪地原著中的「離地十二厘米」在英譯中變成了「離地六吋」。「六吋」顯然不及「十二厘米」的精確,而且無論如何六吋不等於十二厘米。
神父因為表演離地升騰而籌得款項建造教堂,當然是作者的諷刺筆墨。天主教本來就具有一點魔幻性質,不似基督教的樸素。天主教的聖人多行奇蹟,會得遇上基督聖母顯靈。道行高的聖人又能升騰,是謂levitation。那是聖人在祈禱或冥想之際,神魂超拔,肉體轉為輕靈,聖寵從上降下,拉引肉體騰空。但尼卡諾爾.雷依納神父的升騰靠的這一杯熱巧克力,未免可笑,大有神棍之嫌疑。
上海譯文出版社的《百年孤獨》中譯本有這樣的一段: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亞的一家人預備拍一張銅版家庭照。那天早晨,他的妻子烏蘇拉「給孩子們都穿上了最好的衣服,給他們臉上都搽了粉,還給每人一匙骨髓糖漿,以便他們在那架龐大的照相機前一動不動地站上兩分鐘」。這是作者信手拈來的遊戲筆墨,也沾上了一點魔幻色彩。糖漿具有強大的黏性,小孩子喝了想當然地可以在照相機前站立不動,順利拍成一照。
葫蘆變骨髓
只是這個「骨髓糖漿」看來有點古怪,總覺得不像。看英譯,是「marrow syrup」;看西班牙文原著,是「jarabe de tuétano」。「Jarabe」是糖漿,「tuétano」是骨髓,或者類骨髓狀的物體,但卻不好硬生生地譯作「骨髓糖漿」。
原來這裏的「marrow」不是骨髓,而是「vegetable marrow」,又稱「marrow squash」,是一種葫蘆科瓜果,中文名字是西葫蘆,又稱美洲南瓜。結瓜果作長圓形,作墨綠、黃白或綠白色,含糖及澱粉質。原產地為南美洲。所謂「骨髓糖漿」,就是用西葫蘆加糖煮成的透明甜漿。相信將之譯成「葫蘆糖漿」,還說得過去。
後來烏蘇拉垂垂老去,雙目失明,行動不便,便又偷偷地把這葫蘆糖漿翻出來服用,又在眼睛上塗蜂蜜,希望藉此復明。可惜烏蘇拉氣數已盡,她那家常必備的萬靈葫蘆糖漿也隨之失去效驗,再沒有她年輕力壯當家之時的神奇魔力了。
現身麵包隱形人
人假借一副肉身存活在這天地之間;這本來就矛盾、無奈和弔詭。花花世界和天地萬物只是無意識的一片混沌,還得通過人身五官的感受,再經「我」的分析、歸納、組合,才會產生意義。一朵玫瑰就只是一朵玫瑰,但是一旦玫瑰出現在我的面前,我便會說:「這朵紅色的玫瑰很美麗、芳香,而且花瓣柔嫩。玫瑰軟醬塗麵包最是清甜可口,玫瑰香茶也十分怡神。」
可是問題來了,一雙眼睛能看見花鳥彩虹,因此帶來愉悅,但也同時間會看見喪敗醜陋,引起煩惱。我們的五官無一不是既能給予快樂又同時相對地可以帶來痛苦。各種千奇百怪的疾病折磨且不去說他,單只是這副肉身的存在就是負擔。因為我有肉身,我便受時間空間的限制。如果要從家中到上班的地點,便得步行和乘車,還得忍受繁忙時間搭客的互相擠迫、你推我搡。萬一地鐵發生故障,更加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眼睜睜看着自己遲到,一點辦法也沒有。此其時也,恨不能像超人似的施展飛天遁地之術。早就有人感應到這副肉身存在的不可承受的沉重,而幻化出這許多妙想天開的神話童話:人身可以隨意縮小擴大,又或者立時間從此到彼,不費吹灰之力,便能夠和天涯海角的心上人重聚。如果碰到討厭的人物,無從躲避,便借魔戒之助,立時隱身,不亦妙乎。
隱形人的悲劇
英國作家威爾斯(H. G. Wells)的科學幻想小說《隱形人》(The Invisible Man, 1897)說的是中下階層出身的大學生,夢想自己能夠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於是苦心研究,終於調製出一種吃了能叫人完全隱形的藥。他一廂情願地以為一旦隱形,便會給他帶來各種方便和優勢,甚至可以操縱別人來達到他自己的目的。但結果事與願違。他漸漸發覺隱身之後只有帶來更多意想不到的不方便,最後還使他陷於完全孤立的境地,和正常人類的世界脫了節,終於神經失常,患了失心瘋,決定藉着隱身術四出去殺人,企圖以恐怖手段去征服這世界,而結果自己死於槍下。死後赤身露體地再度現了形,落得個慘澹悲涼的下場。
威爾斯寫的不是神話故事,而是科幻小說,因此他的描述必須有某一程度的合理解釋。其實,即使有隱身藥吃了使人全身透明如同玻璃,在光的折射和反射之下也會現形。而且人身的結構如此複雜,縱使全部的骨骼肌肉血管神經內臟都變得絕對透明,那光的折射和反射也會使之變得纖毫畢現。威爾斯也深明此點,因此他說這種隱身藥能使光的折射和反射降至零度。那就完全是大話西遊了。另外一個問題是,一個人完全透明的話,便看不見東西了。眼睛看見東西,全靠不透光的角膜和虹膜。威爾斯自己在給朋友的信中也提及這個漏洞。不過如果一定要苦苦追究下去,也就寫不成科幻小說了。科幻小說,始終有幻想的成分。
隱身之後困難重重,首先是不能穿衣服。這在寒冷的冬天是個大問題。書中有一段描述隱形人向流浪漢誇口:「隱形人是擁有權力的特殊人物。」一語未了,便打了個噴嚏。這當然是最明顯的嘲諷。威爾斯思路細密,奇怪地卻沒有提及隱形人在冬天的另一大困難—只要他一呼吸,便會噴出體內的熱氣,也就出賣了自己的行蹤。
最諷刺的是隱身之後的一大難題是如何使自己再度現形,因為有時候不得已還要和其他人作必要的交往。例如說,他放火燒了寓所之後要另尋居所,入住客棧,便首先得向客棧主人登記。因此他用白布纏頭,裝一個塑料的假鼻,再戴上一副黑眼鏡,穿上衣服,無可奈何怪模怪樣地現身,構成了不少的鬧劇場面。
其中最滑稽的是進食問題。他第一次和客棧女主人吵架就是因為吃:「為甚麼早餐還沒準備好?你以為我能夠不吃而活麼?」一語道破了隱形人最大的困境。他對流浪漢也吐過苦水,說:「我到底還只是一個人,需要飲食和穿衣──但我偏偏又是隱形的。」他又說過:「隱身術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美妙。」他無意中走進了舊同學家中之後,便說:「我受了傷,而且疲倦不堪,給我一點吃的,讓我坐下。」一再說明隱形歸隱形,他還是一副血肉之軀。他和舊同學通宵交談,一邊抽煙喝酒。煙含在他的口腔,在他的咽喉之間遊走,勾勒出一個輪廓出來。
口腹之慾現形時
他隱身和流浪漢交談。流浪漢起初不能相信有隱形人的存在,但後來發現在他面前的一片空虛之中,卻浮現了一些恍似經過咬嚼的食物,並且問道:「你是否剛吃了點乳酪麵包?」隱形人回道:「沒錯,還沒有完全消化掉呢。」這是非常荒誕而又寫實的筆觸。正因為如此,隱形人一旦進食之後,便得躲起來,直至食物完全消化之後方可四出活動。
有一次他墨鏡膠鼻怪模樣地進餐室點了豐盛的晚飯,一下子又想起進食時必須把纏住嘴部的白布去掉,而這一來便會洩露了自己的身份。無奈只得餓着肚子匆匆離開。
警方後來派人前往捕捉隱形人,只見暗地裏一個無頭人坐着,卻戴着手套,一手拿着麵包,一手拿着乾乳酪。盡忠職守的警察看見了,便說:「不管有頭沒頭,捉之可也。」
隱形人和舊同學半夜談天,喝酒吸煙。只見半空中浮着一片火腿,又聽得咬嚼之聲。舊同學看見無頭缺手的一件睡袍坐在椅上,又見一條餐巾奇蹟也似地在抹着隱形的嘴唇。一切是如此的荒誕,他漸漸地懷疑是否自己神經失常,產生了幻覺。
威爾斯《隱形人》的最後訊息也只不過是:「不必胡思亂想去追尋甚麼隱身之術。不要以為會因此帶來方便、權力、幸福。我們挖盡心思在這方面的追求,到頭來都只是荒謬可笑的捕風捉影。我們現有的身軀已是無可奈何之中的最佳存在形態了。」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飲食調情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48 |
文學 |
$ 396 |
中文書 |
$ 396 |
現代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飲食調情
「畢業後一直在教書,一邊卻做了半個業餘寫稿匠。一寫半個世紀,感覺上永遠是在學習,總希望能夠寫得更像樣一點。如今這裏結集的稿子,說的雖然是飲食,談的到底是人情。因此書名就定作「飲食調情」。飲龢食德,首重調味。天下文章,大旨談情。味有味道,情有情理;情味和道理,原本就一脈相承,理路共通。」
——杜杜
飲食是人類的基本生理需求,與人的一生關係密切。本書為專欄文章結集,談的是吃,卻不是食譜或飲食指南,而是作者從平常飲食到人情世故的體會。以食物的烹調、吃法、味道為引子,探討它們在日常生活與藝術世界中的角色,從飲食的愉悅談道德、人性與命運。作者遊走於古今中外的文學、繪畫、電影,從狄更斯、張愛玲、《紅樓夢》到希治閣,旁徵博引,趣味橫生,處處顯露出才情與博識。清新幽默的散文有如一席盛宴,殊堪細味。
作者簡介:
杜杜,原名何國道,江蘇揚州人,上海出生,香港長大。中學時就讀九龍華仁書院,接受愛爾蘭耶穌會神父的天主教教育,思想背景深受其影響。其後在香港大學攻讀英國文學和比較文學。興趣是電影,立志做作家,結果當了老師,然散文、雜文見於香港報刊不輟。結集作品有《住家風景》、《瓶子集》、《另類食的藝術》、《非常飲食藝術》、《飲食與藝術》、《飲食與藝術別集》及《飲食魔幻錄》。現居美國,業已退休。
TOP
章節試閱
非常加料記
周末和老伴共上紐約法拉盛茶樓,喝喝菊普,吃點雞扎鳳爪甚麼的,一邊和老伴閒話家常,也就算是一個節目了。這一個週末在飲茶之際點了一碗蠔豉排骨粥。點心阿嬸問我:「要唔要葱同埋胡椒粉?」我答曰:「乜都要。」這一碗粥吃呀吃的,吃了一條曲曲折折銀光閃閃的兩吋長鐵絲出來。我當下並沒有大驚小怪,還暗自好笑:這下子可應了自己剛才說過的那句話。待穿黑禮服的部長經過我的桌子,我才叫他停下告訴他:「以後應該注意一些。」部長道歉一聲,把點心卡上這碗粥的價錢勾掉。
中國人在異鄉做生意謀生,本來就不容易。我也...
周末和老伴共上紐約法拉盛茶樓,喝喝菊普,吃點雞扎鳳爪甚麼的,一邊和老伴閒話家常,也就算是一個節目了。這一個週末在飲茶之際點了一碗蠔豉排骨粥。點心阿嬸問我:「要唔要葱同埋胡椒粉?」我答曰:「乜都要。」這一碗粥吃呀吃的,吃了一條曲曲折折銀光閃閃的兩吋長鐵絲出來。我當下並沒有大驚小怪,還暗自好笑:這下子可應了自己剛才說過的那句話。待穿黑禮服的部長經過我的桌子,我才叫他停下告訴他:「以後應該注意一些。」部長道歉一聲,把點心卡上這碗粥的價錢勾掉。
中國人在異鄉做生意謀生,本來就不容易。我也...
»看全部
TOP
目錄
主編的話
自序
第一輯:一日三餐
一日三餐
飯前感恩
吃飯修行
今天飯後誰洗碗
吃的便條
洗手須知
為腹不為目——老子的飲食智慧
居安思危啖菜根
吃的禁忌和聯想
飲食論陰陽
牙籤顯風度
小題大做牙籤筒
關於牙籤的二三事
吃人的悲喜劇
快活出恭
出恭入敬大循環
非常加料記
魔幻糖漿
現身麵包隱形人
蛋糕鳴奏曲
芭貝的盛宴
菠蘿的滋味
水墨魚蝦 清品至味
第二輯:菜譜如曲譜
吃的喜悅
吃的想像
做菜容易買菜難
《禮記》中的飲食衛生
菜譜如曲譜
追蹤蘿蔔
說說胡蘿蔔
草爐燒餅的記憶
家廚秘方
正邪...
自序
第一輯:一日三餐
一日三餐
飯前感恩
吃飯修行
今天飯後誰洗碗
吃的便條
洗手須知
為腹不為目——老子的飲食智慧
居安思危啖菜根
吃的禁忌和聯想
飲食論陰陽
牙籤顯風度
小題大做牙籤筒
關於牙籤的二三事
吃人的悲喜劇
快活出恭
出恭入敬大循環
非常加料記
魔幻糖漿
現身麵包隱形人
蛋糕鳴奏曲
芭貝的盛宴
菠蘿的滋味
水墨魚蝦 清品至味
第二輯:菜譜如曲譜
吃的喜悅
吃的想像
做菜容易買菜難
《禮記》中的飲食衛生
菜譜如曲譜
追蹤蘿蔔
說說胡蘿蔔
草爐燒餅的記憶
家廚秘方
正邪...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杜杜
- 出版社: 香港中華書局 出版日期:2016-07-22 ISBN/ISSN:978988836646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32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