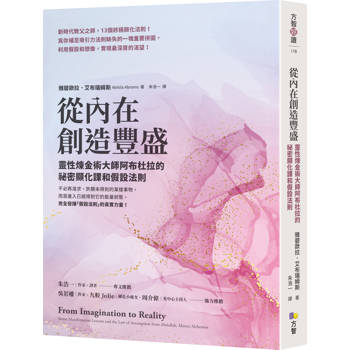這段旅程始於1980年9月,彼時我教英文的沃巴什學院收到一封來自羅伯特.溫德的信,他稱自己為學院最年長的在世校友。儘管七十五年裡沒有一個人聽聞過他的音訊,他的說法卻證明是事實。他解釋道,這些年來自己主要在中國的一流大學任教。
他寫這封信的目的是推薦王汝杰入學。溫德已經指導了王汝杰幾年,認為他已經準備好了接受美國教育。王汝杰的表現無愧於溫德的讚賞。他不只是一個優異的學生,更是一位能幹敬業的老師。我和王汝杰談論書籍和羅伯特.溫德 ── 他曾是王汝杰父母的同事,並擔任過好幾年王汝杰的導師。我對溫德很著迷,這位神秘的老人1923年去了中國,從此幾乎長居於斯,除了二戰期間曾短暫返美。當然,我們也談論中國。在那種語境裡,我好似一個初學者,久久沉迷於唐詩,亞洲泛靈論(我曾去印度旅行),以及“文革”,但實際所知往往寥寥。
那段時日我受《西行漫記》影響很大。久為學者圈中一員,我相信,作為一個階級,如果我們和農民多待一陣兒,分享他們的工作和生活狀況,我們會變成更有趣更進步的人類。我在一間沒有暖氣的粗陋木屋中住了幾年,我珍視在那兒的收穫,與“教養不高”的鄰居一起過較簡單、不那麼舒適的生活,我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我在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其他國家展開艱苦旅行,還認為自己在毛澤東眼中,應該不像我的許多同事那樣亟需一場文化革命來洗禮靈魂。
實際上,我充滿了各種對中國的幻想,即便聽王汝杰講述他當紅衛兵的經歷,我也未能全部擯除這些幻想。例如,他曾經和一群紅衛兵圍攻、審訊身為北大知名教授的父親。但他“文革”故事中淋漓盡致的狂暴讓我著迷。在這所位於印第安納州一塊玉米地的小學院裡,我感受到終身教職的安穩和拘束,令人索然。在某個時刻,我知道,就像一個人一輩子有那麼一兩次會意識到自己真正需要甚麼,我需要去中國。
我的妻子,已經在日本生活過幾年,也對去中國倍感期待。至於我們五歲的女兒安娜……好吧,二十年前我曾帶著兩個小孩去希臘的塞薩洛尼基,我憑富布賴特獎學金在那兒的一所大學教了兩年書,這種連根拔起的生活並沒有傷害到他們,因此我準備再次檢驗自己壯遊的信仰,且帶著孩子。
諸事具備,尚缺教職,王汝杰差不多為我謀了一個。他的父母都是英語系受人尊敬、處於半退休狀態的教授。通過他們,我獲得了一個一年的職位。通告很簡略:“校長邀請您下個學年授課。正式邀請函稍後奉上。”我還記得收到任職電報的那一天。這個巨大飛躍的真實性,讓我倏忽不知所措。我想我臉色蒼白。那時正來學院訪問的羅伯特.布萊(Robert Bly),對我說了三個詞,巨大而永久地改變了我的人生:“That’s just fear。”(那只是害怕)我第一次意識到,那不是害怕,而是恐慌,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當我們在甘迺迪機場踏上登機通道時,相同的震動不出所料地擊中了安娜。“我去那兒過夏天,但不要待一整年”,她宣稱,並死死抓住通道扶手。我不得不把她掰下來,當然很難受。她不肯安定,直到空乘給我們送餐。冒險剝下餐盤錫紙,探尋下面的神奇食物,她沉浸其中,看起來總算發現了這一趟的好處。
我們在華的最初時光有許多值得一說:安娜如何進入一所容納五百個孩子的幼兒園,好幾個月都一言不發,直到會說幼兒園通行的漢語;我們如何騎著自行車勘察校園,發現圓明園毗鄰北大,被毀的宮殿和破損的石獸如何成為安娜最愛的遊樂場。我們起初都因太無知而體會不到文化衝擊。我們眼前的一切是平靜的,即便人們整齊劃一地穿著毛式的中山裝,甚至有顯而易見的軍事主義,而校園廣播一天兩次高吼指令和節拍,要求所有身體健全的人一齊做操。當時還發生了一些神秘之事:比如,我的學生會給我帶來一些官方的紙條,我必須簽署,然後還給那個坐在訪問學者宿舍門口的小幹事 ── 而我花了幾個月才接受事實,即“文革”只是在名義上結束了,我的學生和同事們仍然被緊緊箍在那個令人謹小慎微的系統中。
改變需要一段時間。我多次私下和學生聊天,但其內容必然限於我能理解的範圍。當這個範圍擴大,有些學生,包括那個如同“私人導遊”、文化翻譯的聰明年輕人,開始教我們一些東西 ── 例如,他指著黨內高官集體亮相的新聞照片,說有張面孔不在其中,這是已經發生的一場政治大變動的唯一線索。另有一次,他告訴我,有位畫家被捕,因為他描繪標準場景時多了幾筆陰霾,在當局看來這就是政治批判。
我之所以需要一些時間來看透現狀,還因為,我們有一陣和其他“外國專家”一起下鄉,很多人歡呼當局的仁慈。例如,有次訪問一處解放軍基地,我們目睹某個突擊部隊正在訓練障礙項目和白刃互搏,令人印象深刻,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軍民魚水情。我們離開時深覺中國是和善的。畢竟那時,即便老練如費正清也對毛澤東的革命懷有同情,就像溫德一開始的感覺。
所有這些都發生在1984年的夏末和秋天。更具真實感的事情呈現在我眼前,始於我第一次拜訪羅伯特.溫德,他的寓所在校園北隅。我見他時,他97歲,兩年前被自行車撞後就臥床不起。他常常昏睡或迷糊,絕不像個適於交談的對象。我第一次拜訪他是正式的,目的是給他捎去沃巴什學院院長路易斯.索爾特(Lewis Salter)的口信,帶給他索爾特簽署的榮譽博士學位證(不久它就掛在溫德床頭上方,我不知道這是否出自他本人的意願)。
溫德一開始就吸引了我(主要是第十八章所寫的第一次拜訪),我旋即意識到,我要盡量多地和他交流。我的想法有些自私。如我所說,我對中國歷史一無所知,溫德的經歷讓我看到中國的前景,他在中國度過了動盪喧囂的20世紀。不過我也有不那麼自利的動機。溫德陷入了困頓,病痛和周遭環境讓他無望 ── 他知道這些,也時常抱怨,要我想方設法幫他解脫。講他的故事,對我來說,是我給予他某種解脫的唯一方法。他對自己這一生是否有價值心存疑慮,而我在還不太了解他做過甚麼有價值的事之前,便早已覺得 ── 他此生是值得的。
一開始,我可以拼湊的故事如同幽靈。他腦海中不同時期的人和事件互相交織成一個奇怪的原型。更悲催的是,我對中國歷史實在無知,所以基本無法將訪談材料聚攏起來,只能盡其所能地被動記錄。
我,夢一般地騎著單車,沿著清風拂過的荷花池,去向校園西北角的小屋,在並不太久遠的過去,這一區域尚是皇家獵場的一部分。在門口,溫德的傭人會跟我打招呼,這個姓王的女人並不很情願見到我,因為我的來訪會讓老人變得躁動而難以平靜。不過,她對我仍算和善,希望從我這兒找到下家,她的命運往往取決於先生們的好意。
進了屋,她會帶我穿過一間小的前廳,那是她和丈夫住的地方,走過一條短的廊道,它從右切入一處櫥櫃般的空間,那是老溫德曾經的書房,現在的臥室。這房間窗子緊閉,有一格玻璃由結實的木板取而代之,這樣老人就無法因為暴躁、尿味襲來而打破它。他時常昏睡著,一個大塊頭,穿著有夾層的中山裝,填滿了、甚至看似要溢出那小床,他滿面憔悴,幾如死人。
一套古典雕花的柚木壁櫥覆蓋了整面牆(我無法想像溫德如何在戰亂和逃亡中將它保留下來)。他早期生活的其他痕跡掛在牆上。有幅清代的畫,畫上是一位穿紅色斗篷的大鬍子男人牽著駱駝翻越雪山。人和駱駝都帶著一股聖潔的傲然之氣凝視著澄澈的山巔穹頂。這是一幅行者的圖畫,它讚美那種孤獨和無畏的追尋之旅。它對面的那幅油畫,王岷源告訴我,那是溫德還不到五十歲時的自畫像:如上圖騎馬者那樣大而粗的鬍鬚,有著那種專橫的、英國式的英俊。溫德的另一幅畫,現今屬於我了,上有一位年輕的漁夫直視著我們,右手握著一隻小海馬,明顯是表達情慾。
溫德的藏畫
其他東西只有幾樣:一個卷軸,上面的幾個大字為:“辭舊迎新,百花齊放”;沃巴什學院的獎旗和獎狀掛在溫德床尾那面牆上;一台彩電,這是最後一扇為溫德打開室外天地的窗戶。
譯後記
為了支撐我的荒墟,我撿起這些碎片。
──T.S.艾略特
1923年8月21日,36歲的溫德離開美國,從舊金山登上“東京丸”輪,11天後抵達南京。從此以後的半個多世紀裡,溫德先生以英國文學教授之身份,輾轉於東南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和北京大學,與聞一多、吳宓、瑞恰慈、燕卜蓀、費正清等一批中國現代學術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師共事多年。曹禺、李健吾、錢鍾書、趙蘿蕤、盛澄華、李賦寧、王佐良、何兆武、季羨林、楊絳等下一輩學人皆曾受教於溫德。最為難得的是,溫德先生和中國人一起捱過了抗戰、內戰、“文革”等艱難歲月,他選擇了中國式的命運。
為溫德先生寫一部傳記,把他的一生故事講給世人聽,是伯特.斯特恩(Bert Stern)教授三十年前與即將辭世的溫德先生的一個約定。從此以後,幾乎不懂中文的斯特恩教授努力通過英文世界裡的中國研究著作了解中國歷史,並詳覽溫德先生的日記以及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相關檔案,用近半生完成這個約定。
譯稿先由余婉卉博士譯出一部分(第1 - 3章),餘下部分由我來完成。出於種種不可抗力,中文版延宕許久。斯特恩教授年過八旬,在他與我來往電郵的字裡行間,我能體會到那種深深的時不我待感,也因此當本書終於可以付梓時,我滿心歡喜,為斯特恩教授歡喜,更為溫德先生歡喜。感謝岳秀坤副教授的推薦,也感謝張雅秋博士為這本書的全心付出。今年12月31日是溫德先生128歲誕辰,謹以此書作為給在天上的溫德先生的一份生日禮物。
馬小悟
2015年12月16日
第一章 流亡的印第安納人
那個冬天的空襲多發生在上午十點至下午三點之間,溫德據此制訂計劃,上午工作兩三個小時,下午從三點工作到六點。他習慣了隨時揣上那些他眼中的重要之物,對他來說,那就是他的打字機、眼鏡;一個公文包,內有他所管理的中國正字學會的文件;一件軍用防水大衣,他在壕溝裡躲避槍林彈雨時可鋪在身下。這成了每日必經的程序,他在家信裡說,“和歐洲的情形相比”,只是小兒科。
儘管如此,對他這樣一個“新來者”而言 ── 他從北平南下昆明不過是兩個月之前的事 ── “見到目瞪口呆的女人如看門狗般坐在自家爆炸後的彈坑裡”實在愉快不起來。由於沒有成過家,溫德免去了這種注視。他個人遭受的最大損失發生在1940年11月他剛來沒多久時,小偷劈門而入,用撬槓弄開了他的行李箱。他幾乎丟失了所有私人財物(包括赫爾墨斯便攜打字機),不久前他搭卡車在滇緬公路上顛簸十四天尚能保住這些東西。在這一段歷險記裡,有爆炸的橋樑,瘧疾,沒完沒了的官方拖延,司機企圖偷他的行李,明明白白看到“五輛卡車在一天之內相繼跌入懸崖,或是墜崖後躺在那兒”。
他形同小醜,穿著朋友們給的款式各異的衣服 ── 不過,在昆明,1940年的冬天,一個髮色灰白、憔悴、衣著混搭、身高超過一米八的美國人不算是一道奇異的景觀,因為此時此地混雜著軍人、本地居民,來自山區的少數民族,還有遷徙而來的大學師生 ── 他們很多是步行至此的,從北平到西南地區有兩千多公里,他們要在日軍攫取了北方的廠房機械之後保存大學的實力。
通常,空襲警報會盡早拉響,以便城內居民取道東門逃入山林,一路上得半個小時。偶爾,飛機也能避開耳目,在第一道警報響完之前就進到城內。那便是一片混亂。人們逃向狹窄的東門,頭頂貴重物品。
老婦人背上綁著嬰兒,鴉片吸食者帶著煙槍。跛子,學生帶著整包書,裹腳的主婦懷裡揣著鐘,或有其他寶貝藏在身上,與富人的汽車、官方的卡車混雜在一起。
在溫德抵達之前的幾週,他最親密的朋友,蘇格蘭人吳可讀(Arthur Pollard-Urquhart),剛剛死於左膝傷口惡化而致的併發症,他受傷是因為某天剛到門口就被一輛卡車撞倒。
溫德則像個喜劇角色,當警報如塞壬歌聲般響起,他和助手往山上跑,抬著一台沉重的辦公打字機,溫德從英國領事館借了它來代替那台丟失的赫爾墨斯。有時他陷入窘迫 ── 有次是在墓地,他置身墳墓之間以躲避流彈,經常或輕或重發燒,因為熟睡時被耗子咬到,染上了當地的斑疹傷寒。正如一位中國朋友對他所說,“在這兒,現在沒有時間變老、染病、死亡”。
在滇緬公路染上的腰痛,發展成了坐骨神經痛,讓他幾乎筋疲力盡。某天,值他甫抵昆明一週,已近乎跛行的他,拖在朝大門蜂擁的人群後面,而他從來沒有去到山林那麼遠。在那個非同尋常的十二月,每當飛機襲來,他坐在潮濕的稻田裡,一動不動,而飛機的槍膛正在射擊,不時往人群扔下手榴彈。兩個學生死了,但溫德,像往常一樣幸運,看著飛行員兩次對準他,卻與他擦肩而過。因此他安然無恙,只是六個小時裡警報解除的鈴聲都未響起,之後他又冷又濕地跛回家。次日,他行動困難,好在他的朋友、英國領事好心借給他一個熱水瓶。在昆明,誰的愁苦要是能有熱水瓶的慰藉,那是相當不錯的。
遭受種種的溫德仍從中國人那裡得到慰藉,雖然他們被剝奪了一切,甚至無法遵循傳統敬畏死者。此時已經沒有葬禮。遺體的處理“盡量安靜而迅速”,溫德得知皮雷先生 ── “一位在昆明辦了多年英語學校的法國老紳士”的死訊,還是因為他偶然遇到二十多名學生,肩扛著一副棺材跑向城門。一支竹棍上插著小布旗,上有中文寫著皮雷的名字,表示他們正要將他的遺體帶出去行葬禮。
有太多需要適應的,但“最令人驚詫的是所有人,尤其中國人,很快就適應了。可能是嚴酷的環境讓情感沒有容身之地。我在經受恐怖的一天後無法入睡,但我尚未發現學生們也有相同的反應。我有這種情況,高海拔大概是一個原因。”
他十七年前以某種文化使者的身份來到中國,他可以講莎士比亞和但丁,米開朗琪羅和蒙田,貝多芬和莫扎特,有著吸引人的明晰和激昂。他是來講課的,也是來學習的。他在中國發現了一種西方所匱乏的日常文化和禮節。但現在一切文化念頭都要拋之腦後了。重要的是得活下來。即便一個人身體可以適應,情感的適應卻需要更高的代價。要麼遏制消沉的想法和感受,要麼持續向恐懼敞開,不給想像力留下一席之地。空襲過後,從山上回到城裡,你會遇到:
一個女子的半身,沾滿泥土,空洞地笑著,倚靠在樹根處。路邊有一個塵土翻飛、吐著黑水的池塘,亂蠅無數,水面上泛著白花花的米粒。在池水中央,有一隻鮮紅的小手,手指向天。蓋上她的臉⋯⋯薄棺為何太麼窄?沒有關係,多的是殘肢斷片,但這個赤身裸體的胖男子,肩膀還是齊全的,所以只能用鐵鍬用力壓下去。⋯⋯在我家門口,一個人跪著,屁股高高抬起,就像祈禱中的阿拉伯人。他的頭不見了。他們說,這是我的木匠⋯⋯一個女人爬上被炸毀家宅的廢墟頂上,一直在挖刨著,她漲紅了臉,臉上閃耀著落日最後一道餘暉,悲極不成泣。雙眼中有深不見底的痛苦,諷刺的是,她的唇上卻盡是木然。
今夜還有時間,“用你的手擦拭你的嘴,抿笑”,當你在鎖孔裡旋轉鑰匙,吹熄蠟燭,子彈退回膛,你跌落地上,一口酒突然上頭,掬一把熱淚,直到你再度站起來。床鋪雜亂,“在如呻吟的吱呀聲中,思緒煩亂”。
溫德經受著這些,也一直在觀察與記錄,在悲慘的中心地區繼續目擊,而大多數旅居中國的西方人早就棄之而去了。到了1940年,中國很明顯不再像戰前那樣是外來唯美主義者眼中的天堂。但溫德留了下來,還教書,儘管他認識到他的態度讓許多人想起紀德筆下“普瓦捷的被囚者”,當她被解救出來時,已在那個黑暗骯髒的屋子裡關了二十年,她堅決不讓護士們剪掉她臟亂的頭髮,給她洗個澡,她有生之年不斷在乞求,想回到她“親愛的小窩”。
他為甚麼留下來?溫德與朋友瑞恰慈思忖著這個問題,瑞恰慈已開始暗示他,現在是離開的時候了。這僅僅是一種條件反射嗎,像那位隔絕者?是那種叫做“戲劇性的本能”使他害怕“有序世界的沉悶”嗎?他留下來是因為他“在物質條件惡劣的這張粗糙帆布上”“揮散嘴角眼角的多愁善感”嗎?僅僅是虛榮嗎?他在聯大這所流亡昆明的學校裡每週講授詩歌課,他的課不得不一再搬到更大的講堂以容納更多的人群。
他仍留在中國,純粹是出自“他畏懼被時光拋下了十八年,還得掃清腦中的蜘蛛網嗎?或者他暗暗害怕成為自己在廣播裡聽到的那種美國人?或者害怕文學在更優越的環境裡發揮的意義不會那麼大?”或純粹是因為他不可能遺棄那些人們,他們堅持活下來捍衛國家,咬牙“飲下死難同胞的骨血”。他再也沒法轉身而去,“在這出戲演完之前,不管他們中有多少人會是狡詐冷酷”。
他留下來,因為以上的理由,而還有一個更關鍵的理由是,他在中國找到了一個位置。在北平,他屬於一所大學,它器重他,它以中國式的迂迴使他有臉面地免於飢餓。“這是肯定的”,他告訴瑞恰慈,中國是世界上他唯一能指望獲得那些東西的國家,這一點算是彌補了在這兒生活的弊端。
因此,五十七歲這年,他決然地宣佈自己是這個國家的居民,遠離那並非遙不可及的出生地印第安納州克勞福兹維爾(Crawfordsville),從此疏離他的國家和同胞。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溫德先生:親歷中國六十年的傳奇教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87 |
中國當代人物 |
$ 417 |
社會人文 |
$ 441 |
中文書 |
$ 441 |
學者/科學家 |
$ 441 |
中國當代人物 |
$ 441 |
文學家 |
$ 441 |
社會人文 |
$ 441 |
歷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溫德先生:親歷中國六十年的傳奇教授
本書講述了溫德傳奇的一生。作者曾在1980年代到北京大學做訪問研究,與溫德有直接接觸。此外,作者充分發掘利用了美國方面的資料,尤其是洛克菲勒基金會保存的溫德通信等檔案文獻。內容涉及中國現代教育史和文化史,記錄了溫德同時代一批中國優秀學者的歷史資訊,從一個在華外國人的視角反映了中國現代歷史的變遷。
作者簡介:
伯特‧斯特恩(Bert Stern)
1930年生,長期執教於美國Wabash College,現為Milligan Professor Emeritus of English。
TOP
章節試閱
這段旅程始於1980年9月,彼時我教英文的沃巴什學院收到一封來自羅伯特.溫德的信,他稱自己為學院最年長的在世校友。儘管七十五年裡沒有一個人聽聞過他的音訊,他的說法卻證明是事實。他解釋道,這些年來自己主要在中國的一流大學任教。
他寫這封信的目的是推薦王汝杰入學。溫德已經指導了王汝杰幾年,認為他已經準備好了接受美國教育。王汝杰的表現無愧於溫德的讚賞。他不只是一個優異的學生,更是一位能幹敬業的老師。我和王汝杰談論書籍和羅伯特.溫德 ── 他曾是王汝杰父母的同事,並擔任過好幾年王汝杰的導師。我對溫德很著迷,這位...
他寫這封信的目的是推薦王汝杰入學。溫德已經指導了王汝杰幾年,認為他已經準備好了接受美國教育。王汝杰的表現無愧於溫德的讚賞。他不只是一個優異的學生,更是一位能幹敬業的老師。我和王汝杰談論書籍和羅伯特.溫德 ── 他曾是王汝杰父母的同事,並擔任過好幾年王汝杰的導師。我對溫德很著迷,這位...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1984-1985年,在北京大學講授英語文學和寫作的一年裡,我時常騎車去燕園一角那局促的溫宅拜訪溫德先生,聽他口述人生。當時溫德先生已經九十七歲,他幾年前曾被一輛自行車撞過,後來就幾乎癱瘓在床。不能站立走路是一種痛苦,但與此同時,老年癡呆也如影隨形,他只偶爾有片刻的清醒。連讀書讀報都不能,溫德先生已徘徊在生死邊緣。他問我,能不能做點甚麼減輕他的痛苦,我竟無言以對。也許死亡才是他能期待的唯一慰藉。但是,一個念頭劃過我腦海,也許我可以為他做這件事:把他的人生講給世人聽。我還有一個略微自私的目的:我對中國的歷史...
»看全部
TOP
目錄
中文版序
引言
第一章 流亡的印第安納人
第二章 抵達
第三章 清華
第四章 瑞恰慈與中國正字學會(1923—1937)
第五章 抗日戰爭與中國正字學會
第六章 保衛清華
第七章 去往昆明之路
第八章 聯大之困
第九章 正字學會的終結
第十章 重回美利堅
第十一章 昆明的勝利
第十二章 奮鬥
第十三章 回家
第十四章 誰丟失了中國
第十五章 冷戰到來
第十六章 聞一多的骨灰
第十七章 中國解放
第十八章 “文化大革命”
第十九章 再見,溫德
譯後記
溫德年表
引言
第一章 流亡的印第安納人
第二章 抵達
第三章 清華
第四章 瑞恰慈與中國正字學會(1923—1937)
第五章 抗日戰爭與中國正字學會
第六章 保衛清華
第七章 去往昆明之路
第八章 聯大之困
第九章 正字學會的終結
第十章 重回美利堅
第十一章 昆明的勝利
第十二章 奮鬥
第十三章 回家
第十四章 誰丟失了中國
第十五章 冷戰到來
第十六章 聞一多的骨灰
第十七章 中國解放
第十八章 “文化大革命”
第十九章 再見,溫德
譯後記
溫德年表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伯特‧斯特恩 譯者: 馬小悟、余婉卉
- 出版社: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8-17 ISBN/ISSN:978988836955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商品尺寸:長:168mm \ 寬:230mm \ 高:21mm
- 類別: 中文書> 傳記> 文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