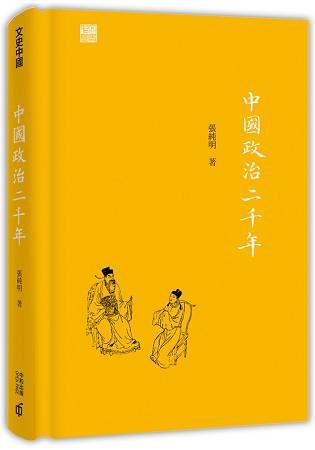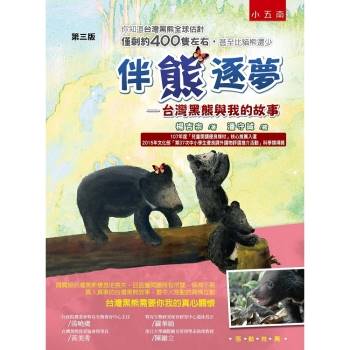本書一九四○年由商務印書館初版。作者以中西文化的視野和洗練生動的文筆,指出中國自秦漢到現代中國政治的特點和動向,把中國二千年紛繁的傳統政治文化,概括得清晰而深刻,具有極強的穿透力。
作者簡介:
張純明
(1902—1984),河南洛寧人,22歲公費赴美留學,主攻社會政治學,在耶魯大學獲政治學博士學位。曾遊歷歐洲多國,對西方政府、政黨、憲法等進行考察研究。歷任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院長兼政治系主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高級秘書、河南省政府委員、立法委員等職。主要著作有《中國循吏研究》、《清代的幕制》、《考評桓寬鹽鐵論》、《中國政治二千年》等。
章節試閱
第一章
皇帝、專制、統一
公曆紀元前二二一年,是中國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一年,因為在那一年裡秦王政完成了合併六國、統一天下的大工作。這是一個前古未有的新政治局面,秦王自己也知道他的成功是值得紀念的。從前的一切文物制度,已經不能代表這個新時代的精神了,所以都要改變,就是君主的名稱也須隨著文物制度而刷新。《史記.始皇本紀》有一段極有意義的記載:
秦初併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採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
後來並有制云:
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這都是表明天下既已統一,一切文物制度以及名號稱謂,皆歸劃一,政權操於皇帝一人之手。從此以後中國的政治和以前的政治完全不同了。皇帝的地位就日見崇高起來,而人民─特別是人民中的文人政客─的地位也就沒落了。在秦統一以前,列國並立,文人政客奔走諸侯之間,在政治上有很大的操縱能力,所以諸侯對於他們也不得不加以相當的敬禮。但統一的皇帝用不著他們的奔走,不必對他們敷衍。政治上獨裁專制的趨向日益顯明,而國家與皇帝差不多變成為一件事。這就是雷海宗教授所謂“皇帝制度之成立”。(《清華學報》第九卷第四期)
但秦享國未久即遭六國遺族、文人政客、士豪流氓的混合作亂而亡國。到劉邦興起,打倒群雄,天下才有第二次的統一。
劉邦以小吏─泗上亭長─而得天下,是中國歷史上平民做皇帝的第一次。但皇帝的地位並不因為他出身微賤而降低,實際上皇帝的地位反從此而更加神秘,更加尊崇。自漢氏興起以後,天下變成皇帝的私產,二千年來的專制政局可以說真正自此開始。
造成新的政治局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英國學者羅素氏(Bertrand Russell)在他近著《權力》(Power: A New Social Analysis )一書裡把權力分為兩大類:傳統權力與新得權力(Traditional power and newly acquired power)。傳統權力有長久的習慣為其後盾,用不著特別的理由以維持它的存在。而且傳統權力差不多都有強有力的宗教或類似宗教的東西來扶持它,如果有反抗的發生,就會被認為大逆不道。除非傳統權力到了快要崩潰的時候,絕對沒有人敢起而與之抗衡。傳統權力比較容易保持,因為它自然地有一般人的同情與擁護。新得權力就不同了。它沒有習慣以為其後盾,它沒有輿論的同情。擁有新得權力的人所以常有自己地位不穩固的感覺。秦始皇統一天下是一種新得權力,因為他開了千古所未有的新政治局面。這種新局面自然要遇著不少的阻力,而使他有朝不保夕的恐懼心。他的苛政,他的焚書坑儒及其他政策,都是這種恐懼心理的表現。劉邦代秦而有天下是中國史上第二次的統一。為鞏固皇帝地位,遂大封同姓諸侯,以為王室的藩屏。免除秦代的苛法是收拾人心的工作。創造神話,說高祖是赤帝之子,封禪及五德受命的宣傳是使皇帝的地位神秘化的工作。但這些工作還是不夠,最重要的是得文人政客的同情與擁護。儒家的學說無疑的是對於皇帝最有利的思想,可以採用以為新得權力的精神基礎。但高祖在最初的時候對於此點並不完全明了。由流氓出身的劉邦對於寒酸不堪的儒生,當然是看不起。他每遇見儒生向他賣弄或討好的時候,他不是破口大罵,就是把他們所戴的帽子解下來,溲溺於其中,以示侮辱。酈生以鼎鼎大名,年高六十餘,身長八尺的老儒,去見高祖,高祖“踞床,使兩女子洗足”慢不為禮。陸賈以詩書說之,高祖大罵道:“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賈的答覆是:“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向使秦已併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陸賈的話是很有道理的。高祖聽了雖大不高興,但終不免有“慚色”。儒者那一套哲學確是陸賈所說的“長久之術”。儒家“正名”、“禮教”的思想,對於維持皇帝地位確是再好不過。試看叔孫通起朝儀的故事,我們就可以知道儒家學說的力量。
第一章
皇帝、專制、統一
公曆紀元前二二一年,是中國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一年,因為在那一年裡秦王政完成了合併六國、統一天下的大工作。這是一個前古未有的新政治局面,秦王自己也知道他的成功是值得紀念的。從前的一切文物制度,已經不能代表這個新時代的精神了,所以都要改變,就是君主的名稱也須隨著文物制度而刷新。《史記.始皇本紀》有一段極有意義的記載:
秦初併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
作者序
在區區幾萬字的小冊子裡討論偌大的題目顯然是不可能的事。如果讀者想從這本小冊裡對於二千年來中國的政治得到一個有系統的敘述,他一定會失望的。好在作者個人並沒有存著這麼大的野心:他的目的不在做一本中國政治史或政治制度史,而在指出自秦漢到現在中國政治的特點和動向。就在這一點上他也沒有系統化的意志,許多應該討論的問題都遺漏了,而在其所討論的問題的範圍以內也難免片段或零碎之譏。
在戰時首都的重慶寫書最大的困難是參考資料的貧乏。極平凡、極普通的書籍在這裡也無從尋覓。回憶三年前,北方各大學圖書館內寫作的便利不禁感慨繫之矣。但參考資料的貧乏並不能使作者對於書內的差誤─無論是見解或事實─不負責任。倘能因作者的差誤而引起讀者的教正,則這本小冊子也不算白寫了。
張純明二十八年八月重慶曾家岩
緒論
清末的人喜歡談洋務,除郭嵩燾及幾個對於西洋有比較深刻認識的人外,他們所謂洋務包括幾項很具體的東西:大炮、洋槍、輪船、火車等物。當時“文化”二字尚未發明(中國以前也用文化二字,是文治教化的縮短,往往與武功相對而言,和現在人所謂文化略有不同),所以當時的人也不知有甚麼中西文化。民國初年我們對於西洋的知識日益增加,漸知西洋人自有其特別的文化,於是高談“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有些人以為西洋文化是“動”的,中國文化是“靜”的,還有些人以為“東西文化的一個根本不同之點”在“一邊是自暴自棄的不思不慮,一邊是不斷的尋求真理”。(《胡適文存三集》卷一,《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這種解釋似乎把中西文化的不同看先天固定的分別,兩方面心理的構造有根本的異點,西洋如此,中國人如彼,有如英國詩人吉卜靈(R. Kipling)的名句所詠:
Oh! 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1 meet.
實際上這種看法是不合歷史事實的。歷代的記載告訴我們,每一個民族都有“靜”的時期,也都有“動”的時期;都有“不思不慮”的時期,也都有“尋求真理”的時期。英國著名經濟史家唐內教授(Professor R. H. Tawney)說:
所謂中國經濟生活中的傳統主義實在不是中國獨有的特點,而文化史上的一階段,就是歐洲也曾經過的。迅速地經濟變轉的事實,繼續不斷地經濟進步的理想,並不是西方歷史固有的音調,而是近四世紀的產物。如果一個歐洲人對於中國人所表現的守舊性不能了解的話,他倘能和他的祖宗見面,一定要發生同樣的感想。在差不多一千年的中間,西方的農夫工匠的技術變革的微小,和在中國所見到的一樣。在前者,猶如後者,一般人把以往的黃金時代而不把將來的可能性看作他們行為的標準與現在的規度;他們無條件地接收他們所承受的環境,視疾病癘疫為當然;對於那些矻矻不休地在那裡以藝術改進自然的人們,並不感覺興趣,如果他們不疑惑他們與惡魔合夥作祟就算好了。在歐洲又如在中國一樣,政治混沌、強盜充斥、內亂、饑饉,都是很普通的現象。
(Land and Labor in China , pp.19-20)
由此觀之,中西文化不是“種類”的區別而是“程度”的區別。馮友蘭先生說:
所謂西洋文化之所以是優越底,並不是因為他是西洋底,而是因為他是近代或現代底。有人說西洋文化是汽車文化,中國文化是洋車文化。但汽車並不是西洋本有底。有汽車與無汽車乃古今之分,非中西之異也。
(《別共殊:新時論之一》,《新動向》一卷七期)
馮先生的看法實在比以前的“動”、“靜”的說法高明多了。近代文化與古代文化的不同不僅在汽車之有無,而且在社會經濟政治的組織與理想。馮先生在另一個地方指出中古的生產方式是以家庭為本位,現代的生產方式是以社會為本位。在生產家庭化的社會裡“一個人的家是一個人的一切,因為他有了家才有了一切;他若無家即無一切。我們亦可了解,何以在生產家庭化底社會裡,一切道德皆以家為出發點,為集中點”。(《說家國:新時論之四》,《新動向》一卷十期)
我國自秦漢以至清末的經濟社會始終沒有走出生產家庭化的階段,無怪中國人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國,對於政治不發生濃厚的興趣,好似“一盤散沙”一樣的無組織了。這並不是因為中國人沒有“任何的政治能力”,或中國的文化根本不是一部政治文化”,而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組織是中古式的。事實上,中國的政治在漢代、唐代也曾放過燦爛的光輝,漢唐的政治文化與同時代的歐洲比之,恐怕要勝一籌。
然而話又說回來了。為甚麼歐洲近幾百年來有偌大的進步,而中國雖然不能說沒有進步,但進步像那樣的遲緩?
這是不容易答的問題。
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一篇論西洋文明的文章裡說歷史上的“自然進步”(Spontaneous Progress)原來很少見。只有埃及與巴比侖的一個時期,希臘在二百年的期間,西歐自“文藝復興”以來。他找不出自然進步的特別原因,除非是由於幾個“極少數出類拔萃的人物”的努力。他的結論是:如果克皮勒(Kepler)、格里由(Galileo)、牛頓(Newton)不幸而幼年夭殤,現代的西洋文化或者就不會發生(見In Praise of Idleness and Other Essays , PP.163-164)。羅素似乎把進步看成歷史上偶然的事跡,不可以常理解釋的。和羅素同一意見的學者有好幾個。
如果羅素的話是對的話,那麼,中國與西洋在近數百年內有幸有不幸。歐洲幸而出了幾個大科學家,中國不幸而沒有產生大科學家。大科學家的產生是偶然的,但我們要問:為甚麼中國沒有偶然地產生幾個大科學家呢?為答覆這個問題我們應該明了中國與歐洲的地理經濟環境及學術風氣。我們當然不能忘記歐洲有極長而且曲折的海岸線及其南北的兩個內海,使國際貿易可以達到任何區域,甚至於使有幾個國家專依航海為生。到十五、十六世紀,歐洲差不多成為海盜世界,幾個大探險家都是海盜的首領,他們的目的在求黃金白銀和香料。然而這班海盜和海盜帶來的商人開闢了無數新地,開拓了人的眼界,抬高了人的想像力。在歐洲本部也有幾個繁榮商業中心的出現,商業的交流很自然地孕育了競爭和模仿的種子,很自然地使人民時常移動,於是幾個國家交相為師,交相為徒。這都是適宜於科學發達的環境。我們不能忘記歐洲在中古的時候人口少而資源多,這種情形正足以激起“工藝發明”(Technical Invention)。產業革命接著起來,生產方法改變了,生產能力加增了。
經濟的進步當然影響到社會政治。商業發達的結果是中產階級的出現,中產階級的出現即封建社會的崩漬,民族國家的產生,於是整個的政治觀念、法律觀念都改變了。當然我們也不能忘記了“文藝復興”對於希臘政治哲學、羅馬政治組織、法律系統及抽象國家的尊崇之發見。這些發見的重要性是不可埋沒的。
中國沒有歐洲那麼幸運。我們的地理環境不如歐洲的優越。我們的版圖超全歐(俄國除外)而過之,而我們的天然交通的便利遠在歐洲之下。而環繞著我們的各民族,其文化都在原始或近原始的態度中,不但不能給我們所需要的剌激和模仿的榜樣,而且助長了我們民族妄自尊大的心理。
本來中國傳統思想也缺少進步的種子。儒家的“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道家的“絕聖棄智”、“清靜無為”都是反對進步的哲學。儒道二家的思想深入人心,遂使我們對於古代的一切是尊崇的,對於獨創的見解是抑制的。我們又有甚麼“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觀念,於是我們鄙視“物質”而崇尚“精神”,其結果是知識是書本的知識,與實物不發生關係,知識階級變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廢物。在這種土壤中自然科學的種子是不能發榮滋長的。當歐洲十七世紀的上半葉,較確切一點說,從一六○六年至一六七五年的中間,正是科學抬頭的時候,望遠鏡發明了、新天文學出現了,格里由、牛頓的工作大成了。在同一時期的中國也有許多大學者的出現。他們─黃宗羲、顧炎武、顏元、閻若璩─用新的方法去研究舊的學問。但他們的方法雖也是科學的,但他們研究的對象是書本而不是實物。中國近世學術和西洋近世學術在這五六十年的中間劃分了,中西文化也在這五六十年中間分道了。自秦漢以來在物質上雖不能說完全沒有進步,但進步的速度究竟是低微的可憐。在同治初年稍明時勢的人已經知道非發憤模仿西洋不足以圖存,但還有許多頑固之流抱殘守缺,以模仿為可恥。他們以為“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一藝之末而奉夷人為師”(倭仁語),是絕大的恥辱。
不幸的很,我們與西洋正面接觸的時候正當國內有巨大的變亂,十餘年太平天國的革命把國家元氣消耗殆盡。內外交攻,國家的存亡岌岌不可終日,從此政治經濟的發展處處受不平等條約的支配,而國人在此種局面下很自然地有兩種病態心理:媚外與仇外。中外關係不能走上正軌,使我們對於西洋文化的接收在事實和心理兩方面都發生很大的障礙。又不幸的很,當外來勢力向我們猛進的時候,我們又是在滿清統治之下。一切對外失敗的痛恨,歸咎於內政之不當,歸咎於統治階級的昏庸,歸咎於滿清政府之腐敗。如果當時統治者不是滿清而是漢人,情形或者可以根本不同。在漢人的統治下,同盟會也就不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過去的歷史很明白地指示我們革命是浪費的,因為每當革命“非群雄並起,天下鼎沸,則舊政府必不可倒,如是者有年。既倒之後,新政府思所以削平群雄,綏靖鼎沸,如是復有年。故吾國每一度大革命,長者數十年,短者亦十數年”(梁啟超:《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見《飲冰室文集》)。這些事實是同盟會諸志士所深知的。他們也知道在強敵壓境,國勢危急的時候,革命足以消耗元氣,減低國家對外的力量。然而他們毅然決然不顧一切而革命者─當然還有別的根本問題,如建共和政體─“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與有力焉。清廷腐敗已達極點,故辛亥革命成功非常迅速。但滿清被推倒之後,接著就十幾年的軍閥割據及混沌的內戰。在內亂的過程中只有破壞沒有建設,我們的現代化又莫名其妙地延遲了許多年。
到現在我們政治經濟都是摹仿西洋的,但我們社會本質(因為農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及生活觀念大體上還沒有改變。我們的瓶是新的,而瓶內所盛的酒是舊的。有許多生活的觀念與現代的新制度是衝突的,是扞格不入的。現代的國家是法治的國家,而我們傳統的儒教的政治哲學是“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人治主義。法律─無論是憲法,是普通的法律或命令─在西洋一字有一字的拘束力,而我們不論政府與人民都視法律為具文,為官樣文章,以致法律與生活不能呼應。我們沒有濃厚的國家觀念、堅強的政治組織,因為在過去的社會裡並不感覺國家的重要及堅強政治組織的需要。堅強的政治組織勢必用其組織以干涉人民的生活,而我們舊社會的政治理想不是干涉而是放任,不是積極有為而是消極無為,不是為民興利而是與民休息。在這個社會裡風俗習慣代替了法律,紳士代替了法官,除納稅上糧外,人民與政府很少發生直接關係。
這一種社會在閉關自守的時候是可以維持生存的,但自海禁大開以來情形大變了。外來勢力侵入中國好似野牛闖進古董店一樣,把架子上的漢瓦宋瓷撞得粉碎。舊社會受了西洋力量的襲擊而呈崩潰的現象,但舊社會的影響依然存在。自辛亥以來歷次革命的使命不僅在取得政權(實際上西方所謂“政權”在中國並不存在),而且要創造政權。我們要樹立一個中央政府,不是有名無實的中央政府,而是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但物質的條件(如交通)不夠,心理的基礎(如國家觀念)欠缺。我們要打倒私人的軍隊、官吏的貪污,而建設國家的武力、廉明的政治。我們不但要有新的制度,而且要有新的法律觀念,新的行政觀念,新的政治道德。制度是可從外國借得來的,而觀念及道德非自己養成不可。因為中國面積之大,人口之多,交通的不便,教育之不普及,所以我們的理想與事實,計劃與實施,往往“圓鑿方枘,鉏鋙難入”。
自清末到現在,我們推行新政治、提倡新教育的結果,不能說完全失敗。把這一次的抗戰與甲午中日戰爭相比較,就可以看出在這四十餘年的中間,中國政治的統一、國民的國家意識確有顯著的進步。甲午之役是李鴻章與日本之戰,是以直隸一省當日本全國,據梁啟超所說:“劉公島降艦一役,當事者致函日軍,求放還兩廣一艦,謂此艦係屬廣東,此次戰役與廣東無涉云云。”(《李鴻章傳》)當時各省對於戰爭漠不相關的態度,於此可見。而此次抗戰則為中國歷史上自來所未有的全民抗戰。我們雖然有了顯著的進步,但到現代化的距離還是很遠。二千餘年所養成社會政治風氣並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變的。但我們確信中國所以落後的原因並不是中華民族之不如人,而是許多歷史、地理、經濟的原素所構成的。中華民族是個優秀而大有作為的民族。此後我們能不能在世界上佔重要的地位全視我們之努力與否。
在區區幾萬字的小冊子裡討論偌大的題目顯然是不可能的事。如果讀者想從這本小冊裡對於二千年來中國的政治得到一個有系統的敘述,他一定會失望的。好在作者個人並沒有存著這麼大的野心:他的目的不在做一本中國政治史或政治制度史,而在指出自秦漢到現在中國政治的特點和動向。就在這一點上他也沒有系統化的意志,許多應該討論的問題都遺漏了,而在其所討論的問題的範圍以內也難免片段或零碎之譏。
在戰時首都的重慶寫書最大的困難是參考資料的貧乏。極平凡、極普通的書籍在這裡也無從尋覓。回憶三年前,北方各大學圖書館內寫作的便利不禁...
目錄
緒論
第一章 皇帝、專制、統一
第二章 有形政府之一─中央
第三章 有形政府之二─地方
第四章 無形政府之一─幕僚
第五章 無形政府之二─書吏
第六章 政治風氣之一─名教、傾軋、高調
第七章 政治風氣之二─貪污
餘論
緒論
第一章 皇帝、專制、統一
第二章 有形政府之一─中央
第三章 有形政府之二─地方
第四章 無形政府之一─幕僚
第五章 無形政府之二─書吏
第六章 政治風氣之一─名教、傾軋、高調
第七章 政治風氣之二─貪污
餘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