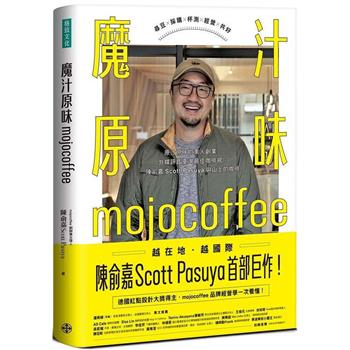陸游作詩最勤的時候,總是他最不樂意當詩人的時候
每次貶謫之初,東坡先生都是戰戰兢兢如驚弓之鳥,合乎人之常情,令政敵滿意,可最多三個月吧,這傢伙就快活了,故態復萌了
形勢緊急了,需要籠絡人心了,辛棄疾呼之即來,挽袖子幹活;稍微安定了,就把他踢回老家待著
「我要這花開到永遠。」這是以有涯向無涯挑戰,是一種疲憊生活中不死的英雄夢想。這就是歐陽修的絕代風流
除了趙明誠,沒甚麼人知道,李清照是個賭徒
2016年亞馬遜中國年度新銳作家傾情講述宋代文人的詩酒風流、愛恨情癡。
一段宋詞時光,追憶一個王朝的美麗與哀愁;
古典傳世名畫,重現文藝盛世的精緻與優雅。
宋朝為何被譽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期?那令後世敬仰尊崇的文化到底有甚麼魅力?《大好河山可騎驢》將詞、史、事相結合,以幽默通達的語言,通過對宋詞、文人、史事的解讀,回溯兩宋時期知識分子的遭遇乃至家國大事。尤其是寫出了宋代士大夫的風骨,他們詩酒風流背面的仁愛之心,寬袍大袖下的鐵肩道義,既心懷天下,又不失日常中的優雅。讓人深切感受到我們的國家真切曾有過從容、風流、精緻而仁愛的社會生活——雖然它也存在許多歷史局限,政治缺陷,人性灰暗。
本書特色
本書文筆幽默、透徹、品評詩詞,將詞、史、事相結合,展示出宏闊又細緻的宋代優雅。
圖文並茂,古典傳世名畫展現文藝盛世的精緻與細膩。
自2012年9月在豆瓣讀書上線以來,一直評分高達9分以上,有讀者稱其是所讀過的寫得最好的歷史文化讀物。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大好河山可騎驢:宋朝的風流與風雅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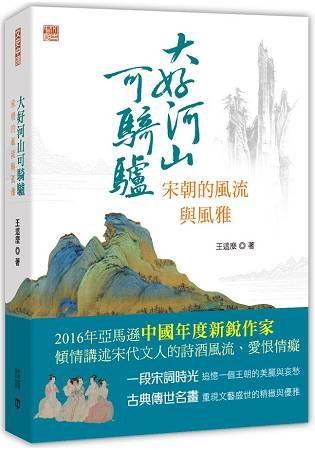 |
大好河山可騎驢:宋朝的風流與風雅 作者:王這麼 出版社: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4-26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 458 |
中國各朝歷史 |
$ 458 |
Literature & Fiction |
$ 493 |
宋元史 |
$ 522 |
中文書 |
$ 522 |
中國歷史 |
$ 52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大好河山可騎驢:宋朝的風流與風雅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王這麼
原名王芳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人。
對宋朝的歷史文化頗有研究,其對細節的發現尤為難得。
2005年開始在豆瓣網低調寫作,其文采斐然,行文犀利而幽默有趣,收穫了一批忠實讀者。曾出版文化隨筆《簪花的少年郎》《萬物皆有傷心處》等。
王這麼
原名王芳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人。
對宋朝的歷史文化頗有研究,其對細節的發現尤為難得。
2005年開始在豆瓣網低調寫作,其文采斐然,行文犀利而幽默有趣,收穫了一批忠實讀者。曾出版文化隨筆《簪花的少年郎》《萬物皆有傷心處》等。
目錄
1.大好河山可騎驢
2.貶謫者的春天
3.我姓辛,艱辛的「辛」
4.詞人醉了,胡說亂道
5.更多的人漂泊在路上
6.「修」要花開到永遠
7.為賭徒的李清照.
8.公子和他的薄情女郎們
9.詞與江湖,都不能給人生以浪漫
10.人人都愛秦少遊
11.錯生帝王家的才子們
12.文藝女青年朱淑真
13.告別青春告別美
14.在洛陽的花與酒中沉醉
15.卻見詞人在高牆
2.貶謫者的春天
3.我姓辛,艱辛的「辛」
4.詞人醉了,胡說亂道
5.更多的人漂泊在路上
6.「修」要花開到永遠
7.為賭徒的李清照.
8.公子和他的薄情女郎們
9.詞與江湖,都不能給人生以浪漫
10.人人都愛秦少遊
11.錯生帝王家的才子們
12.文藝女青年朱淑真
13.告別青春告別美
14.在洛陽的花與酒中沉醉
15.卻見詞人在高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