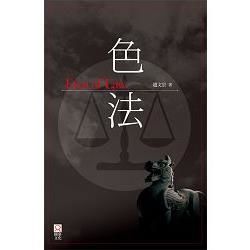本書收錄筆者1996年至2007年間有關大中華地區法律及性別情慾公義政治互動的中文文章。
內容觸及婚姻法/婚外情、女性權益/平等機會、原居民傳統、性罪行、家庭暴力、色情、性工作及性傾向歧視。筆者在分析論述時,既著重法學理論分析,亦重視實際法律運作;一方面運用當代歐美社會──法律哲學,另一方面也強調本土在地化的需要。其中精彩內容包括:
「快樂有罪?——後現代情慾物語」:企圖由後現代哲學分析近代中國內地及香港婚姻法對婚姻形式的規定要求。
「本土傳統 = 歧視豁免權?」:討論反歧視法律,將研讀聚焦在香港「新界男原居民傳統vs歐美平權理念」、「中華文化vs外來文化」等虛擬二元上。
「本土性別政治的重建」:借探討應付家庭暴力的法律機制,再一次研究把海外法改經驗移植本土的可能。
「因為禁、所以愛」:分別從女性主義、後現代文化理論及心理分析的角度解讀香港色情現象及法律政治的互動。
筆者在書中企圖藉探究拆解「法律崇拜」、「法律中立」等神話的同時,可以再現法律機制如何與其他專業系統(如宗教醫療社會工作)協力建構性別情慾大話/敘事,製造他者複製壓迫。
然而,法律又可否轉身成為反抗力量?外地法律改革理論經驗又能否/如何在華人地區落實?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色/法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52 |
中文書 |
$ 352 |
法律 |
$ 360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色/法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趙文宗
香港大學榮譽法律學士,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法學博士,香港城市大學法律碩士,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碩士,蘇格蘭士嘉夫格賴特大學(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法律碩士。1996年加入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任助理教授;之後分別任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高級培訓顧問、澳洲達爾文大學(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法學院講師及占姆士庫克大學(James Cook University)法學院講師。現職香港樹仁大學法律副教授兼法律與商業系系主任。中文著作包括:
2013年世界華人法哲學大會文集(2013)(許章潤合編著)、現代佛教與華人社會(2012)(劉宇光合編著)、兒童•醫療•法律——大中華比較研究(2012)(編)、中華性/別──年齡機器(2011)(編著)、香港實用婚姻法(2011)(何志權合著)、社會福利與法律應用——溝通與充權(2010初版、2011增訂再版、2012第三版)(洪雪蓮、莊耀洸合編著)、中華法哲學發展——全球化與本地化之間(2010)(編著)、中國內地/香港婚姻法及調解:比較與實務(2009)(阮陳淑怡、李秀華合著)、性工作與公義:法律與政策(2009)(嚴月蓮合編著)、兒童性侵犯:聆聽與尊重(2009)(編著)、跨境家庭:踰越與對話(2008)(陳高凌合編著)、迷糊‧情慾‧法律(2006)、中國內地/香港婚姻法實務(2001初版、2004再版、2005內地版)(林滿馨、李秀華合著)、香港法律與社會工作(2000)(林滿馨合編著)、「衣櫃」性史:英美港同志運動史(1995)(周華山合著)、色情現象:我看見色情看見我(1993)(周華山合著)
趙文宗
香港大學榮譽法律學士,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法學博士,香港城市大學法律碩士,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碩士,蘇格蘭士嘉夫格賴特大學(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法律碩士。1996年加入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任助理教授;之後分別任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高級培訓顧問、澳洲達爾文大學(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法學院講師及占姆士庫克大學(James Cook University)法學院講師。現職香港樹仁大學法律副教授兼法律與商業系系主任。中文著作包括:
2013年世界華人法哲學大會文集(2013)(許章潤合編著)、現代佛教與華人社會(2012)(劉宇光合編著)、兒童•醫療•法律——大中華比較研究(2012)(編)、中華性/別──年齡機器(2011)(編著)、香港實用婚姻法(2011)(何志權合著)、社會福利與法律應用——溝通與充權(2010初版、2011增訂再版、2012第三版)(洪雪蓮、莊耀洸合編著)、中華法哲學發展——全球化與本地化之間(2010)(編著)、中國內地/香港婚姻法及調解:比較與實務(2009)(阮陳淑怡、李秀華合著)、性工作與公義:法律與政策(2009)(嚴月蓮合編著)、兒童性侵犯:聆聽與尊重(2009)(編著)、跨境家庭:踰越與對話(2008)(陳高凌合編著)、迷糊‧情慾‧法律(2006)、中國內地/香港婚姻法實務(2001初版、2004再版、2005內地版)(林滿馨、李秀華合著)、香港法律與社會工作(2000)(林滿馨合編著)、「衣櫃」性史:英美港同志運動史(1995)(周華山合著)、色情現象:我看見色情看見我(1993)(周華山合著)
目錄
目錄
增訂再版序
序
導讀(增訂再版)
快樂有罪?——後現代情慾物語:由中國內地《婚姻法》企圖打擊「婚外情」說起
本土傳統 = 歧視豁免權? ——由後殖民性別公義觀審視香港新界丁屋政策
本土性別政治的重建——香港2008年以前處理虐妻法律的後殖民論述
因為禁、所以愛——香港管制色情法律的後現代論述
「可以向你温柔地說不嗎?」——從「婚內強姦豁免權」論爭審視香港強姦法律
「同」法共舞——論香港反性傾向歧視立法
從「公義」審視現行香港管制性工作法律——「非性化」可行嗎?
邊緣的和諧反抗混雜——香港性╱別公義法律論述
成文法索引
案例索引
人名索引
增訂再版序
序
導讀(增訂再版)
快樂有罪?——後現代情慾物語:由中國內地《婚姻法》企圖打擊「婚外情」說起
本土傳統 = 歧視豁免權? ——由後殖民性別公義觀審視香港新界丁屋政策
本土性別政治的重建——香港2008年以前處理虐妻法律的後殖民論述
因為禁、所以愛——香港管制色情法律的後現代論述
「可以向你温柔地說不嗎?」——從「婚內強姦豁免權」論爭審視香港強姦法律
「同」法共舞——論香港反性傾向歧視立法
從「公義」審視現行香港管制性工作法律——「非性化」可行嗎?
邊緣的和諧反抗混雜——香港性╱別公義法律論述
成文法索引
案例索引
人名索引
序
增訂再版序
再印行〈色/法〉一書的想法,近十年一直藏在心裡。
初版印行,我即發覺當中錯印處處,十分心痛。原因不用細想追尋,總之,責任在我,不容置疑。
所以,藉入行教書二十年的契機,我決定把這書增訂再印,作為心理補償也好,作為二十年研究回顧也好,總算是還了心願。也借這次重印,我修正了參考文章書目中不完備的資料,刪除來源不可再追溯的資料,特別加入翻譯引述的原文,補充了近年重大法律改革及理論發展,並把焦點放香港;亦特別收入一篇深化討論理論移植的文章。這文章也是我首次運用德勒茲(Deleuze)哲學的嘗試。我亦大幅修訂性工作一文採索討論的方向。
現在,再細閱原文字,感慨萬千:一直批評批判的事物視點,近十年變化不大。是我們不夠努力?是我們改革策略沒有隨時代轉變?還是香港人太固執,明知自己理虧,卻口舌不饒人,生怕聆聽他人意見就是喪失自我主體,於是寧願死佔領自我舒適區,不作改變?這組問題,我們的確需要細想反省。
二十年前,當開始與非政府組織在一些性別機器議題上合作倡議落實改革法律方案,我便一直恪守堅持一個原則——只給予意見,遊說工作從主動不參與。理由簡單直接:研究寫文是我所喜所長,遊說宣傳卻是我缺點短處,且應是弱勢邊緣訴求者自我肯定逐漸充權的必然必經。
但,自八年前從澳洲回港,開始嘗試行政工作,多了機會與法律專業政府官員交流對話,也逐漸明白了解她/他們的行事模式與思索考慮。於是自以為明瞭企圖破舊立新和懷疑嶄新思維兩陣營的底線及語言,頭腦發熱時忽發奇想便努力嘗試把非政府組織的意見建議介紹給法律專業,也會盡力將政府及專業界別考慮習慣與社運分子分享。但溝通交流始終不暢順,有時嚴重閉塞,有傷和氣,不歡而散;有時則(刻意)忘記溝通,不瞅不睬,浪費精力。
最令倡議(任何)法律改革人士(包括非政府組織及社運分子)不解的應是:明明道理放在面前,明顯時勢已完全改變,為何建制仍頑拒改變?對此,甯應斌及何春蕤在〈民困愁城〉一書中清楚解釋「穩定」的吸引力;當現代社會以理性主導專業知識(如法律醫療)取代傳統習慣來治理組織群眾,強調珍惜的自然是「井井有序、千篇一律」;所有不穩定未知數(如慾望天災)就須控制減少,「以免自我沒有安全感」(1) ——甯和何就以用餐及葬禮現在都以效率及標準為依歸準則作例子,說明不理性在現代社會遭理性化機器收歸的現象,也反証了不規則無名狀被次等化的大趨勢。可是,不單「理性/不理性」根本難以定義及區分;情緒慾望等不理性更往往經歷遭受理性詮釋翻譯後成為現代文化管理不可或缺的部分。
於是德勒茲學派便質疑:一個統一平庸沒個性的主體(包括法律及哲學視角)是否能回應日益加速變化的社會環境脈絡呢?(2) 譬如,現行法律若不可迅速處理網絡世界帶來的改變(如網上欺凌及即時新聞),那法律還有用嗎?布雷多蒂(Braidotti)在〈Nomadic Subjects〉就指出:我們需要的是一份可準確回應嶄新外在因素及內在不停改變的「生命指引」;更重要的是:這份生命指引須不斷自我顛覆並活化中心。(3)換言之,堅持一個表面看來自有永有的主體標準只會謀殺磨滅「創新能力」(Creativity),但正正卻又是這份創新能力令人類可以處理不停湧現的挑戰。(4)
德勒茲理論當然一方面對盲目反對修法陣營當頭棒喝,另一方面也對倡議修法者有警醒作用:以往倡談修法的策略是否仍有效?在過去數年,我曾看到非政府組織社運人士簡單把反對按她/他們路線圖修法的人惡魔化,不再溝通,認為遊說頑固保守派是浪費時間。我固然明白面對冥頑不靈是如何氣餒,但簡單將質疑者統統貶為敵人,又是否犯上現代社會理性化平庸主題的錯誤?是否同樣忘了內視反省自己生命指引遊說策略的適時創新性?同理,反修法者又是否對自己生命指引過於自信貪婪安逸,拒絕聆聽其他體驗呢?
說回德勒茲理論對回應變化社會的重視。要有效率並準確地回應社會的變化,我們須對時間( Time)及空間(Space)非常敏感。意即:我們須先把宰制歷史化,再從傳統虛擬的桎梏枷鎖中掙脫,創新建立新主體,計劃新顛覆策略及設計逃逸路線。(5) 然後,我們(尤其邊緣弱勢)再藉規劃逃逸路線,建造尋找建造適合自己的主體轉化生成空間、確定反抗點及認清當中權力糾纏。布雷多蒂稱以上整個活動為「圖廊」(Figuration)。(6) 圖廊目的在於顛覆既有宰制的「主宰符號」(Master Signifier)——這也應是修法的目的:新法律須揚棄以往不公義法制的理論中心(如陽物中心異性愛霸權)。
由此我們得知主體機器乃是由潛意識推動的一個過程,當中涉及理智的選擇和不同慾望多重權力之間的「交涉」(Negotiation)。德勒茲式交涉是影響主體轉化生成各種力量的談判。換言之,缺乏對話沒有了解,主體沒法創新:同理,本地非政府組織邊緣弱勢是否可在一直以來倡議修法的(失敗)經驗中,創新建造一些嶄新的遊說策略呢?而反修法者又會否願意放下身段與倡議修法者分享自己憂慮呢?
最後一點,不論是在謀劃策略或準備修法中,「學習」都是必須的。學習意指建立關聯;那就是說:非政府組織與法律專業應要互相了解彼此關心議題及背後緣由。(7) 譬如,為何香港不可有「強制起訴」(Compulsory Prosecution)呢?原來起訴與否是律政司司長的專權。那倡議修法者就必須解釋為何某些罪行須特行特辦。又例如,法律專業須明白一些証人(也是受害人)為何如此恐懼上法庭作供,才可釋除協助受害人組織的疑慮。
簡言之,要法律維護公義,法律須與時並進,準繩地解決每一弱勢社群的關心懸疑。反對支持修法兩者須互相清晰了解彼此的關注,才能創立新的法律及策略。只是囿於以往經驗(「我參加社運二十年,我相信憑我熱情必會勝利。」,「我當律師那麼久,不覺這些問題存在。」);或,意氣用事的宣稱:「只要反對者出現會議,我必會令她難受」「我為何要給他面子,只有他上司的上司來會議我才出席」、「她們可以要求開會,五分鐘我就打發她們」,只會令法律發展停滯,公義不得彰顯。
初版成書時,我感謝了Ned這位前上司。他給我的提點批判,至今受用。雖然大家在不同國家不同城市居住工作,我們仍常有聯絡,大家都依然是好友。
然,與她卻完全分離了。雖居於同一城市,已沒有接觸。她啟發我教育的熱誠,引領我入行。在此,再一次多謝她,祝她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註釋:
1 甯應斌、何春蕤(2012:329)。
2 Deleuze & Guattari(1986)。
3 Braidotti(2011:5)。
4 Guattari & Rolnik(2008:54)。
5 Braidotti, Rosi(2011:59)。
6 Braidotti, Rosi(2002)。
7 Cutler & MacKenzie(2011:57-58)。
參考書目:
甯應斌、何春蕤(2012)民困愁城 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Braidotti, Rosi (2002) Metamorphoses Cambridge, UK: Polity.
Braidotti, Rosi (2011) Normatic Subjec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utler, Anna & MacKenzia, lain (2011) ‘Bodies of Learning’ in Guillaume, Laura & Hughes, Joe (eds) Deleuze and the Bod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Deleuze, Gilles & Guattari, Felix (1986) Nomadology New York: Semiotext(e).
Guattari, Felix & Rolnik, Suely (2008) Molecular Revolution in Brazil Los Angeles: Semiotest(e).
序
不經不覺,來了澳洲已超過一年。由當初的戰戰兢兢上課,深怕因不了解本土文化說錯話開罪同學,到現在下課後和同學把酒言歡談天說地;由不能適應本地人的工作節奏,到堅持自己日程效率兼容他人生活悠遊。中間轉接最使我感動的是同學朋友同工的關懷支持,也令我深深體會不斷反省自己及接納多元文化的重要。
每個人都問:澳洲學生和香港學生有甚麼分別?其實這種比較根本意義不大——主體是論述產品,而澳港兩地歷史文化脈絡差異,社會教育制度不同,生命成長固然不會一樣,澳洲及香港人各自內部已經不會千人一面,更何況學生?但,澳洲同學有一特點的確有趣,可與大家分享。我辦的課,都是「法學理論」、「人權法律」及「法律、性別及性慾」等「非賺錢」科目,卻從未曾有人問我:「讀這一科有沒有『用』?」我曾問學生為甚麼要選修這幾課,她/他們反問我:「為甚麼不?」、「讀了那麼多法律,總想知為甚麼還有不公平吧?有甚麼特別?」
我還記得,在香港,曾問一個同學畢業後想做甚麼。她說:「還用問?當然是律師!」「為甚麼?」「讀完法律不做律師?浪費點吧?不當律師,如何賺錢?」,「難道這就是香港法律學生律師的生命觀?除了錢以外,公義及顧客感受利益皆屬其次?」我自問。我不(願)相信,所以在城大最後一課,大膽的問同學:「有誰願意在執業後每年做一次Pro Bono(義務官司)?」只有一位舉手。
我無意再造「澳洲/天上vs香港/人間」「達爾文學生/包容vs香港學生/功利」等二元對立——事實上,亦有澳洲同學說出「千萬不要接觸原居民,只有社工才理她/他們!」「要賺錢?到中國教內地英文吧!」等大白人中心思想宣言。然而,澳洲學生那種容許差異的胸襟、願意探求法律價值取向的態度,卻令我開始明白為何在澳洲,法律及法律界人士並不會如此高高在上,也使法律自然和公義掛鈎。這也解釋了為甚麼澳洲法律可以容納各種反歧視法(除反性別/殘疾/家庭崗位歧視等法例外,更已立法禁止性傾向/年齡/宗教/易性/種族歧視);為甚麼「法律應否介入家庭暴力」等問題根本不須再討論。為甚麼達爾文家事法庭定期與各團體開會檢討現行法律?為甚麼法官也要參加進修班,增進社會科技知識……
我當然不是認為澳洲法律完美無瑕——澳洲至今仍沒有人權法,原居民還是深受歧視。我亦不主張要把澳洲法律精神全盤硬移植香港,人所共知文化土壤不同結果不一樣的道理。然而,簡簡單單地說老外法律文化不適合港人就拒絕外地經驗是否太固步自封?香港社會為何不去反省為何其他文化那麼著重公義多元,而香港主流卻不是?
法律不一定等於公義,社會也不一定需要公義;但誰又願意活在純粹功利環境嗎?
再印行〈色/法〉一書的想法,近十年一直藏在心裡。
初版印行,我即發覺當中錯印處處,十分心痛。原因不用細想追尋,總之,責任在我,不容置疑。
所以,藉入行教書二十年的契機,我決定把這書增訂再印,作為心理補償也好,作為二十年研究回顧也好,總算是還了心願。也借這次重印,我修正了參考文章書目中不完備的資料,刪除來源不可再追溯的資料,特別加入翻譯引述的原文,補充了近年重大法律改革及理論發展,並把焦點放香港;亦特別收入一篇深化討論理論移植的文章。這文章也是我首次運用德勒茲(Deleuze)哲學的嘗試。我亦大幅修訂性工作一文採索討論的方向。
現在,再細閱原文字,感慨萬千:一直批評批判的事物視點,近十年變化不大。是我們不夠努力?是我們改革策略沒有隨時代轉變?還是香港人太固執,明知自己理虧,卻口舌不饒人,生怕聆聽他人意見就是喪失自我主體,於是寧願死佔領自我舒適區,不作改變?這組問題,我們的確需要細想反省。
二十年前,當開始與非政府組織在一些性別機器議題上合作倡議落實改革法律方案,我便一直恪守堅持一個原則——只給予意見,遊說工作從主動不參與。理由簡單直接:研究寫文是我所喜所長,遊說宣傳卻是我缺點短處,且應是弱勢邊緣訴求者自我肯定逐漸充權的必然必經。
但,自八年前從澳洲回港,開始嘗試行政工作,多了機會與法律專業政府官員交流對話,也逐漸明白了解她/他們的行事模式與思索考慮。於是自以為明瞭企圖破舊立新和懷疑嶄新思維兩陣營的底線及語言,頭腦發熱時忽發奇想便努力嘗試把非政府組織的意見建議介紹給法律專業,也會盡力將政府及專業界別考慮習慣與社運分子分享。但溝通交流始終不暢順,有時嚴重閉塞,有傷和氣,不歡而散;有時則(刻意)忘記溝通,不瞅不睬,浪費精力。
最令倡議(任何)法律改革人士(包括非政府組織及社運分子)不解的應是:明明道理放在面前,明顯時勢已完全改變,為何建制仍頑拒改變?對此,甯應斌及何春蕤在〈民困愁城〉一書中清楚解釋「穩定」的吸引力;當現代社會以理性主導專業知識(如法律醫療)取代傳統習慣來治理組織群眾,強調珍惜的自然是「井井有序、千篇一律」;所有不穩定未知數(如慾望天災)就須控制減少,「以免自我沒有安全感」(1) ——甯和何就以用餐及葬禮現在都以效率及標準為依歸準則作例子,說明不理性在現代社會遭理性化機器收歸的現象,也反証了不規則無名狀被次等化的大趨勢。可是,不單「理性/不理性」根本難以定義及區分;情緒慾望等不理性更往往經歷遭受理性詮釋翻譯後成為現代文化管理不可或缺的部分。
於是德勒茲學派便質疑:一個統一平庸沒個性的主體(包括法律及哲學視角)是否能回應日益加速變化的社會環境脈絡呢?(2) 譬如,現行法律若不可迅速處理網絡世界帶來的改變(如網上欺凌及即時新聞),那法律還有用嗎?布雷多蒂(Braidotti)在〈Nomadic Subjects〉就指出:我們需要的是一份可準確回應嶄新外在因素及內在不停改變的「生命指引」;更重要的是:這份生命指引須不斷自我顛覆並活化中心。(3)換言之,堅持一個表面看來自有永有的主體標準只會謀殺磨滅「創新能力」(Creativity),但正正卻又是這份創新能力令人類可以處理不停湧現的挑戰。(4)
德勒茲理論當然一方面對盲目反對修法陣營當頭棒喝,另一方面也對倡議修法者有警醒作用:以往倡談修法的策略是否仍有效?在過去數年,我曾看到非政府組織社運人士簡單把反對按她/他們路線圖修法的人惡魔化,不再溝通,認為遊說頑固保守派是浪費時間。我固然明白面對冥頑不靈是如何氣餒,但簡單將質疑者統統貶為敵人,又是否犯上現代社會理性化平庸主題的錯誤?是否同樣忘了內視反省自己生命指引遊說策略的適時創新性?同理,反修法者又是否對自己生命指引過於自信貪婪安逸,拒絕聆聽其他體驗呢?
說回德勒茲理論對回應變化社會的重視。要有效率並準確地回應社會的變化,我們須對時間( Time)及空間(Space)非常敏感。意即:我們須先把宰制歷史化,再從傳統虛擬的桎梏枷鎖中掙脫,創新建立新主體,計劃新顛覆策略及設計逃逸路線。(5) 然後,我們(尤其邊緣弱勢)再藉規劃逃逸路線,建造尋找建造適合自己的主體轉化生成空間、確定反抗點及認清當中權力糾纏。布雷多蒂稱以上整個活動為「圖廊」(Figuration)。(6) 圖廊目的在於顛覆既有宰制的「主宰符號」(Master Signifier)——這也應是修法的目的:新法律須揚棄以往不公義法制的理論中心(如陽物中心異性愛霸權)。
由此我們得知主體機器乃是由潛意識推動的一個過程,當中涉及理智的選擇和不同慾望多重權力之間的「交涉」(Negotiation)。德勒茲式交涉是影響主體轉化生成各種力量的談判。換言之,缺乏對話沒有了解,主體沒法創新:同理,本地非政府組織邊緣弱勢是否可在一直以來倡議修法的(失敗)經驗中,創新建造一些嶄新的遊說策略呢?而反修法者又會否願意放下身段與倡議修法者分享自己憂慮呢?
最後一點,不論是在謀劃策略或準備修法中,「學習」都是必須的。學習意指建立關聯;那就是說:非政府組織與法律專業應要互相了解彼此關心議題及背後緣由。(7) 譬如,為何香港不可有「強制起訴」(Compulsory Prosecution)呢?原來起訴與否是律政司司長的專權。那倡議修法者就必須解釋為何某些罪行須特行特辦。又例如,法律專業須明白一些証人(也是受害人)為何如此恐懼上法庭作供,才可釋除協助受害人組織的疑慮。
簡言之,要法律維護公義,法律須與時並進,準繩地解決每一弱勢社群的關心懸疑。反對支持修法兩者須互相清晰了解彼此的關注,才能創立新的法律及策略。只是囿於以往經驗(「我參加社運二十年,我相信憑我熱情必會勝利。」,「我當律師那麼久,不覺這些問題存在。」);或,意氣用事的宣稱:「只要反對者出現會議,我必會令她難受」「我為何要給他面子,只有他上司的上司來會議我才出席」、「她們可以要求開會,五分鐘我就打發她們」,只會令法律發展停滯,公義不得彰顯。
初版成書時,我感謝了Ned這位前上司。他給我的提點批判,至今受用。雖然大家在不同國家不同城市居住工作,我們仍常有聯絡,大家都依然是好友。
然,與她卻完全分離了。雖居於同一城市,已沒有接觸。她啟發我教育的熱誠,引領我入行。在此,再一次多謝她,祝她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註釋:
1 甯應斌、何春蕤(2012:329)。
2 Deleuze & Guattari(1986)。
3 Braidotti(2011:5)。
4 Guattari & Rolnik(2008:54)。
5 Braidotti, Rosi(2011:59)。
6 Braidotti, Rosi(2002)。
7 Cutler & MacKenzie(2011:57-58)。
參考書目:
甯應斌、何春蕤(2012)民困愁城 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Braidotti, Rosi (2002) Metamorphoses Cambridge, UK: Polity.
Braidotti, Rosi (2011) Normatic Subjec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utler, Anna & MacKenzia, lain (2011) ‘Bodies of Learning’ in Guillaume, Laura & Hughes, Joe (eds) Deleuze and the Bod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Deleuze, Gilles & Guattari, Felix (1986) Nomadology New York: Semiotext(e).
Guattari, Felix & Rolnik, Suely (2008) Molecular Revolution in Brazil Los Angeles: Semiotest(e).
序
不經不覺,來了澳洲已超過一年。由當初的戰戰兢兢上課,深怕因不了解本土文化說錯話開罪同學,到現在下課後和同學把酒言歡談天說地;由不能適應本地人的工作節奏,到堅持自己日程效率兼容他人生活悠遊。中間轉接最使我感動的是同學朋友同工的關懷支持,也令我深深體會不斷反省自己及接納多元文化的重要。
每個人都問:澳洲學生和香港學生有甚麼分別?其實這種比較根本意義不大——主體是論述產品,而澳港兩地歷史文化脈絡差異,社會教育制度不同,生命成長固然不會一樣,澳洲及香港人各自內部已經不會千人一面,更何況學生?但,澳洲同學有一特點的確有趣,可與大家分享。我辦的課,都是「法學理論」、「人權法律」及「法律、性別及性慾」等「非賺錢」科目,卻從未曾有人問我:「讀這一科有沒有『用』?」我曾問學生為甚麼要選修這幾課,她/他們反問我:「為甚麼不?」、「讀了那麼多法律,總想知為甚麼還有不公平吧?有甚麼特別?」
我還記得,在香港,曾問一個同學畢業後想做甚麼。她說:「還用問?當然是律師!」「為甚麼?」「讀完法律不做律師?浪費點吧?不當律師,如何賺錢?」,「難道這就是香港法律學生律師的生命觀?除了錢以外,公義及顧客感受利益皆屬其次?」我自問。我不(願)相信,所以在城大最後一課,大膽的問同學:「有誰願意在執業後每年做一次Pro Bono(義務官司)?」只有一位舉手。
我無意再造「澳洲/天上vs香港/人間」「達爾文學生/包容vs香港學生/功利」等二元對立——事實上,亦有澳洲同學說出「千萬不要接觸原居民,只有社工才理她/他們!」「要賺錢?到中國教內地英文吧!」等大白人中心思想宣言。然而,澳洲學生那種容許差異的胸襟、願意探求法律價值取向的態度,卻令我開始明白為何在澳洲,法律及法律界人士並不會如此高高在上,也使法律自然和公義掛鈎。這也解釋了為甚麼澳洲法律可以容納各種反歧視法(除反性別/殘疾/家庭崗位歧視等法例外,更已立法禁止性傾向/年齡/宗教/易性/種族歧視);為甚麼「法律應否介入家庭暴力」等問題根本不須再討論。為甚麼達爾文家事法庭定期與各團體開會檢討現行法律?為甚麼法官也要參加進修班,增進社會科技知識……
我當然不是認為澳洲法律完美無瑕——澳洲至今仍沒有人權法,原居民還是深受歧視。我亦不主張要把澳洲法律精神全盤硬移植香港,人所共知文化土壤不同結果不一樣的道理。然而,簡簡單單地說老外法律文化不適合港人就拒絕外地經驗是否太固步自封?香港社會為何不去反省為何其他文化那麼著重公義多元,而香港主流卻不是?
法律不一定等於公義,社會也不一定需要公義;但誰又願意活在純粹功利環境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