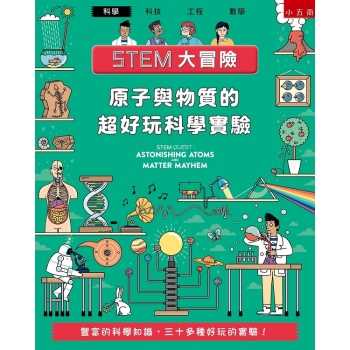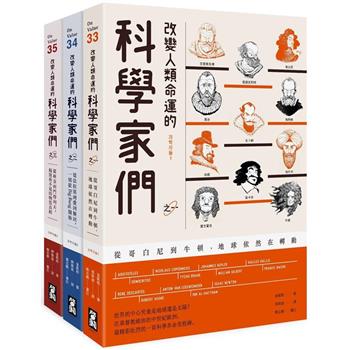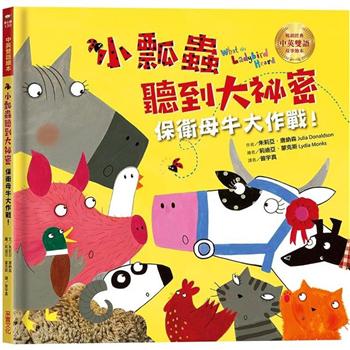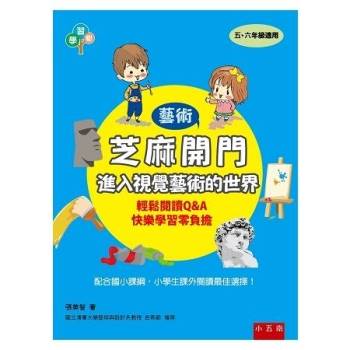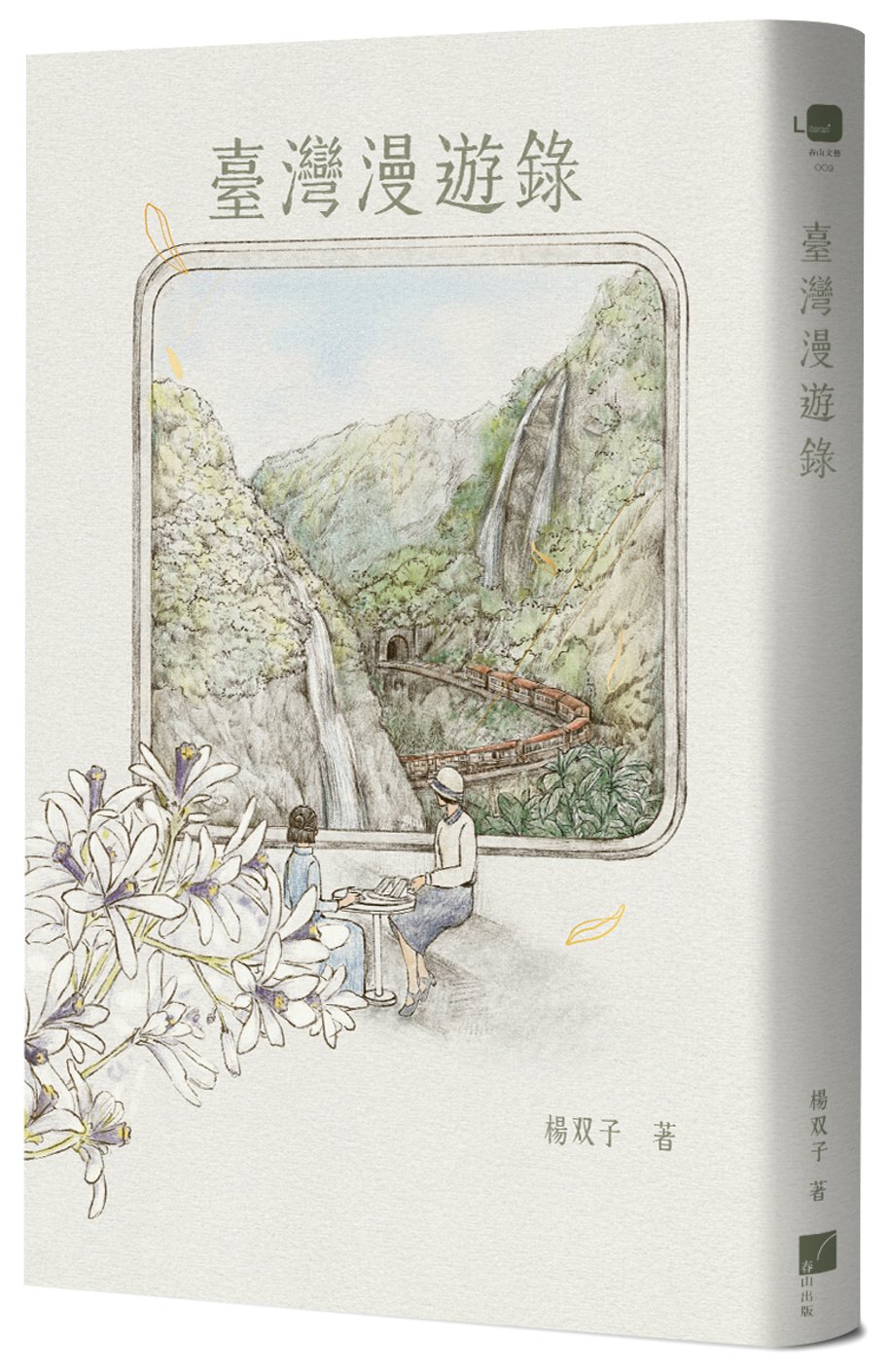聽舒伯特長大
最早對舒伯特的認識和印象是父親書房牆上所掛的一幅他的肖像。父親也是一位作曲家,他最崇拜的西方作曲家就是舒伯特,甚至把自己的形象和舒伯特相比,彷彿還揣摩出幾分相像之處。當然,父親在鋼琴前埋首作曲的時候,更認同舒伯特了,甚至口中唸唸有「調」,把舒伯特的某段曲子先彈出來,然後大讚其作曲法之玄妙:怎麼用這一個奇妙的和弦作結,真是意料不到!有時他甚至會走出書房,向我的母親—另一位音樂家—大談舒伯特的妙處,但母親往往微笑不語,不置可否。父親最激賞的是舒伯特的藝術歌曲,真是佳品無數,曲曲動人,譬如《小夜曲》(Serenade)、《菩提樹》(Der Lindenbaum),當然還有那首驚天動地的《魔王》(Der Erlkönig)。
父親當年在新竹師範教音樂,我在竹師附小讀小學。記得新來的校長高梓女士是位舞蹈家,而且在美國留過學,所以她上任後風格一新,要全校師生都學跳舞,男生也不能例外。所以她特別為我們男生編了一個集體舞,名叫「干戈舞」。我們每一個人赤膊上陣,每人還拿了一支竹竿,互相敲敲打打,並作各種隊型的變幻。練習時,彈鋼琴伴奏的那位助手似乎技巧不足,彈得非常生硬,奏出的音樂也僅為了符合拍子,聽來一無是處。最後,當表演綵排時,我們的音樂老師親自彈奏,音調完全不同了,原來那位助手把不少音符彈錯了,該升的(例如升F)不升,該降的(例如降C)不降,所以才那麼生硬。經過我們的音樂老師照譜還原後,音樂突然顯得生動活潑起來,我們遂聞歌起舞,其樂融融,表演得十分出色。原來高校長為我們選的這首鋼琴曲,就是舒伯特所作的《軍隊進行曲》(Marche Militaire)。
從小學進入中學,我以最低分考上以音樂教育享譽全省的新竹中學。中午休息時間,每間教室和走廊上的擴音器都會播放古典音樂。記得聽得最多的就是莫札特和舒伯特。據說聽莫札特的音樂連母牛都會多奶,不知對我們這群乳臭未乾的小伙子有何滋育的作用。聽來聽去,就是那幾首歌劇序曲:《費加羅的婚禮》(Le Nozze di Figaro)、《魔笛》(Die Zauberflöte)、《女人皆如此》(Così fan tutte, ossia La scuola degli amanti)等。而播出的舒伯特的唱片多是藝術歌曲,特別是那首《魔王》,幾乎每天中午都要聽一次,起先不知所云,後來才知道是一人扮演兩個角色──一個是小孩,另一個是魔王,小孩被魔王的甜言蜜語所騙,最後驚恐萬分,大叫媽媽。但我還是聽不出鬼氣來,只覺得這首曲子頗為動聽,和《聖母頌》(Ave Maria)、《小夜曲》等較流行的曲子不同,但也說不出其所以然來。
中學時代最熟悉的一首舒伯特的曲子,當然是《菩提樹》,幾乎每一個人都能哼唱。據說台灣在日據時代就有聽古典音樂的傳統,而這首曲子也可能有日文版,當然在《一百零一首世界名曲》等教材中也名列前茅,歌詞變成了中文,至今已忘,但曲調仍然深藏腦際,恐怕要伴我終身了。
舒伯特英年早逝,而且死於梅毒,真是令人難以置信,因為在我的心目中,特別是在幼年時代,他是一位最令我感到親切的作曲家。他的音樂世界中沒有半點污垢,更沒有任何人性的瑕疵,我聽他的歌曲時感受到一種心靈上的恬靜,似乎所有的雜念都隨着優雅的琴聲離我而去。我聽不懂德文的曲詞,卻往往被伴奏的鋼琴聲所吸引,所以我聽舒伯特的歌,勿寧說是他筆下的琴音──那種難以形容的節奏,如行雲流水,又那麼溫柔敦厚;像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詩中的那位「高地女郎」那麼天真,但又流露一股看破紅塵的世故;它從不拖泥帶水,但又較潺潺的水聲更有風韻。如果舒伯特的歌曲像一個在溪畔自憐的少女,那麼我寧願潛伏在小溪的流水中偷看她的微笑面容。總而言之,我自幼從聆聽舒伯特的歌曲中得到一種異樣的領悟:它的靈魂不在歌詞,而在鋼琴伴奏的旋律。這種說法,當然大逆不道,更顯露出我對德國古典文學的無知。(然而又不盡然,當我聆聽理查德.施特勞斯〔Richard Georg Strauss〕的《最後四首歌曲》〔Vier Letzte Lieder〕時,特別是那首《九月》〔September〕,歌詞的大意我幾乎背得出來,雖然仍然不懂德文!)
英國的一家唱片公司Hyperion,一口氣出了三十多張唱片,將舒伯特的全部歌曲錄製齊全,演唱的聲樂家不少,但鋼琴家伴奏只有一位──Grant Johnson。多年前德國名男中音迪斯考(D. Fischer-Dicskau),以演唱舒伯特歌曲著稱(我最喜歡的是《冬之旅》〔Winterreise〕,可能與年歲日增有關),但伴奏的鋼琴家傑拉爾德.穆爾(Gerald Moore)幾乎與他齊名,更遑論另外一張樂壇知名的《冬之旅》的唱片。主唱者並不太重要,樂迷趨之若鶩的反而是鋼琴怪傑里赫特(Sviatoslav Teofilovich Richter)舉世無匹的伴奏。我的這個怪論可能也不無道理,如果舒伯特的歌曲是魚(他作了一首著名的鋼琴五重奏,就叫作《鱒魚》〔Forellenquintett〕),那麼必須有相得益彰的行雲流水似的鋼琴伴奏,才能夠「如魚得水」。
中學時代所聽的舒伯特音樂,除了歌曲外,似乎只有那首《未完成交響樂》(Unfinished),也是我當年最嗜聽的曲子之一,而且覺得此曲較莫札特的序曲更有深度。特別是第一樂章開始,大提琴奏出來的旋律,真是娓娓動人,帶我進入另一個恬適的境界。此曲沒有完成,可能是這一個樂章太美了,已臻化境(和布魯克納的第九交響曲一樣),不能再續,正像舒伯特這位音樂家一樣,雖前有古人,但絕對後無來者。沒有任何一位後來的作曲家可以和他相比。
也許就因為如此,我長大成人,從來不知道舒伯特還作過任何其他的交響曲。後來旅美留學,在波士頓聽到他的第九—所謂「大」(The Great)──交響樂,初聽毫無興趣,覺得完全不像舒伯特的作品,甚至大而無當,不斷重複的「重」旋律把我壓得喘不過氣來(記得當時初聽的指揮家是卡爾.伯姆〔Karl Bohn〕,典型的德國派),全曲長幾近一小時,我聽來甚不耐煩。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重返芝加哥任教,有一年夏天,偶然又聽到這首曲子,是在芝加哥交響樂團(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暑期的常駐地拉文尼亞公園。仲夏夜有不少樂迷在此流連忘返,記得我陪着幾個朋友來湊熱鬧,節目單上列出的客座指揮也名不見經傳,最後的壓軸戲就是舒伯特的第九交響曲。我十分勉強地耐着性子聽下去,不料幾分鐘後突覺雲散月出,音樂又回到我腦海中舒伯特的「音像」,淡淡的哀愁,後面似是時隱時現的陰影,好像表現出他為生命所作的最後衝刺。妙的是芝加哥交響樂團的一貫沉重音色(有人說是德奧式的傳統)竟然也輕了許多,而促之產生這種不尋常變化的是一位俄羅斯年輕指揮──瓦列里.格吉耶夫(Valery Gergiev)。十多年後,此公一手擎天,把聖彼得堡的馬林斯基劇院(舊稱基洛夫歌劇院)訓練成世界第一流的音樂團體,以演奏俄羅斯歌劇和交響樂而舉世聞名。然而在我的心目中,他永遠是一位舒伯特的詮釋者,可惜據我所知他從未灌過此曲的唱片。詮釋風格與之接近的是阿巴多指揮歐洲室內樂團(Chamber Orchestra of Europe)演奏的版本(DG公司一九八八年版)。
人過中年以後,我對舒伯特的興趣也逐漸從他的歌曲和交響樂轉向室內樂。舒伯特生前最喜歡和幾位好友一起「玩音樂」,這一類型的室內音樂遊戲,就叫做「舒伯特沙龍」。我無緣躬逢其盛,只能偶爾在夜深人靜時,從唱片中幻想他在這「音樂沙龍」中的風姿。他的鋼琴三重奏和弦樂四重奏中,時有喜氣洋洋的樂章,但我最喜歡的還是他拿手的弦樂五重奏──弦樂四重奏外加一把大提琴,但毫無沉重的感覺,第二樂章迴腸蕩氣,聽來更令人肝腸寸斷。我往往故意把這首曲子當作他的另一首四重奏《死與少女》(Der Tod und das Madchen)來聽,如果後者描寫的是少女多於死亡,那麼前者則可視為舒伯特為死亡寫的前奏曲。我聽了無數張此曲的唱片,但最喜歡的還是最先購得的維也納愛樂四重奏樂團(加上一位大提琴手)演出的版本(Decca出品),奏得不熅不火,因此也更加動人。據說,名鋼琴家魯賓斯坦(Arthur Rubinstein)就指定此曲作為他葬禮的音樂。
二○○二年三月母親過世,我和家妹、妹夫把她的骨灰葬在台北近郊的金寶山墓園,和父親在一起,小山下面就可以看到鄧麗君的墓。安葬完畢後回到香港,似乎覺得悵然若失,我從來沒有問過母親是否喜歡舒伯特,也沒有聽過她彈奏任何舒伯特的鋼琴曲(或教她的學生彈),也許他的鋼琴奏鳴曲太難了,不如讓她聽一兩首舒伯特的《即興曲》(Impromptus)。此曲共有兩組,各四首,我擁有兩個版本,一個是默里.佩拉西亞(Murray Perahia)演奏的,頗為華麗瀟灑;另一個是在香港買的,演奏者是原籍羅馬尼亞的拉杜.魯普(Rudu Ludu),表情似更深刻,還帶有一點淡淡的哀愁。謹以此曲獻給母親以慰其在天之靈,也許她可以和父親共同聆聽。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弦外之音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312 |
文學 |
$ 348 |
Literature & Fiction |
$ 396 |
中文書 |
$ 396 |
音樂 |
$ 396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弦外之音
不但我的前半生和音樂結了緣,後半生更是愈來愈癡迷,幾乎每天沒有音樂就活不下去。也許,到了這個動亂不堪的二十一世紀,我們每一個人都在尋求精神的滋養,音樂對我的意義就更大了。因此,我發現自己的音樂文章背後都含有一種精神上的需求,換言之,我把聆聽音樂的經驗視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我的生活價值又和我心目中的人文精神和廣義的文化傳統密不可分。
——李歐梵
本書以古典音樂為主題,收錄三十八篇散文,分為六輯。作者從個人和家庭與音樂的緣分談起,詳細介紹他尊敬的偉大音樂家、喜愛的交響樂團,記述與妻子在歐洲各大城市作「朝聖」之旅,又暢談音樂與文學和文化的關係。作者深信音樂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在分享數十年來聆聽古典音樂的經驗時,用的是淺白的文字、說故事的語氣,大大拉近了古典音樂與讀者的距離。讀者可藉由本書進入作曲家、演奏家和指揮家的世界,細味古典音樂的魅力。
作者簡介:
李歐梵,著名作家、學者、樂評人。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此後獲美國哈佛大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榮譽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曾先後任教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印第安納大學、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大學。著作包括《狐狸洞話語》、《上海摩登》、《世紀末囈語》、《都市漫遊者——文化觀察》、《尋回香港文化》、《清水灣畔的臆語》、《我的哈佛歲月》、《西潮的彼岸》、《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西文學的徊想》、《蒼涼與世故——張愛玲的啟示》、《又一城狂想曲》、《鐵屋中的吶喊》、《音樂札記》、《人文六講》、《中國文化傳統的六個面向》等。
TOP
章節試閱
聽舒伯特長大
最早對舒伯特的認識和印象是父親書房牆上所掛的一幅他的肖像。父親也是一位作曲家,他最崇拜的西方作曲家就是舒伯特,甚至把自己的形象和舒伯特相比,彷彿還揣摩出幾分相像之處。當然,父親在鋼琴前埋首作曲的時候,更認同舒伯特了,甚至口中唸唸有「調」,把舒伯特的某段曲子先彈出來,然後大讚其作曲法之玄妙:怎麼用這一個奇妙的和弦作結,真是意料不到!有時他甚至會走出書房,向我的母親—另一位音樂家—大談舒伯特的妙處,但母親往往微笑不語,不置可否。父親最激賞的是舒伯特的藝術歌曲,真是佳品無數,曲曲動人,譬...
最早對舒伯特的認識和印象是父親書房牆上所掛的一幅他的肖像。父親也是一位作曲家,他最崇拜的西方作曲家就是舒伯特,甚至把自己的形象和舒伯特相比,彷彿還揣摩出幾分相像之處。當然,父親在鋼琴前埋首作曲的時候,更認同舒伯特了,甚至口中唸唸有「調」,把舒伯特的某段曲子先彈出來,然後大讚其作曲法之玄妙:怎麼用這一個奇妙的和弦作結,真是意料不到!有時他甚至會走出書房,向我的母親—另一位音樂家—大談舒伯特的妙處,但母親往往微笑不語,不置可否。父親最激賞的是舒伯特的藝術歌曲,真是佳品無數,曲曲動人,譬...
»看全部
TOP
目錄
主編的話
自序
第一輯 我的音樂緣分
我自幼喜愛古典音樂
我的交響情人夢
指揮〈獅子山下〉的滋味
聽舒伯特長大
「愛之喜」.「愛之悲」——悼念父親李永剛先生
第二輯 我心中的音樂巨人
「人文巴赫」:一場座談會後的補記
邵頌雄《樂樂之樂》書序
漫談「二流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勞斯
聆聽布魯克納
貝多芬的「晚期風格」
鋼琴詩人的詩意——紀念蕭邦二百周年誕辰
「音樂眼」:蕭斯塔科維奇的「晚期風格」
漫談華格納的歌劇:愛情與救贖
無言的指環
第三輯 指揮家與交響樂團
孤獨的托斯卡尼尼
托斯卡尼尼嚴酷...
自序
第一輯 我的音樂緣分
我自幼喜愛古典音樂
我的交響情人夢
指揮〈獅子山下〉的滋味
聽舒伯特長大
「愛之喜」.「愛之悲」——悼念父親李永剛先生
第二輯 我心中的音樂巨人
「人文巴赫」:一場座談會後的補記
邵頌雄《樂樂之樂》書序
漫談「二流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勞斯
聆聽布魯克納
貝多芬的「晚期風格」
鋼琴詩人的詩意——紀念蕭邦二百周年誕辰
「音樂眼」:蕭斯塔科維奇的「晚期風格」
漫談華格納的歌劇:愛情與救贖
無言的指環
第三輯 指揮家與交響樂團
孤獨的托斯卡尼尼
托斯卡尼尼嚴酷...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李歐梵
- 出版社: 香港中華書局 出版日期:2017-05-26 ISBN/ISSN:978988839447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84頁
- 類別: 中文書> 藝術> 音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