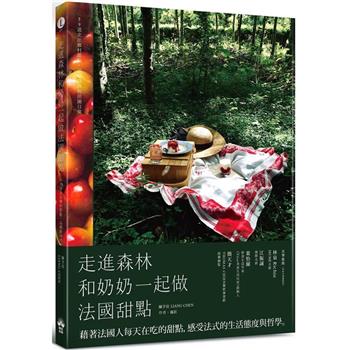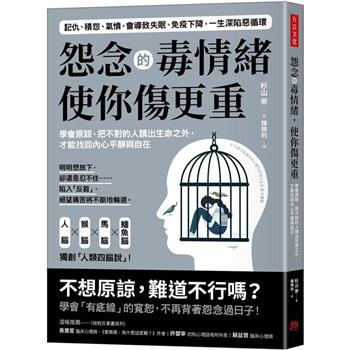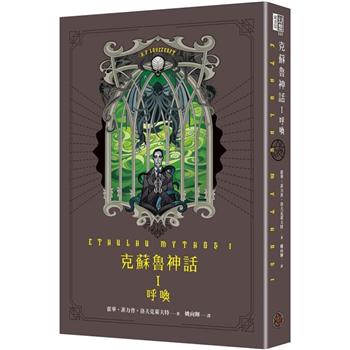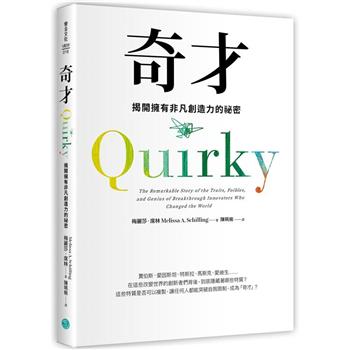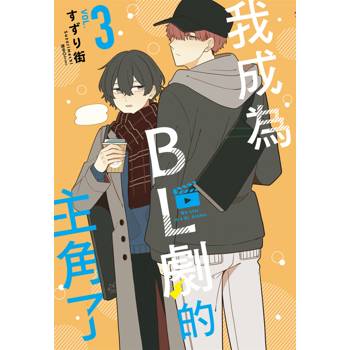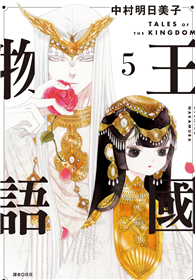一、公眾決策參與機制──一個分析框架
在某些「民主」的鼓吹者中,流行着一種選舉崇拜。判斷一種政治制度民主與否,他們手中只有一把尺子,即選舉:有競爭性選舉的制度便是民主制度,否則就不是。在選舉崇拜者看來,公眾參與政治生活的最佳形式是利用手中的選票,選舉出代議士;其後,就將管理國家大事的責任託付給代議士們。如果還需要什麼制度性補充的話,無非是允許或鼓勵各種利益集團參與政治市場上的競爭,僅此而已。這就是多元代議政治的模式,在這個模式裏,政治參與充其量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
兩百多年前,當代議制民主還沒有形成氣候時,盧梭似乎已經預見到間接參與的潛在危險。他在《社會契約論》中有一段名言:「一旦公眾服務不再是公民的主要關心對象,一旦他們希望用自己的錢包來提供服務而不是親身介入,此時國家就已幾近瓦解了。如果戰爭需要兵士,他們會出錢僱傭而非親自出征;如果舉辦公民集會,他們會派遣代表而自己待在家中。懶惰和花錢的結果是,軍人將奴化國家,代理人將出賣國家。」盧梭還嘲笑英國人,「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期間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後,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於零了」。80多年前,代議制傳入中國不久,孫中山也提醒人民警惕這種政體的「流弊」,即代議士「其始藉人民選舉以獲取其資格,其繼則悍然違背人民之意志以行事,而人民亦莫之如何」。為此,他特別強調「直接民權」。
長期以來,西式民主滿足於幾年一次的選舉。與此相應,西方主流政治學家對政治參與的研究往往聚焦在民眾的投票行為上。然而,過去二三十年裏,西方代議制民主普遍遭遇了先哲們早已預言的危機,其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1)民眾對選舉失去興趣,致使投票率一路下滑;(2)政黨制度日漸衰落,願意集合在政黨旗幟下的人越來越少[6];(3)人們對議會、內閣、總統、文官等「民選」與「非民選」機構的信任持續走低。有人把這些現象統稱為「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在這種背景下,西方國家近年來也有人開始進行一些「民主試驗」,以期重振旗鼓。儘管仍然有人堅持代議式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是最佳的制度選擇,但越來越多的人逐步認識到公眾直接參與決策過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開始推廣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和協商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
既然公民不直接參與政府決策過程就沒有真正的民主可言,我們就必須研究中國公民參與決策過程的趨勢與特點。過去曾有研究表明,中國公眾的政治參與主要發生在政策執行階段。這個判斷的影響之大,以至於一些最近的研究依然把注意力放在政策執行階段,彷彿在政策過程的其他階段(議程設置和政策制定)一切依然如故。但中國是一個急劇轉型的社會,不但經濟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政治生活也日新月異。只有摘除有色眼鏡,才能體會到中國政策過程中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研究表明,中國公共政策議程設置的模式已悄然移易,借助傳媒和互聯網,利益相關群體和民間大眾發揮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事實上,在政策制定層面,過去十年(尤其是過去五年裏)我們也目睹了中央和地方政府進行的大量「民主試驗」,這些試驗在不同程度上拓展了公眾直接參與決策過程的途徑和範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中國,公眾參與不再是西方舶來的概念或理論假說,而是一步步正在展開的真實故事。
為了便於梳理各種「民主試驗」,探討在政策制定階段,中國公眾能以什麼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參與其中,本章第一節試圖從理論上區分公眾參與政策制定過程的四種主要方式,並簡要介紹它們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實踐狀況,為後續討論提供一個清晰的理論框架和橫向參照系。第二節簡略分析毛澤東時代公眾參與的獨有特徵,為理解改革開放以來發生的變化提供一個縱向(歷史)參照系。
公眾參與機制
公眾參與是指可能受政府決策影響的人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對這個簡單的定義,需要作以下說明:
第一,這裏「公眾」並不一定是指全體公民,而是指那些可能受政府決策影響的人,或簡稱為「利益相關群體」。政策不同,受其影響的人群也不同。有些政策也許只會影響很小一部分人,有些政策則可能影響到所有人。因此,「公眾」的含義隨政策性質而變化。
第二,利益相關群體未必是利益相同的人。恰恰相反,利益相關群體很可能是由利益相互衝突的人群組成,如與環保政策相關的污染方與反污染方,與勞工政策相關的勞方與資方。
第三,這裏「政府」不一定是指中央政府或最高決策者,也包括中央政府的各個部門、地方各級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各個部門。一般而言,政府的層級越低,利益相關群體的規模越小;層級越高,利益相關群體的規模越大。
第四,在大多數情況下,「公眾參與」並不意味着「公眾」直接做出決策。政策制定可以細分為政策規劃、方案草擬、方案比較、政策確定四個階段。公眾參與主要是在前三階段對政府的決策施加影響,而不改變政府作為政策最後拍板者的責任。當然,在例外情況下,公眾也可以在第四階段直接決定政策,如瑞士進行的那些具有約束力的公民投票。
第五,公眾影響政府決策的渠道很多,可以歸為兩大類:一類是政府通過法規設置的體制內參與渠道;一類是體制外渠道,如請願、抗議、罷工、示威、騷亂等。前者越完善,後者被利用的可能性越小。但歷史地看,後者往往是推動前者發展的原因。儘管如此,本章關注的重點是體制內的公眾參與渠道,或簡稱為公眾參與機制。
從以上定義可以看得很清楚:公眾參與是公眾與政府間的互動過程。公眾「輸入」,政府「產出」。政府產出的是政策,那麼,公眾可以輸入什麼呢?概括地說,在政策形成過程中,公眾有三類資源可以輸入。第一類是「民意」,即民眾的政策偏好;第二類是「民智」,即民眾針對政策方案提供的建言;第三類是「民決」,即民眾對政策備選方案的取捨。不過,公眾的輸入不能無的放矢。為了參與政策制定過程,公眾必須從政府獲取相關信息。政府的信息公開是公眾參與的前提。如果一個政府以保密為由,不對公眾發放其運作信息,公眾參與將無從下手。
由此看來,公眾與政府的互動有四個關鍵環節,即「信息公開」、「聽取民意」、「吸取民智」以及「實行民決」。在政策制定的不同階段,這四個環節發揮着不同的作用。信息公開在所有四個階段都至關重要;聽取民意的作用主要體現在政策規劃階段,偶爾也會影響方案比較階段;吸取民智在方案草擬與方案比較階段尤為凸顯,實行民決則只有在政策的提出和拍板階段才能顯露身手。
為了分析的便利,以下我們依次分別討論這四個環節及其在西方國家的實踐,目的是為以下分析中國樹立一個橫向參照系。需要指出的是,現實世界往往比抽象的分析框架更為複雜,這四個環節的界限並不總是那麼清晰,幾個環節混雜在一起是常見的事。
信息公開
信息公開是指政府就其事務向民眾公佈有關信息。從嚴格意義上講,信息公開本身並不屬於公眾參與的範疇,因為在這裏,信息只是從政府到公眾的單向流動。儘管如此,信息公開的意義不可低估,它是公民知情權的體現,是政府對人民負責的基礎,是公眾與政府雙向互動的前提。因此,討論公眾參與不能不首先討論信息公開。
信息公開的主體是行使公共權威的機構與個人,包括各級政府部門、國有企業、其他公立機構(如學校和醫院)及其負責人。信息公開的內容包括公民基本權利、法律政策、法律草案、政策規劃、政府組織架構、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相關行政和執法程序等。信息公開的形式有兩大類:一是被動提供,一是主動提供。前者是指只有當公民提出要求後,政府才向申請者提供所需信息,如公民要求查看某些政府檔案等文獻。在這種情況下,信息公開法規一般會明確回覆時間以及收費標準(有些國家完全免費,如奧地利和芬蘭;多數國家以信息性質決定是否收費)。後者是指政府主動向社會大眾公佈的信息,如統計數據、預決算、公報、年度報告、政策推介材料、公民教育讀本,以及其他有關政府運作的信息。這類信息對增強政府的透明度、促進公眾參與的意義重大。關於信息公開的範圍,各國做法差異較大。不過,所有國家都承認政府信息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公開。多數國家在信息公開法規中,將涉及國家安全、個人隱私、公司機密的信息作為排除條款;還有不少國家把限制範圍擴展至政府內部工作的記錄文件。信息公開的途徑可謂五花八門,例如利用大眾傳媒、發佈廣告、設立信息中心、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提供電話問詢服務、給公民直接發送郵件、舉辦信息發佈活動等。現代信息技術的普及(包括互聯網、手機)在拓寬信息公開途徑的同時,也降低了傳遞信息的成本,增加了信息的可及性。
儘管早在1766年,瑞典便通過了世界上第一部有關政府信息公開的法律,但實際上,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將信息公開寫入法律也是相當晚近的事情。直到1980年,只有大約20%的西方發達國家以立法的形式保證信息公開;到1990年,這個比例也才升至40%。20世紀最後十年,情況激變,到2000年,已有80%的發達國家採納了有關信息公開的法律。換句話說,由於制度化的時間並不長,即使是西方發達國家,實施信息公開的經驗也十分有限。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中國治道的圖書 |
 |
中國治道 作者:王紹光 出版社: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7-22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87 |
政治 |
$ 441 |
中文書 |
$ 441 |
社會人文 |
$ 441 |
政治 |
$ 466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中國治道
對比中式政道思維與西式政體思維
梳理傳統與現實融合中的當代政治理想及實踐
本書挖掘古今中西的政治思想資源,對中式政道思維與西式政體思維的異同作了深刻分析。作者以中式政道思維,基於中國政治發展實踐,從國際比較的視野,辨析了當代中國政治發展中一些最前沿的理論問題,梳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多年在政治、社會、經濟方面的艱辛探索及其成就。
作者簡介:
王紹光,1954年生於武漢,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講座教授、系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江講座教授,重慶大學人文科學高等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青島大學碩士研究生導師。1982年獲北京大學法學學士學位,1984、1990年分獲美國康奈爾大學政治學碩士、博士學位,1990—2000年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系。中英文專著、合著約有三十本,如《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即推動中國分稅改革的「王胡報告」)、《分權的底限》、《政治學的本土化》、Nationalism,Democracy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China、《安邦之道:國家轉型的目標與途徑》、《民主四講》、《祛魅與超越:反思民主、自由、平等、公民社會》、《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等,在中英文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上百篇,學術雜誌The China Review主編。
TOP
章節試閱
一、公眾決策參與機制──一個分析框架
在某些「民主」的鼓吹者中,流行着一種選舉崇拜。判斷一種政治制度民主與否,他們手中只有一把尺子,即選舉:有競爭性選舉的制度便是民主制度,否則就不是。在選舉崇拜者看來,公眾參與政治生活的最佳形式是利用手中的選票,選舉出代議士;其後,就將管理國家大事的責任託付給代議士們。如果還需要什麼制度性補充的話,無非是允許或鼓勵各種利益集團參與政治市場上的競爭,僅此而已。這就是多元代議政治的模式,在這個模式裏,政治參與充其量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
兩百多年前,當代議制民...
在某些「民主」的鼓吹者中,流行着一種選舉崇拜。判斷一種政治制度民主與否,他們手中只有一把尺子,即選舉:有競爭性選舉的制度便是民主制度,否則就不是。在選舉崇拜者看來,公眾參與政治生活的最佳形式是利用手中的選票,選舉出代議士;其後,就將管理國家大事的責任託付給代議士們。如果還需要什麼制度性補充的話,無非是允許或鼓勵各種利益集團參與政治市場上的競爭,僅此而已。這就是多元代議政治的模式,在這個模式裏,政治參與充其量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
兩百多年前,當代議制民...
»看全部
TOP
目錄
一、公眾決策參與機制──一個分析框架
公眾參與機制
信息公開
聽取民意
吸取民智
實行民決
公眾參與的位階
毛澤東的逆向參與模式:群眾路線
二、挑選決策者階段的新趨向
城鄉基層選舉
人大代表選舉
行政首長的選舉
三、中國公共政策議程設置的模式
關門模式
動員模式
內參模式
借力模式
上書模式
外壓模式
小結
四、改革時期的公安分權與集權──中國國家強制能力建設的軌跡與邏輯
調動地方資源──公安行政分權的意義
...
公眾參與機制
信息公開
聽取民意
吸取民智
實行民決
公眾參與的位階
毛澤東的逆向參與模式:群眾路線
二、挑選決策者階段的新趨向
城鄉基層選舉
人大代表選舉
行政首長的選舉
三、中國公共政策議程設置的模式
關門模式
動員模式
內參模式
借力模式
上書模式
外壓模式
小結
四、改革時期的公安分權與集權──中國國家強制能力建設的軌跡與邏輯
調動地方資源──公安行政分權的意義
...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王紹光
- 出版社: 香港中華書局 出版日期:2016-07-22 ISBN/ISSN:978988839481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50頁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