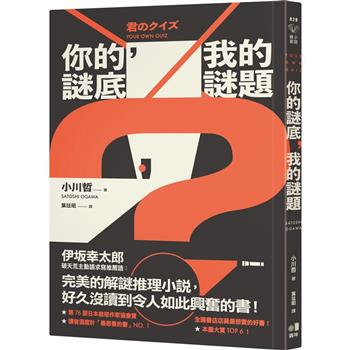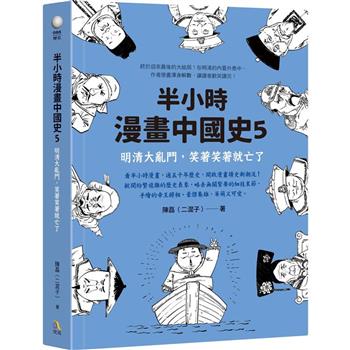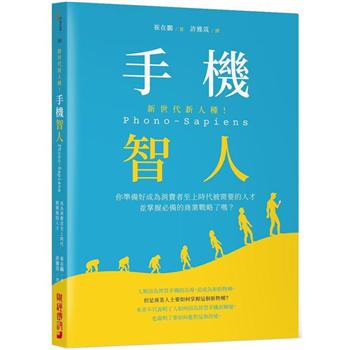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性別與話語權:女性主義小說的翻譯的圖書 |
 |
性別與話語權:女性主義小說的翻譯 出版社:中華 出版日期:2016-09-16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00頁 / 17 x 23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13 |
社會人文 |
$ 419 |
文學 |
$ 477 |
中文書 |
$ 477 |
性別研究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翻譯與話語權:論女性主義小說的翻譯》是一本跨文化跨學科的著作。作者從性別視角討論女性主義作品的翻譯,並結合哲學、文學、性別研究、翻譯研究、文化研究等學科的相關論述,分析性別因素對翻譯的影響,也探討女性主義作品在中英對譯中的話語權問題和性別問題。本書將性別研究與翻譯研究結合起來,可說是這兩個領域的一次聯姻。
作者簡介:
故宮博物院
SHAN JIXIANG, was born in Beijing in 1954. He received his doctorate degree in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from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studied in Japan from 1980 to 1984. After his return to China, Dr. Shan held several posts such as deputy director of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ity Planning, director of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director of Beijing Municipal Commission of Urban Planning, and director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ince January of 2002, Dr. Shan has taken up positions of director of the Palace Museum, researcher of the Palace Museum, director of China Cultural Relics Academy, and vice chairman of China Building Decoration Association.
WANG LIANQI, was born in Jiaxiang county of Shandong province. He finished his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in 1966 due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n, he studied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n his own and became the student of Mr. Li Qingyun and Mr. Xu Daxian. Since 1979, he has been working in the Palace Museum. He received Mr. Qigong’s guidance with regard to ancient paintings, calligraphy and the evaluation of rubbings. Now he is the research fellow of the Palace Museum, a member of the academic committee,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Cultural Relics. With decades of experience in th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work of ancient Chinese paintings, Mr. Wang is a contemporary expert in the evaluation of ancient calligraphy, paintings and rubbings.
- 作者: 劉劍雯
- 出版社: 香港中華書局 出版日期:2016-09-16 ISBN/ISSN:978988839488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00頁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性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