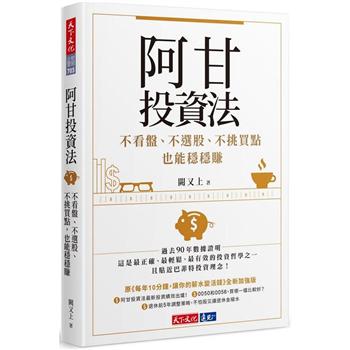第一章 古文的歷史發展
所謂古文
“古文”兩個字可以有幾種不同的意義。我們現在所說的古文,則是指與現代語體文相對的一切文言文。事實上,在五四以前,幾乎一切正式行用的文章都是用文言寫的,從上古一直到五四前的一個時期,在漫長的年代中,儘管文體經過很大的變化,在今天看來,都算是有別於現代漢語的文體。所以都可加上“古文”的名稱。
當然,用文言寫的不一定都是好文章。但是在舊時代裡,著名作家們所寫的,有不少精湛卓越、不可磨滅的作品,非但可供我們今天的師法、借鑒,而且事實上我們一直受到這些作品的影響,其中有些詞彙、成語、語法以及修辭技巧,都還在日常應用的語文中活生生地繼續使用著,並沒有完全遠離我們,所以值得欣賞、學習,汲取其優點。
作為一個文體來說,古文的名稱起於唐宋。因為當時流行的文體,大部分是追求華靡形式的,語法也不很嚴格。通過幾個先進作家的創導,直接採取了漢以前比較樸素的風格,加以變化,使其條理暢達,簡潔有力,這種文體,名為“古文”。雖然名為古文,實際卻含有革新的意義。由宋到明清,這種古文的影響逐步加深加廣,為文學界所普遍接受,雖然仍舊名為古文,實際已經是比較符合時代要求的文體了。不過當時也還有兩種文體不屬於這個範疇。一是駢體,在美文方面仍然通用,一是制藝,在科舉考試中是必須使用的。所以在那時代,古文別於那兩種而言。
這種從唐宋以後興起的所謂古文,是我們所要學習的主要部分,因而必須有清晰的認識。
上古的文章
不言而喻,上古的文字是非常簡略的。我們所能看到的不過是些記事的文字,只用些實體詞記載事實的概略,動詞形容詞都用得極少,其他介詞連詞都不如後來的多,所以讀起來覺得枯燥質樸,沒有情調。在古器物的銘文上看見的都是這種。從現在的習慣說來,還不能算是文章。然而也已經有了一些特定的表示語氣。例如記事文在開始的時候總是用“惟”字引起下文。又如由此事以至彼事則用“乃”字(古字寫作迺)以表因果關係。又如在頌祝的時候用“其”字表示希望。這些就是文言語法中的助字(虛字)所由來。逐步發展下去,這類的用語多了,於文氣的抑揚轉折,理路的層次脈絡,就大有幫助,因而成為文言文的主要特徵。
上古的用字幾乎全不是我們所習慣的。非但我們今天不習慣,司馬遷在西漢時代已經覺得《書經》的文字難於理解,所以不得不用當時通用的字來代替《書經》上的字,試舉一節《書經》和司馬遷《史記》的譯文對照起來看。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囂訟可乎?”(《書經.堯典》)
信飭百官,眾功皆興。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史記.五帝本紀》)
從這裡可以看出司馬遷用的字確實距離我們近了一些。然而這不等於說《史記》的文章好過《書經》的文章。相反,《書經》有《書經》的優美風格,司馬遷的翻譯也不免破壞了原有的優點,變得直率無味了。假使司馬遷按照他的自由意志來改寫,必然會好得多。所以知道文章風格是各自獨立的,並不因為時代遠了就貶低價值。
至於用字,誠然各時代的習慣不同,然而也正因為一個意思可以用不同的字表達,才使我們的詞彙日益豐富。例如《書經》上的“庶”字和“咸”字,在今天看來,果然不如“眾”字和“皆”字的熟悉,但是“庶”字和“咸”字也並沒有完全僵死,一直還可以替換著使用。所以,由於悠久歷史的積累,新的不斷產生,舊的也存儲備用,文言就提供了充裕的詞彙資源,足以應付多方面的需要。像《書經》這樣簡括肅穆的文風,仍然是唐宋以後古文所追求效法的對象之一,特別在碑銘一類的文章中,更為適宜。
《詩經》
在助字使用方面,與《書經》表現相反趨向的,就是《詩經》。在《詩經》裡,可以發見大量而且經常使用的助字。這些助字往往也是後人所不熟悉的。然而不難看出:憑藉這些助字,語氣就非常活潑生動,情調也非常宛轉纏綿。因而大不同於《書經》和上古器物上的銘文了。舉下列的句子為例:
于以採蘋,南澗之濱,于以採藻,于彼行潦。(《詩經.召南》)
已矣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詩經.邶風》)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詩經.鄘風》)
第一例的語氣多麼從容美妙;第二例又多麼沉痛;第三例又多麼憤激!為甚麼能有這樣細膩的表情,使我們讀起來恰和聽見作者親口念出來一樣呢?完全是由於助字的大量使用。這些助字多半屬於“聲態詞”的性質,在當時本來就是按口語寫出的,口中發出怎樣的聲音,筆底下就寫出怎樣的字,這樣自然活潑而宛轉了。到了後來,口語的語法上起了些變化,習慣就愈離愈遠,有些助字的用法就完全不同了,譬如在第一例中,句子開始用“于”字,這在現代國語中簡直沒有相當的字可以代替,因而很難體會其語氣。至於第二第三例中的“矣”、“哉”、“也”等字,用法還和現代國語中的某些字相當,所以我們讀起來還親切有味。
唐宋以後古文的特點就是適當運用這些助字,把它們容納在語法規範之中。其結果就能使文言與口語保持著不太遠的距離。
《論語》
文言文中的助字,到了孔子時代記錄下來的議論和記事文章,才充分發揮了作用,現從傳誦最廣的《論語》,舉下列一段為例: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歟)?”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避)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慨然曰:“鳥獸不可以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吾不與易也。”(《微子》)
這段的原意大略如下:長沮、桀溺兩人合夥耕田,孔子走過這裡,派子路向他們探聽一下過河的渡口。長沮說:那位趕著車的是誰啊?子路說:是孔丘。長沮說:是魯國的孔丘嗎?子路說:是。長沮說:那他一定知道渡口在甚麼地方了。子路又去問桀溺,桀溺說:你是甚麼人?子路說:我名叫仲由。桀溺說:是魯國的孔丘的門徒嗎?子路說:是的。桀溺說:天下滔滔都是一樣的,換來換去還不是這樣?並且與其跟那避人之人在一起,何不跟避世的人在一起呢?說罷還是不停地鋤地。子路把這話走去回報孔子,夫子甚為感動說:鳥獸是沒有法子合夥的,不同這班人一起,又同誰一起呢?即使天下太平了,還是要讓他們獨行其是的。
試看這段敘事,層次分明,交代清楚,固不必說。在問津之下用一個“焉”字,在執輿之上用一個“夫”字,這都本不是必須用的字,但用了以後,就使人感覺前者顯出停頓的語氣,而後者顯出提起的語氣,在行文之中發揮著修飾的作用。孔子答話的時候,用慨然二字形容被感動的神情,這又是文言中的特點,善於使用簡練的語言表達複雜的情感。
再看一段孔子的議論文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季氏》)
這樣文義顯露,娓娓動聽的文章,只在《論語》中初次遇見,在以前是不會有的。《論語》的文章所以不同於以前的文章,主要是廣泛使用的句首的助字,如“今”、“夫”、“今夫”,以及句尾的助字,如“與”、“矣”、“也”。一篇之中,反覆數次地出現。這樣一來,表達講道理、論是非的語氣就更為有說服力了。比前面所舉的一例,又進了一步了。
孔子在聽到將伐顓臾的消息時,就說:“求啊!這件事只怕做得不對吧!講到顓臾,當初的天子原是叫他坐鎮蒙山地區的,而且已經畫在我國領土之內的了。它就是忠於我們國家的臣子啊!為甚麼要去伐他呢?”冉有自己辯解說:“他老先生要這樣辦,其實我們兩個在他手下本不贊成的。”於是孔子說:“求啊!上古周任有句話說:‘各人按照各人的能力走上自己的崗位,如果沒有能力就應當退下來。’假使看到危險不能去支持,倒下地來不能去扶起,那又何必要甚麼輔佐的人呢。而且你這話也說錯了,如果養的野獸跑出籠子來,貴重的寶物在匣子裡受到損壞,試問是誰的過失呢?”冉有又說,“論起顓臾這個地方,是個險要所在,而又離費邑太近,不把它拿過來,必然會替後世子孫留下禍害的。”孔子說:“求啊!君子所恨的,就是不說自己想這樣罷了,偏要找出理由來強辯。按照我的意見,無論當國當家,所怕的並不是缺乏而是不均勻,並不是貧窮而是不安定。因為均勻就無所謂貧窮,和諧就不至於缺乏,安定就不至於危險。既然是這樣,那末,遠方的人有不服的,可以採用和平的方法,引導他們來,來了就要使他們安定。現在呢,由與求,你們兩人輔佐他老先生,遠方的人不服,並不能夠把他們引導來,國內分裂破散,也不能夠保持完整。倒要打算在自己國內使用武力,我恐怕季孫擔憂的不是顓臾的事,而是自己家門內的事啊!”
兩下對照,就知道句首的助字幫助“起、承、轉、合”而句尾的助字幫助語氣的抑揚頓挫,這就是文言的特徵。在《論語》中表現得最為顯著,也最為明確。
《孟子》
到了孟子的時代,繼承了《論語》的文法,又進一步增加了一些推論的詞句,由簡而趨向於繁。剛好有一段也是討論冉求的議論文章,可以聯繫起來看: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闢)草菜任土地者次之。(《離婁》)
按照孟子的口氣,就是:冉求這人作季氏的家臣,一點也沒有改善季氏的行為,只是把賦稅增加得超出以前一倍。孔子說過:“冉求不是我們的同道,你們這些後生小子簡直不妨大張旗鼓攻擊他。”照這樣看來,為君的不行仁政,倒替他想法子弄錢,這種人都是孔子所要唾棄的。何況還要替他進行橫蠻的戰爭呢?為了爭奪一塊地方而戰爭,就會殺死遍地的人,為了爭奪一處城池而戰爭,就會殺死滿城的人。就是這樣為了追求領土而吃人肉,雖死也抵不了所犯的這種大罪。所以會打仗的,應該處以最嚴厲的刑罰,聯合各國結盟的,次一等,開闢土地(為了備戰)的,又次一等。
孟子這篇文章用了“由此觀之”、“況於”、“此所謂”等等推論語氣的短語或字句,表達了更加複雜細緻的意思,因而增加了文章的矯健。
孟子又特別善於變換使用句尾的助字來增加文章的生動活潑,例如: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萬章》)
按照現代語的口氣就是:萬章問:“有人說:百里奚以五張羊皮的代價把自己賣給秦國養牲口的人作奴隸,為的是藉著餵牛向秦穆公謀求錄用,真有這事嗎?”孟子說:“沒有,不對。這是喜歡造謠的人造出來的。百里奚原是虞國人。晉國拿出寶玉和名馬向虞國請求通過虞國的國境出攻虢國。宮之奇勸阻虞君不要答應晉國的請求,百里奚卻不去勸阻。他是知道虞君不聽勸說的,因而離開虞國去到秦國,年紀已經七十歲了。難道連用餵牛來干求秦穆公是件卑污的事都不懂得,這能算得明智嗎?明知無法勸就不去勸,這能不說他是明智嗎?知道虞君要亡國,先就離開到秦國去,這不能不說他明智啊!到了適當的時機,在秦國活躍起來,知道秦穆公是個可以合作而能成功的人,就去輔佐他,這能不說他是明智嗎?輔佐他以後果然使他的君主顯名天下,傳於後世,不是個賢人,能夠這樣嗎?若是為了成就他的君主而出賣自己作奴隸,鄉里中但知潔身自好的人都不肯這樣幹,你說一個賢人肯幹嗎?”
凡是遇到反覆深入分析問題的時候,這種文法是非常合適的。
同時還要注意:現代語有必須加字方能清楚的地方,文言是可以簡省些的。然而是文法上的簡省,不是修辭上的簡省。在整個結構上只要發揮透徹,話雖多並不嫌多。這也是孟子文章風格的特點。當時的人就說孟子好辯,果然他是辯論的好手。
孟子本來是戰國時代諸子之一,戰國時代的諸子各有獨特的文風,其中如莊子,尤其對後世的文學,有著深切的影響。但是還遠不如孟子影響之大。因為他是儒家的正統派,直接繼承孔子,很久以來就把他當作經書讀,所以《孟子》和《論語》的文法已經成為一般文言文法的基礎。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文言淺說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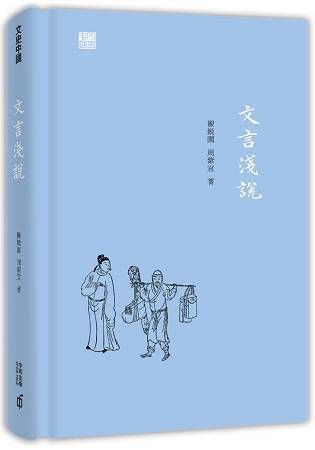 |
文言淺說 作者:瞿蛻園、周紫宜 出版社: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5-17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55 |
二手中文書 |
$ 277 |
中國古典文學 |
$ 277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298 |
閱讀/賞析 |
$ 298 |
小說/文學 |
$ 315 |
中文書 |
$ 315 |
閱讀/賞析 |
$ 315 |
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文言淺說
這本文言知識的入門讀物,是繼《學詩淺說》之後,由名家瞿蛻園與近代才女周紫宜合著的又一本普及讀物,雖篇幅短小,著者卻寥寥數筆,點出文言的奧竅,功底可見一斑。時隔半個世紀,今天讀來,著者的學識、才情和溫雅依然清晰可感。書中所談文言常識,對於希望掌握文言的初學者,既有引導閱讀,理解文言的性質、特點,培養閱讀、欣賞的能力之用,進而還有實際運用文言的助益。
文史學者俞汝捷先生青年時代師事瞿蛻園先生,他曾作一篇長文追憶當年所見所聞,是目前有關介紹瞿蛻園先生生平和學術的文章中,最為全面、詳實的一篇,極具史料價值。本書作為附錄刊出,以饗讀者。
作者簡介:
瞿蛻園(1894-1973)
原名宣穎,字兌之,晚號蛻園,湖南長沙人。現代史學家、文學家、書畫家。他出身望族。早年師從晚清大儒王闓運等,曾在南開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等校執教。抗日戰爭期間,滯留北京。1949年後,寓居上海,以著述為業。曾被聘為中華書局上海編譯所特約編輯。他博學多才,涉獵廣泛,著述宏富。主要著作有《方志考稿》、《歷代官制概述》、《養和室隨筆》、《銖庵文存》、《秦漢史纂》、《中國駢文概論》、《漢魏六朝賦選》、《劉禹錫集箋證》等。
周紫宜(1908-2000)
名鍊霞,字紫宜,別號螺川,江西吉安人。現代著名畫家和詩人。早年先後師從晚清四大詞人之一的朱孝臧和徐悲鴻的岳父蔣梅笙等學習書畫詩詞。她才貌雙全,高雅風致,人稱“金閨國士”,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文壇、藝壇最活躍的才女之一。著名作家董橋稱其為“再世易安”。晚年移居美國。
TOP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古文的歷史發展
所謂古文
“古文”兩個字可以有幾種不同的意義。我們現在所說的古文,則是指與現代語體文相對的一切文言文。事實上,在五四以前,幾乎一切正式行用的文章都是用文言寫的,從上古一直到五四前的一個時期,在漫長的年代中,儘管文體經過很大的變化,在今天看來,都算是有別於現代漢語的文體。所以都可加上“古文”的名稱。
當然,用文言寫的不一定都是好文章。但是在舊時代裡,著名作家們所寫的,有不少精湛卓越、不可磨滅的作品,非但可供我們今天的師法、借鑒,而且事實上我們一直受到這些作品的影響,其中有些...
所謂古文
“古文”兩個字可以有幾種不同的意義。我們現在所說的古文,則是指與現代語體文相對的一切文言文。事實上,在五四以前,幾乎一切正式行用的文章都是用文言寫的,從上古一直到五四前的一個時期,在漫長的年代中,儘管文體經過很大的變化,在今天看來,都算是有別於現代漢語的文體。所以都可加上“古文”的名稱。
當然,用文言寫的不一定都是好文章。但是在舊時代裡,著名作家們所寫的,有不少精湛卓越、不可磨滅的作品,非但可供我們今天的師法、借鑒,而且事實上我們一直受到這些作品的影響,其中有些...
»看全部
TOP
推薦序
寫在前面
《文言淺說》是繼《學詩淺說》之後,瞿蛻園(1894—1973)與周紫宜(1908—2000)合著的又一普及讀物,1965年初版於香港,後在台灣有過盜版,而在內地則是50年來首次問世。
雖是普及讀物,卻因所談係文言常識,既要引導閱讀,更要教會寫作,這就需要作者自身具備熟練駕馭文言的能力。這樣的人才現已寥若晨星,故而對於希望掌握文言的讀者來說,本書的出版可謂正當其時。
我青年時代有幸師從蛻老,也見過被鄭逸梅譽為“金閨國士”的周紫宜。當年他們撰寫本書之際,正是我經常登門請益之時。多年來我在回憶文章和相關書序中已不...
《文言淺說》是繼《學詩淺說》之後,瞿蛻園(1894—1973)與周紫宜(1908—2000)合著的又一普及讀物,1965年初版於香港,後在台灣有過盜版,而在內地則是50年來首次問世。
雖是普及讀物,卻因所談係文言常識,既要引導閱讀,更要教會寫作,這就需要作者自身具備熟練駕馭文言的能力。這樣的人才現已寥若晨星,故而對於希望掌握文言的讀者來說,本書的出版可謂正當其時。
我青年時代有幸師從蛻老,也見過被鄭逸梅譽為“金閨國士”的周紫宜。當年他們撰寫本書之際,正是我經常登門請益之時。多年來我在回憶文章和相關書序中已不...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前言
這部書的意圖是為了幫助初學能夠理解文言的性質、特點、作用,培養閱讀、欣賞的能力,進一步便能在實用上運用文言,而不是局限於一些理論。但總的說來,仍以提供有關的基本知識為主。
因此,全書分五部分,第一是古文的歷史發展,從遠古到近代,顯示一個粗略的輪廓。第二是古文文法的特點,特別就文言與口語的對照,來幫助讀者掌握虛字的用法。第三是通過古文選本的介紹,提供一些關於體裁、風格等等的說明。第四是學習文言的要點。第五是實際運用文言的範例。
第一第二兩部分本來屬於文學史及語法書的範圍,現在只重點地介紹,以...
這部書的意圖是為了幫助初學能夠理解文言的性質、特點、作用,培養閱讀、欣賞的能力,進一步便能在實用上運用文言,而不是局限於一些理論。但總的說來,仍以提供有關的基本知識為主。
因此,全書分五部分,第一是古文的歷史發展,從遠古到近代,顯示一個粗略的輪廓。第二是古文文法的特點,特別就文言與口語的對照,來幫助讀者掌握虛字的用法。第三是通過古文選本的介紹,提供一些關於體裁、風格等等的說明。第四是學習文言的要點。第五是實際運用文言的範例。
第一第二兩部分本來屬於文學史及語法書的範圍,現在只重點地介紹,以...
»看全部
TOP
目錄
一 古文的歷史發展
所謂古文
上古的文章
《詩經》
《論語》
《孟子》
《左傳》和《史記》
兩漢的文章
六朝人的“文”與“筆”
元和古文運動
南宋以後的文體
比較近代的變化
二 古文文法的特點
古文中的字和詞的用法
助字的用法
句首助詞
句尾助詞
三 古文的體裁與風格
《古文辭類纂》——古文選本之一
《古文觀止》——古文選本之二
學習古文的關鍵
文章的基本規律
四 學習文言的要點
五 文言應用範例
語體文言對照的範例
附錄 花朝長憶蛻園師(俞汝捷)
所謂古文
上古的文章
《詩經》
《論語》
《孟子》
《左傳》和《史記》
兩漢的文章
六朝人的“文”與“筆”
元和古文運動
南宋以後的文體
比較近代的變化
二 古文文法的特點
古文中的字和詞的用法
助字的用法
句首助詞
句尾助詞
三 古文的體裁與風格
《古文辭類纂》——古文選本之一
《古文觀止》——古文選本之二
學習古文的關鍵
文章的基本規律
四 學習文言的要點
五 文言應用範例
語體文言對照的範例
附錄 花朝長憶蛻園師(俞汝捷)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瞿蛻園、周紫宜
- 出版社: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5-17 ISBN/ISSN:978988846600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精裝 頁數:216頁 開數:32開
- 商品尺寸:長:188mm \ 寬:128mm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中國古典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