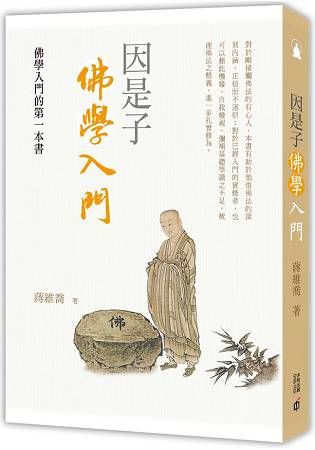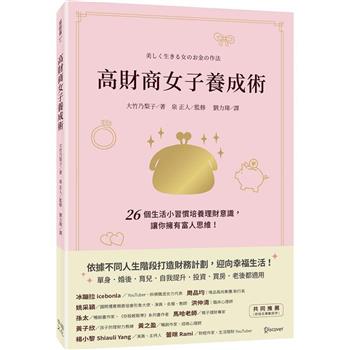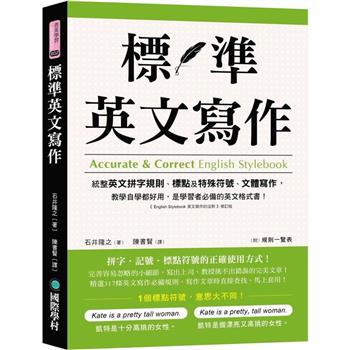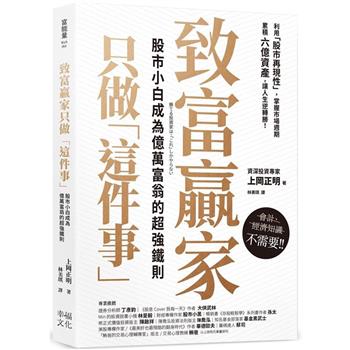第一節 甚麼叫做佛學
佛陀的意義
這個「佛」字是從印度梵文裡翻譯出來的名詞,如果音譯就是「佛陀」(Baddha)兩字。它的意思,就是「覺者」。這「覺者」又含三種意義:一曰自覺;二曰覺他;三曰覺行圓滿。
甚麼叫做自覺?就是說佛自己先能覺悟。
甚麼叫覺他?是說佛不單是自己覺悟,並且化導他人,叫他人也能覺悟。
甚麼叫覺行圓滿?是說佛自己覺悟,又覺悟他人,這兩種德行,已到了圓滿無缺的地步。
這「佛陀」兩字,平常習慣用省略的稱呼就叫做佛。
佛教與佛學
世界無論哪種宗教,各宗各有其依據的哲理,但多少總帶些迷信的色彩,唯有佛教的基礎是完全建築在理智上的。所以佛教包含的哲理,很高很深,非但任何宗教所不能及,就拿東西洋的各種哲學來比較,也沒有哪一種哲學能夠趕得上的。我們略去佛家的宗教形式,單拿它的學理來講,也覺得包羅萬有、趣味宏深。這是稍微涉獵的人都公認的。因此,用這種方式將佛教當做一種學問去研究,就可以叫做佛學。
第二節 研究佛學怎麼樣下手
大藏經與一切經
佛家的經典,全部整個兒的,稱為《大藏經》,又叫做《一切經》。這名詞是甚麼時候起的呢?那是隋朝開皇元年,朝廷命京師以及諸大都邑地方,一律用官家經費,抄寫一切經書,安放在各寺院裡。又另外抄寫一份,藏在皇家的秘閣裡面。這就是「藏經」和「一切經」兩個名稱的來源。照此看來,「藏」字最初是含有貯藏的意味,到後來又加添了包藏豐富的意味。
經律論三藏
《大藏經》的內容,分為三大部分:一曰經藏;二曰律藏;三曰論藏。經藏的梵音叫做「素呾纜」(Sūtrapit4aka),乃是記錄佛的言說。「素呾纜」的本義,是用線去貫串花鬘(花鬘是印度人的裝飾)的意思。佛的言說能夠貫串一切的道理,所以拿「素呾纜」來做此喻。我國古來稱聖人的言說為經,經字的義,訓為常,訓為法,其意是指聖人的言說就是常道,是可以為世間所取法的。並且,織布時,直線為經,橫線為緯,這也有用線去貫串的意思。所以古時翻譯的人,就譯「素呾纜」藏為經藏。律藏的梵音叫做「毗奈耶」(Vinayapit4aka),這乃是佛所定的戒條。「毗奈耶」的本義是滅,是說佛弟子遵守這種戒條,就可以消滅身、口、意三業的過惡的意思(我們有所造作,名為業,一切造作的業,不外身的動作、口的說話、心的主使,這叫作身、口、意三業),這和我國的律令意味相同。所以古時譯「毗奈耶」藏為律藏。論藏梵音,叫做「阿毗達摩」(Abhidharmapit4aka)。「阿毗」譯為對,「達摩」譯為法,就是用對觀真理的智慧,得到的涅槃妙法的意思(「涅槃」是梵音,意為寂滅,佛家超脫生死,到得不生不滅的地位,名曰「涅槃」)。換句話說,論藏所收穫得的,大抵是菩薩(「菩薩」是梵音,意為覺有情,言其既能自己覺悟,又能度脫眾生。眾生有生命情感,故稱有情。菩薩之地位,次佛一等)發揮經義、教誡學徒的議論,學徒得這種教誡,就能觀察其理,發生智慧,照此方法修行,可以超脫生死的苦,到達不生不滅的境界。
研究藏經的下手方法
提到《大藏經》,那就是一部二十四史,真不知從何處說起了。這部龐大的經,卷帙的繁多、義理的高深、文字的古奧,三件的中間,有了一件就能叫學者望洋興歎,況且這三件都是完備的呢!然而我們不要害怕,凡是一種學問,無論怎麼樣艱難,總有下手的方法。這方法就是:先要提綱挈領,曉得它的來源和大概,尋到入門的門路;然後就我們天性所近的,去細加研究。研究時當然要用泛覽和精讀兩種功夫。
但是佛學進中國以後,發達經過幾千年,卻從來沒有人為初學者做過入門的書。數十年中,方才有人注意到此,出了幾本《佛教初學課本》、《佛教問答》等書,著者也曾做過《佛學大要》、《佛教淺測》兩書,然而不是失之太深,就是失之太略。這也難怪,凡百事體,在草創的時期,這種毛病總是免不掉的,如今做這部書,就是要達到詳略得當、文理明白,叫讀者容易了解的地步。
第三節 佛學和學佛要分清楚
佛學與學佛是兩件事
佛學是一件事,學佛又是一件事,二者驟然看來沒有分別,實則大有分別,學者不可不先弄清楚。怎麼叫做佛學?就是深通經典、精研教理,成為博聞強記的學者。這種全在知識方面用功的,可以叫做佛學。怎麼叫做學佛?原來我佛教化眾生的本意,是叫人依照他的方法去修行,得以超出生死苦海,方算成功。所以佛所說的種種經典,那是對眾生的種種毛病開的藥方,並不是叫人熟讀這張藥方裡的藥名,就算了事,而是要拿藥吃下去,除掉病根的,病根果然除掉,這藥方就用不著的了。我們可以依照佛法修行,從精神方面用功,方可叫做學佛。
「說食不飽」的譬喻
佛經上常常提到一句話叫做「說食不飽」(「如人說食,終不能飽」語見《楞嚴經》卷一)。這話是甚麼意思?是說我們飢餓時總要想吃,吃時總要想飽,那是人人相同的。倘然有一種好說空話的人們,對著飢餓的人說得天花亂墜,羅列出許多山珍海味,單有空名,並沒有食物,結果枉教飢餓的人聽是聽得有味,腹中仍不得一飽,這就叫「說食不飽」。就是比喻佛經裡面的道理窮高極深,我們單從知識方面去求廣博的學理,不從精神方面去求實在的受用,那麼和「說食不飽」毫無兩樣。所以我們要研究佛學,還是先學佛最重要。
【問題】
一、研究佛學和日常學問有何不同之處?
二、經、律、論三藏之意義如何?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因是子佛學入門(第二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48 |
宗教命理 |
$ 316 |
佛教經典/解說 |
$ 360 |
中文書 |
$ 360 |
佛教 |
$ 360 |
宗教命理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因是子佛學入門(第二版)
佛學入門的第一本書。
作者蔣維喬先生同時具有學者和修行者雙重身份,因此,能更好地以理性、客觀的角度來談佛學與佛教。
對於剛接觸佛法的有心人,本書有助於領悟佛法的深刻內涵,正信而不迷信;對於已經入門的實修者,也可以藉此機緣,自我檢視,彌補基礎學識之不足,梳理佛法之精義,進一步扎實修為。
本書從佛學的定義、佛學和學佛的區別、佛教的成立開始講起,介紹佛教的歷史、教理、經論,並講述了佛家的修行方式 ── 戒定慧、禪觀、念佛及持咒等,內容豐富淺顯,易於領會,是佛學界公認的普及讀物中的絕佳版本。讀之,可快速地直達核心,了解佛教的整體概貌。
作者簡介:
蔣維喬(1873 - 1958)
字竹莊,別號因是子,江蘇武進人。著名教育家、養生家。早年致力於教育事業,曾任教育部秘書長、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東南大學校長等職。後皈依諦閑大師,法名顯覺,成為虔誠的佛教徒。後又親隨太虛大師學習因明學。主要著作有《因是子靜坐法》、《中國佛教史》、《廢止朝食論》、《世間禪》等。
TOP
章節試閱
第一節 甚麼叫做佛學
佛陀的意義
這個「佛」字是從印度梵文裡翻譯出來的名詞,如果音譯就是「佛陀」(Baddha)兩字。它的意思,就是「覺者」。這「覺者」又含三種意義:一曰自覺;二曰覺他;三曰覺行圓滿。
甚麼叫做自覺?就是說佛自己先能覺悟。
甚麼叫覺他?是說佛不單是自己覺悟,並且化導他人,叫他人也能覺悟。
甚麼叫覺行圓滿?是說佛自己覺悟,又覺悟他人,這兩種德行,已到了圓滿無缺的地步。
這「佛陀」兩字,平常習慣用省略的稱呼就叫做佛。
佛教與佛學
世界無論哪種宗教,各宗各有其依據的哲理,但多少總帶些迷信的色...
佛陀的意義
這個「佛」字是從印度梵文裡翻譯出來的名詞,如果音譯就是「佛陀」(Baddha)兩字。它的意思,就是「覺者」。這「覺者」又含三種意義:一曰自覺;二曰覺他;三曰覺行圓滿。
甚麼叫做自覺?就是說佛自己先能覺悟。
甚麼叫覺他?是說佛不單是自己覺悟,並且化導他人,叫他人也能覺悟。
甚麼叫覺行圓滿?是說佛自己覺悟,又覺悟他人,這兩種德行,已到了圓滿無缺的地步。
這「佛陀」兩字,平常習慣用省略的稱呼就叫做佛。
佛教與佛學
世界無論哪種宗教,各宗各有其依據的哲理,但多少總帶些迷信的色...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有一天,我友舒新城來說:「中華書局現在擬編一套百科叢書,專供中學程度的人閱讀。擬定的目錄中間,有《佛學綱要》(編者註:今改名為《因是子佛學入門》)一種,要請您擔任,但有兩個條件:一是不可太深;二是要用白話。」我聽他這話,想了一想,頗難立刻回答。因為佛教的本身,是建築在理智上面的,比任何宗教,來得精深博大,要說得十分淺近,根本上就有點為難;至於白話文字,我向來雖沒有做過,倒可以遷就的。
隔了幾天,舒君居然送到正式函件,一定要我擔任這工作。我想一二十年前,自己研究佛典,得不到淺近入門書,枉費了無數的...
隔了幾天,舒君居然送到正式函件,一定要我擔任這工作。我想一二十年前,自己研究佛典,得不到淺近入門書,枉費了無數的...
»看全部
TOP
目錄
例言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甚麼叫做佛學
第二節研究佛學怎麼樣下手
第三節佛學和學佛要分清楚
第二章 佛教的背景和成立原因
第一節佛出世前印度思想界
第二節佛出世前印度的社會
第三節佛教成立的原因
第三章 釋迦牟尼史略
第一節釋迦成道以前的狀況
第二節釋迦成道的時期
第三節釋迦的轉法輪
第四節釋迦的入涅槃
第四章佛教的立腳點和基本教義
第一節佛教的立腳點
第二節佛家的教法
第五章釋迦滅度以後弟子結集遺教
第一節第一次結集
第二節第二次結集
第三節第三次結集
第四節第四次結集
第五節大乘經典的結...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甚麼叫做佛學
第二節研究佛學怎麼樣下手
第三節佛學和學佛要分清楚
第二章 佛教的背景和成立原因
第一節佛出世前印度思想界
第二節佛出世前印度的社會
第三節佛教成立的原因
第三章 釋迦牟尼史略
第一節釋迦成道以前的狀況
第二節釋迦成道的時期
第三節釋迦的轉法輪
第四節釋迦的入涅槃
第四章佛教的立腳點和基本教義
第一節佛教的立腳點
第二節佛家的教法
第五章釋迦滅度以後弟子結集遺教
第一節第一次結集
第二節第二次結集
第三節第三次結集
第四節第四次結集
第五節大乘經典的結...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蔣維喬
- 出版社: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5-10 ISBN/ISSN:978988846602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40頁 開數:16開
- 商品尺寸:長:228mm \ 寬:154mm
- 類別: 中文書> 哲學宗教> 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