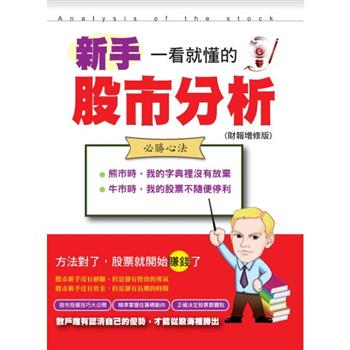清末民初的文學生態
晚清的文學生態今人已不太易理解。主要是今天的話語方式比過去簡單,反而把複雜的存在簡單化了。我們看後來白話文學的出現,包括政黨政治文化和各個文化生態的出現,跟晚清的文化格局的流變有很大的關係。這個過程流失了許多存在,也增加了新的東西。曾經有學者形容它是中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我覺得是對的。我們從文章學、從文學的角度進入那段歷史,審視那一代中國文人的生活狀況,發現那時候人們的漢語表達,能夠確實折射中國在悄悄地變化,這給後來的人們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結果。
首先是文章觀念發生了變化。大家知道,西學東漸後,新觀念進入中國,文人的文章風格就開始發生變化了。在中國社會,八股取士限制了人們的自由表達。千百年來,中國的讀書人寫文章都是一個套路,就是要頌聖,或引經據典,自己的內心隱秘被藏起來。人的心需要自由,可是卻被甚麼力量抑制住了。只是在一些旁門左道的文章裡,在一些私密的辭章裡有心性的自由在。值得一提的是,民間流傳的一些小說裡有有趣的東西,是鮮活和生動的存在。這和士大夫的文章形成一種差別。
到了晚清,桐城派的古文,在整個學界,在文壇,佔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桐城派的古文很有特點,今天看來,這學派學者們的文章都很講究,延續著古風。他們的文章注重義理、辭章和考據,所有的文章裡要有學理、辭章,要有分寸,還要帶上考據之趣。如果這三個元素佔據了,文章應當是好文章。曾國藩在《歐陽生文集序》提到桐城派的姚鼐時說:「姚先生獨排眾議,以為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為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這個流派的文章,掌握了文學的一種規律,應當說很不簡單。古文的表達在這裡有了理論的自覺。
可是在一些有想法人的思想裡面,文章是有多種可能的。作文應當是自己心靈發出的一種聲音,它不是為了外在功名,不是為了虛榮來寫作的。當西方傳教士把西洋的文明帶來以後,中國的一些文人突然發現,西洋人在表達自己生命感覺的時候,常常能夠抓住自己生命的鮮活的覺態,比如《浮士德》《復活》。可是前人留下的文章,常常是比較溫吞的、節制的、含蓄的,那種放蕩的韻致卻被遮掩了。
清代後期,文壇與官場被偽飾的文字所包圍,能夠抵抗這種世風者不是很多。大家知道龔自珍這個人是很有學問的,他的詩和文章都很好,也在北京做過小官。他是在整個文學史裡比較獨特的一個人。通常詩詞寫得好的人字寫得也好,龔自珍字卻不好,文章卻很不凡。他到北京當官後,漸漸厭惡起官場。在回到南方的時候,曾經寫過一首詩,這首詩寫道:「詩格摹唐字有棱,梅花官閣夜鎪冰,一門鼎盛親風雅,不似蒼茫杜少陵。」他說當時滿朝文武都在附庸風雅,但是與杜甫比遠甚。有人間情懷,有個人理想的人的文字是好的,很多附庸風雅的人沒有這樣的情懷,表達出現問題。龔自珍的憂患,是文學危機的一種反映。這種反映,在後來的黃遵憲、陳三立的詩文裡都有一些,不過無奈的是,他們的作品還不足以抗拒這股潮流。
晚清人寫文章,尤其是寫詩,是老八股,那狀態永遠超不出唐宋。比如同治和光緒兩帝的老師翁同龢,算是大學問家,但他的作品實在沒有多少新意。有一年我去他的老家,買了一冊他的詩文集,閱讀前特別期待,帝師的文章怎麼樣?看完以後就很失望,那些詩實在無味,文章沒有甚麼毛病,可它是非常規矩的,缺乏奇思。比如他有一首詩,叫《壽陽道中》:「一雨動秋潦,客程亦許遲。野花開五色,天氣備三時。走卒慣乘險,征夫常苦飢。太行天下脊,未敢輒題詩。」態度很隨順,人的厚道一看即知。他的詩歌裡感覺到古人套路的連續,自我內心獨特的感受與前人的一些詩歌是重疊的。他是在一種模式裡來寫作,所以這類詩文在晚清,已經被一些有世界眼光的人所厭惡了。
最早擺脫這個套路的,是那些有出國經歷的文人。1840年後,讀書人改良的觀念開始出現了。文章的理念也隨之不同於過去。我們發現魏源在《海國圖志》裡所表達的對於世界的理解,黃遵憲《日本國志》的思維方式,王韜的《淞隱漫錄》《淞濱瑣話》的意象,以及所運用的辭章已經跟前人不太一樣了。像郭嵩燾、薛福成、梁啟超、章太炎、章士釗、陳獨秀這些人的文章,已經偏離了明清文人的傳統,有了個性的張力。
黃遵憲是清代末期不能不提的大詩人。梁啟超、胡適、周作人都對他的成就頗為肯定。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創辦《時務報》,將梁啟超、汪康年召集於麾下,提倡維新。他與陳寶箴、譚嗣同都有很深的交往,思想是極為活躍的。年輕的時候對詩歌創作提出自己的獨到看法:「我手寫吾口」,要創意新路。他在《日本雜事詩》《人境廬詩草》裡表現的境界,與前人不同。王韜在《〈日本雜事詩〉序》中則說:「殊方異俗,咸入風謠。舉凡勝跡之顯湮,人事之變易,物類之美惡,歲時之送迎,亦並纖悉靡遺焉,洵足為鉅觀矣。」道出其間不俗的氣象。黃遵憲在《人境廬詩草》的序言中說:
僕嘗以為,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今之世異於古,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嘗於胸中設一詩境:一曰,復古人比興之體;一曰,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一曰,取離騷、樂府之神理而不襲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其取材也,自群經三史,逮於周、秦諸子之書,許、鄭諸家之註,凡事名物名切於今者,皆採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舉今日之官書會典方言俗諺,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其煉格也,自曹、鮑、陶、謝、李、杜、韓、蘇訖於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專一體,要不失乎為我之詩。誠如是,未必遽躋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
這個思路,早於五四那代改良家的思路,胡適後來的白話詩理念,實在也是黃氏思想的變異,可見其影響之大。胡適說他的平易、簡樸受到了日本文化的影響,由域外的經驗而發現了民歌的價值,遂在詩中多見口語,且民俗意味濃厚。高旭在《願無盡廬詩話》中說:「世界日新,文界、詩界當造出一新天地,此一定公例也。黃公度詩獨闢異境,不愧中國詩界之哥倫布矣,近世間無第二人。」這個評價,係覺悟的知識人的感慨,希望文章與詩詞泛出新意,是那時候有眼光的人的共識。
梁啟超是在文章學層面最早顛覆桐城派文章觀念的人。他最早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號。1896年,他任上海《時務報》總撰述,文風已變;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在《新民叢報》上發表大量作品,思維方式都有些出格,和桐城派的文章在章法上已經大不相同了。有人因之譏其為野狐禪。他自己的思路既有韓愈的遺緒,也有報紙新聞的味道,理論與詩情都有,精神的亮度多了。他的文章,「汪洋恣肆」,浩浩然有江海氣魄。他的語體,把日常的口語和中國古文章那種氣勢給表達出來了,更具有了現代的新意。比如在《過渡時代論》裡面,他就用很有力量的語句來描述自己對世界的看法。他說:「其現在之勢力圈,矢貫七札,氣吞萬牛,誰能御之?其將來之目的地,黃金世界,荼錦生涯,誰能限之?故過渡時代者,實千古英雄豪傑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剝而復、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美哉過渡時代乎!」他當時用這樣的一種文體來表達對世界的認識。這與桐城派的文人有別了。他在講到桐城派時說:
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以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梁啟超在文體上的這種變化,是中國文人精神狀態的折射,這影響了當時的許多讀書人。夏曉虹在《晚清文學改良運動》一文,談及梁氏的影響力,正反兩方面的聲音都在文壇中出現。儘管爭議很大,但是梁啟超的文風也輻射到科舉考試中。「作慣八股文的讀書人驟然失去依徬,梁啟超帶有『策士文學』風格的『新文體』便成為應試考者的枕中之秘」(《燕園學文錄》,110頁)。梁啟超對文學影響最大的,是他發表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他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國家新道德、新風尚、新人格、新學藝,都必「新小說」。1902年,《新小說》創刊,他在小說《新中國未來記》中貫穿了自己的思想,用小說表達自己的政治觀、文化觀,文風與寓意帶有革新的面貌,一時被讀者所喜愛。
梁啟超對文學和歷史的思考,有很大的格局。他從社會政治、宗教、國民性等幾個角度思考問題。語錄多「新」字,文章就有《新史學》《新民說》等,有一絲除舊佈新的意味。而背後的理論根據則是進化論。在《變法通議》中說,「變者,天下公理也」。他後來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說,中國人因接觸西學,便發生精神的變化。一是從器物上感到自己的不足,第二是發現自己的制度存在瑕疵,第三呢,是意識到文化出現了問題。而改變這些,只有改良。這個思路,在那時候很有代表性,他的文章,也明顯帶有過渡時期的痕跡。
那個時候,魯迅剛去日本留學,受流亡海外的民族主義文化影響,對官樣文章不太喜歡。他受到梁啟超的影響,閱讀興趣在悄悄變化。留學生崇尚漢唐氣魄的文體,陽剛之氣的文字頗受歡迎。魯迅曾經說,當時留學生最喜歡的幾句話,叫「披髮大叫,抱書獨行,無淚可揮,大風滅燭」。這樣一種狂士之風,在那時候已經興起。當時流亡到海外的一些人都放開了手腳,思想活躍起來。康有為和梁啟超跑到日本辦報、寫文章,染有一絲新風。還有章太炎這類人,文體是周秦漢時期的樣子,一洗明清的舊氣。中國不買他的賬,就到國外去,思想的革命與文章的革命就都來了。
日本是中國新文化的搖籃。1905年的時候,在東京的中國文人創辦了一個雜誌叫《民報》。當時孫中山這些同人們出力頗多,像胡漢民、汪精衛均在其列。1906年,雜誌的社長、主編變成了章太炎。《民報》是比較有意思的一本雜誌,是後來國民黨的一個黨刊,算是一本機關雜誌。這本雜誌當時刊登了很多帶有「排滿興漢」思想的文章。而文章絕沒有晚清以後中國文人的那種氣脈,是非常狂妄的。在章太炎看來,中國最好的文章應該是明代之前。到了明代晚期的時候,中國的文化已經達到相當高的高度。明代知識分子的文字是非常有個性的,可是到了清代,文章出現了變化,人們只是去搞考據,做純粹的版本思考,而不是關心生命哲學,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在《民報》裡面,好多人發表了有趣的文章。這些文章的風格、行文的方法都跟過去有了很大的不同,涉獵面開始廣闊起來,也有一種狂傲之氣。就是前面所說的「大風滅燭」那樣的一種陽剛之力的美。
章太炎在《民報》期間也搞講學活動,當時很多人跟他在東京讀書,學生中有錢玄同、沈兼士、周作人、朱希祖、魯迅(那時候用周樹人這個名字)。我們現在看朱希祖的日記,能夠感受那時候的講課氛圍,很是有趣。章太炎當時在講《說文解字》,言外也有時局、政治。他講課時流露出一種情緒,中國過去的文化是很燦爛的,可是現在不行了。漢代的時候,人的骨骼非常強大,有一種甚麼樣的精神呢?那是一種尚武的精神,可是元代以後,少數民族入中原,此類精神弱化,遂日落西山了。章太炎是民族主義者,有今不如昔的意識。他的研究發現,近代以來中國的男人已經沒有偉岸的骨骼和高大的身軀了,男人都變成小男人。所以文化也隨之萎靡。他說清代文章裡的陰柔之氣遠遠超過了陽剛之氣,有很大的問題。這是一種媚態的文化,或者說我們的文字表達出現了甚麼問題。我們的表達是一種奴性的表達,它成了專制統治下的一個工具,所有讀書人都知道稱頌,都是要在皇權下面書寫對世界、對人生、對自我的看法,個人的那種遊歷於宇宙之內的自由的暢想東西完全被抑制住。這個思路,在《民報》的文章裡都能夠看到。它表現出了一種文風的變化。
章太炎在文章學上是一個復古主義者。他自己喜歡魏晉文章,對清代文學的看法不好,以為梁啟超等人的文章不過一點小的聰明。梁啟超的文章是新式的,然而章太炎卻發現它們不過是明末小品的氾濫,言外不足為道。而他認為,中國的古語很有生命力,現在人們把它忘記了。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演說辭》中有這樣一段話:
像他們希臘、梨俱的詩,不知較我國的屈原、杜工部優劣如何?但由我們看去,自然本種的文辭,方為優美。可惜小學日衰,文辭也不成個樣子,若是提倡小學,能夠達到文學復古的時候,這愛國保種的力量,不由你不偉大的。
章太炎的文章,是自覺走復古的路的,可是那時候能夠讀懂其文章者甚為寥落。他所使用的詞語多是老的、死去的古語,能識其妙意者不多。胡適就以為這樣文章的方向是大有問題的。說他:
章炳麟的古文學是五十年來的第一作家,這是無可疑的。但他的成績只夠替古文學做一個很光榮的下場,仍舊不能救古文學的必死之症,仍舊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的盛業。他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卻沒有傳人。有一個黃侃學得他的一點形式,但沒有他那「先豫之以學」的內容,故終究只成了一種假古董。章炳麟的文學,我們不能不說他及身而絕了。
《民報》曾刊登過長篇小說《獅子吼》,作者叫陳天華。他是寫過一些政論文的,像《猛回頭》等即是。不僅政論文有特點,小說也很好看。這個小說基本還是從中國《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孽海花》《鏡花緣》等的邏輯下延伸出來的。可是這個小說利用舊形式,思想卻是新的。陳天華在小說裡邊,已經把中國傳統的八股取士的教育制度作為一個毒瘤來看待。小說裡邊寫了中國有出息的孩子,從鄉村走出來,走出來不是八股取士,而是留洋。回來以後他們在一個村莊搞試驗,來建造自己的一種樂園,有一種精神夢想在裡邊。《民報》上有這樣的小說,是個大事情,說明審美與精神哲學都有了變化。可是《民報》主要發表的是一種政論文章,這些文章,比小說的影響更大。魯迅就回憶說,看到章太炎與康有為等人論戰的時候,那血氣的文字,令人神往。
章太炎最有影響的書是《訄書》,他的文風古奧,試圖挽救晚清頹敗的文風。在他的文字裡,幾乎看不到明清文人的那種散淡之風,多的是峻急之氣。他欣賞古體詩,對近體詩則多有不屑。文章則推崇六朝之前者。章太炎覺得,文章與學識有關,但學識又會成為詩文之累。這一點,魏晉文人,頗多可取處。他在《論式》中說:「魏晉之文,大體皆埤於漢,獨持論彷彿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為百世師矣。」回到六朝尋找資源,可以說是一種文章學的新夢。他對於問題有所警覺,卻未深談,留下了許多探討的空間。
受到章太炎影響的魯迅,在1907年就寫了一篇文章《摩羅詩力說》,介紹西洋的這種個性主義的詩人,還有《人之歷史》《文化偏至論》等。在這裡,明顯可以看出章太炎的某些片影,尼采、克爾凱郭爾和施蒂納的個人主義思想也是有的。魯迅看出了我們的文化的問題,流行的文章之道、詩文之道、文化之道都出現了問題。他認為,未來的文化,「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我們的文化主要的內容是甚麼?就是立人,人立了以後,每個人都成為自己,而不要成為別人,如是,我們的文化才有希望。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民國文學十五講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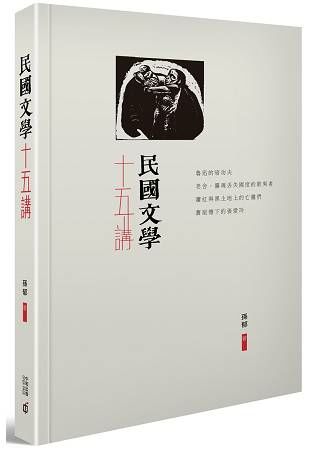 |
民國文學十五講 作者:孫郁 出版社: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6-2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318 |
二手中文書 |
$ 348 |
華文文學研究 |
$ 348 |
古典文學 |
$ 348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374 |
中國文學總論 |
$ 396 |
中文書 |
$ 396 |
華文文學研究 |
$ 396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民國文學十五講
從清末民初舊文學,到中共延安新文學路線,
數十年精彩變化一氣呵成。
「孫郁的研究,從魯迅、胡適等人出發,觀察舊時代的文人氣象,審度當下的寫作風向。他儒雅溫潤的文辭,體察靈魂的苦痛,傳遞生命的悲喜,經他講述的思想和人生,沉重、真實,倍感親切……」
── 第十二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文學評論家‧授獎詞
本書為孫郁在大學教授現代文學課的講稿整理而成。話題的時間跨度為清末民初至1949年,內容涵蓋了清末民初文學生態、新文學運動、舊派小說、舊詩詞、魯迅、新詩、老舍、曹禺、沈從文、學人筆記、戲曲、左派小說、蕭紅、張愛玲、草根及政治與文學等十五個專門主題。其中有民國文學個別領域的論述,也有對作家的專門研究。作者獨到的個人趣味、視角,與精專的議論和發現,讓本書兼具閱讀趣味與學術價值。
作者簡介:
孫郁
1957年出生。曾任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北京日報》文藝週刊主編,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魯迅研究月刊》主編。主要著作有《百年苦夢》(1997)、《周作人和他的苦雨齋》(2003)、《寫作的叛徒》(2013)、《革命時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閒錄》(2014)等。
TOP
章節試閱
清末民初的文學生態
晚清的文學生態今人已不太易理解。主要是今天的話語方式比過去簡單,反而把複雜的存在簡單化了。我們看後來白話文學的出現,包括政黨政治文化和各個文化生態的出現,跟晚清的文化格局的流變有很大的關係。這個過程流失了許多存在,也增加了新的東西。曾經有學者形容它是中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我覺得是對的。我們從文章學、從文學的角度進入那段歷史,審視那一代中國文人的生活狀況,發現那時候人們的漢語表達,能夠確實折射中國在悄悄地變化,這給後來的人們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結果。
首先是文章觀念發生了變化。大家...
晚清的文學生態今人已不太易理解。主要是今天的話語方式比過去簡單,反而把複雜的存在簡單化了。我們看後來白話文學的出現,包括政黨政治文化和各個文化生態的出現,跟晚清的文化格局的流變有很大的關係。這個過程流失了許多存在,也增加了新的東西。曾經有學者形容它是中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我覺得是對的。我們從文章學、從文學的角度進入那段歷史,審視那一代中國文人的生活狀況,發現那時候人們的漢語表達,能夠確實折射中國在悄悄地變化,這給後來的人們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結果。
首先是文章觀念發生了變化。大家...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後記
我在大學教書已近十年,講的最多的是文學史。這本書是多年的一點心得,枝枝葉葉中,卻沒有甚麼系統。在文學院教書,自然要對文學史有一個表述框架,但突破流行的模式,並不容易。我只是以自己的趣味,做了一點嘗試。講稿本來要好好打磨一下,一些參考資料、註釋等工作還沒有來及做,便被病魔困住了。
兩個月來,躺在病床上,心裡惦記著舊事,籌劃著還能做一點甚麼。但彷彿夢者多多,餘力寥寥,難免帶有堂.吉訶德的傻相。而細想一下,如果沒有這傻相,自己會更為空虛。所以,有時候也深深感謝那幻影的到來,而自己多年的工作,也恰...
我在大學教書已近十年,講的最多的是文學史。這本書是多年的一點心得,枝枝葉葉中,卻沒有甚麼系統。在文學院教書,自然要對文學史有一個表述框架,但突破流行的模式,並不容易。我只是以自己的趣味,做了一點嘗試。講稿本來要好好打磨一下,一些參考資料、註釋等工作還沒有來及做,便被病魔困住了。
兩個月來,躺在病床上,心裡惦記著舊事,籌劃著還能做一點甚麼。但彷彿夢者多多,餘力寥寥,難免帶有堂.吉訶德的傻相。而細想一下,如果沒有這傻相,自己會更為空虛。所以,有時候也深深感謝那幻影的到來,而自己多年的工作,也恰...
»看全部
TOP
目錄
清末民初的文學生態
新文學的起點
舊派小說
舊詩詞的餘暉
魯迅的暗功夫
新詩之路
老舍,靈魂丟失國度的歌哭者
曹禺的宿命之舟
沈從文的希臘小廟
學人筆記
梨園筆意
左派小說
蕭紅與黑土地上的亡靈們
舊屋檐下的張愛玲
草根與政治
後記
新文學的起點
舊派小說
舊詩詞的餘暉
魯迅的暗功夫
新詩之路
老舍,靈魂丟失國度的歌哭者
曹禺的宿命之舟
沈從文的希臘小廟
學人筆記
梨園筆意
左派小說
蕭紅與黑土地上的亡靈們
舊屋檐下的張愛玲
草根與政治
後記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孫郁
- 出版社: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6-21 ISBN/ISSN:978988846613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12頁 開數:18開
- 商品尺寸:長:230mm \ 寬:154mm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華文文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