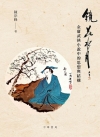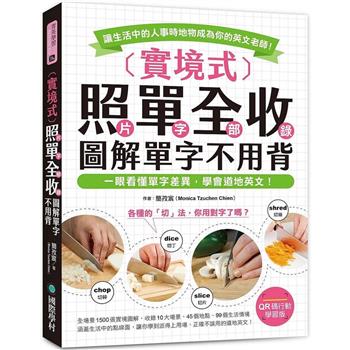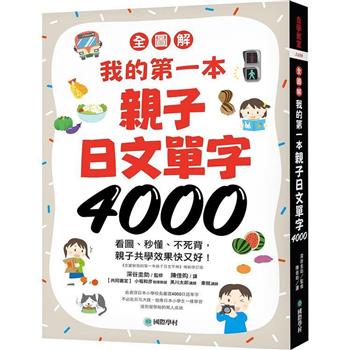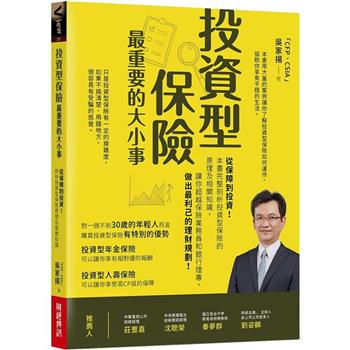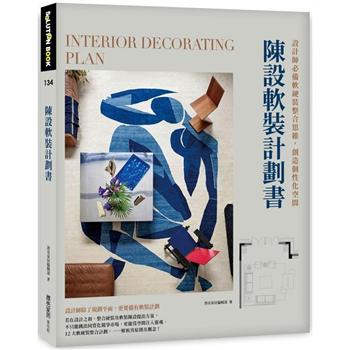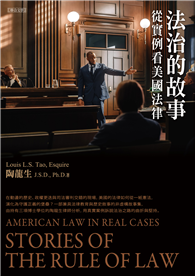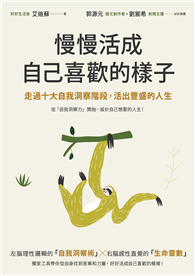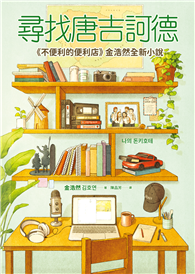此次在短時間之內邊閱讀邊在書上作評論以及作筆記,由此寫下《醍醐灌頂: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思想世界》與《文學考古:金庸武俠小說中的「隱型結構」》。前者在釐清金庸武俠小說之重要概念,既讓讀者對把握金庸的思想以及其武俠小說中的重要概念有一系統化的認識,更重要是針對當前金庸研究之雜亂無章而發。至於後者,則更是揭示金庸創作之謎,亦是昭示金庸武俠小說與中外小說的互涉之所在。
我為金庸研究,耗力甚多,所幸者此兩書自面世不久,即大獲好評,且兩書上市不久即告售罄,故此將兩書合訂為一,前者乃思想探索,後者則為文學考古,現分作上、下編,在文字上略作修訂,並冠以總論一篇於前,以作統攝。
作者簡介:
陳岸峰,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文學博士,現任職於香港大學。研究範圍涉及中國詩學、魏晉文學、文學史、現當代中國小說,以及史學方面的戰國史、魏晉史、唐史、明史。著述包括在香港出版的《鏡花水月: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思想與結構》(中華書局2017)、《文學考古:金庸武俠小說中的隱型結構》(中華書局2016,香港書展十大好書)、《醍醐灌頂: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思想世界》(中華書局2015)、《甲申詩史:吳梅村書寫的一六四四》(中華書局2014,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文學史的書寫及其不滿》(中華書局2014,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評論推薦獎)、《詩學的政治及其闡釋》(中華書局2013)、《戰國策》(中華書局2013;北京中信2014)、《世說新語》(中華書局2012;北京中信2013)、《神話的叩問:現當代中國小說研究》(天地圖書2012),以及2011年在大陸齊魯書社出版的《沈德潛詩學研究》與《疑古思潮與白話文學史的建構:胡適與顧頡剛》(「華東地區古籍優秀圖書獎」二等獎)。與此同時,他也一直致力於書畫的創作及藝術史的研究。
章節試閱
上編: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思想世界
第一章 導論
一、前言
金庸武俠小說是二十世紀文學界的旋風,席捲全球華人圈。1 金庸從1955年開始書寫《書劍恩仇錄》,直到1972年《鹿鼎記》完成之後封筆,歷時十八載,成書十四部,撰成對聯是為:「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在破碎的時空裏,金庸武俠小說以虛擬的形式,回歸傳統,成為漂散於各地的華人的心靈慰藉,形成了一個以傳統價值為核心的文化共同體。
然而,一次文壇排座次的評選卻引發所謂的雅俗文學之爭。一切始於《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小說卷》的評選,主編王一川將九位小說家排座次,金庸排名第四,在魯迅(周樹人,豫才,1881-1936)、沈從文(1902-1988)、巴金(李堯棠,芾甘,1904-2005)之後,而卻在老舍(舒慶春,1899-1966)、郁達夫(1896-1945)、王蒙、張愛玲(1920-1995)、賈平凹之前。2 所謂的「嚴肅文學」與「俗文學」分壘的「傳統」,3 亦不外是一場滑稽的鬧劇。文學史上有多少「經典」不是來自民間的通俗作品?從《詩經》、樂府、元明戲曲以至於明清小說,莫非如此,而這些作品不亦一一進入文學史的殿堂而成為「經典」?無論如何,此次評選的排座次亦足以反映金庸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具有衝擊傳統文學觀念的動能及實力,而其所引發的論爭,亦正是金庸武俠小說之成就尚未完全為世人或學界所理解之所在。以下將分別論述金庸在武俠小說的境界與語言上的傳承與創拓,下及其中蘊含的政治批判與文化想像,以還其在文學史上應有的位置。
二、武俠新境界
1. 俠的現代闡釋
金庸武俠小說之所以風靡天下,實乃其在武俠境界上有所突破所致。有論者指出清末以來武俠小說的桎梏在於「理性化傾向」:
清代是武俠小說鼎盛期,理性化傾向更為嚴重。《三俠五義》、《施公案》中,俠客變成皇家鷹犬,立功名取代了超逸人格追求,武俠小說甚至蛻變為公案小說。歷史經驗證明,古典武俠小說循着偏重社會理性一途走到了盡頭。4
即是說,在清廷的高壓下,俠客難以有所作為,甚至淪為官府的鷹犬,武俠小說的發展備受壓抑,也是現實的反映。故此,民國初年的武俠偏向於情而非義:
民國初年開始了這種轉向,情取代義成為俠客人格的主導方面;江湖成為俠客主要活動場景,不是替天行道,而是情仇恩怨成為主題。《江湖奇俠傳》是這種轉變的標誌,它開闢了武俠小說的新天地,帶來了本世紀上半葉武俠小說鼎盛期。5
民國時期,武俠小說突然「轉變」,以至於「鼎盛」,亦屬必然。杜心五(1869-1953)、王五(子斌,1844-1900)、霍元甲(俊卿,1868-1910)等大俠的出現,正是時代劇變的徵兆。6 在此關鍵時刻,金庸在武俠小說中藉易鼎之際的書寫而令武俠擺脫淪為朝廷鷹犬,豪氣重現。此中,《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及《鹿鼎記》等長篇的背景均屬易鼎時代。《天龍八部》乃以北宋末年宋、遼爭持的場域為背景,《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及《倚天屠龍記》則從宋、金對峙寫起,歷元蒙勃興以至於元末群雄並起,《碧血劍》寫「甲申之變」,7《鹿鼎記》與《書劍恩仇錄》則述天地會之反清復明故事。故有論者指出金庸武俠小說之突破在於:
金庸以及他所代表的新派武俠小說沿着民初武俠小說道路發展,並有所突破,它真正對俠進行了現代闡釋,完成了古典武俠小說向現代武俠小說的轉化。8
所謂俠的「現代闡釋」,實即指金庸武俠小說傳承了五四文學中「感時憂國」9 的歷史意識,在中華民族的各個轉折時代均作出想像的書寫之外,同時面對當代的政治人物以及歷史事件,如毛澤東(潤之,1893-1976)及文化大革命,均成為其筆下的隱喻及批判所在。故此,有論者指出:
他寫着武俠,寫着政治,又不時透出對武俠愚昧的嘆惋和對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根本上的鄙棄。正因為這樣,金庸的小說才拓出了武俠的新境界,成為二十世紀裏真正有現代意義的作品之一。10
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主人公均是武功蓋世且心存天下蒼生。例如,郭靖從蒙昧少年,及至中原後便深受范仲淹(希文,989-1052)、岳飛(鵬舉,1103-1142)的心繫天下蒼生的思想所感召,從而投身於保家衞國之行列;楊過更是捨小我之仇恨,承傳嵇康(叔夜,223-263)之「魏晉風度」,最終亦追隨郭靖抗擊蒙古大軍;張無忌在張三丰的精神感召之下,負起抗擊元蒙之重擔,最終又顧全大局而甘願飄然遠去。即是說,金庸確是既寫武俠,復寫政治,而主要的是突顯俠之正義與忘我,實乃對俠魂之召喚,而非「對武俠愚昧的嘆惋」,至於「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亦不能做到「根本上的鄙棄」,只是讓俠客在歷史的時空中參預演出,卻無法逆轉既定的歷史現實。
2. 歷史詮釋
金庸武俠小說的另一創造性突破更在於融入個人的歷史詮釋,有論者認為:
金庸小說「歷史感」之強烈,往往使讀者分辨不出究竟他是在寫「歷史小說」還是「武俠小說」。11
事實上,只有將武俠置於歷史環境之中,俠客才能綻放異彩。從司馬遷(子長,約前145—前87)《史記.遊俠列傳》中最早關於俠所記載的「俠以武犯禁」12 俠之使命由此凝定,沒有特定的歷史時空,俠的「以武犯禁」亦必將落空而失去其存在的價值。金庸的歷史意識於晚年的修訂本中益發深入,除了在有歷史證據之處作出說明之外,甚至將具體的年代標示出來或增入史料,如《天龍八部》的〈釋名〉中,舊版(1963年香港武史出版社)原無「據歷史記載,大理國的皇帝中,聖德帝、孝德帝、保定帝、宣仁帝、正廉帝、神宗等都避位為僧」、「本書故事發生於北宋哲宗元祐、紹聖年間,公元1094年前後」;舊版的《射鵰英雄傳》原僅有「山外青山樓外樓」一詩引首,略敘其歷史背景,而修訂版中則改為「張十五說書」,以引出其時宋、金的局勢。金庸在中國歷史的各個轉捩點上均予以省思,實乃傳承自魯迅以降對國民性的拷問,例如:《天龍八部》中的胡漢之分與蕭峰的捨身餵鷹;《神鵰俠侶》中楊過與小龍女的抗議名教與抗擊蒙古之後返回古墓隱居;《倚天屠龍記》中的復仇與寬恕;《笑傲江湖》中的正邪之辨。這一切,均是國民性的關鍵以至於哲學思考的重大命題,絕非坊間談情說愛的俗套小說可以企及。
事實上,金庸武俠小說在其批評者夏志清(1921-2013)對現代小說所評價的「感時憂國」的思潮上走得更深更遠,而在想像的空間上則拓展得更廣更闊,誠如舒國治所言:
其文體早已卓然自立。今日我國人得以讀此特殊文體,誠足珍惜。而金庸作品之涵於當代中國文學範疇,亦屬理所當然。13
確是的論。由此而論,若將金庸武俠小說置於五四文學之中,亦是獨樹一幟,光芒萬丈,不可逼視。治文學史者以陳見陋習而排斥武俠小說於文學史之外而聲言尋求現當代文學傑作,何異於刻舟求劍?
----------------------------------------
1 有關金庸武俠小說的翻譯及其以電影的方式而流行的情況,可參閱柏楊:〈武俠的突破〉、林以亮:〈金庸的武俠世界〉,分別見三毛等:《諸子百家看金庸》(香港:明窗出版社,1997),第4冊,頁144,154-156。有關武俠小說與武俠電影的相互激盪的論述,可參閱劉登翰:《香港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頁263-264。
2 陳墨:〈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劉再復、葛浩文、張東明等編:《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2000),頁59。
3 田曉菲便在〈從民族主義到國家主義:《鹿鼎記》,香港文化,中國的(後)現代性〉一文中指出:「金庸小說和香港電影都蒙受『俗』的批評,但是,我們的世紀需要的不是已經太多的『雅』,而是一點『俗』。」而朱壽桐亦在〈在與精英文學的比性已經成為一種事實狀態」。分別見吳曉東、計璧瑞編:《2000’北京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369,154。
4 楊春時:〈俠的現代闡釋與武俠小說的終結——金庸小說歷史地位評說〉,劉再復、葛浩文、張東明等編:《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81。
5 楊春時:〈俠的現代闡釋與武俠小說的終結——金庸小說歷史地位評說〉,劉再復、葛浩文、張東明等編:《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81。
6 劉登翰先生將新派武俠小說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1912年至1922年為萌芽期;1923年至1931年為繁榮期;1932年至1949年為成熟期。關於新派武俠小說發展的論述,可參閱劉登翰:《香港文學史》,頁265。
7 有關「甲申之變」的專著,可參閱陳岸峰:《甲申詩史:吳梅村書寫的一六四四》(香港:中華書局,2014)。
8 楊春時:〈俠的現代闡釋與武俠小說的終結——金庸小說歷史地位評說〉,劉再復、葛浩文、張東明等編:《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81。關於「新武俠」小說,劉登翰分別從敘事角度、結構、語言,以及人物的心理、性格的深度、語言方面在明清傳統與現代語的結合,還有現代意識如對「快意恩仇」的否定與人道主義的揄揚等元素的加入作出論述。詳見劉登翰:《香港文學史》,頁264。有論者則指出:「金庸以及其影響下的武俠創作,正因為一方面牢牢把握住了接受主體的情感投入基礎,一方面又通過主體的能動創造在讀者心中構建了如此紛繁燦爛的武俠世界,才使得武俠小說最終成為了人們所喜聞樂見的一種文藝形式。這也就是『新派武俠小說』所以稱之為『新』的關鍵所在。」見吳秀明、陳擇綱:〈金庸:對武俠本體的追求與構建〉,《當代作家評論》,1992年第2期,頁50。
9 「感時憂國」乃夏志清在〈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一文中提出:「當時的中國,正是國難方殷,無法自振。是故當時的重要作家——無論是小說家、[轉下頁〕劇作家、詩人或散文家……都洋溢着愛國的熱情……作家和一些先知先覺的人物,他們的憂時傷國精神,除了痛感內憂外患,政府無能之外,更因為紛至沓來的國恥,反映出中國在國際地位上的低落,也暴露了國內道德淪亡,罔顧人性尊嚴,不理人民死活的情景。」見夏志清:《愛情.社會.小說》(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5),頁80。嚴家炎先生指出新武俠小說與「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一脈相承,異曲同工。見嚴家炎:〈新派武俠小說的現代精神〉,《明報月刊》,1996年2月號。此處乃轉引自劉登翰:《香港文學史》,頁264。
10 吳予敏:〈金庸後期創作的政治文化批判意義〉,劉再復、葛浩文、張東明等編:《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46。
11 林保淳:〈通俗小說的類型整合——試論金庸的武俠與歷史〉,劉再復、葛浩文、張東明等編:《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62。
12 司馬遷著;馬持盈注:《史記今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第6冊,卷124,頁3219。
13 見舒國治:〈小論金庸之文學〉,三毛等:《諸子百家看金庸》,第4冊(香港:明窗出版社,1997),頁140。
上編: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思想世界
第一章 導論
一、前言
金庸武俠小說是二十世紀文學界的旋風,席捲全球華人圈。1 金庸從1955年開始書寫《書劍恩仇錄》,直到1972年《鹿鼎記》完成之後封筆,歷時十八載,成書十四部,撰成對聯是為:「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在破碎的時空裏,金庸武俠小說以虛擬的形式,回歸傳統,成為漂散於各地的華人的心靈慰藉,形成了一個以傳統價值為核心的文化共同體。
然而,一次文壇排座次的評選卻引發所謂的雅俗文學之爭。一切始於《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小說卷》的評選,主編王一川將九位小...
推薦序
推薦辭(王晉光教授)
四十多年前,有一天,國文老師在課堂上說,美國許多華人教授,一下班就閱讀金庸小說,人手一冊。聽後頗感詫異,一則,理工科教授也追捧武俠小說,真是不可理解,心裏總覺得武俠神魔志怪分別不大;二則1967 年「五月風暴」發生後,金庸被左派人士目為支持港英的「漢奸」,這「漢奸」的書怎麼會有那麼多高等知識分子喜愛?有一段時間,我對梁羽生、金庸和蹄風的若干武俠作品,很感興趣。我未嘗習武,對於招式一向看不懂,看書時就輕輕忽略。某天終於想起,這些作品,如《書劍恩仇錄》、《射鵰英雄傳》、《白髮魔女傳》、《七劍下天山》等等,幾乎都在談明清易代之事,以至宋元交替之史,才驀然驚覺,這哪裏是講武俠,分明是故國之泣!戰後東西壁壘,逃亡海外的人士,無論貧富,其為知識分子或草根勞工,潛意識中,多少哽咽着「亡國」哀愁。蘇俄勢力延伸歐亞,而宋明淪喪於滿蒙,心理上容易類比。武俠者,其寄託哀傷乎?後來讀到其他材料,知道梁羽生和金庸,這兩位了不起的武俠小說家,都出身於大公報,但是,不約而同,兩家的父親在解放初期都被地方幹部鎮壓誅殺。所謂寧為太平犬,莫為亂離人,中年以後,更深切體會,上一代飽受百年戰爭之苦,家散人亡,倖存者孤苦伶仃過其餘生,令人悲憫。而所謂俠義,無非揭示亂世男女情懷,在痛苦的現實中找尋午夜夢回的傷逝而已。無論說得多麼堂皇動聽,人間政權交替,改朝換代之際,除政治野心家之外,家家戶戶都是受害者,此即諸人筆下反清復明,抗元扶宋之真義。海內外流離失所者感同身受,其理亦在此。年輕時,我是這樣理解他們的作品的。
陳岸峰教授此書可謂彙集諸家研究成果。數十年來,金庸作品風行海內外,正版盜版翻版,各有巿場。有機會閱讀及探析金庸作品的,或觀看電影電視片集的,固不限於中國內地及港臺,遠至南洋歐美,凡有華人之處,幾乎都能取金庸故事內容為話題。評論文章,見於報刊雜誌,實不計其量,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然則一般讀者,若想了解各地評論家之寶貴意見,存世材料如此繁富,搜集之功,何從做起?現在手持一冊《醍醐灌頂: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思想世界》(本書上篇),即可間接了解其中奧妙,而可以代替無窮之複印和抄寫。想進一步探討金學,亦可按圖索驥,根據陳教授書中提示之資料來源,進一步查找,即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陳岸峰教授此書是一部完整的、系統性的金庸研究的學術著作。導論、總結而外,中間細分為江湖、武功、俠義、情為何物、魏晉風度、異域六項論述,每一項底下還有七至八個細節,確實做到綱舉目張,而又四平八穩。這個結構,表面看來簡單,實際上包含作者的智慧和心血。要將眾說紛紜、取自多方、原來複雜繁蕪的文字概括為條理清晰、簡樸扼要的項目,沒有縝密的思慮,沒有高度的學養,是無法做到的。駕馭材料,是學術人員的基本功,處理得巧妙,則反映研究者「內功」根柢深厚,不可小覷。「總結」之章,最能見到作者之視覺焦點、興趣所在與概括能力。這一章內容,既論述金庸一再修改其著作之經過,又揭示金庸作品優劣之情節,真可以為金庸文學之評價劃上句號。古人如歐陽修,終生改文,以期留傳千古。金庸一生所嚴肅期望者,其在此乎!陳教授指出當中仍有未盡善者,乃世間常態耳,須知道,「止於至善」,是一種理想,乃遙不可及之事,只有傳說中的至人神人聖人方可臻其境界。
王晉光
香港藝術發展局評審委員/香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
2015年3月9日
推薦辭(王晉光教授)
四十多年前,有一天,國文老師在課堂上說,美國許多華人教授,一下班就閱讀金庸小說,人手一冊。聽後頗感詫異,一則,理工科教授也追捧武俠小說,真是不可理解,心裏總覺得武俠神魔志怪分別不大;二則1967 年「五月風暴」發生後,金庸被左派人士目為支持港英的「漢奸」,這「漢奸」的書怎麼會有那麼多高等知識分子喜愛?有一段時間,我對梁羽生、金庸和蹄風的若干武俠作品,很感興趣。我未嘗習武,對於招式一向看不懂,看書時就輕輕忽略。某天終於想起,這些作品,如《書劍恩仇錄》、《射鵰英雄傳》、《白髮魔女傳》...
作者序
小說之所以是小說,必須有故事,故事必須給讀者帶來或是趣味盎然,或是探索思考,在驚訝、震懾以至於愉悅中,獲得仿如西方戲劇中的「淨化」(Catharsis)作用:愛情或可此恨綿綿,而正義必須昭彰。在金庸筆下,蕭峰與阿朱的患難與共,此情不渝;郭靖與黃蓉俠侶相伴,最終戰死襄陽,柔情俠骨而悲壯;楊過與小龍衝開倫理禁忌,謳歌愛情,抨擊禮教之滅絕人性;令狐沖與任盈盈相契於魏晉風度,嘯傲江湖。以上種種的愛情,崇高而純美,風靡天下,淨化了幾代人心。趣味方面則乃金庸俠小說能吸引廣大青少年之關鍵所在。《天龍八部》中,天山童姥乃一畸人,其身心皆殘,以吸血而存活,而武功絕倫,其輕功真可謂御風而行。其携虛竹飛行一幕,真可謂金庸的神來之筆,閱後之感嘆,至今難忘。《射鵰英雄傳》中,郭靖在西湖初見女妝的黃蓉,其飄然出塵,猶如藐姑射之神人,開啟了郭靖懵懂的愛戀,兩情相悅,悄然而生。在此,讀者與文本互應,讀者進入文本,融入吸血的震慄、飛行的快感、初戀的甜蜜,此乃閱讀小說的趣味,這亦是小說魅力之所在。至於「降龍十八掌」、「凌波微步」、「打狗棒法」、「黯然銷魂掌」、「獨孤九劍」以及其他種種不同名目的絕世功夫,皆是超群的想像與優美的國語相結合的武俠新創境。
閱讀小說,參悟金庸,必須咀嚼湯顯祖在《牡丹亭.作者題詞》中的這段名言: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必因薦枕而成親,待掛冠而為密者,皆形骸之論也。……人世之事,非人世可盡。自非通人,恆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邪!1
對於湯顯祖來說,「情」具有「出生入死」的無窮威力,故而他才說:「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因此,「情」在湯顯祖的思想世界中實具有一超越的地位,甚至進而由此「情」觀更推進一步肯定「夢」的功能。「夢」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乃邪思綺念之源,而湯氏卻說:「夢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湯氏大膽地指出傳統中的禁忌──「夢」可以成真,這正是對傳統的禁忌正式提出挑戰。而且,湯氏認為「夢」乃人性中不可缺少的合理成分。既然是合理的成分,那便沒有禁制的必要與理由。從而,湯氏曰:「必因薦枕而成親,待掛冠而為密者,皆形骸之論也。」「情」純屬自然,實無忌而不談的必要,而且在湯氏的文學觀來說,甚至是首要的。其情觀實乃其哲學與文學思想的結合,而且更進一步地將其情觀融入實際的劇本創作中,從而實際地發揮了情觀的影響力,得到天下不少有情人的共鳴。2湯顯祖有關「情」、「夢」及生死之觀念在文學創作而言,可以說乃開創了超越寫實的桎梏,故而死而可以復生,現實與虛構並存,由此方有「詩的正義」,歷史現實的殘酷與遺憾可以彌補於文學想像的書寫之中。曾經是編劇,更以小說成名的金庸必然深契湯顯祖以上思想之三昧:故蕭峰可以臥於馬匹之腹,在千軍萬馬中擒殺楚王父子,化解叛變;郭靖與黃蓉可以在五指峰上的危難之躍上大鵰,比翼而去;楊過可以在十六年後重逢小龍女於碧水潭中,終成眷侶;令狐沖與任盈盈可以相契於「廣陵散」的琴音中,笑傲江湖。此夢耶?非夢耶?夢與非夢,現實與想像,歷史的的燭影搖紅,江湖的兒女情長,這一切均幻化成為浪漫、悲壯而隱含具有時代思想意義的武俠傳奇,在淒風苦雨中慰藉無數彷徨愁苦的心靈。
以武俠而重構歷史,以武俠而刻劃人性,並創造性地融會貫通於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之中,這一切都是金庸畢生所致力的書寫。武俠的恩怨情仇,江湖的波譎雲湧,多少人假俠義而行兇,多少人沉冤待雪,最終亦是鏡中花,水中月,終歸寂滅。金庸筆下人物,遭遇各有不同,故事迥異,或以悲劇告終,或能超然物外。這一切,均是中外小說對金庸的啟迪。故此,閱讀金庸,則必旁涉中外小說,金庸武俠小說與中外小說的文本互涉,揭示其「隱型結構」,又何嘗不是另一層次的水中花、鏡中月的折射?故以《鏡花水月: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思想與結構》為名。
陳岸峰
----------------------------------------
1 湯顯祖著,徐朔方、楊笑梅校注:《牡丹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頁1。
2 《牡丹亭》一劇在當時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力,獲得很多女性觀眾,甚至理學家的共鳴。而且,《牡丹亭》對後來很多的戲劇創作亦有頗大的影響。相關論述可參徐朔方:〈《牡丹亭》和婦女〉,《湯顯祖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147-153﹔徐扶明﹕《牡丹亭研究資料考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213-320。
小說之所以是小說,必須有故事,故事必須給讀者帶來或是趣味盎然,或是探索思考,在驚訝、震懾以至於愉悅中,獲得仿如西方戲劇中的「淨化」(Catharsis)作用:愛情或可此恨綿綿,而正義必須昭彰。在金庸筆下,蕭峰與阿朱的患難與共,此情不渝;郭靖與黃蓉俠侶相伴,最終戰死襄陽,柔情俠骨而悲壯;楊過與小龍衝開倫理禁忌,謳歌愛情,抨擊禮教之滅絕人性;令狐沖與任盈盈相契於魏晉風度,嘯傲江湖。以上種種的愛情,崇高而純美,風靡天下,淨化了幾代人心。趣味方面則乃金庸俠小說能吸引廣大青少年之關鍵所在。《天龍八部》中,天山童姥乃...
目錄
總論 iii
上編: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思想世界
推薦辭(王晉光教授) xvii
第一章 導論
一、前言 2
二、武俠新境界 3
三、理想的國語 14
四、人的文學 22
五、政治批判 24
六、文化想像 28
七、研究綜述及章節安排 30
第二章 青衫磊落險峰行:江湖真相與政治互動及其重塑
一、前言 34
二、所謂「江湖」 35
三、寶藏秘笈 47
四、幫派 50
五、江湖與政治 57
六、重塑江湖 58
七、結語 60
第三章 奔騰如虎風煙舉:武功與文化及其創造性
一、前言 64
二、武功與福澤 65
三、武功與文化 67
四、武功之神妙 73
五、武功之創造性 84
六、武功之兩極化 89
七、天下第一 98
八、結語 104
第四章 雖千萬人吾往矣:俠之觀念與譜系建構及其演變
一、前言 108
二、「俠」的概念及其內涵 109
三、俠與政治 115
四、俠客與英雄 117
五、俠之譜系的建構 121
六、俠之演變 124
七、結語 127
第五章 燭畔鬢雲有舊盟:情之正變及情俠結構之突破
一、前言 130
二、貪嗔癡 131
三、因情成魔 138
四、心象 142
五、一往情深 144
六、情俠結構的突破 151
七、結語 152
第六章 丈夫何事空嘯傲:「魏晉風度」的建構及傳承
一、前言 154
二、「魏晉風度」譜系 155
三、一往情深 162
四、任誕 164
五、飲酒與服藥 166
六、長嘯 168
七、〈笑傲江湖〉與〈廣陵散〉的傳承關係 170
八、結語 172
第七章 塞上牛羊空許約:武俠的異域書寫與歷史省思
一、前言 176
二、西毒東來 176
三、邪功異能 181
四、胡漢之爭 187
五、胡漢之戀 195
六、潛修去國 198
七、結語 201
第八章 總結 203
下編:金庸武俠小說中的「隱形結構」
推薦辭(黃坤堯教授) 213
第一章 導論
一、西潮的衝擊及其影響 218
二、「隱型結構」的定義 220
三、「隱型結構」三重奏 224
四、歷史時空的傳承結構 226
五、移植、創造及「文學考古」 228
六、研究綜述與章節安排 230
第二章 頓漸有序:《射鵰英雄傳》中郭靖的原型及其英雄歷程
一、前言 232
二、身世、結義及婚姻 232
三、奇遇 235
四、文化認同 246
五、角色抉擇 252
六、從俠客到英雄 256
七、結語 261
附錄 263
第三章 欲即欲離:《神鵰俠侶》中楊過與小龍女的原型及歸宿
一、前言 274
二、豬八戒、沙僧及白龍馬 274
三、命名及成長經歷 286
四、緊箍咒與情花痛 291
五、火焰山與碧水潭 295
六、不同的歸宿 300
七、結語 303
附錄 304
第四章 何足道哉:《倚天屠龍記》中張無忌的複合原型及其領悟
一、前言 314
二、俠義有源 315
三、神力與神功 318
四、兩代情緣 324
五、奇遇、江山及美人 335
六、何足道哉 341
七、結語 346
附錄 347
第五章 鏡花水月:《天龍八部》中蕭峰的原型及其命運
一、前言 364
二、蕭峰與武松 365
三、雪夜情挑 376
四、快活林與遼國皇位 384
五、化裝逃亡及歸宿 388
六、鏡花水月 392
七、結語 396
附錄 397
第六章 竹林琴音:《笑傲江湖》中令狐沖的「魏晉風度」
一、前言 430
二、「魏晉風度」譜系 431
三、一往情深 433
四、任誕 435
五、飲酒、服藥及長嘯 439
六、《笑傲江湖》與〈廣陵散〉 444
七、結語 453
附錄 454
第七章 任誕與假譎:《鹿鼎記》中韋小寶的原型及其意義
一、前言 458
二、任誕 458
三、嗜賭 463
四、假譎與智謀 466
五、武功的現實主義 470
六、俠之省思 473
七、結語 479
第八章 《三岔口》與《十日談》的混合結構
一、前言 482
二、《射鵰英雄傳》中的「牛家村密室」 483
三、《天龍八部》中的「窗外」 486
四、《倚天屠龍記》中的「布袋」、「皮鼓」及「山洞」 487
五、《笑傲江湖》中的「磷光」、「雪人」及「桌下」 492
六、《鹿鼎記》中的「衣櫃」、「蠟燭」及「破窗而出」 496
七、《鹿鼎記》與《雪山飛狐》中的「說故事」 500
八、結語 504
第九章 總結 506
徵引書目 509
後記 515
總論 iii
上編: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思想世界
推薦辭(王晉光教授) xvii
第一章 導論
一、前言 2
二、武俠新境界 3
三、理想的國語 14
四、人的文學 22
五、政治批判 24
六、文化想像 28
七、研究綜述及章節安排 30
第二章 青衫磊落險峰行:江湖真相與政治互動及其重塑
一、前言 34
二、所謂「江湖」 35
三、寶藏秘笈 47
四、幫派 50
五、江湖與政治 57
六、重塑江湖 58
七、結語 60
第三章 奔騰如虎風煙舉:武功與文化及其創造性
一、前言 64
二、武功與福澤 65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