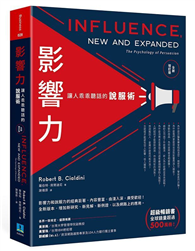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家.寶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301 |
歷史小說 |
$ 340 |
其他類型 |
$ 378 |
中文書 |
$ 378 |
小說 |
$ 387 |
現代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家.寶
余家寶,八十後,土生土長香港人。
被起名「家寶」,父母卻先後離家,留下她與嫲嫲相依為命,視名字為世界上最短的詛咒──她從「余家寶」三字開始,認識周遭的一切,遇上名字相同性格迥異的同學,愛上一個願意許諾她姓氏的人,見證一些名字的輝煌與墜落。
幾十年間,她從嫲嫲的孫女,變成她人的母親;生活的城市從借來的地方,成為了她立志面對命運之地。一路走來,她見證人事轉變,經歷屬於這地的喜怒哀樂。
因為名字,我們記得,我們保存,我們重逢,我們聯繫。一切從名字而生,這是余家寶的故事,也是香港的故事。
「《家‧寶》的創作起始點也是源於生命的痛。於我,她是一個向內心挖掘傷痛的故事,由成長而來的疑惑,到命運弄人的殘酷,再進一步挖掘在歷史的宿命加諸幾代人身上的傷痕。如果命運是一場不能避免的大風暴,似乎人就只能走進風暴之中,消化苦難存在的意義,在蕩漾著的苦痛生命中結出花果。」──蔣曉薇
作者簡介|
蔣曉薇
先後於香港中文大學取得中國語文及文學學士學位和相互文化研究文學碩士學位,公餘時間創作小說及舞台劇。二○一六年出版《家.寶》,獲香港劇團「三角關係」改編為同名舞台劇。二○一七年再與「三角關係」合作,創作舞台劇《秋鯨擱淺》。其後,在TBC網上平台發表《單身公寓》,並在《虛詞》發表評論及散文。二○二○年在香港出版《幻愛》(電影小說),並在台灣出版著作《秋鯨擱淺》。二○二一年為普劇場兒童文學劇《蛐蛐》擔任編劇,並在《皇冠雜誌》發表短篇小說〈炎夏的一場麵粉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