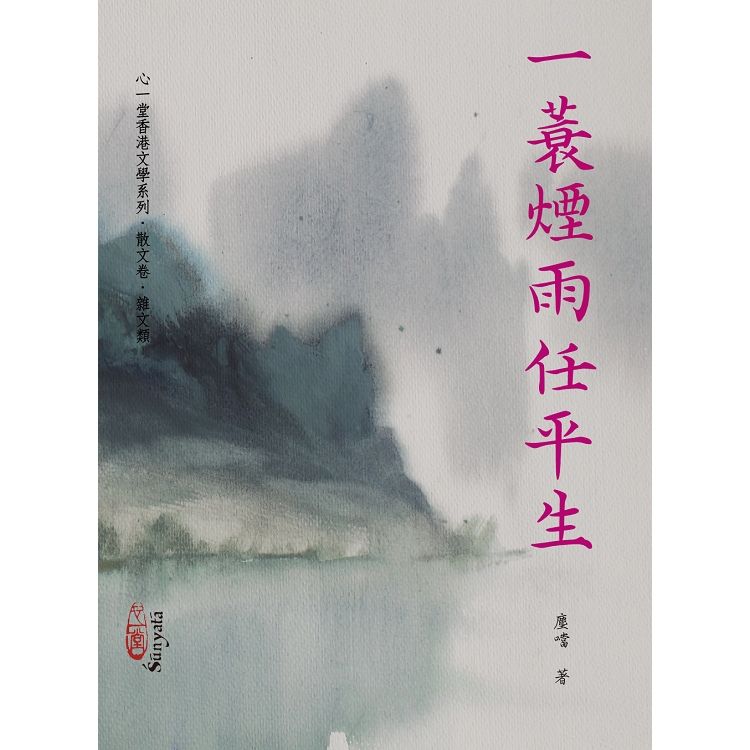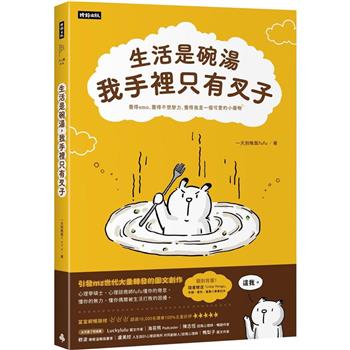何老師(代序)
何師不怒自生威,
鎮日營營正校風。
源源豐盛桃李茂,
師嚴道尊敬心中。
六年前二零一一,九龍華仁書院七一屆香港重聚,我見到了何老師。回家後,老師與同學的影像令我浮想聯翩。近四十年未寫中文了。花了幾天時間,在電腦前敲敲打打,敲出了一篇〈華仁的回憶〉。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把文章送給老師與同學們。
老師囑咐,請繼續寫,支持同學會網站。遂遵師命交功課,從此不斷地寫,永遠支持。
只寫了三篇,老師就問:「噹,你這幾十年在做什麼?」
「老師啊,我這幾十年在做 I.T 工作,也人在江湖。雙管齊下,養妻活兒。」
我不是好學生,生性貪玩。老師說,多讀多寫會進步。聽老師的話,為寫文章迫著自己重拾書本,唐詩宋詞,紅樓三國,老殘儒林,溫故知新。
老師是網站編輯,我的文章必經他過目,挑出錯字,撿出言不及義句子。有時候,他還會找到圖片配合,使之圖文並茂。
多倫多九華網站遊覽者眾,老師功不可沒。深夜短訊對話,常對我說,是夢會周公時候了,明天再做。
大師董橋寫他老師八十歲生日:「喜見人老了還有老師在,可以隨時問字。」我也是。這是我的福,我的緣。
老師姓何,名鎮源。我曾經在文章中稱他校長。他更改了,改為副校長。高大壯碩,國字口臉,眉目間自然地傳出教育者的友善,威武中帶著一股文氣。講故事娓娓道來,聲線低而緩慢。那口廣州話,仿佛在兒時聽過,現在已經失傳。
老師西裝筆挺講故事:
「市橋皇帝李朗雞,牌九輸錢問人借『兩雞』,『兩』、『朗』同音,所以叫佢做李朗雞……」老師在講述解放前市橋惡霸,把我帶回我爺爺講故事的年代。
雲淡風輕交往幾年,對老師有更多的了解。他從廣州來,兒時讀沙面小學。他的母親是南海仙崗村人,與我同鄉。
老師愛看體育運動,愛看跑馬,所以關於網球,籃球,跑馬等文章,他必愛。那些故鄉的遊記與回憶,就更不用說了。
時常惶恐寫作的內容不「正確」,有誤人子弟之嫌。但老師確定放行無阻,並且來一句,another good one,鼓勵鼓勵。
有時所寫的確是離譜,文字與內容走火入魔。老師會說:「老師愚邁,這類文章,敬謝不敏。」他勸我,請勿浪費精神,把腦筋放在這些東西上。
匆匆又五年,二零一六。七一屆同學香江四十五週年再會,老師興高采烈參加,準備故地重遊,看看廣州西關。不幸,柴灣拜山摔倒。重歸故里,去尋找老家童年回憶的夢成泡影。
老師在醫院,來探望請安的九華各屆同學絡繹不絕。躺在病床,提起精神與學生們聊天,所講多是九華陳年趣事。幾天後出院,七一屆同學邀請他舊地重遊看跑馬,樂了大半天。
那一天,我送老師往機場。他臨別叮囑,好好保重。看着老人坐在輪椅上,機場人員把他推進關卡,我毫無臨別依依之離情。今天交通方便,幾小時就從洛杉磯飛到多倫多了,那來此去關河萬里呢?我想的是下一篇有何題目交給他。
摔倒後老師不再開車。這對一個好動的人,無疑是大打擊。我則覺得這壞事可變好事,多倫多冬天路滑霜濃,老人開車易失控。
近日,我向老師問候,順便告知,正在寫一篇關於他的文章,而且務求寫得正經得體。
「I am doing ok. Waiting for your article. Should be fun to read.」
後記
陳瑞文同學讀了上文之後,有感而發,賦詩兩首,其一置於篇首,其二則如下:
同鄉殊親切,
音聲更難忘。
老來師猶在,
勵策若往常。
二零一七年七月四日.
江紹倫教授序
近五六年,塵噹寫了一系列文章,一鳴驚人。他心聲高唱,寫作風格極盡逍遙。進入電子通訊年代,人人都泡浸在即時對話的汪洋中,無以或息。可幸,優秀的文學始終砥柱中流,根基永固。噹在我們華仁博客的文章,可證明此言不虛。每當有新作刊出,點擊即以百計。好文章就如人的精神食糧,心靈養分。
噹非專業作者,亦非習文出身,他曾受教育於耶蘇會華仁中英書院,粗習中英文字。記得噹最初執筆為文,多方探問請教,至今百篇之後,蔚然成書。
我讀百篇文章過後,喜見題材豐碩,創意澎湃,妙趣橫生,情真意切。他確實不愧是網球好手,球路靈巧刁鑽,例不虛發。令觀者鼓掌叫好不停。
名家寫作,不用筆墨文字,靠的是開放心扉,與眾共享。如今,心理學家都說:情感指導人類行為,遠超智理。在西方,情感被理解為單純的感覺。在中國文化,它涵義更深。漢字的「情」,包含愛戀、感情、同情心、同理心、慈悲、扶助、關懷與關顧。這些都在老子與襌學的睿智中充份表達了。噹的每一篇文章都從心底流露真情。
我舜有不解:噹是從哪攝取到這麼深的中華傳統智慧?想是傳承自他的父母,尤其是他那藝術家的父親。國畫用的是空架透視法,捨目視而以心觀物,可畫四維空間,更超越時空。就是他心中的非凡視野,讓噹觀賞和解構他的多方世界;天地、人物與社羣,在美、中、港、澳各地。
二十世紀的文學,幸得偉大小說家卡夫卡開拓了全新視域。一九二一年,卡夫卡從朋友那裏聽說,他鍾愛的城市家園布拉格引進了攝像機,為它留造永恆的絕美景象。他聽後當即哀嘆,它將從此失去它的內在美。他推動大眾,以詩詞記述和吟頌該城歷史,尤其是它的靈魂精髓。
卡夫卡主張寫情與迷、歌與吟、笑與泣、嘲諷與錄記、挑釁與和諧、往事與願景,一切從心、從知覺、從良知出發。他又主張文學應講些平常的和詭異的、正常的和瘋癲的、幽閉的和風流的事物。我所讀到噹的文章,講述他逃離故土的驚歷、多番回鄉之行見證巨大變遷,以及憧憬着的光明未來。
凡作者寫作之前,不免刨根自問:「我是誰?我將是甚麼樣的人?」這尋根過程,對離鄉別井另建家園的人來說,特別艱辛與痛苦。移民內心來回掙扎著一個難題:究竟向誰效忠才對?曾經歷兩個國家的孕育和對碰的作者在尋根之時,都會格外惶恐,在作品中不時顯露。這患得患失的心情有正反兩面,正的一面使作者更清晰描繪他真正永久的安身立命之地,即以人性為家之鄉。只有把人性的真義表現於胸,才能推動這時代的作者穿透具體物象,着迷於誠摯地還原人性;包含普世價值觀與情懷、願望與圓融、慈悲與共濟,以至宇宙終極中的人的狀況,世代關愛……
噹選擇了蘇軾的詞句為本書命名。偉大詩人幼年在佛教寺院受教育,其後醉心於老莊崇尚自然及體道歸宿之說。我們用心讀噹的文章,必能明白他安身立命的歸宿。
最後,我謹以噹所選用蘇軾《定風波》的末句作結:
歸去
也無風雨也無晴
江紹倫於香港
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編按:
江紹倫教授,出生於香港一九六一年獲加拿大渥太華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專長教育及文化心理學。先後在皇后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斯坦福大學,劍橋大學及多倫多大學從事教學或研究工作,曾以社會開發專家身份服務多國政府及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洲基金,世界銀行等。現任多倫多大學終身榮休教授,世界和平獎頒發委員會審裁理事。出版專著四十五部,發表學術論文二百餘篇。熱心社會服務,所獲榮譽包括:加拿大國家勳章,世界和平獎,耶路撒冷聖十字爵士,英女皇金禧獎,俄羅斯社會科學院院士,國際多元宗教研究院名譽院長及多項榮譽博士。
蘇軾《定風波》: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一蓑煙雨任平生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一蓑煙雨任平生
著名學者江紹倫教授誠意推薦!
作者以本書獻給恩師前九龍華仁書院何鎮源副校長!
五零後「廣州仔」的省、港、洛杉璣三城成長故事,為您娓娓道來。
深情雜憶,包括:我家三代、同學少年、吾土吾民、美國美國、球場春秋、吾友才子……賢妻頌。
早歲飲珠江水長大,南下香江入讀英文中學名校,遠渡太平洋升學,開闖一片新天地、落地生根……
中港台澳海峽兩岸四地年青學子,在新大陸異鄉奮鬥的酸甜苦辣、喜怒哀怒印記……
少小離家、鄉音鄉情不改……
為人子、為人友、為人夫、為人父……的忠實回顧
散文雜文分為:我家三代、同學少年、吾土吾民、美國美國、球場春秋、吾友才子共六章,並以賢妻頌作結。
作者簡介:
陳柏齡,筆名塵噹,祖籍廣東南海仙崗村。少年時就讀廣州三十六中,後進入香港九龍華仁書院中學。畢業於美國加州洛杉磯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畢生從事兩份工作:其一,美國大企業 I.T 行業三十年,最後任職經理。其二,投資美國餐飲彈子房,親力親為。
一生熱愛網球運動。曾奪香港少年網球賽單雙打冠軍。現任洛杉磯蒙特利市華人網球會長,世界華人網球會理事。
退休後愛寫作。六十六年後深情回憶往事。
作者序
何老師(代序)
何師不怒自生威,
鎮日營營正校風。
源源豐盛桃李茂,
師嚴道尊敬心中。
六年前二零一一,九龍華仁書院七一屆香港重聚,我見到了何老師。回家後,老師與同學的影像令我浮想聯翩。近四十年未寫中文了。花了幾天時間,在電腦前敲敲打打,敲出了一篇〈華仁的回憶〉。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把文章送給老師與同學們。
老師囑咐,請繼續寫,支持同學會網站。遂遵師命交功課,從此不斷地寫,永遠支持。
只寫了三篇,老師就問:「噹,你這幾十年在做什麼?」
「老師啊,我這幾十年在做 I.T 工作,也人在江湖。雙管齊下,養妻...
何師不怒自生威,
鎮日營營正校風。
源源豐盛桃李茂,
師嚴道尊敬心中。
六年前二零一一,九龍華仁書院七一屆香港重聚,我見到了何老師。回家後,老師與同學的影像令我浮想聯翩。近四十年未寫中文了。花了幾天時間,在電腦前敲敲打打,敲出了一篇〈華仁的回憶〉。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把文章送給老師與同學們。
老師囑咐,請繼續寫,支持同學會網站。遂遵師命交功課,從此不斷地寫,永遠支持。
只寫了三篇,老師就問:「噹,你這幾十年在做什麼?」
「老師啊,我這幾十年在做 I.T 工作,也人在江湖。雙管齊下,養妻...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目錄
何老師(代序)
江邵倫教授序
第一章 我家三代
母親寫信
浮生六記
兩兄弟
兒子,網球,與我
父親的詩
放生
滑雪
好先生與我
塵噹教仔
Banff──何妨長作班芙人
花旗參煲雞
風城探仔
Father and Son
唱粤曲
大學畢業
July 4th 煙花
老人院
老年游
圓圈論
戒煙
曼谷按摩
領養愛犬
五斗米折腰──小費
第二章 同學少年
舊事如煙話當年
華仁的回憶
南北宗
王宮
四百里弔喪祭德爺
徵婚
世紀之戰最新報導
崢嶸歲月
賭城奮鬥記之一:前輩,進城
賭城奮鬥記之二:工會,工種
賭城奮鬥記之三:苦幹
...
何老師(代序)
江邵倫教授序
第一章 我家三代
母親寫信
浮生六記
兩兄弟
兒子,網球,與我
父親的詩
放生
滑雪
好先生與我
塵噹教仔
Banff──何妨長作班芙人
花旗參煲雞
風城探仔
Father and Son
唱粤曲
大學畢業
July 4th 煙花
老人院
老年游
圓圈論
戒煙
曼谷按摩
領養愛犬
五斗米折腰──小費
第二章 同學少年
舊事如煙話當年
華仁的回憶
南北宗
王宮
四百里弔喪祭德爺
徵婚
世紀之戰最新報導
崢嶸歲月
賭城奮鬥記之一:前輩,進城
賭城奮鬥記之二:工會,工種
賭城奮鬥記之三:苦幹
...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