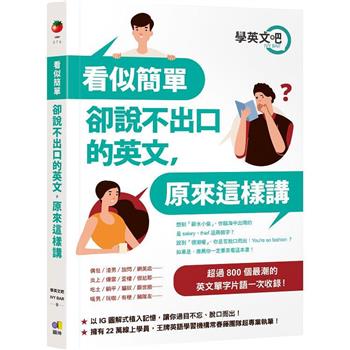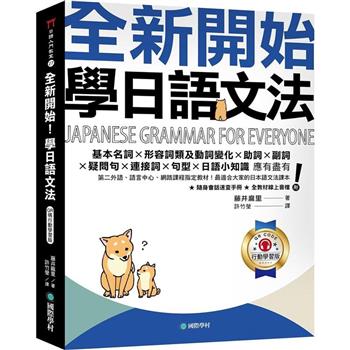三 蔣總司令正告日本各界
蔣總司令為日軍在濟南暴行建議中樞致日本各政黨及名流電
民國十七年五月廿九日發
譚主席並轉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密。日本內閣,自起爭潮,最近形勢,均漸於我有利,派遣代表一節,益宜設法延宕;並擬請用本黨名義致書日本各政黨及頭山滿、犬養毅等各同志,宣布濟案發生以來之情形。茲擬全文如下:「中國國民黨領導之國民革命,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此為一般文明國人民共有之要求。國民革命軍為反對北方軍閥而出兵北伐,更純為中國內政問題,絕非他國所可任意誣蔑、藉辭干涉者也。保護僑民,自有常軌;乘機出兵,已屬叵測;不謂更有如濟案發生以來之強暴舉動,我中日兩國之邦交,東亞和平之前途,將為一、二軍人破壞淨盡,此非僅本黨所痛心疾首,亦必貴黨貴同志等所戚然不安者。濟案發生之直接原因,今尚各執一辭,當有待公正之調查。茲因福田師團長要求先訂軍事協定,故一切調查,無從著手。而我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自北伐以來迭頒嚴令,保護外僑;事變猝起,更竭力制止所部之抵抗及其不採取敵對行動;旋復命令各部隊,遠離濟南;此種事實具在,不能不認為避免衝突解決糾紛之誠意。至國民革命軍到濟南以後對各國僑民之行動如何,當可覆按。
各國記者及貴國各通訊社五月一日、二日之電報,豈以異口同聲推許為紀律嚴明之軍隊;僅一日之隔,盡變面目。然則此不幸之事件,無論因何發生,必有和平解決之方法。乃福田師團長既縱使所部盡情殘殺,捕戮山東交涉員,轟炸無線電台;復於七日下午提出極蠻橫苛刻之五條件,限於即晚十二時以前答覆,其書面又僅寫七日午時,並不註明正午或午前午後幾時;直至當日午後四時方提交趙交涉員,遽於是日夜半即向濟南及其附近之處開始砲擊;雖彼自辯為軍事開始行動之時,未違背其原定十二小時之期限,然衡以國際間最後通牒之慣例,豈得如此?而當時情勢,絕無提出最後通牒之必要,更不待言。蔣總司令兩次派代表前往磋商調停辦法,均被其拒絕談判,且禁止發言。其口頭表示履行條件之辦法,更為嚴酷,如指肇事之原因,應以其片面之調查為根據,我方不得有何異議;其所指應負責任之軍隊,為革命軍之第二軍團陳調元部、第三軍團賀耀組部、第四軍團方振武部,均須於日本軍面前解除武裝。此而猶謂不欲消滅我軍,阻礙北伐,其誰能信?蔣總司令至此,知與福田已無談判解決之希望。且我軍既已不惜忍受北伐軍事上之障礙,實行退出濟南及膠濟路沿線二十里以外,事實上尤無再在前方訂結協定之必要,故呈請政府將此案完全移歸外交解決。
我外交部提議以後,貴政府亦已表示同意。乃福田猶進逼不已,其步哨斥堠既常越出濟南三十里至五十里以外,飛機且時至泰安拋擲炸彈,傷害人民,至今未止;而一面仍要求蔣總司令派遣全權代表前往濟南,簽訂所謂臨時協定;同時並謂若不簽訂軍事協定,則濟南事件將有益加擴大之虞。夫濟案事實已成為外交問題,自有交涉之正軌可循,何為必以強制承諾之協定相迫?且所謂益加擴大者,果將以何種形式擴大之乎?更將擴大至何種程度乎?苟以無道行之,何求不得?我革命軍既已百端忍讓,固始終不出敵對之行動;惟世界公理尚未盡泯,中國人民猶未盡絕,福田師團長之行動,是否為中日兩國睦誼之障礙,貴國國民與各政黨當必有公正之態度,以保持我中日兩國之親善也。
近日貴國政府及海陸軍方面,復有種種之覺書與照會:陸地則不許我軍在天津、北京及東三省敵軍主力所在地點作戰;海上則不許我軍在青島、煙臺、龍口、大沽口、秦皇島、營口各處二十海里以內作戰;其為侵害我國主權,干涉我國內政,既顯然易見;而猶日言對南北兩軍不偏不倚,祇求保護其僑民。試問此等舉動,是否已溢出護僑意義之外?奉軍所屬之渤海艦隊可至廈門等地開砲轟擊;而自山東以至奉天海岸,概不許作戰,即此一端,明明祇許奉軍南侵,不許我軍北伐,謂非袒護奉天軍閥,有意延長中國內亂,更將何說?本黨領導之國民革命,既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為目的,有阻礙此目的者,必以全力反對之;而於我中日兩國之邦交,東亞和平之前途,追念我孫總理希望貴國國民為王道之干城,與夫中日兩國作真正之同存共榮者,輒惓惓不能自己。謹布腹心,唯貴黨貴同志等諒察之。」以上詞意。是否妥洽?敬待公同修正。中意黨與政府立場不同,日本之兩重外交,利在鬼祟秘密,我必須有以破之。今以黨之名義向其國民說話,似無流弊;且彼既起內爭,顯非舉國一致,此書必可引起若干影響。如尚認為未妥,則以中央委員個人名義連署發表亦可。統希公決,惟必以從速發表為宜。蔣中正叩,艷申印。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近代中日關係史料彙編:國民政府北伐後中日直接衝突的圖書 |
 |
近代中日關係史料彙編:國民政府北伐後中日直接衝突 作者: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 出版社: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源流成 出版日期:2020-01-02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70 |
中文書 |
$ 270 |
中國歷史 |
$ 270 |
中國史地總論 |
$ 270 |
中國歷史 |
$ 270 |
社會人文 |
$ 270 |
Social Sciences |
電子書 |
$ 300 |
中國史地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近代中日關係史料彙編:國民政府北伐後中日直接衝突
19 世紀中葉以後,西方勢力進入中國,因國力懸殊,中國頓成列強瓜分角逐場所,不平等條約既是帝國主義勢力的依憑,也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油然而生的根由。廢除不平等條約既是國民革命目標,北伐後爭取國際地位平等是國民政府外交努力的方向,也是中國與列強爭執的焦點。國民政府北伐進行過程中,發生若干涉外事件,本書所輯南京事件(1927-1934)、漢口事件(1927-1931)、日本第一、二次出兵山東(1927-1929)均與日本有關。
本系列蒐羅各方資料,亦對照原始檔案,以增加準確性。
章節試閱
三 蔣總司令正告日本各界
蔣總司令為日軍在濟南暴行建議中樞致日本各政黨及名流電
民國十七年五月廿九日發
譚主席並轉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密。日本內閣,自起爭潮,最近形勢,均漸於我有利,派遣代表一節,益宜設法延宕;並擬請用本黨名義致書日本各政黨及頭山滿、犬養毅等各同志,宣布濟案發生以來之情形。茲擬全文如下:「中國國民黨領導之國民革命,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此為一般文明國人民共有之要求。國民革命軍為反對北方軍閥而出兵北伐,更純為中國內政問題,絕非他國所可任意誣蔑、藉辭干涉者也。保護僑民,自有常軌;乘機...
蔣總司令為日軍在濟南暴行建議中樞致日本各政黨及名流電
民國十七年五月廿九日發
譚主席並轉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密。日本內閣,自起爭潮,最近形勢,均漸於我有利,派遣代表一節,益宜設法延宕;並擬請用本黨名義致書日本各政黨及頭山滿、犬養毅等各同志,宣布濟案發生以來之情形。茲擬全文如下:「中國國民黨領導之國民革命,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此為一般文明國人民共有之要求。國民革命軍為反對北方軍閥而出兵北伐,更純為中國內政問題,絕非他國所可任意誣蔑、藉辭干涉者也。保護僑民,自有常軌;乘機...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總序
編輯凡例
第一章 南京事件
第二章 漢口事件
第三章 日本第一次出兵山東
第四章 日本第二次出兵山東
編輯凡例
第一章 南京事件
第二章 漢口事件
第三章 日本第一次出兵山東
第四章 日本第二次出兵山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