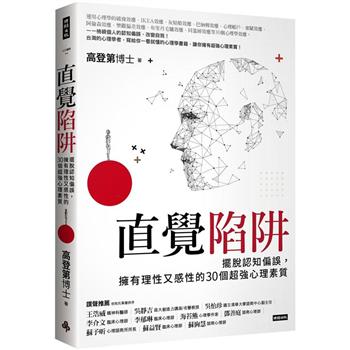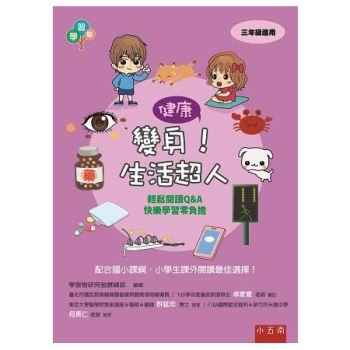序
張岱(1597 — 1689),字宗子、石公,號陶庵、蝶庵,浙江山陰(今浙江紹興)人。
他為人們所熟知,首先是因為他的山水美文,《西湖夢尋》《陶庵夢憶》等著,格調高古,境界敻絕,而文筆清新婉麗,時露胸次灑落氣象。現代以來,周作人、施蟄存等皆對其推崇備至,黃裳則稱其為「絕代的散文家」。
但張岱不只是一位「絕代的散文家」,還是一位著名的史學家。他有大量的史學著作,如《古今義烈傳》《史闕》《石匱書》《石匱書後集》等。尤其是《石匱書》與《石匱書後集》,其「事必求真,語必務確」,以至於「五易其稿,九正其訛」,為有明一代存其信實可靠之史,實與談遷《國榷》、萬斯同《明史稿》同光於史林。然張岱又不只是一位著名的史學家,其《四書遇》之著,又使之躋身於思想家之列。
《四書遇》原為未刊抄稿本,初藏於江蘇常熟周氏鴿峰草堂,浙江圖書館於1934 年購得此本,將其列為甲級特藏稿本。
《四書遇》是張岱對四書的解釋。書之所以名為「遇」,張岱說:「蓋遇之云云者,謂不於其家,不於其寓,直於途次之中邂逅遇之也。」語雖寥寥,而其用心之勤苦已然深蘊於其中。因此所謂「遇」者,正是張岱獨特的經典解釋方式。
在《四書遇序》中,張岱又大略說了其「遇」的基本手段:「間有不能強解者,無意無義,貯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讀他書,或聽人議論,或見山川雲物、鳥獸蟲魚,觸目驚心,忽於此書有悟,取而出之,名曰《四書遇》。」
然則所謂「遇」者,悟也,非搜求於各家注疏、牙籤滿屋,而悟之於山川雲物、鳶飛魚躍之當下生命,而遇之於道阻水長、流離顛沛之倉皇困頓之間者也。故《四書遇》之撰著,前後歷時四十年,亦可謂傾其全付精神,而為其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之獨立人格的文字見證。雖當明清易代「天崩地解」之時,作者播遷於亂離,蹎蹶於道途,而猶妥為珍藏:「余遭離亂兩載,東奔西走,身無長物,委棄無餘。獨於此書,收之篋底,不遺隻字。」足見張岱對這一作品的特為重視。
雖說張岱之所「遇」乃其獨特心得,但並不是說他只是獨運孤明。恰恰相反,《四書遇》的文獻徵引極為廣博,據朱宏達先生統計,書中引文所涉人物有二百六十七人之多。許多不見於其他史料的人物,藉《四書遇》而得以留存其思想之吉光片羽。然則《四書遇》又匯存了大量的中晚明思想史料,豈不彌足珍貴!
雖說「不讀朱注」,但就《四書遇》的內容來看,張岱對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實諳熟於心,書中多明引或暗引朱熹之說,或贊同,或批判,在與朱注的對話中出以己意,自出手眼,不落窠臼。
張岱自謂「凡學問最怕拘板。必有活動自得處,方能上達」。故凡書中所論,無非其「活動自得」之處,是其獨特心得。然必有博學審問,方能獨得機杼;必有明辨篤行,方能獨有心得;必有別出心裁,方顯知識專精。
《四書遇》對於四書的解釋,深受陽明心學的影響。張岱有深厚的家學淵源。其曾祖張元忭(1538 — 1588)為隆慶五年(1571)進士第一,從學於王陽明大弟子王畿,是「浙中王門」的重要人物之一。其祖父張汝霖(1561 — 1625)繼承張元忭的心學取向,對張岱的思想格調與治學方法影響最巨。
張岱之基於陽明心學視域來解讀四書,正與其家學淵源及其時代風氣精神相接。因此《四書遇》所呈現出來的基本面貌,無論其思想意趣、解釋路向,還是其語言風格、解釋形式,均與朱熹的《四書集注》迥然有異。其最為突出者,是融入佛道二家之說,甚至認為「孔子、佛氏之言相為表裏」。馬一浮先生曾說:「明人說經,大似禪家舉公案,張宗子亦同此血脈」,然「卷中時有雋語,雖未必得旨,亦自可喜,勝於碎義逃難、味同嚼蠟者遠矣」。
張岱博洽通才,學問淹貫,而《四書遇》內涵宏富,徵引廣博,解釋方式靈活,可謂氣象萬千。書中時見珠璣,然因時代不同,閱讀習慣有異,今人讀來,或頗見扞格。為使《四書遇》合於今人閱讀,以領會其思想,在語言形式上予以「現代轉換」,實為勢在必行,此則本套叢書之所以著也。
《四書遇》原書不錄四書原文,編著者又據《四書集注》配上原文,亦予語譯。本套書編著者之一馮寧寧博士是我的學生,碩士、博士皆隨我學習,在前後五年的時間裏,始終表現出對於中國哲學的專業興趣,踏實勤奮,好學深思,而又懷抱「君子三畏」之心態,治學嚴謹。她的主要研究領域為陽明學及陽明後學,博士論文即以《四書遇》為主要研究對象,因此,本套書的《論語》部分由她來主筆,甚為恰當。我相信,她的語譯不會對張岱原文有太多偏移。
隨着本書的出版,張岱將為更多人所熟知,其獨特的四書解釋維度將在現代語境之下為人們帶來新的心靈啟迪,而為今日傳統文化之繁榮更添新彩,是則可跂而望者也。
本書付梓之際,承馮寧寧之請,爰弁數語於卷端。是為序。
董平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日於浙江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當才子遇上論語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444 |
經史子集 |
$ 603 |
中文書 |
$ 603 |
中國哲學 |
$ 603 |
哲學 |
$ 603 |
社會人文 |
$ 603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當才子遇上論語
《四書》作為儒家根本經典,是記載聖賢思想的重要經典。明朝才子張岱的《四書遇》作爲一本語錄體的讀經著作,以別開生面‚將心比心的解經思路,凸顯作者重視「情理」的修學工夫,糾正了壟斷《四書》解釋權威的朱熹官學混淆「情理」與「物理」的偏失,是一部極其難得的以會通心學的活潑態度來解讀四書的作品。從體例上,本叢書借用現代人常用的微信對話的形式,使張岱與他的古今朋友組成了一個「四書討論群」,就四書的一段甚至一句話進行探討,妙語連珠,使現代人也能從淺顯的譯讀中會心會意。
作者簡介:
作者
張岱字宗子,又字石公,號陶庵,別號蝶庵居士,山陰(今浙江紹興)人。作為公認成就最高的明代散文學家,他的《湖心亭看雪》被收入內地人教版中學語文課本八年級上冊,思想和作品引起越來越多的讀者關注。雖然黃裳稱他為「天下無與抗手」的散文第一名家,但他的創作成就並非「散文家」所能概括,著述涉及經史子集各部。
作者序
序
張岱(1597 — 1689),字宗子、石公,號陶庵、蝶庵,浙江山陰(今浙江紹興)人。
他為人們所熟知,首先是因為他的山水美文,《西湖夢尋》《陶庵夢憶》等著,格調高古,境界敻絕,而文筆清新婉麗,時露胸次灑落氣象。現代以來,周作人、施蟄存等皆對其推崇備至,黃裳則稱其為「絕代的散文家」。
但張岱不只是一位「絕代的散文家」,還是一位著名的史學家。他有大量的史學著作,如《古今義烈傳》《史闕》《石匱書》《石匱書後集》等。尤其是《石匱書》與《石匱書後集》,其「事必求真,語必務確」,以至於「五易其稿,九正其訛」,為...
張岱(1597 — 1689),字宗子、石公,號陶庵、蝶庵,浙江山陰(今浙江紹興)人。
他為人們所熟知,首先是因為他的山水美文,《西湖夢尋》《陶庵夢憶》等著,格調高古,境界敻絕,而文筆清新婉麗,時露胸次灑落氣象。現代以來,周作人、施蟄存等皆對其推崇備至,黃裳則稱其為「絕代的散文家」。
但張岱不只是一位「絕代的散文家」,還是一位著名的史學家。他有大量的史學著作,如《古今義烈傳》《史闕》《石匱書》《石匱書後集》等。尤其是《石匱書》與《石匱書後集》,其「事必求真,語必務確」,以至於「五易其稿,九正其訛」,為...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
張岱《四書遇》自序
學而第一
為政第二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公冶長第五
雍也第六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子罕第九
鄉黨第十
先進第十一
顏淵第十二
子路第十三
憲問第十四
衞靈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陽貨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子張第十九
堯曰第二十
張岱《四書遇》自序
學而第一
為政第二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公冶長第五
雍也第六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子罕第九
鄉黨第十
先進第十一
顏淵第十二
子路第十三
憲問第十四
衞靈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陽貨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子張第十九
堯曰第二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