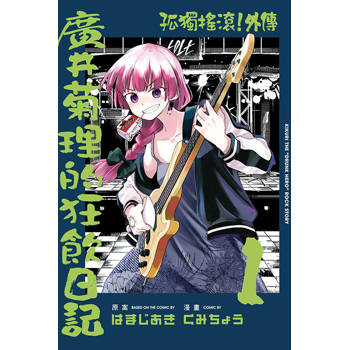序螳臂錄朱少璋
一
司空圖〈歌者〉其六有「胸中免被風波撓,肯為螳螂動殺機」之句,「殺機」典故,與蔡邕有關。話說演奏者在彈琴時看見螳螂捕蟬,蟬將去未去之間,螳螂一前一卻之際,演奏者看得入神,分了心,居然代入了螳螂的處境:「恐螳螂之失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隔壁的蔡邕耳朵特別靈敏,居然聽得出琴音中的點點殺機。
「螳螂」二字疊韻,都屬「七陽」,唸起來特別動聽;螳螂外形也優美,前臂如鐮似斧,有點殺氣又帶點裝腔作勢,一雙螳臂總能引人注目。若從修辭的「借代」角度看——以局部代全部——螳臂肯定是典型的例子。螳臂之於螳螂,是帆之於船,巾幗之於女子,鬚眉之於男士,朱門之於富貴;總令人印象深刻。螳螂的一雙前肢其實是由股節及脛節組成的「前足」,說「螳臂」多少帶點擬人的聯想。螳臂可以捕蟬,原來也可以捕蛇。《聊齋誌異》卷五有一則「螳螂捕蛇」,事甚離奇:
張姓者偶行溪谷,聞崖上有聲甚厲。尋途登覘,見巨蛇圍如碗,擺撲叢樹中,以尾擊柳,柳枝崩折。反側傾跌之狀,似有物捉制之,然審視殊無所見,大疑。漸近臨之,則一螳螂據頂上,以刺刀攫其首,攧不可去,久之,蛇竟死。視額上革肉,已破裂云。
聊齋先生姑妄言之我等讀者姑妄讀之,可惜先生沒有在這則奇譚之後補寫一段「異史氏曰」。世人總謂螳臂力量有限,捕蟬有餘,鬥蛇顯然不自量力,但《聊齋》所誌,畢竟奇異,故事中的小螳螂,以臂刀攻擊蛇首要害,蛇既無法反噬,又不能掙脫,最終裂首而死。我初讀這段故事,即覺心潮澎湃,向來以小勝大以弱勝強的情節,在精神上鋤強扶弱,分外令人讀得痛快。蘇舜欽讀《漢書》至「誤中副車」及「君臣相與」,各浮一大白;今讀《聊齋》「螳螂捕蛇」,亦可浮一大白。下酒文章,相信不以《漢書》專美。
螳螂捕蛇的故事是真也好是假也好,起碼可以作為勢弱者精神上的慰藉。像愚公移山,像鐵杵磨針,讀者明知虛構但這些故事卻世世代代支持着不少善良的人加倍努力地去做一個有毅力的傻人,哪怕一輩子都移不了山磨不成針,花盡力氣抬頭青山依舊鐵杵如椽,有些人,還是堅持行不繞路針不現買;類似的堅持,我們有時稱之為「信念」。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說到底也許只是不自量力自討沒趣。讀《莊子‧人間世》一段,令人氣短: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夫螳螂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顧非敵耳。今知之所無奈何而欲強當其任,即螳螂之怒臂也。
顏闔要當衞靈公太子的老師,臨行前蘧伯玉借螳臂當車跟他講知所進退的道理。人生,到底應該知難而退,還是知難而進?同樣講螳臂當車的故事,讀《淮南子》一段,相信可以下酒:
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謂螳螂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
螳螂擋路,司機是決定輾過去還是「迴車而避之」?螳螂是愚是勇,該死不該死,原來也視乎開車的是誰。
二
「螳螂」也是昆蟲分類上的一個「目」,「螳螂目」(Mantode)之下的成員都通稱「螳螂」。我始終覺得,「作家」都應該是「螳螂目」的成員。作家,到底應該知難而退,還是知難而進?作家寫文章時枕腕、提腕或懸腕,像擋在大車前的螳臂,既不自量力亦滿有勇氣,或傻勁;雖千萬人,吾往矣。是不自量力嗎?可能是;是於事無補嗎?可能是;是功不唐捐嗎?也可能是。
二○一八年與人合編散文集,糊裏糊塗居然決定以「香港人」為組稿的總主題,終於得到二十七位香港作家支持供稿。成書前對書名多番斟酌,本擬用「亮相」,但最終又是糊裏糊塗地,居然決定以「香港.人」為書名,那一點間隔號既是營造美感的應有距離也是點睛之筆。劉偉成支持,供稿寫梅艷芳寫得實實在在,我讀了印象深刻。文章重輯在他最新出版的個人散文集中,足證此文素質既高亦有代表性。
偉成既寫詩又寫散文,散文集《持花的小孩》與詩集《陽光棧道有多寬》都獲獎,植物、人物、街巷,種種見聞與感受左右逢源,入詩入文。偉成自一九九七年出版首部詩集,廿多年來還在努力創作,詩歌與散文交替成書,移山磨針的信心毅力,都具備。寫於二○一四年的詩句——「帶走胡椒莽撞的辛辣」、「口罩可拓印出張眼微笑」——道路與廣場的開合與翕辟,是車輪前小螳螂的仰視角度。偉成也有螳螂擋車的勇氣。
二○一八年七月新書《香港.人》在香港書展首發,出版社安排幾位供稿作家主持講座。偉成幫忙主講一個環節,我當司儀在開場前先跑跑龍套,一時感觸笑說「香港人」這個詞語很快就會湮沒,代之而起將會是「大灣人」。事隔不到一年,呼喊「香港人」之聲在城中此起彼落,默契是在後面用力地加喊一句「加油」。不知這會否是「香港人」在消失前的迴光反照,卻只知道大家都努力地喊,語氣堅定,而且自信。遊行期間有食店贈飲贈食,飲品和乾糧堆放在店外,免費任取,上插紙牌寫着「香港人加油」,令我想起十九首的名句「努力加餐飯」,五字短句後連用三枚粗體感歎號都不覺誇張。像這樣的贈食舉措,都尋常而又不尋常:人心與世道,總會正比或反比地相互襯托,或反諷,或互補,或搭配,或拼砌。
「加油」這個詞,我是在《青春火花》中首次聽到的。七十年代日劇《青春火花》的女排隊員常大喊「加油」,偉成年輕可能印象模糊,那是中譯對白的經典語例。年紀大了我漸漸傾向說「努力」,含蓄些,上世紀青春的幾星火花,畢竟易逝。長大後,我有好長的一段日子沒有用「加油」這個詞。尤其在我當上了老師之後,總覺得這個用語活潑有餘得體不足,因此我給學生的鼓勵,大都改用「努力」。卻原來「加油」已慢慢滲入了英語世界,還居然出現了港式英文用語「Add oil」,連二○一八年英國牛津大學英語詞典也收錄了這個詞。如此一來,「加油」這個詞一時間登堂入室,變得「正式」起來。打從二○一九年六月開始,「香港人」和「加油」屢屢連結在一起:直幡橫額單張海報都用,見慣了;男女老幼前線後援都喊,聽慣了。
事實上,這幾年我也常常對偉成說「加油」。二○一八年他應邀到愛荷華交流我跟他說「加油」;回港後繼續創作我跟他說「加油」;在工餘繼續博士研究我跟他說「加油」——二○一九年偉成終於完成博士論文取得學位,我滿心歡喜答應穿禮袍出席他的畢業禮,見證他學術上的成就。當年博士畢業師長建議我自置一套禮袍,說在大學教書典禮多總用得着。但自置的禮袍十多年來卻只穿過兩次,一次是出席自己的畢業禮,另一次是出席阮佩儀博士的畢業禮。本來可以為偉成再穿一次,但碰上己亥風潮社會氣氛異常緊張,大學取消所有活動,包括畢業典禮。早已熨得挺直的禮袍最終給摺疊再裝箱,像心情一樣,打疊好,再置諸高閣。
三
偉成散文多長篇,佈局與經營都認真,難得以詩人身份兼寫散文卻堅持不乞靈於詩歌的意境,散文一字一句都絕不詩化地含糊。散文集《影之忘返》觸及繪本、香港、旅遊、回憶、評論,底氣來自「博讀」與「博覽」,筆下題材要多「散」有多「散」。「繪本守夢人」或多或少是作者個人的「重像」或「疊影」。「清倫的盪漾」圖片不少,旅程亦長,〈啊!好一位富士行僧〉由日本人「凡事往小裏縮」的民族性說到「不知不覺間,縮小的自我,真的還原成一顆因自然美景而充滿確幸感覺的心,不亢不卑地綻放出『中台八葉院』的蓮花,將閉固的結界無限推遠」,這點感悟是偉成人生境界的另一「合目」。「渡渡鳥歲月」逮得住回憶的尾巴,許多人、事、物、情,都跟渡渡鳥一樣,漸次絕跡:〈消失中的文具〉會否漸次變成「消失中的文字」、「消失中的文章」、「消失中的文學」、「消失中的文化」甚或「消失中的文明」?「從城堡出發」有分析宮崎駿動畫的長文,宮崎駿拒絕為籌辦東京奧運製作影片,是拿着畫筆的螳臂抵住了借申辦奧運以粉飾太平的大車。「香港這種人」寫梅艷芳、張國榮、小思、鍾玲、陶然及麥華嵩的文章我讀得格外有共鳴。西西的文學世界慚愧我是至今都無法進入,偉成的〈候鳥織巢寄春望〉談西西談得好廣好博我讀了還是無動於衷,反而他說「童言敘事,不同於『童言』本身」令我印象最深刻。
擋在駛往「遺忘」的大車前,偉成用力地揮動着螳臂,手不停書,用筆,或虛晃或實寫;縱然那輛駛往「遺忘」的大車已經駛過了好一段時間。回憶的零片又多又細碎,正如偉成在〈姆明屋與喬屋〉提到日本雜誌分期附送姆明屋模型的部件:「不知要多少期才能拼出完整的一幢。」文字向來與螳臂一樣,都脆弱,但千百年來文學史所記載的,泰半都是螳臂當車或以卵擊石的歷史,在血肉與蛋漿的黏稠與模糊中,永垂不朽。文字有靈或無靈,未必就決定在大車輾過的一刻,而是在大車輾過後的一段很長的時間,文字經歲月的醖釀與磨洗,才慢慢煥發出其應有的光彩與感召力,像〈流動到燈火明淨的記憶〉:
我不禁想起那道滿佈傘圓的街道,就像是雨落在長河上泛起的漣漪。在天橋的制高點上,前後俯視燈火通明的長街,我清楚知道「我城」還像畫卷一樣流動着,或者該說給「牽動」着,只是即使我自詡頗具編輯眼光,善於將流動光影看成停駐不動,也不知道究竟該回望一九九七年「急於回家」的心情,還是自囿於二○四七年的「大限想像」中。
偉成,始終還是擋在大車前的螳螂。螳臂收起置於胸前,有人說是擋車也有人說是禱告:英語螳螂praying mantis 就帶有「祈禱」的屬靈聯想。讀偉成的文章倒真的讓我依稀想起Jean Baptiste Camille Corot 畫筆下靠在大石旁禱告的Madeleine。何妨讓「香港的冬季已漸漸消隱,連春天的氣息也漸漸遠去,街上的店鋪彷彿從不打烊,全年無休,彷彿這裏只剩下不懂言倦的齒輪在互相推動,甚至沒閒分神去留意傷痛,停下來自我療癒」(〈浪盪在街燈的灑滌中〉)跳接到「當你放下偏見,心眼自然會明亮起來,會看見許多遺忘的記憶斷片漂浮在時間的涓流上」(〈帶着偏見,旅行到安徒生跟前〉),自成段落。
螳螂不自量力賈其餘勇舉起雙臂原來要為路過的大車禱告——這層深意,恐怕連蘧伯玉齊莊公都不曾明白。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影之忘返(灰綠色封面)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影之忘返(灰綠色封面)
本書共有兩款封面(灰綠色、藍色)
「忘返」一詞,暗示遇上樂事、不忍離去;「回家」則代表歷險完畢、功德圓滿,是令人拒絕忘返的理由。
在安徒生的〈影子〉裏,影子離開主人,在詩神處看盡世間的絢爛,起初樂而忘返,最終選擇回歸。這本散文集的各輯文章,也可說是作者從出走到忘返到回歸的軌跡紀錄——有源於繪本的感悟,有外地旅遊的文化觀察,有童年點滴的記錄,有文藝作品的解讀,也有現實中遇到的人的故事。這些見聞、故事、記憶、夢想,都是生命中閃亮的碎片,也是讓作者拒絕忘返、決定回歸的情感的錨。
作者的文字時而雋永優美,時而冷靜銳利,既審視過去,亦思考未來。他以詩化的筆觸記錄生活中所思所感,滿載感情;探討繪本及動畫等題材,思辨性強,能引起讀者思考。敘寫人、事、物、情,都在在反映其獨特的視野、深廣的學養與真誠的反思。
作者簡介:
劉偉成,香港土生土長,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哲學博士,從事統籌出版事務工作,又於本地大學兼職教授寫作、編輯與出版相關課程。二○一七年獲邀赴美參加愛荷華大學的國際作家工作坊。曾出版散文集《持花的小孩》(獲第十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散文組推薦獎)、《翅膀的鈍角》,詩集《瓦當背後》、《陽光棧道有多寬》(獲第十三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詩組首獎)、《果實微温》。
作者序
序螳臂錄朱少璋
一
司空圖〈歌者〉其六有「胸中免被風波撓,肯為螳螂動殺機」之句,「殺機」典故,與蔡邕有關。話說演奏者在彈琴時看見螳螂捕蟬,蟬將去未去之間,螳螂一前一卻之際,演奏者看得入神,分了心,居然代入了螳螂的處境:「恐螳螂之失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隔壁的蔡邕耳朵特別靈敏,居然聽得出琴音中的點點殺機。
「螳螂」二字疊韻,都屬「七陽」,唸起來特別動聽;螳螂外形也優美,前臂如鐮似斧,有點殺氣又帶點裝腔作勢,一雙螳臂總能引人注目。若從修辭的「借代」角度看——以局部代全部——螳臂肯定是典型的例子...
一
司空圖〈歌者〉其六有「胸中免被風波撓,肯為螳螂動殺機」之句,「殺機」典故,與蔡邕有關。話說演奏者在彈琴時看見螳螂捕蟬,蟬將去未去之間,螳螂一前一卻之際,演奏者看得入神,分了心,居然代入了螳螂的處境:「恐螳螂之失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隔壁的蔡邕耳朵特別靈敏,居然聽得出琴音中的點點殺機。
「螳螂」二字疊韻,都屬「七陽」,唸起來特別動聽;螳螂外形也優美,前臂如鐮似斧,有點殺氣又帶點裝腔作勢,一雙螳臂總能引人注目。若從修辭的「借代」角度看——以局部代全部——螳臂肯定是典型的例子...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螳臂錄朱少璋
自序 拒絕忘返的理由
一 繪本守夢人
失去影子的人
從繪本轉出來的人
守夢人——觀梵谷《星夜》真跡
二 清倫的盪漾
姆明屋與喬屋
咖啡館的清倫
浪盪在街燈的灑滌中
帶着偏見,旅行到安徒生跟前
挽救傳統的華麗補丁——日本「人孔蓋」考察
海鷗銜索回眸間——從《海鷗食堂》看芬蘭的「希甦力」
零至一——一張從愛荷華寄回家的明信片
浪花點化的涯岸——我於愛荷華完成的三首「日蝕詩」
出走,尋找善喻
駱駝男
啊,好一位富士行僧
那一夜,我住在百貨店的閣樓
三 渡渡鳥歲月
錄音帶磁碟機
歲月的童話
消失中的文具
蛇吞象擺...
自序 拒絕忘返的理由
一 繪本守夢人
失去影子的人
從繪本轉出來的人
守夢人——觀梵谷《星夜》真跡
二 清倫的盪漾
姆明屋與喬屋
咖啡館的清倫
浪盪在街燈的灑滌中
帶着偏見,旅行到安徒生跟前
挽救傳統的華麗補丁——日本「人孔蓋」考察
海鷗銜索回眸間——從《海鷗食堂》看芬蘭的「希甦力」
零至一——一張從愛荷華寄回家的明信片
浪花點化的涯岸——我於愛荷華完成的三首「日蝕詩」
出走,尋找善喻
駱駝男
啊,好一位富士行僧
那一夜,我住在百貨店的閣樓
三 渡渡鳥歲月
錄音帶磁碟機
歲月的童話
消失中的文具
蛇吞象擺...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