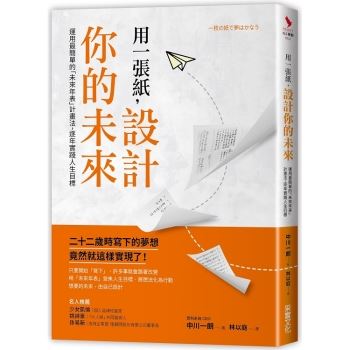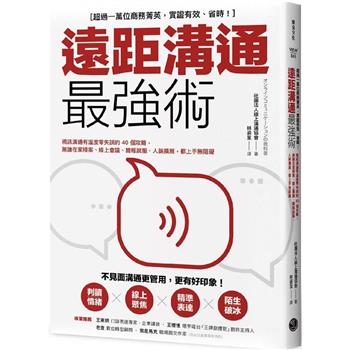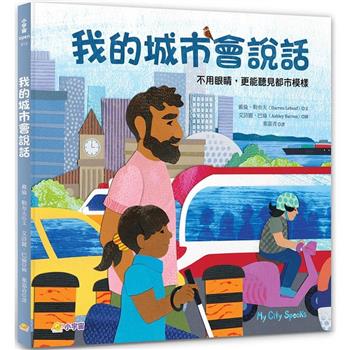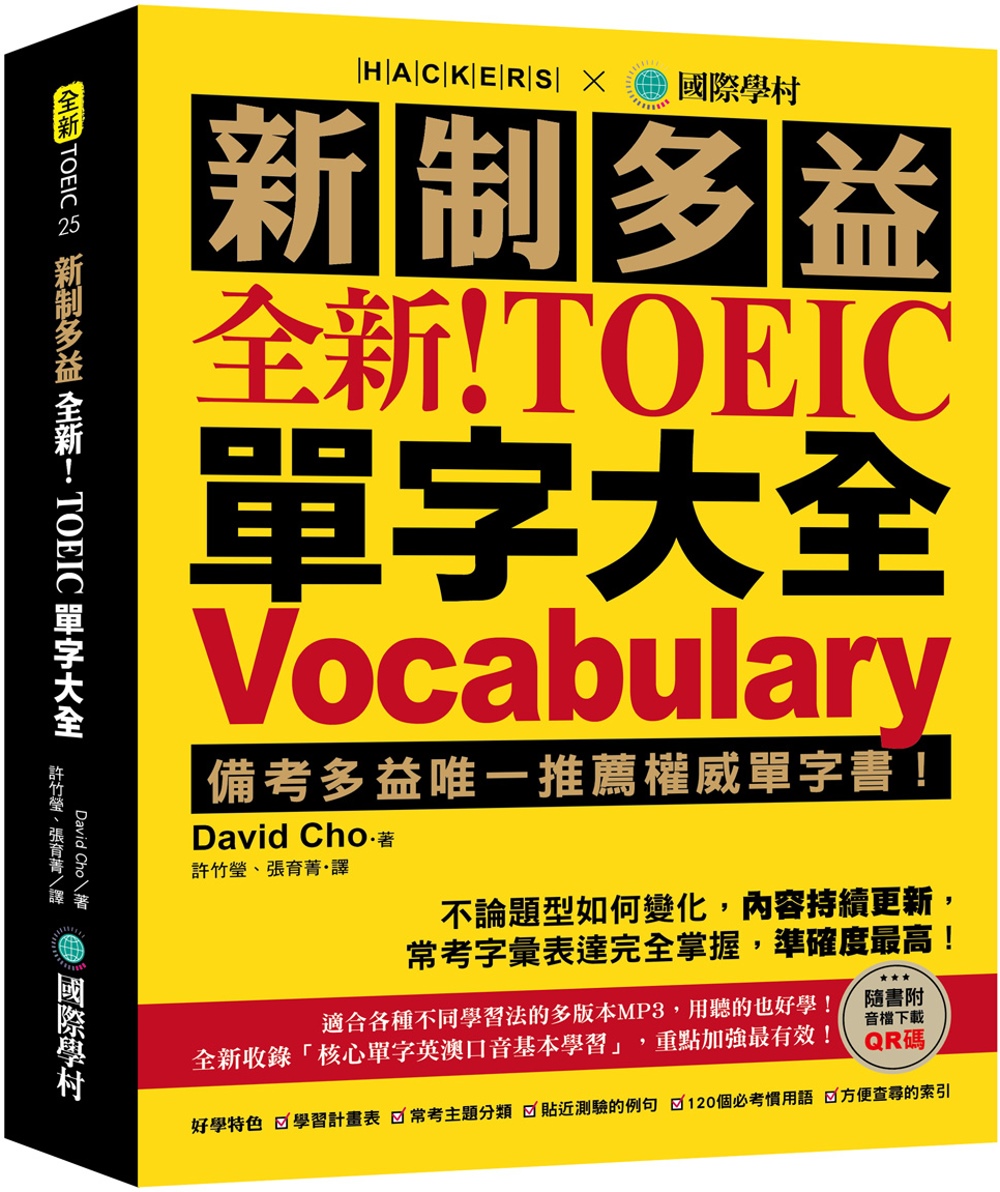迄今為止,在大學裏教授小說創作已逾十年。
每於首堂課,我會引用韓少功先生在一次演講中的發言。他說:寫作是不可教的。
由是而觀,文學寫作是一種很難被量化傳授的技藝。確乎如此,我們常說「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同樣,文學作為藝術的一種,並非以精準取勝的門類。其沒有明確的成功座標與準繩,更多依賴於閱讀者的感受與判斷。當我們評論一部文學作品的時候,我們不可能對其文本進行單純的技術考量。如若不然,只會導致後學者對經典作品的學習,陷入類似模仿的境地。將注意力聚焦於作品的類型化特點,模仿者隨之失去了更為寶貴的東西,即作為藝術主體的個性,使其此後創作流於「匠氣」。而「匠氣」,也是保持藝術生命獨特性的大忌。齊白石說「學我者生,似我者死」,足見真正可學的,應是藝術的感覺與靈韻。
但技術仍是重要的,這是我們成為好的寫作者的前提,而不是全部。在此前提之上,實現對文字的駕馭能力,達至一種寫作的自由,才是我們應關注的重點。
獲得這種自由並不容易,首先需明確寫作這種行為對於作者的意義。卡夫卡(Franz Kafka)曾將寫作喻作「紙牢」,可見其作為雙刃劍的性質:一方面,作品是作者存在的唯一證據;因為有了寫作的行為,才有了後者的身份;另一方面,他亦將寫作的桌子比作巨盜普洛克路斯忒斯(Procrustes)的鐵床,因其必受扭曲與拉伸之苦。這一比喻其實表現了寫作者的基本困境,必須依靠寫作來證明存在,但寫作的過程似乎也正在對現實世界進行扭曲。
我們都聽過一句話,叫「戴着腳鐐跳舞」,更早是由美國文學評論家布里斯.佩里(Bliss Perry)教授提出。而我們更為熟悉的,是聞一多在闡發新詩的一篇文章〈詩的格律〉中所談及「樂意戴着腳鐐跳舞」,表示願去接受藝術格律的束縛。當我們將一切關於技術的元素統稱為「格律」,我們會發現,實際上「格律」才是真正達到自由的基礎。語言文字有一種內在的規律,使得我們對文學乃至小說的審美觸類旁通、舉一反三。在這種通與變的過程中,我們也逐漸樹立起了自己的觀念。當然,這一切都需要一個基石,即要有足夠的藝術自覺與警覺。
而我們所說寫作的能力,也必然指向通過技巧達到一種更自由的境界。這涉乎小說這種文體的獨特,事實上,在各種文體中,小說的確是一種更為趨向自由的文體。昆德拉說:「小說的歷史是不存在的(統一持續的演進)。只有小說的諸史:中國小說的、希臘─羅馬的、日本的、中世紀的。」這是從橫向的角度梳理,世界範圍內小說的來源紛呈。而回到縱向一脈,中國小說昔稱「稗說」,更是隱含的無盡的開放姿態。所以,就這種文體進行全方位的歸納與解讀,在相對較短的週期內,或許難盡其意。而就其可行性而言,對技術元素的提取,更有助於尋找這種文體內在的規律。因此我曾在課程中設「開首、人物、情節、主題、敘事角度、情境、腔調、懸念」等一系列專題。並開列相關中外短篇小說名作,作為樣本,在課堂上和學生進行剖析與講解。但我始終感到遺憾的是,因為課程時間有限,難以就某些作家的文學經典之作,與學生在內容意蘊、審美意趣乃至更為微妙的人物及時代之互動關聯的角度,作出鉅細靡遺的闡發。
我想,這本《筆下——文學經典的六個專題》,從某種意義上彌補了這種遺憾。因為它帶來了相對廣闊的空間,就我經年精讀的文學佳作進行更為深入而全面的論析,且致力於通過解讀,挖掘其在某一主題上的共性,並釐清其相異的表現手法,在各自的創作語境中所展示的紛呈的可能性。如「第一章作家們的少年敘事」,我選取了塞林格、麥克尤恩、莫迪亞諾、奈保爾和太宰治五位小說家的代表作。少年時期大約是作家創作歷程中永遠的心理原鄉,換言之,可視為其對應於寫作人格的文字鏡像。以此主題為切片,可管窺作家的整體創作軌跡,也可對其敘述方式、美學品性乃至文字風格作出相應的認識。因應於各自的成長,所處的歷史斷代與社會環境,甚至地域與民俗背景,幾位小說家對「少年」意象各自作出了獨具一格的文學詮釋。諸章如是,在此不一一贅述。而深入文本,對其作出與之相關的剖析,也正是此書致力的重心。
最後,感謝我的出版方中華書局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得以與我的讀者就心目中的文學經典進行恰如其分的分享與交流。閱讀永遠是美好的事情。及至今日,我們仍要向這些作家致敬,因他們筆下有光,照亮前路。
寫於庚子年夏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筆下:文學經典的六個專題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32 |
華文文學研究 |
$ 276 |
中文書 |
$ 276 |
華文文學研究 |
$ 277 |
Literature & Fiction |
$ 308 |
Books |
$ 315 |
華文文學研究 |
$ 315 |
文學作品 |
$ 315 |
世界文學論集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筆下:文學經典的六個專題
《筆下》是葛亮博士長期研究、寫作與教學的專業經驗結晶。
在書中,作者深入而透徹地論析文學經典之作,涉獵J.D.塞林格、伊恩‧麥克尤恩、帕特里克‧莫迪亞諾、石黑一雄、太宰治、白先勇、黃碧雲等中外名家;全書以主題設章,同中釋異,捭闔古今,在文學評論著作中可謂匠心獨具。藉由作者解讀,可一窺方家創作軌跡,並對其作品文字風格、內容意蘊、審美意趣等有豐瞻而全面的認識;亦從文學創作導引之角度,令讀者在題材選取、遣詞用句、敘述手法等層面皆有所獲益,進而由好讀者邁向好作者之境。
作者簡介:
葛亮,香港大學中文系博士,現任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創意寫作、文學與電影藝術等。
作品出版於兩岸三地,著有學術專著《此心安處亦吾鄉》、《清風有信月無邊》、《繁華落盡見真淳》;小說《北鳶》、《朱雀》、《七聲》、《戲年》、《謎鴉》、《浣熊》、《問米》,文化隨筆《紙上》、《繪色》等。部分著作譯為英、法、意、俄、日、韓等國文字。
曾獲香港浸會大學「傑出青年研究學者」獎、香港藝術發展獎、首屆香港書獎、台灣聯合文學小說獎首獎等獎項。長篇小說《北鳶》、《朱雀》兩度獲選「亞洲週刊華文十大小說」。
作者序
迄今為止,在大學裏教授小說創作已逾十年。
每於首堂課,我會引用韓少功先生在一次演講中的發言。他說:寫作是不可教的。
由是而觀,文學寫作是一種很難被量化傳授的技藝。確乎如此,我們常說「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同樣,文學作為藝術的一種,並非以精準取勝的門類。其沒有明確的成功座標與準繩,更多依賴於閱讀者的感受與判斷。當我們評論一部文學作品的時候,我們不可能對其文本進行單純的技術考量。如若不然,只會導致後學者對經典作品的學習,陷入類似模仿的境地。將注意力聚焦於作品的類型化特點,模仿者隨之失去了更為寶貴的東西...
每於首堂課,我會引用韓少功先生在一次演講中的發言。他說:寫作是不可教的。
由是而觀,文學寫作是一種很難被量化傳授的技藝。確乎如此,我們常說「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同樣,文學作為藝術的一種,並非以精準取勝的門類。其沒有明確的成功座標與準繩,更多依賴於閱讀者的感受與判斷。當我們評論一部文學作品的時候,我們不可能對其文本進行單純的技術考量。如若不然,只會導致後學者對經典作品的學習,陷入類似模仿的境地。將注意力聚焦於作品的類型化特點,模仿者隨之失去了更為寶貴的東西...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自序
第一章作家們的少年敘事
一、二掌相擊,何若孤手拍之——J.D.塞林格《九故事》
二、他們都是時間中的孩子——伊恩‧麥克尤恩《最初的愛情,最後的儀式》
三、迷宮如霧,及記憶的把手——帕特里克‧莫迪亞諾《緩刑》
四、胸抱彩虹,向光而生——太宰治《斜陽》
五、導演是時日,演員是你——V.S.奈保爾《米格爾街》
第二章過去時態中的小說文本
一、與君分袂,各自東西不回首——本哈德‧施林克《朗讀者》
二、塵封的作品,與人生的幽靈——斯蒂芬‧茨威格《昨日之旅》
三、他們在一起純潔地成長——杜魯門‧卡波特《蒂凡尼的早餐》
四、...
第一章作家們的少年敘事
一、二掌相擊,何若孤手拍之——J.D.塞林格《九故事》
二、他們都是時間中的孩子——伊恩‧麥克尤恩《最初的愛情,最後的儀式》
三、迷宮如霧,及記憶的把手——帕特里克‧莫迪亞諾《緩刑》
四、胸抱彩虹,向光而生——太宰治《斜陽》
五、導演是時日,演員是你——V.S.奈保爾《米格爾街》
第二章過去時態中的小說文本
一、與君分袂,各自東西不回首——本哈德‧施林克《朗讀者》
二、塵封的作品,與人生的幽靈——斯蒂芬‧茨威格《昨日之旅》
三、他們在一起純潔地成長——杜魯門‧卡波特《蒂凡尼的早餐》
四、...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