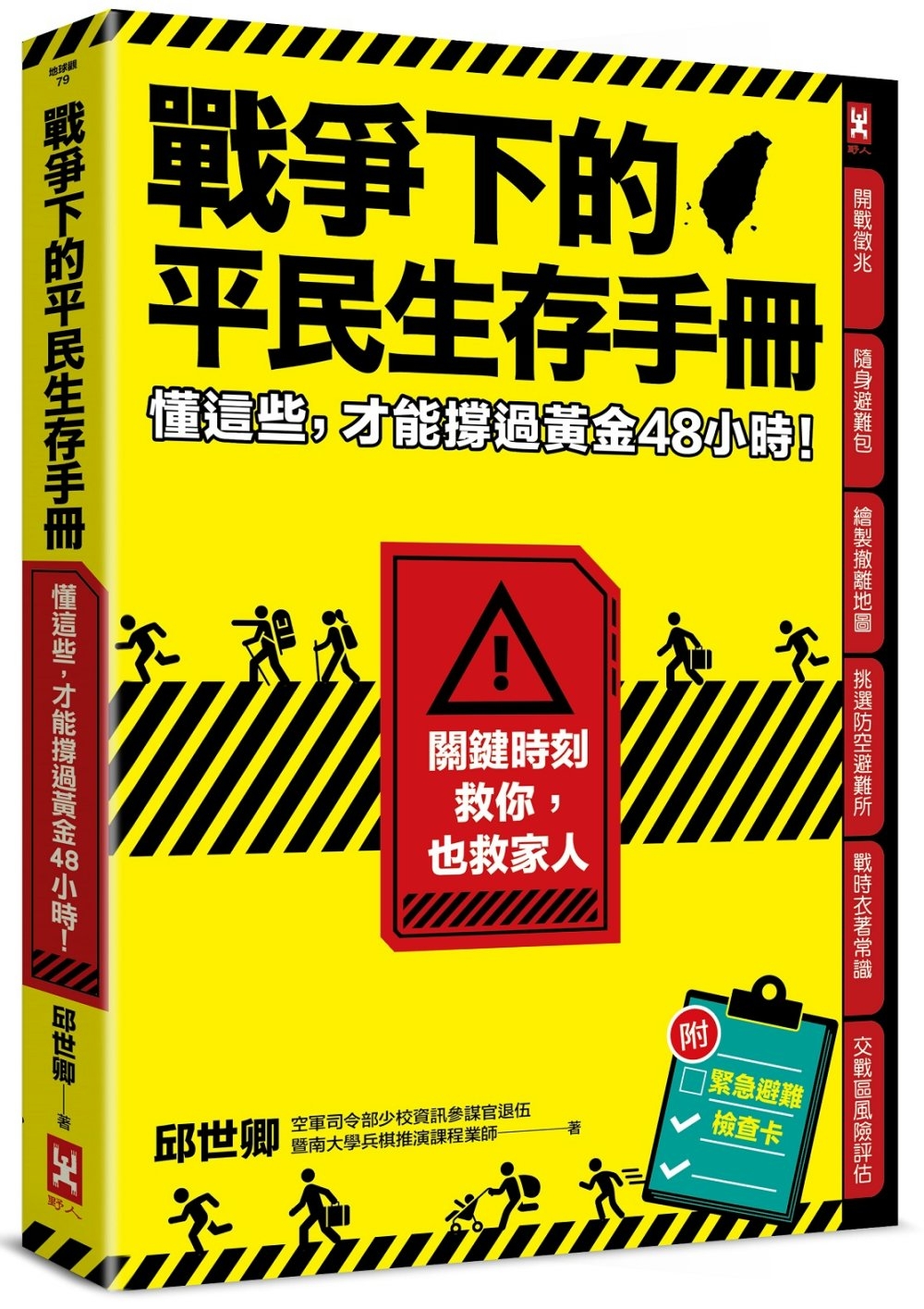第一講 我與敦煌學
我是從一無所知慢慢走到喜愛敦煌學的,其間經歷,相當艱苦,許多條件不允許我做得很痛快,是輾轉地想着法子,拼拼湊湊地把這個工作做下去的。現在想起這段經歷來,一面覺得有些不舒服,另一面卻又感到非常高興:因為在條件如此不充足的情況下,居然讓我做成了一些事。
敦煌學之所以吸引了我,與我的興趣及我的家庭教育和老師教育有關。近年來,我有一個關於教育的設想:就是一個做科研工作的人一定要同他自身的一切條件相配合。條件有兩種:一種是生理條件,一種是社會環境。譬如一個人記憶力很好,他可能搞歷史;另一個人理解力很強,他就適於搞哲學或自然科學。所以,一個人生理上的特點,與他的前途、成就,有很大的關係。在此,我想講講自己生理上的優劣。老師、親友往往說我的天賦是比較強硬的,但是,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很遲鈍的人。也因為遲鈍,才引出幾件事情來。其一是我一輩子不做欺騙人的事情,一輩子讀書都是規規矩矩,老老實實,從頭做起,不敢偷懶的,也就是說自己知道廉恥。孔子曰:知恥近乎勇。因此,我在學術研究道路上,就有一種毫不為人所難的脾氣。30 年代,在很艱難的條件下,靠教書積攢起來的幾個錢,到歐洲去。假如沒有這個戇脾氣,我自然也不會鑽進敦煌學,因為那個時候,我沒有地位和經濟支持。等我到了巴黎,看過幾十個博物館以後,才下決心把我國文物搞回來。為此,我連從巴黎大學得博士學位的機會也放棄了,聽從王重民先生的話,加入他們的行列。這個行列,當時在歐洲只有三個人:王重民、向達和我。他倆是以公費到歐洲去的,我卻是自費的。因此,我奮鬥的範圍是比較小的,王重民先生分我搞漢語音韻,我自己稍微擴大了一點,也搞儒家經典、道家經典等卷子。假如我不是戇頭戇腦的話,哪個不想得個博士學位歸國呢!生性使我這樣。另一方面是家庭和老師的教育。我父親是雲南東部昭通十二州縣光復時的領導人之一,年輕時,就接受梁任公、章太炎先生的影響,是非常愛國的人。他平常教我愛國思想,從小就要我讀格致教科書等科學知識的書。總結父親給我的影響,主要是這兩方面。有一回,我躲在稻草堆下看《紅樓夢》,被父親發現了。他啟發我:孩兒,你要看《紅樓夢》,是怎麼看的?講給我聽聽。我怎麼講得出來,不過是看故事嘛!父親就說:裡邊的人仔細看看,到底有哪些人?你給我找出分別來。我得了這個題目,《紅樓夢》是仔仔細細地看過的。所以,現在還稍稍有點《紅樓夢》的知識,雖然,從那以後,我不看了,從中學畢業到考上大學,再也沒有看過。我想我的情況對大家會有所啟發的,所以,希望大家了解自己,首先了解自己應該走甚麼路。譬如搞敦煌學吧,有的人對搞佛教經典有興趣,有的人對搞儒家經典有興趣,有的人可能有興趣搞歷史,也有的人想搞藝術,等等,因人而異。你們對於自己的思想、生活及性情脾氣有個了解以後,走起路來是輕快的,是能夠堅持到底的。不然的話,見異思遷就完了。我父親有一件事情使我非常感動,他喜歡文天祥的《正氣歌》,幾乎每年都要寫一次,並且都寫成大的條屏,可以在牆上掛的。所以,我八歲時就把它背熟,父親給我講解。我一生之所以有一些愛國主義思想,恐怕要數父親的影響來得大。
我也有缺點,一生脾氣很戇的,到處和人家不合。解放初,我沒有發表過一篇文章,因為拿出去,人家不歡迎,發表以後要受批評的,所以,就不發表,這是我的缺點。我不大聯繫群眾,但是,我一生職業是教書,所以,我對青年是熱愛的。為了青年,再大的苦我都吃得,這也是我的脾氣。
我從事敦煌學,也同這脾氣有關。早年在四川讀書,一位老師教我讀詩詞,告訴我朱彊村的《彊村叢書》收的第一種詞集是敦煌發現的,即《雲謠集》曲子詞。從此,我開始知道敦煌有材料,但是,還不懂。後來到北京讀書,王國維先生經常告訴我們:某個東西敦煌卷子裡邊有,你們去看看吧!某個東西敦煌卷子裡邊也有,你們去看看吧!因此,我經常去清華圖書館找敦煌的東西看,從此,產生興趣。及到後來,見了王重民,要我去搞敦煌的音韻卷子,我同意了。抄了許多卷子,拍了許多照片,又看了許多壁畫。伯希和的《敦煌圖錄》給我很大的啟發,在這本書裡,我發現我們整個文化史裡許許多多的東西,突然愛好敦煌藝術了。抗戰期間,我正在四川,他們組織了一個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委員會,請了三個人:向達、常書鴻和我,要我們到敦煌去設計一下。向達和常書鴻去了,我沒有去。向達回來告訴我敦煌藝術的體系是怎麼樣子的,又給我看了許多照片,更激發我對敦煌藝術的愛好。當時,我在四川三台的東北大學教書,由於找不着材料,身邊只有從巴黎拍攝回來的幾百張敦煌卷子的照片。既然不能研究敦煌藝術,就研究敦煌卷子吧!但是,時刻想念着敦煌藝術。這個時候我在讀五代人的詞,看到許多同敦煌藝術有關係的材料。記得有個學生來問我:《木蘭詞》的「對鏡貼花黃」怎麼個講法?他說:我們看了若干書,都講不出來。我說我從《敦煌圖錄》裡看出來了。原來唐末五代的婦女喜歡剪些花鳥貼在臉上,譬如剪個蝴蝶、牡丹花,甚麼蟲鳥之類,貼在臉上。後來我又在溫庭筠的十八首《菩薩蠻》詞(專講婦女裝飾的)中下工夫,拿敦煌文物來證明溫庭筠的詞,得到了說明。不過,我這個說法多少還是一種感性認識,還沒有落到理性,等到我在三台做了三年多的研究工作,完成了《瀛涯敦煌韻輯》之後,才從感性轉到理性。這裡不單單是讀讀詩詞而已,而是整個敦煌文物都在說明與中國全部文化有關係。因此,我轉而搞歷史,搞音韻學。這個時候,我完成了幾個東西,一個是《瀛涯敦煌韻輯》,一個是敦煌傳記,譬如關於敦煌王的傳記,那時稱陀西王,有兩家:張家和曹家。我給他們作了很詳細的注解,補了《唐書》和《五代史》。還寫了一篇關於敦煌科學家的傳。以上是我從事敦煌學研究的兩個階段,從藝術品慢慢地轉入遺書。到現在為止,我仍然以敦煌卷子為基礎,到底有些甚麼結果,很難說。我也不敢說我取得的一些結果就完全成熟了,現在也還想加深、修訂。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敦煌學概論的圖書 |
 |
敦煌學概論 作者:姜亮夫 出版社: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07-28 語言:中文/繁體 規格:平裝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16 |
人類與考古 |
$ 316 |
中國各朝歷史 |
$ 316 |
Social Sciences |
$ 316 |
Others |
$ 360 |
中國歷史 |
$ 360 |
考古學 |
$ 360 |
中文書 |
$ 360 |
社會人文 |
$ 360 |
文化研究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敦煌學概論
1.中國第一本講授敦煌學的簡明教材
2.自費留法抄錄敦煌古卷,回國教授敦煌學第一人的講義筆記
3.涵蓋敦煌學、敦煌經卷、敦煌藝術、敦煌卷子的研究方法幾個主題,為讀者開啟了敦煌學的實藏之門。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重新面世後,大量珍貴古代寫本流失海外,在世界上,敦煌學迅速形成。
然而早期國內學者卻寥若晨星,遠赴歐洲尋訪敦煌寫卷的更屈指可數,其中就有姜亮夫先生。
姜亮夫先生是中國第一位在高校開辦敦煌學講習班的大師,這本《敦煌學概論》就是根據他在1983年的講課錄音整理而成,涵蓋了敦煌學、敦煌經卷、敦煌藝術、敦煌卷子的研究方法幾個主題。言簡意賅,卻決不亞於一些煌煌巨著。
這本小書是姜亮夫先生教學與研究敦煌學的結晶。
本書還附錄了《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節選。對敦煌和敦煌學有興趣的讀者,實為難得的讀物。
作者簡介:
姜亮夫
1902-1995,原名寅清,以字行,雲南昭通人,語言學家、敦煌學家。1926年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學習,師從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1935年自費遊學巴黎,專心抄錄英、法所藏敦煌寫卷。曾任復旦大學、雲南大學、杭州大學教授,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中國訓詁學會顧問。生平著述宏富,著有《文學概論講述》、《屈原賦校注》、《陸機年譜》、《中國聲韻學》、《古文字學》、《敦煌學概論》等,有《姜亮夫全集》(24卷)行世。
章節試閱
第一講 我與敦煌學
我是從一無所知慢慢走到喜愛敦煌學的,其間經歷,相當艱苦,許多條件不允許我做得很痛快,是輾轉地想着法子,拼拼湊湊地把這個工作做下去的。現在想起這段經歷來,一面覺得有些不舒服,另一面卻又感到非常高興:因為在條件如此不充足的情況下,居然讓我做成了一些事。
敦煌學之所以吸引了我,與我的興趣及我的家庭教育和老師教育有關。近年來,我有一個關於教育的設想:就是一個做科研工作的人一定要同他自身的一切條件相配合。條件有兩種:一種是生理條件,一種是社會環境。譬如一個人記憶力很好,他可能搞歷史;另...
我是從一無所知慢慢走到喜愛敦煌學的,其間經歷,相當艱苦,許多條件不允許我做得很痛快,是輾轉地想着法子,拼拼湊湊地把這個工作做下去的。現在想起這段經歷來,一面覺得有些不舒服,另一面卻又感到非常高興:因為在條件如此不充足的情況下,居然讓我做成了一些事。
敦煌學之所以吸引了我,與我的興趣及我的家庭教育和老師教育有關。近年來,我有一個關於教育的設想:就是一個做科研工作的人一定要同他自身的一切條件相配合。條件有兩種:一種是生理條件,一種是社會環境。譬如一個人記憶力很好,他可能搞歷史;另...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目錄
001 第一講 我與敦煌學
025 第二講 敦煌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價值
048 第三講 敦煌經卷簡介(上)
072 第四講 敦煌經卷簡介(下)
101 第五講 敦煌藝術內容簡介
118 第六講 敦煌卷子的研究方法
152 附錄:《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節錄)
001 第一講 我與敦煌學
025 第二講 敦煌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價值
048 第三講 敦煌經卷簡介(上)
072 第四講 敦煌經卷簡介(下)
101 第五講 敦煌藝術內容簡介
118 第六講 敦煌卷子的研究方法
152 附錄:《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