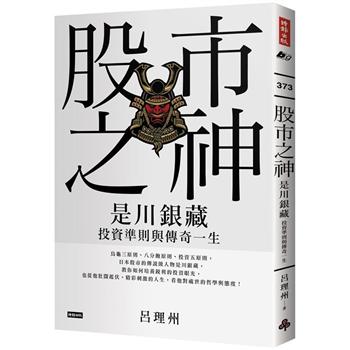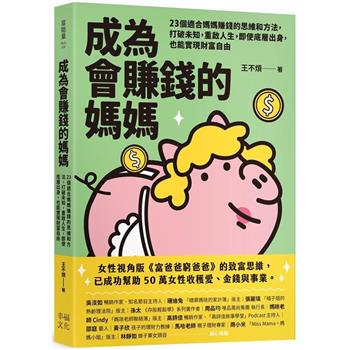他者(der Andere)的時代已然逝去。那神秘的、誘惑的、愛慾的(Eros)、渴望的、地獄般的、痛苦的他者就此消失。如今,他者的否定性讓位於同者(der Gleiche)的肯定性。同質化的擴散形成病理變化,對社會體(Sozialkörper)造成侵害。使其害病的不是退隱和禁令,而是過度交際與過度消費,不是壓迫和否定,而是遷就與贊同。如今的病態時代標誌不是壓制,而是抑鬱(Depression)。具有毀滅性的壓力並非來自他人,而是來自內心。
作為一種內部壓力,抑鬱引發自殘行為動向。抑鬱的功能主體(Leistungssubjekt)彷彿被自己打死或扼殺。具有毀滅性的不僅僅是他者的暴力。他者的消失觸發了另外一個全然不同的毀滅過程,即自我毀滅(Selbstzerstörung)。暴力辯證法無處不在:拒絕他者否定性的體系,會引發自我毀滅動向。
同質化的暴力因其肯定性而不可見。同質化的擴散日漸嚴重。自某一特定的點開始,生產不再是創造性的,而是破壞性的;信息不再是有啟發性的,而是扭曲變形的;交流不再是溝通,而僅僅是言語的堆積而已。
如今,感知(die Wahrnehmung)本身呈現出一種「狂看」(Binge Watching)的形式,即「毫無節制的呆視」(Komaglotzen)。它指的是無時間限制地消費視頻和電影。人們持續不斷地為消費者提供完全符合他們欣賞品位的、討他們喜歡的電影和連續劇。消費者像牲畜一樣,被飼以看似花樣翻新實則完全相同的東西。如今社會的感知模式完全可以用這種「毫無節制的呆視」來概括。同質化的擴散不是癌症性質的,而是昏睡性質的。它並未遭遇免疫系統的抵抗。人們就這樣呆視着,直至失去意識。
他者的否定性對患病是負有責任的,雖然他者可介入同一者(das Selbe),促使抗體的形成。與此相反,梗死則源於過多同質化的東西,源於系統的臃腫不堪。這種梗死不具備傳染性,而是癡肥所致。針對肥胖無從形成抗體。沒有任何免疫系統能阻止同質化的擴散。
他者的否定性給同一者以輪廓和尺度。沒有了這一否定性,同質化便會滋長。同一者和同者是有區別的。同一者總是與他者成對出現。與此相反,同者則缺少能限定它、塑造它的辯證的對立面。如此一來,它便肆意滋長成一團不成形的東西。同一者是有形的,一個內部的集合,一個內部世界,這要歸功於它與他者的不同。同者則是沒有固定形態的。因其缺少辯證對立,從而產生了一團彼此無差別化、蔓生的、不能相互區別的東西:「唯當我們思考區分之際,我們才能說同一。在區分之分解中,同一的聚集着的本質才得以顯露出來。同一驅除每一種始終僅僅想把有區別的東西調和為相同的熱情。同一把區分聚集為一種原始統一性。相反,相同則使之消散於千篇一律的單調統一中。」[1]
同質化的恐怖(Terror des Gleichen)席捲當今社會各個生活領域。人們踏遍千山,卻未總結任何經驗。人們縱覽萬物,卻未形成任何洞見。人們堆積信息和數據,卻未獲得任何知識。人們渴望冒險、渴望興奮,而在這冒險與興奮之中,自己卻一成不變。人們積累着朋友和粉絲(Follower),卻連一個他者都未曾遭遇。社交媒體呈現的恰恰是最低級別的社交。
數字化的全聯網(Totalvernetzung)和全交際(Totalkommunikation)並未使人們更容易遇見他者。相反,它恰恰更便於人們從陌生者和他者身邊經過,無視他們的存在,尋找到同者、志同道合者,從而導致我們的經驗視野日漸狹窄。它使我們陷入無盡的自我循環之中,並最終導致我們「被自我想像洗腦」[2]。
他者和「改變」的否定性形成深刻的經驗。所謂形成經驗是指:「某些事情在我們身邊發生,我們碰見了它,遭遇了它,被它推翻,被它改變。」[3] 其本質是痛楚。然而同者卻不讓人感到痛楚。如今,痛楚讓位於「點讚」(Gefällt-mir),這讓同者大行其道。
信息唾手可得,而獲取深刻的知識卻是一個平緩而漫長的過程。它展現出一種全然不同的時間性。知識是慢慢生長成熟的。時至今日,這種慢慢成熟的時間性已經漸漸被我們所遺失。它與當代的時間策略格格不入。如今,人們為了提高效率和生產率而將時間碎片化,並打破時間上穩定的結構。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他者的消失的圖書 |
 |
他者的消失 作者:韓炳哲 / 譯者:吳瓊 出版社: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07-06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15 |
中文書 |
$ 315 |
西方哲學 |
$ 315 |
社會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他者的消失
本書是德國學者韓炳哲的一部哲學小品文集。
作者廣納海德格爾、列維納斯、康德的哲學思想,深刻剖析現代社會的數字化超交際所引發的「同質化」問題,解讀自戀、自殘、自我異化、過勞、抑鬱、恐懼、恐怖主義這些表象下的同質化本質,批判新自由主義對生產和績效的極端追求,鼓勵人們走出自我空間,傾聽和容納「他者」的聲音。
作者簡介:
韓炳哲(Byung-Chul Han)
德國新生代思想家。1959年生於韓國首爾,80年代在韓國學習冶金學,之後遠渡重洋到德國學習哲學、德國文學和天主教神學。他先後在弗萊堡和慕尼黑學習,並於1994年以研究海德格爾的論文獲得弗萊堡大學的博士學位。2000年任教於瑞士巴塞爾大學,2010年任教於卡爾斯魯厄建築與藝術大學,2012年起任教於德國柏林藝術大學。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18-20世紀的倫理學、社會哲學、現象學、文化哲學、美學、宗教、媒體理論等。著有《愛慾之死》《倦怠社會》《暴力拓撲學》等。被西班牙《國家報》(El País)譽為「德國哲學界的一顆新星」。
譯者簡介:
吳瓊
翻譯碩士,畢業於德國波恩大學,現執教於上海外國語大學賢達經濟人文學院德語系。已出版譯著《德國室內設計》,編著《我的第一本德語書》《千姿百態看德國:社會篇》等。
章節試閱
他者(der Andere)的時代已然逝去。那神秘的、誘惑的、愛慾的(Eros)、渴望的、地獄般的、痛苦的他者就此消失。如今,他者的否定性讓位於同者(der Gleiche)的肯定性。同質化的擴散形成病理變化,對社會體(Sozialkörper)造成侵害。使其害病的不是退隱和禁令,而是過度交際與過度消費,不是壓迫和否定,而是遷就與贊同。如今的病態時代標誌不是壓制,而是抑鬱(Depression)。具有毀滅性的壓力並非來自他人,而是來自內心。
作為一種內部壓力,抑鬱引發自殘行為動向。抑鬱的功能主體(Leistungssubjekt)彷彿被自己打死或扼殺。具有毀...
作為一種內部壓力,抑鬱引發自殘行為動向。抑鬱的功能主體(Leistungssubjekt)彷彿被自己打死或扼殺。具有毀...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目錄
同質化的恐怖 001
全球化與恐怖主義的暴力 017
真實性的恐怖 031
恐 懼 043
門 檻 055
異 化 059
對抗體 067
目 光 075
聲 音 085
他者之語言 099
他者之思考 111
傾 聽 119
註 釋 132
同質化的恐怖 001
全球化與恐怖主義的暴力 017
真實性的恐怖 031
恐 懼 043
門 檻 055
異 化 059
對抗體 067
目 光 075
聲 音 085
他者之語言 099
他者之思考 111
傾 聽 119
註 釋 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