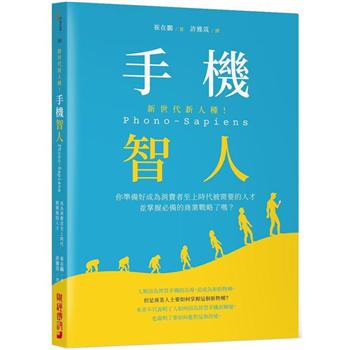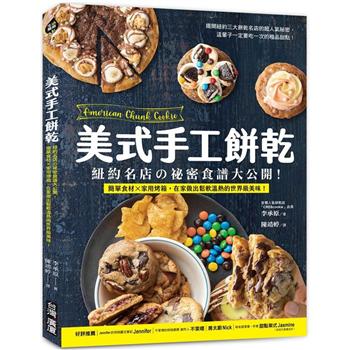一
以下是我努力復原的情景,時間是1974年7月14號。
瀋陽市中心,一座六層的灰色大樓,有人在走廊裡叫:小萬!小萬!呼喊聲在樓道裡撞來撞去,發出迴響。這座樓是瀋陽軍區前進歌劇團的駐地,當時我正在樂隊女生宿舍裡聊天,聽到喊聲趕緊跑到走廊上。原來是教導員找我,我有些詫異,他找我幹甚麼呢?
下樓來到辦公室,敲門,喊:報告!屋子裡只有教導員自己,坐在辦公桌後面。一直以來的直覺告訴我這位領導並不喜歡我,原因不明,也許是我們之間太少交集,彼此漠不關心,是天天見面的陌生人。他找我幹甚麼呢?這位臉色黑黑的小個子男人,看到我進來沒有立即開口說話,這個不正常的停頓讓我察覺到他並不願意找我來,是不得不這麼做。到底他找我幹甚麼?
是這樣,他說,我們接到電話,你媽媽病重,團裡研究了一下,批准你今天就回去。這有一封你的電報。他從桌上拿起一張紙遞向我。
我拆開信封,看到電報紙下方五個很小的字:母病重,速歸。我沒有反應,人卡在一個混沌的縫隙裡,動彈不得。也許幾秒鐘,也許十幾秒,忽然想到一個問題:誰打來的電話?
你家的鄰居,姓周。教導員回答。
我知道那個姓周的,我當然知道那個人。打電話是很困難的,尤其是長途電話,連想都不要想。但周同志打來了電話,他從哪打的?單位嗎?應該是單位。那爸爸呢,他在哪兒,在幹甚麼?思緒蠕動着,毫無方向。已經沒有甚麼話可說了。好,我說,只說了好,然後轉身離開。
我的表現很冷靜,怎麼會那麼冷靜,在不該冷靜的時候。後來當我逐漸對自己有所了解,發覺在某種緊要關口我總是回身關門,把別人、把世界阻擋在外面,把自己留在孤島上,對我來說這孤島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容易忍受,更安全。
記憶從來不可靠,尤其是對痛苦的記憶。情感會淹沒很多細節。離開教導員辦公室,上樓回到宿舍,接下來我做了甚麼,怎麼做的?沒有多少清晰的回憶可以填補那段混混沌沌的時間,只有些若隱若現的影像。我去找了小閆,幸虧有小閆。她是列車員,跑的就是瀋陽至北京的特快,那晚不是她值班,但她保證我能上車,告訴我找誰。當我想起小閆,她的樣子栩栩如生,頭上紮着兩個小抓鬏,愛笑,笑起來嘴咧得大大的,露出兩排方方的大牙齒。好多次她從北京給我帶東西來,都是我爸爸到北京站買張站臺票,找到她的車次,再找到她,把東西交到她手上,有糖果,有裝在瓶子裡的肉末炒榨菜,有《基督山恩仇記》。
7月14號那天還有其他人,歌劇團裡我的朋友,雪樺,亞蘭,小曲,她們知道了「母病重,速歸」一定給予我很多的安慰,幫我安排些必要的事,但是我甚麼也想不起來了。我在孤島上。
我是通過工作人員的入口進站的,軍裝很有用,沒有人喜歡為難一個穿着軍裝的小姑娘。小閆的同事讓我先在列車員休息的地方坐坐,等開車再給我找座位。我聽到了發車的鈴聲,聽到列車員「嘭」地關閉車門,感覺到咣當一震,站臺開始向後移動。二十點四十分。正點。
列車咔嗒嗒咔嗒嗒從黑夜衝向黑夜。我看見自己映在車窗上那張困頓茫然的臉。我知道她已經不在人世了嗎?我那樣想過嗎?答案很肯定,不,沒有。我不認識死亡,也不想認識,更關鍵的是我不能與死亡為伴度過那麼漫長的一夜旅途。
媽媽,媽媽,我沒有翅膀,我不會飛,不會魔法,無法穿越濃密的黑夜……只能坐在擠滿旅客的車廂裡。座位上的人七倒八歪,在照度不足的燈光下像是昏迷過去了,個別人的睡姿那麼難看,甚至像死去一樣。我一分鐘也沒有睡,沒有閉眼,一夜不閉眼是很可怕的,但在那種情況下很正常。是的,前方有件事在等着我,或者說我在等着它,隨着列車前進的節奏我和它的距離在縮短,越來越近,它正一點點褪去衣服,露出巨大而赤裸的模樣,咔嗒嗒咔嗒嗒咔嗒嗒……
發現她死的時候,她躺在床上,是孫阿姨在早晨發現的。掀開蓋在她身上的被子,她的身旁身下全是藥片,安眠藥。她不是自殺,是吃多了藥,吃了又吃,根本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根本無所謂了。但她沒想死,這點我可以肯定,她沒有那麼勇敢,也沒有那麼膽小,最關鍵的是她愛我們,還想見到我們。她的問題是離不了安眠藥,依賴它,1974年7月的這個夏夜,安眠藥要了我媽媽的命。
即便已經過去了四十三年,回憶仍然令人痛苦,令人望而卻步。活得越久我越懂得要感恩一件事,忘卻,我感激忘卻,沒有忘卻人很難正常健康地生活下去。
我突然明白寫這本書對我的意義了,它要求我活得健康,有健康的心態,不是醫學的標準,是我自己的標準。我必須是一個沒有太多心理疾病的心態正常的人,一個寫作者。我夠格嗎?
媽媽和爸爸,他們兩個人都在吃藥,都離不開安眠藥。只有安眠藥能讓他們離開1974年的中國,北京,東城區,張自忠路5號,後院裡那兩間陰暗的屋子。我不知道吃藥之後他們去了甚麼地方,但想必那地方是不可怕的,不必恐懼甚麼,不必一刻刻熬時間,苦苦想念女兒,也談不上絕望,因為根本不必希望,那裡沒有明天的概念……如果媽媽是從那裡出發,離開這個世界,也許我應該為她高興。這樣的想法是不是有點殘忍。
回到剛才的問題,我夠格寫這本書嗎,我足夠強大、具有這樣的能力了嗎?
我怕痛苦,像所有人一樣,至今仍然怕。但是還有一種更佔上風的慾望,表達。我需要表達,我想要表達對媽媽的愛,表達我對爸爸媽媽的感情,而他們已不在人世。作為一個靠寫作為生的人,除了寫還有甚麼其他更好的方法嗎?
1974年,當我回到家,媽媽已經不在家裡了,在醫院的太平間。我妹妹也回來了,那時我們倆都在當兵,我在瀋陽她在煙臺。我記得很清楚,我們倆坐在窗下低矮的破沙發上,另一位鄰居、一個阿姨面對我們坐在小板凳上,講述媽媽是怎麼被發現死去的。我下意識地哭了,並沒有大哭,抽抽噎噎的,有些懵懵懂懂,然而我還是有所知覺,能感知到周圍的事物,對我妹妹的表現感到一絲驚訝。她沒有哭,語調鎮定地問了幾個問題,像個局外人,一個嚴肅的調查者。人生第一次,我感到我妹妹是獨立的個體,在此之前她只是我生活中必然存在的一部分。我發現我們雖是一母所生,生長在同樣的環境,人和人卻那樣不同。這個淺顯而實在的道理我是在那個時刻被啟蒙的。
接下來有些事情要辦。需要找一套衣服給媽媽穿。我知道媽媽不久之前給自己做了一套深藍色的嗶嘰套裝,一件外衣和一條褲子,很容易就在箱子裡找到那套衣服,幾乎沒穿過,捨不得穿。但最終我沒有選那套衣服,而是選了一套她日常穿的,一件黑色帶着隱約白條紋的呢子上衣,一條黑褲子。為甚麼做了這樣的選擇呢?我一生都在責備自己。為甚麼不讓她穿平時捨不得穿的新衣服?難道我也捨不得嗎?難道我自己想穿那套新衣?我當然沒有穿過,那是不可能的。那套衣服我一直留着,在箱子裡保存了幾十年,後來消失了,不記得從甚麼時候不見了,也不記得它的下場,應該是被處理了。
東西的價值是甚麼?我們為甚麼保存沒有任何用處的東西?為了紀念,為了自己的心情,為了證明我們活過,經歷過?不管為了甚麼,我的箱子裡依然保存着一件藍布中山裝,春秋天,媽媽最經常穿的一件外衣。那是個舊皮箱,多年沒有打開過一次,但是我知道衣服在裡面。
爸爸始終不在場,或者是在我的記憶裡他一直不在場,或者我並沒有關心他在哪兒,在幹甚麼,似乎覺得他不在場是自然而然的事。
事實上他在,就在他那間小書房裡。是一排小平房中的一間,被前面更高又離得很近的房子擋住了所有的陽光,靠牆的書櫃遮住了牆上一塊塊發黑的霉斑,但沒有辦法能消除陰濕的潮氣。屋裡有一張床,他躺在床上,始終躺着。我們去醫院的太平間見媽媽最後一面他沒有去。這可能嗎?難道是我記憶失效?我又詢問了妹妹,得到肯定的回答,他確實沒去。
現在我知道了,他在他的孤島上。不,那不是一座孤島,是一個深淵,他掉在深淵裡,無法想像有多深,多黑暗,多麼哀痛。
因為媽媽去世,我有一個月的假期。能在北京待一個月是多麼令人激動啊。這一個月我和妹妹去了兩次頤和園,和朋友們爬山、划船。7月的太陽當空照射,昆明湖如一面白晃晃的大鏡子,映得我們的面龐熠熠發光。朋友帶了一部120的海鷗照相機,照片上的我坐在船上,快樂地笑着,穿着游泳衣,那時候昆明湖可以游泳。
我爸爸躺在小屋裡,一個人。
從甚麼時候起我才認識到青春的殘酷無情?壓抑的大石頭可以被輕而易舉地推動,骨碌碌滾開,注意力已經轉移到有趣的事物上了。我們逃得那麼迅速,快得不可思議,不合情理,如今,這屬於孩子、屬於青春的能力,我早已喪失殆盡。
我爸爸躺在小屋裡,他聽到我們出門,聽到我們回家,看到我們的臉被太陽曬得紅通通,興奮又疲憊,他會是甚麼感覺?會為我們一整天忘卻了失去媽媽的悲痛而心寒,愈發覺得自己孤單,愈發哀傷?不,他不會,他看着我們,聽着女孩兒細碎的說笑聲,他想:哦,青春,戰無不勝的青春啊!他肯定是這麼想,我了解他。
就這樣,在我二十二歲的時候,我的媽媽離開了人世,我失去了媽媽,被拋在一個沒有媽媽的世界裡,從此生活中的一切恩怨只能自己解決了。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你和我的圖書 |
 |
你和我 作者:萬方 出版社: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12-21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19 |
中文現代文學 |
$ 477 |
現代散文 |
$ 477 |
中文書 |
$ 477 |
藝術家傳記 |
$ 477 |
藝術人物傳記 |
$ 477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你和我
「有些事物會消失,如同從未發生過;有些事件永遠存在,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塵封已久的情書、飽含父愛的家書、與一生摯友的書信;
跨越近百年的六十餘幅家族照片;
面對家族記憶,挖掘心底隱痛;
一經問世便感動無數人的年度好書。
曹禺是中國戲劇大師。二十四歲即發表處女作《雷雨》,最重要的代表作還有《日出》《原野》《北京人》等。
本書是曹禺先生的女兒萬方的一部非虛構作品,一種如戲劇舞臺般穿梭時空的家族回憶錄。又不僅是一部回憶錄,還是一段穿梭於歷史、回憶和現實中的旅程。構成這段旅程的,是作者對父母人生的追問和記錄,是對真相的好奇,也是對理解的渴望—理解父母,同時原諒曾經的自己。
●感動讀者之作
女兒對父母的回憶和記錄,理解父母的歷程
●穿梭父母的回憶中
在記錄中收集父母的回憶,仿如穿越父母的過去
●四十八段的感動
從一至四十八段故事記憶著與家人相處的情感
編輯推薦:
.感受藝術家的情感細膩,穿越共讀作者對父母的回憶
.作者嘗試拼湊歷史碎片還原父母的愛,理解父母對她的情感
.與讀者產生共鳴,每段故事都能讓讀者回憶與家人之間的片段
作者簡介:
萬方
當代著名作家、劇作家。
自幼受父親曹禺影響,對文學、戲劇藝術產生濃厚興趣;「文革」中插隊、當兵;八十年代開始創作小說、舞臺劇、電影及電視劇。
代表作有小說《紙飯館》《空鏡子》等,電視劇《空鏡子》《女人心事》等,電影《日出》《黑眼睛》,舞臺劇《冬之旅》《新原野》等。作品曾獲得「金雞獎」「金鷹獎」「文華獎」等各類獎項。
章節試閱
一
以下是我努力復原的情景,時間是1974年7月14號。
瀋陽市中心,一座六層的灰色大樓,有人在走廊裡叫:小萬!小萬!呼喊聲在樓道裡撞來撞去,發出迴響。這座樓是瀋陽軍區前進歌劇團的駐地,當時我正在樂隊女生宿舍裡聊天,聽到喊聲趕緊跑到走廊上。原來是教導員找我,我有些詫異,他找我幹甚麼呢?
下樓來到辦公室,敲門,喊:報告!屋子裡只有教導員自己,坐在辦公桌後面。一直以來的直覺告訴我這位領導並不喜歡我,原因不明,也許是我們之間太少交集,彼此漠不關心,是天天見面的陌生人。他找我幹甚麼呢?這位臉色黑黑的小個子男人...
以下是我努力復原的情景,時間是1974年7月14號。
瀋陽市中心,一座六層的灰色大樓,有人在走廊裡叫:小萬!小萬!呼喊聲在樓道裡撞來撞去,發出迴響。這座樓是瀋陽軍區前進歌劇團的駐地,當時我正在樂隊女生宿舍裡聊天,聽到喊聲趕緊跑到走廊上。原來是教導員找我,我有些詫異,他找我幹甚麼呢?
下樓來到辦公室,敲門,喊:報告!屋子裡只有教導員自己,坐在辦公桌後面。一直以來的直覺告訴我這位領導並不喜歡我,原因不明,也許是我們之間太少交集,彼此漠不關心,是天天見面的陌生人。他找我幹甚麼呢?這位臉色黑黑的小個子男人...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目錄
一 008
二 014
三 019
四 023
五 029
六 032
七 034
八 040
九 046
十 059
十一 070
十二 078
十三 082
十四 083
十五 089
十六 093
十七 102
十八 106
十九 113
二十 122
二十一 124
二十二 126
二十三 160
二十四 165
二十五 169
二十六 172
二十七 179
二十八 181
二十九 185
三十 188
三十一 196
三十二 198
三十三 201
三十四 205
三十五 211
三十六 242
三十七 245
三十八 248
四十 259
四十一 269
四十二 271
四十三 283
四十四 286
四十五 289
四十六 293
四十七 295
四...
一 008
二 014
三 019
四 023
五 029
六 032
七 034
八 040
九 046
十 059
十一 070
十二 078
十三 082
十四 083
十五 089
十六 093
十七 102
十八 106
十九 113
二十 122
二十一 124
二十二 126
二十三 160
二十四 165
二十五 169
二十六 172
二十七 179
二十八 181
二十九 185
三十 188
三十一 196
三十二 198
三十三 201
三十四 205
三十五 211
三十六 242
三十七 245
三十八 248
四十 259
四十一 269
四十二 271
四十三 283
四十四 286
四十五 289
四十六 293
四十七 295
四...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