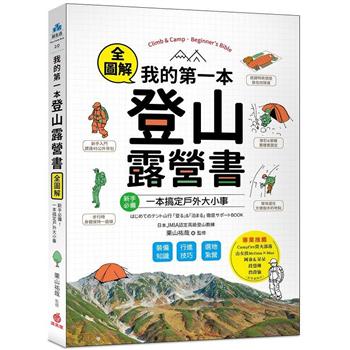前言
2018年12月18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40周年的紀念日,因此把1978年視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元年當然也是有道理的。實際上,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中央還召開過為期36天的工作會議,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做準備。而在工作會議之前,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紛紛出國考察和訪問,使得那一年成為40年來中國高層領導人出訪最為密集的一年。那一年,鄧小平本人就訪問了日本、新加坡等國。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鄧小平還專程到了平壤,他告訴金日成,中國要準備改變了,發達國家的技術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可以說,就在那一年,鄧小平決定推動變革,中國開始了非凡的學習之旅。
海內外的經濟學家,包括我自己,過去30多年來為中國經濟改革取得成功的經驗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中國的改革經驗被概括為已有經濟學理論的實驗室,也被認為可以成功拓展現有經濟學理論的分析範圍,可對經濟學的發展做出貢獻。但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研究都是基於對改革結果的觀察,而對那些為推動改革做出貢獻的主要人物和事件沒有給予同等的關注。在改革經歷40年後的今天,對於那些需要更深入理解中國改革的讀者來說,這是一個缺憾。
不可否認,中國的改革過程和推動改革的社會力量的形成無疑是中國在改革之初所具有的制度遺產及政治條件的產物。不了解這個背景和初始條件,我們無法知道中國的改革為甚麼是漸進的、增量式的和分步走的,為甚麼中國在改革中總是形成雙軌體制,並且可以做到「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正是這些制度遺產和政治條件使中國在改革方式和對改革方案的選擇上變得不那麼激進。
一旦我們把視野轉入中國改革進程中的「投入」側而不是「產出」側,你立刻就會發現中國改革的精彩之處在於改革如何從黨內的思想鬥爭和政治較量中形成主流;在於改革如何在關鍵時候由政治領導人的智慧與眼光所推動;在於改革成為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的互動過程;在於改革成為能讓更多人參與其中的社會過程;在於改革是一個基於局部經驗推廣和試錯法的社會實驗;更在於改革成為一個關於技術和制度的學習與擴散過程。
是的,作為後來者,即使在全球看,中國也毫無疑問是過去40年間向先行國家和地區學習技術和制度最快的國家。這一點讓我深信不疑。但意識到這些精彩之處卻是在十多年前。2006年底,我開始接觸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早期文字資料和有關文獻,並被推動中國經濟轉變的許多重要的人物和事件深深觸動,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在我第一次看到有關1978年這一年的記載文獻和資料時,對那一年發生的重要事件,我簡直不能想像。那個時候我剛剛入高中讀書,對北京發生的這一切基本無知。進入復旦大學經濟系後,從課堂上知道了在一些農村地區發生的包產到戶的自發改革,也聽到過一些關於深圳特區建設和四川國有企業可以被允許留存部分利潤的試點傳聞。但直到1984年秋,在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之後,經濟改革這個概念才真正進入我的視野。而正是1984年同一年的稍早時候,我從部分年輕教師那裡得知,在浙江的莫干山上舉行了首屆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的研討會,一大批來自國內各高校、政府和社科院系統的年輕經濟學者,意氣風發,給改革建言獻策,好不精彩。
1983—1985年,我對參加在學校舉行的各種講座格外有興趣,聽過朱嘉明、周其仁在校園做的報告。也特別關注老一代經濟學家關於當時宏觀經濟過熱和治理通貨膨脹的頻繁爭論。我記得,吳敬璉教授從耶魯回來不久就被我們請到復旦大學經濟系做過報告,後來他又陸續兩次來經濟系就經濟過熱和宏觀改革問題的各種意見做過介紹。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我的導師宋承先教授也開始研究價格改革和宏觀不平衡問題,對我影響頗大。
不過我真正開始從經濟學上去研究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這個主題還是90年代之後的事情,我在別處曾經記述過自己研究興趣的轉變過程,在這裡我就不再贅述。但那些研究還是純學術性的,並局限在學術界之內的傳播和交流,還一直沒有寫過以中國經濟改革歷程中那些精彩故事為敘事內容的非學術性著作。
差不多是在2007年春節過後不久,我突然有想法,希望自己能寫出一本記述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那些精彩事件的書。我是想以我的眼光把1978年前後到20世紀90年代間的許多重要改革過程和主要改革方案形成的精彩片段記錄下來。但我不是歷史學家,而是經濟學家,所以在決定寫出這樣一本書的時候,必須把注意力放在跟經濟改革方案有關的事件和參與其中的那些經濟學家的身上。那時候,我甚至設想應該可以在記述每個重要改革事件之後,尋找到一篇經濟學家的相關研究論文附在其後,以此提升我們對該重要改革認識的水平。作為試驗,我先動手整理資料和文獻,寫下了關於財政分權和分稅制這個主題的改革敘事,結果沒有想到這篇文章居然寫了將近四萬字。
從那之後,我便集中精力在復旦大學圖書館收集文獻並制訂寫作計劃,開始了寫作進程。2007年初夏,我帶着大量的文獻資料飛到加拿大東部的皇后大學,在那裡住了三個多月,集中寫作,完成了另外兩篇長文,分別是關於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和1985年的「巴山輪會議」,字數超過十萬字。不僅如此,我還忍不住將之前寫的關於財政分權的長文改寫成一篇標準的文獻綜述式的文章,2007年底發表在了《經濟學(季刊)》上,並深受讀者喜愛。
從加拿大回到上海之後的半年裡,因忙於教學和其他工作,寫作進程變得緩慢。2008年春節過後我又被學校派去耶魯大學負責籌備一個代表處,在那兒又住了三個月,但也只寫完了關於深圳特區的一章。回國後,正好趕上迎來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的日子,各種紀念活動和學術研討會接踵而至,使得我的寫作幾乎沒有太大進展,但我有機會在那年去多地就改革30年的話題發表演講,包括應邀去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新西蘭奧克蘭大學、美國芝加哥大學和日本大阪工業大學等學府出席紀念中國改革30周年的學術會議並發表主題演講。2008年11月初,我被《南方都市報》邀請去了廣州,在「嶺南大講堂」做了一場講座,取名「不為公眾所知的改革」,後來《南方都市報》專版發表了我那次演講的內容。
就在那個時候,杭州的吳曉波先生創辦財經出版中心「藍獅子」工作室,邀請我能就中國經濟改革寫一本書。考慮到我已有的寫作章節,便欣然答應。但由於各種研討會和演講的邀請,加上教學安排,一直拖延到2009年4月才勉強完成書稿交給吳曉波並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書名就用了廣州演講的題目「不為公眾所知的改革」。很遺憾,由於趕出版時間,那本書只有六章,計劃想寫進去的另外一些重要內容最終沒有來得及完成。
2018年恰逢中國經濟改革第40個年頭,似乎有理由重新增補整理這本書。非常巧合的是,世紀文景的姚映然女士也有這個想法,希望我能增補並修訂這本書,文景願意重新出版。就這樣,我於2018年5月開始動手寫作,增加了全新的兩章「自下而上的農業改革」和「浦東開發」,並在已有的章節裡又補充了一些值得記述的精彩事件。現在全書共有八章,字數也增加了將近十萬字。經過多次溝通,本書的新版定名為《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繁體版則由頗具口碑的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承接出版,並將主書名更名為《大國改革》。
我還要感謝國元證券的蔡詠董事長和上海鑽石交易所副總裁顏南海校友。蔡董事長為我在合肥找到並寄來了反映安徽改革30年的《安徽改革開放大事記(1977.6—2008.6)》一書,對於我核實安徽農村地區自發的包乾到戶情況非常有幫助。南海贈我的口述史《破冰:上海土地批租試點親歷者說》對於我進一步了解上海在土地批租試驗中的許多重要事件的細節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我的學生們在我需要尋找數據時也給予了我有效率的支持。
最後,我要感謝復旦大學人文社會學科傳世之作學術精品研究項目(2015)以及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2014年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項目的慷慨資助。
謹以本書獻給過去40年來為推動中國經濟改革進程做出貢獻的所有人。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大國改革: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90 |
經濟貿易 |
$ 558 |
經濟史 |
$ 558 |
中文書 |
$ 558 |
經濟 |
$ 558 |
財經企管 |
$ 558 |
經濟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大國改革: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
●揭曉改革細節
一線經濟學家講述鮮為公眾所知的改革內幕
●回顧改革歷程
一本書講清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的來龍去脈
●驚嘆精彩時刻
一次讀懂身在其中卻不見真容的「中國奇跡」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經濟所經歷的巨變包含了太多引人入勝的故事。本書以一位經濟學家的視角,回顧了農業改革、價格改革論戰、通貨膨脹辯論、深圳特區建立始末、浦東開發開放等諸多影響深遠的事件,帶領讀者重返精彩紛呈的改革現場,細述不為公眾所知的改革歷程。
同時,本書罕見地從參與改革的經濟學家內部的視角出發,描繪改革歷經的各種探索和博弈,刻畫了一群積極推動改革的經濟學家的活躍身影。以事件為線索,通過人物與事件的相互關聯鋪展論述,讓讀者用最短時間了解中國改革的核心、理解中國改革的未來。
作者簡介:
張軍
1963年生,經濟學家。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現任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他是第八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和理論經濟學聯席召集人、教育部全國高校經濟學教指委副主任、復旦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副主任暨社科與管理學部主任、復旦大學黨委委員和校務委員會委員。兼任上海經濟學會副會長、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理事、廣東省決策諮詢顧問委員會委員、重慶十四五規劃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等。曾任上海市委決策諮詢委員會委員、民進中央特邀諮詢研究員等。他2015年榮獲上海市先進工作者稱號。
張軍教授被海內外公認是中國經濟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在學術界影響廣泛。2015年7月受邀出席李克強總理主持的經濟形勢座談會。2015年10月榮獲第七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2018年獲美國比較經濟學會(CES)的最佳論文獎Bergson Prize 。 2020年11月獲得《中國新聞週刊》評選的年度影響力人物⸺「年度經濟學家」稱號。
章節試閱
前言
2018年12月18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40周年的紀念日,因此把1978年視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元年當然也是有道理的。實際上,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中央還召開過為期36天的工作會議,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做準備。而在工作會議之前,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紛紛出國考察和訪問,使得那一年成為40年來中國高層領導人出訪最為密集的一年。那一年,鄧小平本人就訪問了日本、新加坡等國。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鄧小平還專程到了平壤,他告訴金日成,中國要準備改變了,發達國家的技術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可以說,就在那一年,鄧小平決定...
2018年12月18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40周年的紀念日,因此把1978年視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元年當然也是有道理的。實際上,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中央還召開過為期36天的工作會議,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做準備。而在工作會議之前,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紛紛出國考察和訪問,使得那一年成為40年來中國高層領導人出訪最為密集的一年。那一年,鄧小平本人就訪問了日本、新加坡等國。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鄧小平還專程到了平壤,他告訴金日成,中國要準備改變了,發達國家的技術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可以說,就在那一年,鄧小平決定...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目錄
前言 001
代序 不為公眾所知的改革 007
第一章 自下而上的農業改革 029
農業集體化 030
安徽樣本 038
推廣農業改革 048
80 年代的農業增長 058
第二章 莫干山上論戰價格改革 068
莫干山會議 069
雙軌價格的經驗 091
關於雙軌制的爭論與「配套改革」動議 097
價格雙軌制:是奇跡還是神話 106
第三章 巴山輪會議 121
「巴山輪會議」上的經濟學家 122
1985 年的通脹辯論 128
「巴山輪會議」的七大論題 136
中國經驗的理論貢獻 143
第四章 特區試驗場 152
試驗改革的回聲 154
成立特區的過程 160
設立經濟...
前言 001
代序 不為公眾所知的改革 007
第一章 自下而上的農業改革 029
農業集體化 030
安徽樣本 038
推廣農業改革 048
80 年代的農業增長 058
第二章 莫干山上論戰價格改革 068
莫干山會議 069
雙軌價格的經驗 091
關於雙軌制的爭論與「配套改革」動議 097
價格雙軌制:是奇跡還是神話 106
第三章 巴山輪會議 121
「巴山輪會議」上的經濟學家 122
1985 年的通脹辯論 128
「巴山輪會議」的七大論題 136
中國經驗的理論貢獻 143
第四章 特區試驗場 152
試驗改革的回聲 154
成立特區的過程 160
設立經濟...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