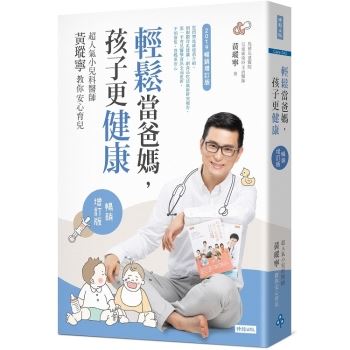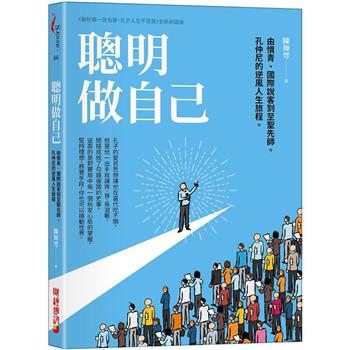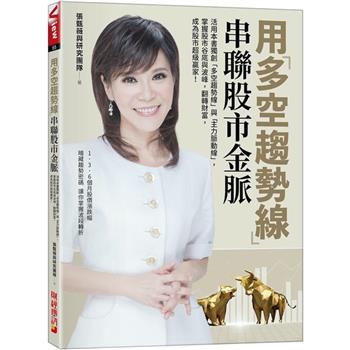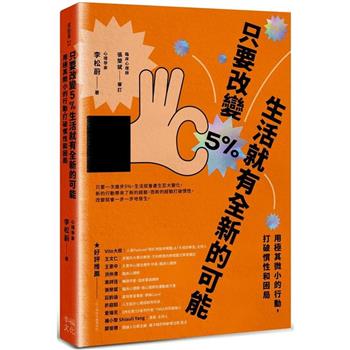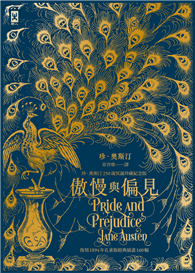序 大龍鳳(阮兆輝教授)
欣聞岳清老弟以「大龍鳳」為主題成書,單是「大龍鳳」三字,已令我掀起回憶,且觸及情意結。雖然以「大龍鳳」為班牌的粵劇團早已有之,也聽叔父輩說,從前還有「鹹龍」、「淡龍」之稱,因為廣州是河水,淡的,香港是海水,鹹的,即是說廣州、香港兩地都曾有「大龍鳳劇團」。但以前歸以前,近七十年來,人人樂道的「大龍鳳」,就是先師麥炳榮、女姐鳳凰女領導的「大龍鳳」。也不知從何時開始,「大龍鳳」成了「大陣仗」的代名詞,連電影及傳媒都常出現「同你做場大龍鳳」的對白,可見「大龍鳳」三字真的深入民心。
「大龍鳳」既是我師父為文武生的班牌,而我在近年亦執筆寫書,為甚麼卻沒親自寫「大龍鳳」呢?其實我與「大龍鳳」的關係雖是千絲萬縷,但我卻不是「大龍鳳」的必然成員。最初的「大龍鳳」,我是未加入,直到一九六○年拜師,師父要我跟着開班,學他演出,便將我帶入「大龍鳳」。由《十年一覺揚州夢》至《不斬樓蘭誓不還》,其實年份不長,後來我更是除了經常在遊樂場及神功戲演出,還間中去新加坡、馬來西亞一帶走埠,一去就是半年。我在港沒戲演時,師父開班,我一定去服侍他,但我有演出及不在港時,當然就不能去「大龍鳳」了。既然我只是斷斷續續在「大龍鳳」演出,又怎麼有資格去寫「大龍鳳」呢?況且我一向不是長於在圖書館查舊報紙,找年、月、日的人,所以一直不敢寫,因為不知就裏的人,一定以為我很熟悉「大龍鳳」,其實大謬不然,所以岳清老弟肯費心去收集「大龍鳳」的資料,我還該向他致謝才對。希望常將「搞場大龍鳳」掛在口邊的人,今次真能知道甚麼是「大龍鳳」。
---------------------------------------------------------------------------------------------------------------------------------
序 苦幹中尋求突破和創造奇跡的「大龍鳳」(陳守仁教授)
從本人與研究團隊近年整理及統計粵劇劇目的發現,今天香港粵劇戲班大概流通約二百二十個劇目,當中屬「常演劇目」的約有一百個。這些劇目的首演資料顯示,「一百個常演劇目」中,超過一半由三位文武生「包辦」,分別是麥炳榮(開山二十齣)、任劍輝(十七齣)和林家聲(十七齣),足見這三位前輩演員對香港粵劇的影響力歷久不衰。麥炳榮開山的二十齣戲裏,十五齣與鳳凰女合作;與羅艷卿、吳君麗、余麗珍合作的共有五齣。
常演劇目的「榜首十大」中,麥炳榮與鳳凰女的首本戲《鳳閣恩仇未了情》(1962;第四位)、《燕歸人未歸》(1974;第五位)、《雙龍丹鳳霸皇都》(1960;第八位)與唐滌生的經典名作《獅吼記》(1958;第二位)、《紫釵記》(1957;第三位)、《雙仙拜月亭》(1958;第六位)、《帝女花》(1957;第七位)、《白兔會》(1958;第九位)和《火網梵宮十四年》(1950;第十位)分庭抗禮,互相輝映。
麥炳榮、鳳凰女合作開山的常演劇目還有《百戰榮歸迎彩鳳》(1960)、《癡鳳狂龍》(1972)、《蠻漢刁妻》(1971)、《桃花湖畔鳳求凰》(1966)、《刁蠻元帥莽將軍》(1961)、《金鳳銀龍迎新歲》(1965)和《旗開得勝凱旋還》(1964)。麥炳榮和其他名伶開山的常演劇目則有《枇杷山上英雄血》(1954)、《梟雄虎將美人威》(1968)、《蓋世雙雄霸楚城》(1966)和《雙珠鳳》(1957)。此外,麥炳榮、鳳凰女的《十年一覺揚州夢》(1960)和《榮歸衣錦鳳求凰》(1964)雖然不常演出,但堪稱「奇葩」。
話說回來,1950年代是香港粵劇的輝煌時代,原動力固然是來自一代編劇大師唐滌生的粵劇改革,和任劍輝、芳艷芬、白雪仙、何非凡、吳君麗等紅伶努力下的協同效應。當中,其實麥炳榮和鳳凰女早已不只嶄露頭角。唐滌生於1959年9月不幸逝世,任、白至1961年才重組「仙鳳鳴劇團」首演由葉紹德執筆的《白蛇新傳》,之後「仙鳳」雖仍間中演出,但沒有再開山新戲,而芳艷芬也於1959 年告別劇壇,相信種種因素令粵劇觀眾大量流失。
與此同時,香港娛樂文化在1960 至1970 年代發生很大變化,是源於新媒體和新形式的興起,與屬於傳統大眾娛樂的粵劇、粵曲產生激烈競爭。這時候,麗的呼聲電視(1957 年啟播)、商業電台(1959年啟播)、無綫電視(1967年11月啟播)、陳寶珠、蕭芳芳的青春電影、粵語流行曲、國語電影、國語時代曲、歐美電影、歐西流行曲等媒體和形式爭相成為娛樂主流,不斷把粵劇、粵曲、粵劇電影推向邊緣。
從當代粵劇發展的進程來看,麥炳榮、鳳凰女及「大龍鳳」的班主、一眾編劇、演員和拍和樂手崛起於「後唐滌生時代」的1960年代,並且奮鬥至1970年代。他們在粵劇低潮中力爭上游,最後創造了奇跡,為後世留下一批珍貴的劇目,故「大龍鳳時代」也標誌憑苦幹尋求突破的精神。
岳清的《大龍鳳時代—— 麥炳榮、鳳凰女的粵劇因緣》載錄了詳盡的傳記、掌故、首演劇目和圖片資料,既填補了過去研究的空白,也為香港粵劇觀眾提供珍貴的集體回顧和回憶,並將成為研究者珍貴的參考文獻。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大龍鳳時代:麥炳榮、鳳凰女的粵劇因緣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大龍鳳時代:麥炳榮、鳳凰女的粵劇因緣
本書全面解說大龍鳳劇團的成員、發展與經典劇目,從「鐵三角」麥炳榮、鳳凰女和譚蘭卿說起,到「超級班主」何少保,重量級演員林家聲、陳好逑、阮兆輝、高麗,編劇家劉月峰、潘一帆,音樂領導麥惠文、高潤權等;再介紹劇團代表性的演出如「六一八雨災」義演、保良局百周年籌款義演,戲寶如《十年一覺揚州夢》、《鳳閣恩仇未了情》、《燕歸人未歸》等。輔以近二百張劇照、定妝照、戲橋、特刊、唱片封套等珍貴圖片,讀者可由此走進光彩耀目的舞台世界。
作者簡介:
岳清,香港懷舊文化研究者,另有筆名一諾、殷信希,多年來於戲曲雜誌撰寫專欄。已出版作品包括:《烽火梨園》(2005)、《錦繡梨園》(2005)、《粵劇文武生梁漢威》(2007)、《新艷陽傳奇——芳艷芬》(2008)、《光影尋源——解構1948-1969香港電影的繆斯》(2009)、《萬紫千紅——李麗華》(2015)、《花月總留痕——香港粵劇回眸(1930s-1970s)》(2019)、《今夕是何年—任劍輝的光影傳情》(2019)、《萬能旦后鄧碧雲》(2020)、《網紅貓偵探社—尼羅河之心》(2021)、《Wil l You Remember Me——張國榮為你鍾情》(2022)。
作者序
序 大龍鳳(阮兆輝教授)
欣聞岳清老弟以「大龍鳳」為主題成書,單是「大龍鳳」三字,已令我掀起回憶,且觸及情意結。雖然以「大龍鳳」為班牌的粵劇團早已有之,也聽叔父輩說,從前還有「鹹龍」、「淡龍」之稱,因為廣州是河水,淡的,香港是海水,鹹的,即是說廣州、香港兩地都曾有「大龍鳳劇團」。但以前歸以前,近七十年來,人人樂道的「大龍鳳」,就是先師麥炳榮、女姐鳳凰女領導的「大龍鳳」。也不知從何時開始,「大龍鳳」成了「大陣仗」的代名詞,連電影及傳媒都常出現「同你做場大龍鳳」的對白,可見「大龍鳳」三字真的深入民心。...
欣聞岳清老弟以「大龍鳳」為主題成書,單是「大龍鳳」三字,已令我掀起回憶,且觸及情意結。雖然以「大龍鳳」為班牌的粵劇團早已有之,也聽叔父輩說,從前還有「鹹龍」、「淡龍」之稱,因為廣州是河水,淡的,香港是海水,鹹的,即是說廣州、香港兩地都曾有「大龍鳳劇團」。但以前歸以前,近七十年來,人人樂道的「大龍鳳」,就是先師麥炳榮、女姐鳳凰女領導的「大龍鳳」。也不知從何時開始,「大龍鳳」成了「大陣仗」的代名詞,連電影及傳媒都常出現「同你做場大龍鳳」的對白,可見「大龍鳳」三字真的深入民心。...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 大龍鳳(阮兆輝教授)
序 苦幹中尋求突破和創造奇跡的「大龍鳳」(陳守仁教授)
緣起
第一章 大龍鳳鐵三角
麥炳榮小傳
鳳凰女小傳
譚蘭卿小傳
第二章 大龍鳳編劇人才
劉月峰
李少芸
潘一帆
徐子郎
潘焯
葉紹德
梁山人
勞鐸
第三章 大龍鳳時代
超級班主何少保
大龍鳳人才濟濟
皇都首次演粵劇
黃千歲加盟
黃炎另起鳳求凰
羅艷卿加盟
大龍鳳遠征新加坡
雙班制出奇制勝
寶人和成絕唱
第四章 粵劇演出與義演
六一八雨災義演
香港節粵劇演出
保良局百周年籌款義演
香港藝術節粵劇演出
第五章 大龍鳳名劇巡禮
《百戰榮歸迎彩鳳》
《十年一覺揚...
序 苦幹中尋求突破和創造奇跡的「大龍鳳」(陳守仁教授)
緣起
第一章 大龍鳳鐵三角
麥炳榮小傳
鳳凰女小傳
譚蘭卿小傳
第二章 大龍鳳編劇人才
劉月峰
李少芸
潘一帆
徐子郎
潘焯
葉紹德
梁山人
勞鐸
第三章 大龍鳳時代
超級班主何少保
大龍鳳人才濟濟
皇都首次演粵劇
黃千歲加盟
黃炎另起鳳求凰
羅艷卿加盟
大龍鳳遠征新加坡
雙班制出奇制勝
寶人和成絕唱
第四章 粵劇演出與義演
六一八雨災義演
香港節粵劇演出
保良局百周年籌款義演
香港藝術節粵劇演出
第五章 大龍鳳名劇巡禮
《百戰榮歸迎彩鳳》
《十年一覺揚...
顯示全部內容
|